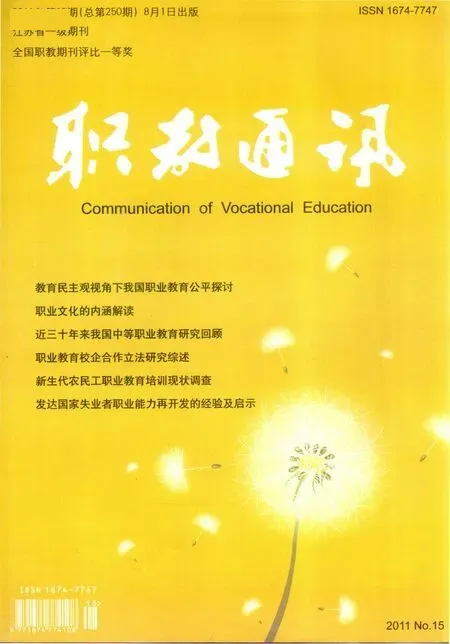非真实的真实
臧志军
非真实的真实
臧志军
近十几年,日本人每年会票选一个年度世态汉字用以标志该年度所发生的重大事件的影响。此风西渐,台湾、香港和大陆每年都有人也搞类似的活动。如果有可能在中国职教界搞这样一个活动,我想选“真”字。
在“校企合作、工学交替”的大旗下,中国职业教育开始视模拟、实训为落后之物,真实的工作任务、真实的生产过程、真实的劳动情境成为人们竞相追逐的当红明星,于是传统的学术化课程受到批评和排挤、学校里出现了企业的生产车间、学生开始把整整1/3的学习时间用来进行真实的生产劳动……“真”字在职业教育中已经获得了某种神物的超然地位,人们只消说“不符合生产实际”或“不贴近企业需求”就可以宣判某种教育实践的死刑。
在一些以校企合作为特色的学校或专业,学生在真实情境中的工作时间已经超过他们在传统课堂上的学习时间,在外界看来,这无异于利用学生的廉价劳力谋利,因此,对真实性的宗教般热情不仅带来了职业教育的全新面貌,也带来了社会各界对职业教育不绝于耳的批评。我们当然不能一味斥责批评者对于职业教育的无知,因为他们至少提出了一个我们还没有准备好答案的问题:我们在追求真实性的道路上该走多远?
从哲学层面上看,齐泽克和鲍德里亚告诉我们,与十九世纪人们追求乌托邦不同,整个二十世纪的基本特征是“对真实的激情”;从实践层面看,中国职教的血液里本来就缺少产业的基因,对真实的追求不仅是一种“矫枉”,更是对职教本义的回归。从这些意义上讲,职业教育对真实性的追求既符合普罗大众的社会心态,也是职业教育必为之事。所以问题的实质不是我们是否还应在追求真实性的道路上走下去,而是沿着怎样的路往前走。
杜威是“教育即生活”的鼓吹者,但他并不认为学校要复制外部世界,他更喜欢强调“学校是特殊的环境”,因为学校环境应是简化、清洁和平衡的。既然学校环境是被设计、塑造或创造出来的,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学校环境是外部世界的某种虚拟物,而不可能是外部世界本身。那种把外部世界或外部世界的某一部分原封不动地移植进学校的努力无非会有两种可能,一是让学校消亡,二是本身归于失败。
鲍德里亚有句名言:虚拟比真实更加真实,他的理由是当一切都成为信息,“一切都变得可操作”,不确定性就消失了。教育的功用之一就是向受教育者提供在日常生活中无法体验的生活经验:让他们在专制的社会感受民主,让他们在丑陋的现实感受美好,让他们在一个只需要机械劳动的生产环境感受现代科技之美……通过对外部世界的抽象化和要素化,教育可以实现对现实生活更高层次的虚拟,按照鲍德里亚的逻辑,这是一种比现实生活更加真实的真实。也许,我们可以稍微改造一下柏拉图那个被贴上唯心主义标签的“摹本”理论:对现实生活中无数事实的模拟才最接近自然本有之物,才是最真实的。
就职业教育而言,我们必须在教育真实与生产真实之间做出选择,需要记住的是能移植进学校的所谓真实的生产只是现实的一个或若干个碎片,远非真实的生产本身,只有经过教育化的、抽象化的改造才能具有更加普遍的教育意义。
同时,不要忘记杜威的另一句教诲:我们从来不是直接地进行教育,而是间接地通过环境进行教育。现在的我们好像正在做相反的事情,在现在的中国,无论是普教、职教,甚至高教,都把对知识的直接传授作为唯一的目标。可以说,在中国,只存在教书,而不存在教育,这样做的结果是,知识与学习这种知识的人相分离,受教育者被异化了(教育者其实也难逃厄运)。而教育本应是促进人的社会化的活动,绝不仅是使人知识化的过程,为促进社会化,教育应创设与受教育者当前和未来生活相关的环境,换句话说,教育中的真实情境应与受教育者的生活相关,而不仅是与知识相关。这说明,我们不仅误解了生产的真实性,也误解了教育的真实性。
如果仅是误解,还不算是最坏的事,更可怕的是我们在进行误导。学生的业余时间几乎已全部被电脑游戏所占领,我们是否设计了足够的课程或机制告诉学生如何应对现代科技的冲击?现在的学生有过度成人化的倾向,我们是否向学生提供了公开讨论爱与性的问题的平台?那些从富士康的窗台上跳下去的年经人在学校时是否被告知了高度工业化的生产现场的真实情况?我们在试图向学生描绘一个虚假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知识与技能是最重要的,而最不重要的是人。这种情况下,让学生与真实的外部世界绝缘是最佳选择,所以才会出现中国独有的怪现象:学生不许染发、不许带手机、不许在校园内吃食物……
脱离了学生当下和未来生活的教育没有资格自称为真实的教育,更确切地说,没有资格自称为教育,如果真有人把“真”字作为职教的关键词,大概应理解为一种讽刺吧!
写到结尾处才想起我其实跑题了,起笔时曾想写职教中的真实与模拟的关系,没想到又空发了许多议论。有位老前辈带话给我,希望我不仅批判还应有建设性。确实,空谈无益,下个月我们聊一下如何把生活带进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