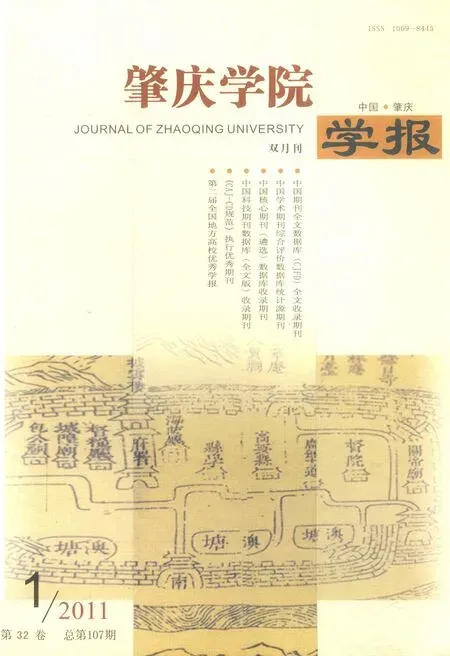论梁宗岱诗学批评“真的追寻”
张仁香
(肇庆学院 文学院,广东 肇庆 526061)
论梁宗岱诗学批评“真的追寻”
张仁香
(肇庆学院 文学院,广东 肇庆 526061)
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梁宗岱是有着鲜明个性的诗学批评家:诗人的敏感、重文采,评论家的理性与逻辑的严明,熔铸在梁宗岱的批评文字之中。梁宗岱的批评执着于“真的追寻”。“较真儿”体现出他的批评个性:重视文章中字、词、句甚至文法、结构的批评,强调文章表达要“中肯”与“确当”。梁宗岱的这类批评有的放矢,针对性强,尖锐,不留情面;梁宗岱有诗人的气质,在其诗性批评中彰显浪漫与理想情愫,有强烈生命意识及情感张力,追求艺术恒久价值,这恰是我们今天多元文学批评时代所缺乏的。
梁宗岱批评;真的追求;诗性理想
梁宗岱 (1903—1983)广东新会人,是我国“五四”时期出现的诗人,在诗歌翻译、诗评论及比较诗学等方面卓有成就。他早年出版的诗集《晚祷》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具有独特风格。他留欧期间出版的法译《陶潜诗选》由法国象征派大诗人瓦雷里作序,得到大作家罗曼.罗兰的高度评价。在上世纪30年代他结集出版的诗评论《诗与真》《诗与真二集》在中国早期比较诗学、诗学批评等领域占有重要地位。近年来,对梁宗岱的诗歌创作及象征主义诗论的研究有所深入,但对其诗学批评的整体研究仍有很大空间,本文尝试阐述梁宗岱诗学批评的个性特点、批评风格及在中国现代诗学批评中的意义。
一、“较真儿”——梁宗岱的批评个性
梁宗岱是诗人。诗人的审美直觉比一般人更强烈;梁宗岱又从事翻译,翻译过中外经典作家的作品,使得他的诗性美感更纯粹。
梁宗岱发表在1923年上海 《文学旬刊》84期的《杂感》,主要是对成仿吾一首英文诗翻译的批评。文中说到成仿吾指责郁达夫的《孤寂的高原刈稻者》(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诗)译得不好,自己重来译。梁宗岱批评道:“郁氏的译文,我曾于《沉沦》看过,好坏现在已记不清楚了。可是我读成氏所译的,不独生涩不自然,就意义上也很有使我诧异。觉得有些费解的!……第四行的‘Stop here,or gently pass’一句,原文的口气原是写‘刈稻者’的或行或止的(当然只是意译),译者竟把它译作‘为她止止步,或轻一点’,这居然是当为作者自己的‘止步’了。……原诗的第三节(即译文第二节)末二行的‘Some natural sorrow,loss,or pain,that has been,and may be again’,‘may be’二字含有些‘将来’的意思。他就是说‘那些自然的悲哀,丧失或痛苦,在过去已经是了,而将来也会再遇到的’(译意)。成君译作‘几回过了,今却重来’,‘今’字可不知从何而来!”[1]4-5梁宗岱很不客气地指出 “我们举目看看现在所谓批评家,很有因为自己未曾了解,或者自己做不到而指摘或径修改他人的”[1]4。成仿吾对许地山的小说《命命鸟》中描写的批评,被梁宗岱讽刺为“只恨许君不曾像舆地教员般,先将缅甸的风俗习惯详细解释一番”[1]6以至于不愿再读下去了。
在这篇《杂感》之后,成仿吾给该刊主编郑振铎的信中表示,为了两句英文,被梁宗岱搞得欲哭无泪。当时梁宗岱20岁。读过梁宗岱的批评文章,令人想起一个成语“锱铢必较”。“锱铢”固然喻“小”,似乎不值得计较,然而在这“斤斤计较”的批评背后,彰显了作者敏锐、精确的语言把握能力以及独到的文学鉴赏力。该《杂感》不仅批评成仿吾,对郭沫若翻译的雪莱诗也提出质疑。读其文想其人,便觉后生可畏!要知道,当时的成仿吾与郭沫若已是创造社的名人。梁宗岱这种论辩风格在其一生中成为其为人为学的一道风景,显示出不同于他人的特立独行的品性。
梁宗岱是诗人,有对自己审美直觉的坚执。梁宗岱又是诗论家,喜读西方哲学著作,也培养了他较强的思辨力。他写于1937年的两篇批评文章:《从滥用名词说起》以及《〈从滥用名词说起〉底余波——致李健吾先生》是梁宗岱对朱光潜、李健吾文章中“名词滥用”及“论证不严”和“举例不当”的批评。读了梁宗岱的文章,我们信服梁宗岱的批评,也敬畏他能抛开世俗人情,直扣文本,不留余地指出其中的错误。这是需要一种勇气与胆识的。
梁宗岱自己也承认像朱光潜、李健吾这样的大家,一个是对美学有着系统的研究;一个是对文学创作形成自己的批评风格。“瑕不掩瑜”,这小疵并不能淹没大批评家的成就,但也正因为是“大家”的文章,它有可能造成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梁宗岱在《〈从滥用名词说起〉底余波——致李健吾先生》中曾致歉,觉得自己的《从滥用名词说起》一文“语气欠正”,是“激于一时的冲动”,所引起的不健全的反响与作者的“初衷是大大相悖的”。但尽管如此,梁宗岱的批评倾向决不是针对个人,而是文坛的风气:“我们底散文界渐渐陷于一种极恶劣的倾向:繁琐和浮华。作者显然是极力要作好文章;可惜才不逮意,手不应心,于是急切中连‘简明’,‘清晰’,‘条理’等一切散文底基本条件都置诸脑后了,只顾拼命堆砌和拉长,以求观瞻上的壮伟。明明是三言两语便可以阐说得致的,作者却偏要发为洋洋洒洒的千言或万言。结果自然是:不消化的抽象名词,不着边际的形容词,不恰当的譬喻等连篇累牍又翻来覆去地使用。”[1]55-56梁宗岱同时指出,他的文章所抨击的不仅是文坛的恶劣倾向“如果我们留心观察,便会发见我们学术界流行着一种浮夸,好炫耀,强不知以为知,和发议论不负责的风气:那才是文坛底流弊底根源。”[2]56
梁宗岱的批评何以这样“较真”?文学批评家李长之说:“他冲口而出,没有世故,也不怕打人兴头,他充分表现出对于艺术的爱护和作人的真挚。……如果艺术也是一种宗教的话,梁先生真当得起最虔诚的一个信徒。”[2]115-116的确,艺术对梁宗岱而言,是一种理想,一种信仰,一种对完美的追求。对写作,他强调“中肯”和“确当”。他认为这是行文底一切(用字,选词,命意和举例)最高标准,也是一切文章风格最高的理想。对文学批评,他试图努力树立一种绝对“无私”的态度:“这就是说,我们对于作品的评价,对于事理之是非,要完全撇开个人感情上的爱恶,而当作一种客观的事实或现象看待。”[1]59梁宗岱生性浪漫的天性在这里彰显无疑。从这个角度说,与传统知识文人相比,梁宗岱的文化人格更倾向西洋文化中的个性表现与自我张扬。也正是西方文化的人文模式建构了梁宗岱的个性心理:“我虽不敏,自幼便对于是非很认真。留学巴黎的几年,又侥幸深入他们底学术界,目睹那些学术界第一流人物——诗人,科学家,哲学家——虽然年纪都在六十以上了,但在茶会中,在宴会席上,常常为了一个问题剧烈地辩论。他们,法国人,平常是极礼让的,到了那时,却你一枪,我一剑,丝毫也不让步,因为他们心目中只有他们所讨论的观念,只有真理。而对方底理由证实是充足的时候,另一方面是毫不踌躇地承认和同意的。我羡慕他们底认真,我更羡慕他们底自由与超脱。我明白为什么巴黎被称为‘新雅典’,为什么法国各种学艺都极平均发展,为什么到现在法国仍代表欧洲文化最高的水准。回头看看我们知识阶级底聚会,言及义的有多少?言及义而能对他底主张,他底议论负责的又有多少?除了‘今天天气哈哈哈’,除了虚伪的应酬与恭维,你就只听见说长道短了。”[1]60
二、诗性批评中彰显浪漫与理想情愫——梁宗岱的批评风格
中国现代诗学批评,是与中国现代诗学实践相互生长的。因此,“现代性”的独特文化语境,在以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下,立足于中国现代的民族土壤中所生成的现代生活方式,决定了现代人的诗学表达。在这种新语境中,一些有着深厚西学背景的诗学家,借鉴西方诗学理念,融合中国古典传统中优秀成分,形成了自己一套诗学批评方式方法。比如,朱光潜对“诗”的批评体系,就是借助西方20世纪的心理学等理论与中国古典诗学范畴契合中建构起来的;李健吾的文学批评是直接借鉴了法国印象主义批评,结合自己个性特点生成的;梁宗岱的诗学批评秉承了古希腊的"诡辩"派某些风格,结合中国传统诗学中的 “诗性”思维方式形成了自己的批评特色的。
如果比较一下3个人的批评个性,会有助于我们把握梁宗岱的批评特点。
梁宗岱与朱光潜有着显著的不同。性情方面,两人差异很大。朱光潜的生平经历不如梁宗岱那样富有传奇色彩;就个性而言,梁宗岱颇具自我意识,朱光潜更近调和折衷;就学问来说,朱光潜对哲学、心理学、美学、文学都做过一番系统的研究;梁宗岱是诗人,是由诗歌创作、诗歌翻译到诗歌评论,是从创作到理论。
梁宗岱与李健吾有相近之处。两人同有留学法国的背景,都从事翻译,同样爱好文学,不过梁宗岱是诗人,李健吾写剧本。从两人批评风格看,李健吾不乏诗性的敏感,作家的智慧,但含蓄、谦撝;梁宗岱更富想象力与思辨力,明晰、透彻。就“批评”风格来讲,梁宗岱比李健吾更具有浪漫理想色彩。
在批评方法上,梁宗岱既不像朱光潜那样评论作品注重作者或人物的心理分析,承认文艺鉴赏中的“个性心理差异”,也不同李健吾“叙述灵魂在杰作之间的奇遇”。朱光潜对批评追求的普遍价值持怀疑的态度,李健吾也强调批评不是“评判”而是“表现”,批评本身就是艺术。
梁宗岱与他们不同:一是偏偏追求诗学批评的“绝对价值”,强调艺术的恒久生命力。二是梁宗岱的批评既评判也赏鉴。梁宗岱好“较真”——论辩,“不破不立”要立出自己的观点,一定先要驳斥他所否定的观点。梁宗岱的“破”——“慎思明辨”——严谨、深刻、清晰,抓住对方的弱点阐发自己所言明的诗学主张,但“立”并非建立一套逻辑体系的批评概念或术语,而是用诗性的感悟来生发自己的美学理想。
在梁宗岱的诗学批评中,主要是通过对诗学范畴的“误读”,或依赖其审美化的直觉与主观化的诠释来建构起他的诗学理想。在这个意义上,梁宗岱的诗人秉性占据了上风,使得他的批评更具有艺术性、心灵性。这方面的代表作即《象征主义》、《论崇高》、《试论直觉与表现》等。
梁宗岱的《象征主义》是将“象征主义”视为“无论任何国度,任何时代底文艺活动和表现里,都是一个不可缺乏的普遍和重要的原素”[3]。文章从对“象征”一词的辨析说开来,不讲任何外在因素与条件,直切主题,将中西诗学范畴进行比照,提出了象征与“兴”的关联,又借鉴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提出评价诗词的两种境界:“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比较了晋代大诗人谢灵运与陶渊明的名句,得出了象征的两个特征:融洽或无间;含蓄或无限。很显然,梁宗岱将“象征”与王国维的“意境”混为一体。梁宗岱将“象征”与“兴”等同,实在是一种“误读”,而将象征的境界与中国诗词中“意境”浑融一体,使得这种误读走得更远。梁宗岱何以要“误读”?当代学者姜涛指出“这种对中西诗学的双重误读虽然构成了梁氏诗学的严重缺陷:缺乏客观性和严密性。但‘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作为推崇前者的梁宗岱,这种误读正是他建构自我诗学体系时的一个合理性策略”[4]。这里所说的“策略”就是指作为诗人的梁宗岱寻求中西象征诗学的“通途”——象征之道——诗的最高艺术境界。这一境界不仅存在于中西诗学的传统里,也正是中国现代白话新诗的指路明灯。因此,梁宗岱在《象征主义》一文中忘情地,甚至是忘我地描述了这一境界的“辉煌”景象:“从那刻起,世界和我们中间的帷幕永远揭开了。如归故乡一样,我们恢复了宇宙底普遍完整的景象,或者可以说,回到宇宙底亲切的眼前或怀里,并且不仅是醉与梦中闪电似的邂逅,而是随时随地意识地体验到的现实了。”[5]74
如果说《象征主义》是通过对诗学范畴的“误读”来寻求中西诗学汇通的途径以及终极艺术理想的追求,那么,在《论崇高》中,梁宗岱是因为词语的翻译,在与朱光潜的辩论中,走向他内心的诗性崇高,这里不是以“误读”为策略,而是诗人的审美直觉力对理性的胜利。
朱光潜收在《文艺心理学》中一篇论文——《刚性美与柔性美》,对中西审美现象形态进行分类讨论,其分类的目的是要“在殊相中见出共相”,并指出这两种美的共相,在中国便是刚柔或阴阳,在西洋便是Sublime与Grace。而Sublime与Grace朱光潜主要依据康德的学说将之译成 “雄伟”与“秀美”。朱光潜为说明两种美的类型,引述了几个例证,认为米开朗基罗的作品在性格上、艺术上都是刚性美的代表,达.芬奇则与之相反,《蒙娜.丽莎》是女性美、柔性美的代表,《最后的晚餐》中的耶稣也正象“抚慰病儿的慈母”。梁宗岱则认为,用妩媚与秀美来形容《蒙娜丽莎》与《最后的晚餐》不亚于用“乖巧”形容瀑布那样不合时宜,因为在梁宗岱看来,刚性美是令人震撼的,而柔性美是宁静的平和的。梁宗岱这样描述凝视这两部作品时的感受“我们将发现,啊!异迹!这里(异于米开朗基罗)没有夸张,没有矜奇或恣肆,没有肌肉底拘挛与筋骨底凸露,它底神奇只在描画底逼真,渲染底得宜,他底力量只是构思底深密,章法底谨严,笔笔都仿佛是依照几何学计算过的,却笔笔都蓬勃着生气——这时候我们应该用什么来形容我们的感觉呢?……唯一适当的字眼,恐怕只有Divine(神妙)或Sublime(崇高)
罢。 ”[5]112-113
可见,朱光潜对两部作品的审美评判,是为他的理论作注解,仅仅囿于对象本身的表征形态,而梁宗岱是从创作者的角度、力的角度对艺术家精工制作的技巧之高反复玩味,因此给人的审美感受决不是一般的宁静平和的优美感受,而是非同寻常的,蕴含着艺术匠心的“崇高”之美。
梁宗岱提出Sublime一词译成“崇高”比“雄伟”更切近字源,因为根据拉丁文Sublime,从动词Sublimare变出来,有高举的意思(其实朱光潜在翻译时也提到,这一词在中文里没有恰当的译名“雄浑”、“劲健”、“伟大”、“崇高”、“庄严” 诸词都只能得其片面的意义),“崇高”与“雄伟”也有词义的区分问题。特别是当用这些概念来分析具体作品,应当充分考虑到作品本身的个性化风格以及概念的适用性。在梁宗岱看来,“雄伟”(梁先生用到了‘雄浑’,这是中国古典诗学中特有的范畴,用在此处也不恰切)仅仅是指其外在的,形态上的,而“崇高”更侧重内在的,技巧的。他又从创作家的角度对“崇高”予以新的阐释,认为,真正的"崇高"应是一种美的绝境,相当于我国文艺批评所用的“神”或“绝”,而这“绝”字与其说是对象本身的限制,不如说是我们内心所起的感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所不能至,心向往之”。为此,崇高的一个特征与其说不可测量或未经测量的,不如说不能至与不可企及的。在梁宗岱看来,大海的波动汹涌就不如其宁静莫测更能引起人的崇高感受。前者之高是以其态势让人畏惧的,后者之高则是以其神秘震慑灵魂的。梁宗岱认为后者之高乃为真正的“崇高”,而这“崇高”的境界并不是人人都能体会到的。
梁宗岱提出对这种“崇高”的感受,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需要识得一种“力”,即“智慧之力”。这种“力”表现于创作中是自由的精神,是艺术家在创作时“想做”与“能做”,“能做”与“应做”间一种深切的契合。如何识得这种“力”?梁先生讲了一个故事:印度的一位圣者,一天从田陇中走过,天是一色的蔚蓝,微风吹拂,偶一抬头见一行白鹭在青天飞过,瞬间悟道,于是矢志修行至于得道。至此,梁宗岱将这“力”又归附到了佛家心性当中。
三、梁宗岱诗性批评的现代意义
梁宗岱“崇高”境界的探讨,当代学者温儒敏认为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诗学的风气有极大的批判意义:
30年代是革命的变动的年代,社会审美心态比较倾向于刚烈的、粗犷的风俗,因而“崇高”这一概念在美学界、批评界很常使用,但普遍的认识是流于肤浅的。例如,当时文艺创作包括诗作中往往推崇“力之美”,认为只有题材宏大,线条活跃,色彩强烈及章法横肆,才能体现“力度”,也才能达到“崇高”的美学效果。梁宗岱对此很不以为然。他要重新探讨“崇高”的美学含义。在他看来,“崇高”的特征与其说是雄伟、刚性、强大、粗犷,等等,不如说在其所唤起的“不可企及”的感受。“纯诗”中所引发的对宇宙和人生奥义的感悟浩叹,就跟“不可企及”、“不可思议”有关,他认为这是“崇高”之源。而新诗中那种太实、太情绪化的写法,即使用了“大题材”,也断不能引发对宇宙人生的宏阔的想象,也不会“崇高”起来。至于艺术形式风格上的“力”的追求,梁宗岱认为也不能单纯理解为物质、体力或道德上的“力”,更要着重心智的“力”。真正的“力”之美是在“智慧的深处”,要依靠博大的襟怀与清明的理性,依靠完善的人格素养。而且“力”之美主要并不表现为浮泛的夸张、粗放、强烈、横肆之类,更应体现为“一种内在的自由与选择”,通过心智调控达到“抑扬高低皆得其宜”,体现在形神之间的均衡、集中与和谐。梁宗岱还从中外名诗的创作经验分析去进一步论析,认为艺术处理上的“波动”并非达至“崇高”的唯一的和最佳的途径,但显然不赞同当时的新诗作者普遍追求创作风格上的“波动”感,他认为这不过是一种浮躁。梁宗岱宁可回归古典美,有意推崇宁静、内倾、和谐、清明的创作风格,主张由宁静和谐走向崇高。梁宗岱很欣赏法国19世纪的诗人格连的一句格言:“我的灵魂爱宁静比波动多。”他用这种美学追求来为“纯诗”创作境界作注解[6]。
梁宗岱诗学批评之“诗”,表现出诗人敏锐的直觉,恣肆的想象,充沛的激情以及对艺术倾其生命地投入。他独具慧眼地发现,有针对性地批评,注重审美对象在人内心所起的感觉,能够细腻地区分美感中微妙的差异。我们前面说过,梁宗岱的美感胜过智性,正因此,他也常常让感觉、灵感侵占了智性的位置,他的文章会将人们引向不知所云的境地,他的批评虽说也追求真实、客观的的阐释,但大多融进了相当的主观抒情——一种诗性的表达。这种表达使得梁宗岱的批评文脉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与对理想的坚挚追求,而这种浪漫与理想恰是我国“五四”以来的现代启蒙思想所应该张扬的人文精神与理念,也是我们今天多元文学批评时代所缺乏的精神。
[1] 梁宗岱.诗与真续编[M].刘志侠,校注.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2] 李长之文集:第四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
[3] 梁宗岱.诗与真诗与真二集[M].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63.
[4] 姜涛.论梁宗岱的诗学建构及批评方式[M]//黄建华,伍方斐.宗岱的世界评说.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194.
[5] 梁宗岱.梁宗岱文集评论卷[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6] 温如敏.梁宗岱的“纯诗”论]M].黄建华,伍方斐.宗岱的世界评说.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114-115.
Views on Liang Zongdai’s Poetry Criticism “Pursuit of Truth”
ZHANGRenxia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Zhaoqing University,Zhaoqing,Guangdong,526061,China)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criticism,Liang Zongdai was a poetry critic with vivid personality.His poetic sensitivity,literary writing,critical rational and strict logic are seen in his critical comments.His criticism was laid on “pursuit of truth”.His “critical attitude” reveals his critical personalityhis criticism is focused on words,phrases,sentences,even grammar and structures,and also emphasizes on“being earnest” and “appropriation” of expression of the passage.Liang’s sharp and merciless criticism was right to the targets.Liang’s poetic style demonstrated in his criticism is what we need in our era of rich literary criticism.
Liang Zongdai’s criticism;pursuit of truth;poetic ideals
101
A
1009-8445(2011)01-0011-05
(责任编辑:禤展图)
2010-12-06
张仁香(1961-),女,辽宁凤城人,肇庆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