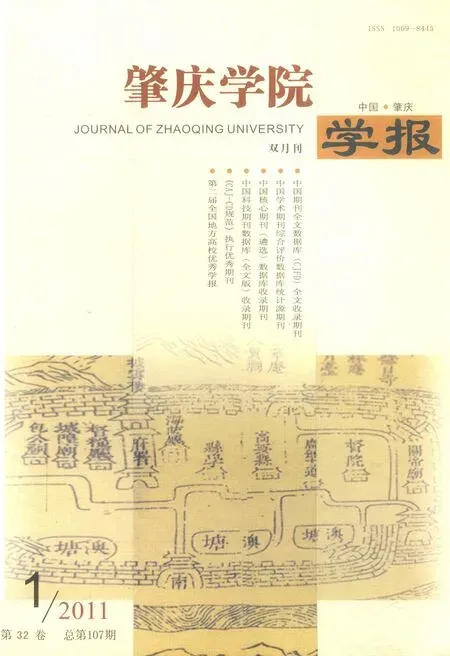明清时期广东西江走廊聚落地名特征研究①
黄秀莲,王 彬
(福建师范大学 a.文学院;b.地理科学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明清时期广东西江走廊聚落地名特征研究①
黄秀莲a,王 彬b
(福建师范大学 a.文学院;b.地理科学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聚落地名反映了人类社会在变迁过程中对自然和社会人文地理环境的选择和适应。明清时期,西江走廊人口密度进一步增大,从平原、河谷到低山、丘陵等地区都有人口的分布。但受自然和社会地理环境的作用,聚落类型发生相应的变化。在聚落地名方面,除保留原有自然特征和古越语聚落地名外,民族和方言类型地名大量涌现,充分反映出明清时期西江走廊地带民族变迁和方言播衍方面的状况,并且奠定了以后本地区聚落地名在民族和方言等方面的分布空间格局和命名特征。
聚落地名;地名特征;西江走廊;明清时期
聚落是人类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以特定方式创造的群体活动行为空间,它的形成和发展必然与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聚落的命名即聚落地名则是这一人类活动过程中的具体体现之一。透过地名,我们可以窥见某一地区自然、社会、民族、文化等的演变过程或历史时期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本文试图透过聚落地名分析,对明清时期广东西江走廊地带自然和社会的演变作一考察,阐述特定时期西江走廊地带的人们社会生产和生活等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
一、民族变迁与聚落地名
聚落是人类对环境的一种适应和选择。在早期的人类活动中,自然环境的优劣,对聚落的出现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最早形成或出现的聚落也许是没有名称的,但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社会的发展,信息交流显得越来越重要,聚落便逐渐有了名称。这一时期的聚落名称依然多是人类对环境的一种认识和反映,所以,它折射出当地自然地理环境对名称的影响。地名与民族都是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产物。不少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风俗、语言等方面,都与地名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民族的形成和分布还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这些都可以在聚落地名中找到印记。
西江走廊因其特殊的交通地理位置,在岭南开发过程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根据司徒尚纪先生研究,按广东开发历史阶段,在空间上表现为自北向南,从西往东,交汇于珠三角,继及沿海和岛屿。也就是说,在唐代以前,地处重要交通位置的西江走廊地带一直是广东开发最早和经济发达的地区[1]。这在郡县设置中得到明显反映。秦定岭南,顺五岭通道、沿江而下,在西江、东江、北江设郡县,如秦代在广东设5县,四会、番禺、博罗、龙川,均在南下通道处,粤东仅设揭阳1县(一说设于汉),辖境包括今梅州市。汉在粤北置桂阳郡(今连州),下辖曲江、连县、英德,西江地区置广信、封阳(两县约今封开)、端溪(德庆)、高要,故我国最古老长沙马王堆出土《地形图》,在今广东境内只标“桂阳”、“封中”两个地名,即粤西北和粤西贺江流域。这种设置情况一直延续到隋唐时期。唐代以后,虽然大庾岭的开凿给西江走廊的交通地位带来改变,但其作为重要的交通和经济发达地区依然存在。而宋元时期,西江地区的进一步开发(特别是对陂、塘开挖和坡、堤的围垦等)和民族活动频繁,则极大地改变了当地的人文环境,为明清时期聚落地名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社会历史文化基础。
明清时期广东政区体系已基本形成。明万历十年(1582年),广东西江走廊隶属肇庆府和罗定直隶州,共9县(高要、高明、四会、新兴、广宁、封川、开建、东安、西宁)2州(罗定直隶州、德庆州),今怀集县属广西布政司梧州府所辖。到了清代,依然沿用明代政区格局,广东西江走廊仍划归肇庆府和罗定直隶州所辖,县州与明代基本相同。虽然这一时期广东经济重心和政区空间格局向珠江三角洲和粤东韩江三角洲转移,但西江的肇庆府仍然是重要的次一级政治、经济中心。据《大明一统志》和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所载,广东“里”(当时的基层政区)数统计,肇庆府和罗定直隶州里数之和约占全省11.86%[2],仅次于广州府,居第二位,足见其地位的重要性。
广东西江走廊地带自古以来都是重要的交通要道,是早期中原汉人南下和汉文化传入岭南的必经之路之一,也是岭南与西江其他地区、巴蜀及岭外地区交流的要塞之地。道光《肇庆府志》称“阻山濒海”,“居广东上游,当五州要路。”自先秦以来,这里一直是多民族杂居之地。《汉书地理志》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通考舆地考南越》也记曰:“越以百称,明其族类之多也。”广东的越族,古代主要称为“南越”,大概包括后代的壮族、黎族和旦家[3]。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说:“广东瑶、壮二种,瑶及荆蛮,壮则旧越人也。”还有此前的“俚人”、“僚人”等。如《隋书 南蛮传》说:“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旦 、曰狼、曰俚、曰僚、曰,俱无君长,随山洞而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这些壮族和黎族先人散居于广东省的广大地区,而西江走廊地带是其主要分布地区之一。但随着后来汉人的大量迁入,他们一部分人逐渐汉化了,一部分则迁移到偏僻的粤西和西江走廊地带的山区和丘陵地带。事实上,北方汉人的南迁从秦代甚至更早既已开始,如“(始皇)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以适遣戍”,约50万军人与越人杂处。后又因赵佗“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始皇可其万五千人”[4],使其与留岭南的秦军官兵结合成个体小家庭,杂处越人之间。这些北来汉人的相当部分分布于西江走廊地带。历经魏晋南北朝、唐宋元等朝代,大量北方汉人南迁岭南。到了明清时期,西江走廊地带已经形成以汉人为主体、少数民族杂居其间的分布格局,这突出地表现在以“村”字为通名的聚落地名大量分布。而在此以前,岭南极少见到以“村”字命名的聚落地名,它是北方汉人对聚落的一种称呼。起初,村落被称为“乡村”,是远离城市中心的社区。 “村”字别体从邑,写作“ 屯 阝”,它是从原始氏族的集聚地转化而来的。“乡”(乡字繁体从邑)这个字,无论金文、甲骨文,都是像两人相向对坐共食一簋之形。也就是说,“乡”的字形,指的是两个人面对面坐着,当中放一个饭桶。所以杨宽先生在《古史新探》中说,乡这个字,“是用来指自己那些共同饮食的氏族聚落的”。后来聚落就统称为“乡里”、“村镇”等。根据清代方志统计,西江走廊地带“村”字聚落地名大量增加,而且其所占比例也是随着时间推移大幅度地提高,如新兴县在乾隆年间聚落605个,带“村”字聚落地名有83个,占13.72%[5];封川县在道光年间聚落569个,带“村”字聚落地名已有344个,占60.46%[6]。在这些聚落地名中,虽然也会包含有其他民族聚落的称呼,但依然不难看出汉族已占居主体地位。这些大量以“村”字为通名命名的聚落地名,在结构上既有一般的“××村”的表现形式,如界首村、岐槎村、料塘村、 艹麻 园村、佛子村、铺边村、沙田村、古冈村、苏村、冼村、廖村、欧村等;也有“壮侗语地名+村”的形式,如黎洞村、良塘村、云简村、排村等。此外,还有大量“粤方言或客方言+村”字结构的聚落地名,如口村、上 良 村和新屋村、屋底村等[7]。这些“村”字结构聚落地名的大量存在,除了反映出汉族已成为当地主体居民外,也说明汉人在向此地迁移过程中部分表现为家族性聚居;而“壮侗语地名+村”形式的出现,则清楚地反映出当地少数民族聚落地名深受汉族文化影响的特征,或者先前为少数民族聚落,后来为汉人居多数的聚落;或由于种种原因,少数民族被汉化,采用汉族聚落名称,这种现象在全国其他地区也经常见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地名命名遵循“先入为主”和“名从主人”的原则。汉人到来后,一方面遵循或认同当地少数民族地名,另一方面又稍加变通、采用汉语读音方式来称呼原有地名。所以,这种移民造成西江走廊地带聚落地名文化层次非常明显的现象。
明清时期,西江走廊地带还是少数民族活动较为活跃的地区之一,在聚落地名中的表现也极为突出,最为明显的是瑶族和壮族。瑶族并非西江走廊土著居民,是南朝末年以来从长沙武陵蛮或五溪蛮迁移而来(一说从广西迁移而来)。隋唐时期,粤北已有莫瑶记载。北宋庆历间,连、韶二州已有瑶族在劳动生息。宋室南渡之后,瑶族又向东西两翼扩展到珠江三角洲和西江走廊地区,瑶族记述也逐渐增多。到了元代,瑶族又进一步向南向东以及四邻拓展。当时广东大陆的10路9州中,除粤东之惠州、潮州二路和梅州之外,其余8路8州皆有瑶人活动,与明代比较仅差惠州一府。《粤大记》记载:“罗旁东界新兴,南连阳春,西抵郁林、岑溪,北尽长江(指西江),与肇庆、德庆、封州、梧州仅界一水,延袤千里,万山联络,皆瑶人盘据其间,世称盘瓠氏遗裔,租赋不入,生齿日繁,蚕食旁近诸村,州县赋税因而日缩……国朝自申国公邓镇讨平后,寻叛”[8]。瑶族活动地域不断扩大,人口也大量增加。明清时期,瑶民由于“食尽一山,复徙一山”的耕作方式和其它原因,除排瑶外,辄不断流徙。为此,封建政府加大了对瑶民的“征剿”,但瑶族的分布在西江走廊地带依稀可见。明初至中叶,广东瑶族进入繁盛时期;明后期至清康乾之世,瑶区发生深刻变化,逐渐形成今日的分布格局。根据道光《肇庆府志》记载,高要县(同瑶,下同)山9,四会县山58,新兴县山54,阳春县山94,阳江县山13,德庆州山49,封川县山2,开建县山35,合计314。除此之外,各县还有非人独占的山,其中高要县有43座;高明县有2座;德庆州9座;封川县51座;开建县有3座;合计114座,总计为428座[7]。除去非属西江走廊地带的阳春县、阳江县的山107,仍有321座。足见当时瑶人分布的广泛性。由于瑶人“以耕山为生”,“寻山捕猎,砍种养生”,“刀耕火种……游山转岭打猎。”这种常徙不定的游耕生活,人们形象地称之为“过山瑶”,山就成了瑶人的聚落称呼,瑶山即瑶村聚落,这在聚落地名上是一种特殊现象。但也深刻反映了当时瑶人的生产和生活环境。除此之外,在县志中也可以找到以“瑶”、“排”、“寨”“”等命名的瑶族聚落地名,如新兴县有金 皿 围、洞、排村、凤凰寨、上寨、下寨等[5];东安县也有树陂、西路、歌村、北路、云容、云廉、大寨、清水寨等[9];其它州县也都有这类聚落地名存在,不再一一列举,充分反映出瑶人在当地的活动和分布。
壮族地名,主要体现在以“云”、“古”、“都”、“罗”、“思”、“布(步、阜)”、“扶”、“良”等命名的聚落地名。其皆属壮语地名用字,“云”指人,作“村”解;“古”、“都”表示村寨,在规模上,“都”比“古”大;“罗”指山谷,即村落;“思”同“虚”,即圩,集市;“布”同“埠”,即渡口;“扶”指那边;“良”指黄色,引申为黄族居地之意。根据县志统计,在罗定直隶州534个乡村聚落地名中,有78个,占14.60%[10];在新兴县605个聚落地名中,有85个,占14.05%[5];在封川县的569个聚落地名中,有109个,占19.16%[6];到了光绪年间,在四会县统计的784个聚落地名中,也有75个,占9.57%[11]。在其它(州)县志中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壮语聚落地名存在,足见壮语聚落地名分布的广泛性,反映壮族在此活动的痕迹和影响以及当时的社会环境状况。广东壮族有“主”、“客”之分,“主”壮是岭南古越人的后裔。清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 广东七》即说:“瑶及荆蛮,僮(同壮,下同)则旧越人也。”“客僮”也主要来自广西,他们进入广东的途径或方式有三种,即奉调征守的亻 良 兵,主动留居的土兵或士兵,以及自由迁徙的僮民。其入粤的时间,始于北宋,然多在明清[12]。他们大部都保留自己的语言和生活习惯,或自成聚落,或与当地僮人杂居,成为广东大陆僮的一部分。所以,明清时期是西江壮族发展的高潮阶段,壮语聚落地名也较为明显,以致形成今天广东西江地区壮语地名分布格局。这一时期壮语地名从空间上看,主要分布在与广西交界的西江走廊地带,其内部也是从西向东呈递减的趋势,即靠近广西的西宁县、德庆州、封开县、怀集县、广宁县、东安县等明显多于东部的高要县、高明县、四会县。清人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和民国时期徐松石先生的《粤江流域人民史》中皆有论述。如“自阳春至高、雷、廉、琼地名,多曰那某、罗某、扶某、过某、牙某、峨某、陀某、打某”[13]。徐松石先生则在罗列了“那”、“都”、“思”、“古”、“六”、“罗”、“云”等字的倒装地名以后,又总结说“壮族地名具有分类密集的现象。例如,云字地名集中于广东的南部和广西的东部;罗字地名也集中于同一个地方;六字地名集中于广东的西部南部和广西的中部东部;思字地名的集中地带也与六字相同;……黎字地名集中于广东的中部南部,并广西的正东区域;……至于良字都字和古字的地名,就除东江和北江的北段以外,粤江流域其他各地都很普遍”[14]。据司徒尚纪先生研究,表示自然地理的壮语地名,如“洞(峒、垌)、罗、六(禄、渌)、黎、陇、弄、南(氵 南)、濑、塘、潭”等字,“以广西至为集中,在广东主要分布在西南部和中部,次则北部,而东江、兴梅、粤东(潮汕)地区则很少,甚至几乎绝迹”[15]。究其原因主要是与当时封建政府的“征剿”瑶族和壮族活动有关。根据明代以来文献中出现大量有关僮的记载来看,粤西西江走廊地带无疑是广东壮族主要分布区之一。《广东民族关系史》也说:“综合封开、开建、怀集和连山等县志,今封开县罗董、杏花两镇以北,连山县吉田镇以南的广大地区均为僮区,其中连山、怀集之交和怀集、封开毗连的山区则是其聚居中心”[12]。直至今天,这种壮语地名仍然大量存在,如据粗略统计,怀集县含“罗”、“古”、“都”、“那”等壮语地名有195个,其中永固乡即有36个[15],足见壮族的历史变迁和影响之深远。
在西江走廊地带,明清时期还出现“少数民族地名+少数民族地名”或“少数民族地名+方言地名”的新聚落地名现象,如黎、潭黎、古楼、思文寨、林 田 厄寨,等等。“黎”为古越语或现黎语用字,“黎”指山岭,即“俗呼山岭为黎,人居其间”[16]; “古”、“潭”为古越语或现壮语用字,“古”指村寨;潭指池塘;“思”同墟,即圩,集市;“寨”为瑶语用 字,指村落;“林 田 ”指 水塘 ,演变为 聚 落名[17]。反映此时也有少数民族之间相互杂居或融合的现象。
二、方言扩散与聚落地名
地名是语言的化石,透过地名,我们可以了解一个地区语言的变迁过程。美国语言学家柏默说:“地名的研究实在是语言学家最引人入胜的事业之一。因为他们时常供给重要的证据,可以补充和证实历史家和考古家的话。”还说“语言的历史和文化的历史是相辅而行的,他们可以互相协助和启发”[18]。所以,从地名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个地区语言的变迁过程。
广东是我国方言最为复杂的省份之一,拥有三大方言,即粤方言、客方言和闽方言。而广东西江走廊地带除了前面所提到的壮语、瑶语等其它少数民族语言外,也存在着汉方言的变迁过程。通过聚落地名分析,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到明清时期本地区的方言的演变。
明清时期,西江走廊地带聚落地名中粤方言和客方言聚落地名的分布是相当抢眼的一个现象,这与粤方言的形成和发展是密不可分的。方言是“语言的地方变体”,粤方言是中原汉族居民向南迁移造成汉语言的分化而形成的。西江走廊典型的粤方言地名通名如“涌(甬、冲)”、“朗( 朗土、良、 良山等)”、“坪(步)”、“坭”等。 根据统计,在罗定直隶州534个乡村聚落地名中,有84个,占15.73%[11];在新兴县605个聚落地名中,有51个,占8.43%[5];在封川县的569个聚落地名中,有48个,占8.44%[6];到了光绪年间,在四会县统计的784个聚落地名中,有111个,占14.16%[11]。四县合计共有294个,占总聚落地名的11.80%。在其它(州)县志中也都有不同程度的粤方言聚落地名存在,充分反映出粤方言的传播和扩散情况,也反映西江走廊地带与珠江三角洲居民之间的交流和社会活动。众所周知,粤方言是汉语的一种,它是北方汉人移入珠江三角洲地带形成粤方言后,不断向外播衍的结果。特别是随着宋代以来广东的大开发,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粤方言向周边扩散的速度。加上西江走廊系扼交通要道以及广州与岭北和广西、巴蜀等地区交流的扩大,使得粤方言迅速扩展。“广东商人则溯西江而上,再沿各支流移动,大多聚居在沿途各圩镇,也有的聚居乡村垦荒务农”[19]。根据黄启臣先生研究,明清时期,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两广的经济关系更加密切,商业贸易往来更加频繁并得到了全面的、空前的发展,大量的粮食、食盐、矿产品、手工业产品及土特产等往返两地[20]。如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高要县陈廷标等商人,到梧州贩米,“经由高要、新兴、广宁、四会、三水售卖”[21]。这些产品是以民生用品为主,主要是接近于下层人们,更有利于粤方言的接受和传播。此时期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城市商品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也在较大程度上促进了两广地区间的贸易。所以,大量的物品贸易和人员往来,为粤方言的加速传播提供了渠道和场地。因此,本时期西江走廊地带出现许多粤方言地名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从这一时期粤方言聚落地名的空间分布来看,主要分布在西江干流及其主要支流两岸水陆交通较为便利的地方,总的趋势是由东向西递减,靠近珠江三角洲的地区明显高于西部地区。一方面反映了汉人从三角洲地区向外迁移;另一方面反映交通便利或枢纽地区是粤方言传入的主要地区。
客方言聚落地名的出现和分布,主要是与客民在明清时期向粤西和西江走廊地带迁移活动有关。客家先民早在东汉末年或更早时期,由于种种原因便开始向闽、粤、赣交界地区迁移。历经南北朝、唐宋和元代,粤东不断有北方汉人迁入。由于大量客民迁入和自身繁衍,到了明清时期,粤东客县人平均耕地面积仅为一点三八亩,低于广府县的平均水平[22]。更为重要的是地权的高度集中,极端繁苛的租税、剥削和土客矛盾,客家人生活更加困难,于是有相当部分客家人从广东东部、北部向省外和省内其它地区迁移,西江走廊地带就是其中迁入地区之一。同时,西江走廊地带还是客家人迁往广西和“湖广填四川”的交流要道,部分客家人在中途停留、居住下来,与早先零星迁入的客家人一起成为西江走廊地带的客民。根据县志聚落地名统计(这里主要以客家典型聚落地名用字“屋”来统计),在罗定直隶州乡村聚落地名中,有三屋、谭屋岗、屋儿寨、屋地、屋林等[10];在新兴县聚落地名中,有彭屋、旧屋坑、龙屋等[5];在封川县的聚落地名中,有屋耸村、石屋洞、林屋迳村、利屋冈、屋镜村、屋底村、新屋村、屋洞村、白屋村等。而且,在本县的修泰乡二十七甲中,有界首甲、料塘甲等15甲直接记“内有客户”[6];到了光绪年间,在四会县统计的784个聚落地名中,有46个,占5.87%[11]。在其它(州)县志中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客方言聚落地名存在。在这些以“屋”字命名的聚落地名中,大都遵循客家地名命名的传统,即以“姓氏+屋”的命名结构,反映客家人迁移时家族性和宗族观念的巨大影响,如罗屋、谭屋、黎屋、曾屋、黄屋等;但也有以“屋+××(少数民族地名)”结构的聚落地名,如屋洞、屋林、屋儿寨、屋地、邹屋排等,反映客家人到来后深受当地古越语、壮语或其他少数民族地名的影响及与其融合的现象。
三、结 论
通过对聚落地名的分析,可以看出,地名隐含着明清时期西江走廊地带历史、民族、社会、文化等的变迁。在聚落地名上明显地反映出当地的社会性特征,特别是民族和方言聚落地名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明显的民族和人口迁移活动痕迹,即壮语聚落地名呈现由西向东递减的规律,粤方言地名则相反,这与壮族从西向东、再沿西江两岸迁移和粤方言从三角洲向外扩散的方向是一致的。聚落地名结构又从另一个方面——古越族活动和民族融合两个侧面反映此地区的人类活动,特别是齐尾式结构聚落地名,反映深受古越族或其它少数民族的影响;“姓+通名或其它方式地名字”的结构则反映此地区家族或族群活动、发展的过程,明显反映聚落地名的地区分布特色。为本地区今后相关学科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佐证和借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司徒尚纪,许桂灵.广东开发史[J].岭南文史,2005,23(2):1-10.
[2]司徒尚纪.广东政区体系——历史、现实、改革[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53-55.
[3] 李新魁.广东的方言[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33.
[4]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淮南衡山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 新兴县志(乾隆):卷十五“坊都”二,乡村[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4.
[6] 封川县志(道光):“舆地”乡里[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4.
[7] 肇庆府志(道光):卷二“舆地”山川[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
[8] 郭棐.粤大记:卷三“事纪类”山箐聚啸[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
[9] 东安县志(道光):卷二“坊都”墟市[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4.
[10] 罗定直隶州志(康熙):卷九“闾里”乡村[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
[11] 四会县志(光绪):编一,廂乡[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
[12] 练铭志,马建钊,朱洪.广东民族关系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619-627.
[13]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一“文语”土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4] 徐松石.民族学研究著作五种:上 [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204.
[15] 练铭志.试论粤西“标话”人与百越的关系[J].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1988(2):28-33.
[16] 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十六“儋州”风俗[M].北京:中华书局,2000.
[17] 司徒尚纪.广东文化地理[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353-368.
[18] 罗常培.语言与文化[M].北京:语言出版社,1989.
[19] 覃彩銮.壮族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282-283.
[20] 汤明檖,黄启臣.纪念梁方仲教授学术讨论会文集[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230-252.
[21] 黄启臣,庞新平.明清广东商人[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1:236.
[22] 刘佐泉.观澜溯源话客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52-154.
Analysis of Characteristics of Place Names Along West Rive Corridor of Guangdong Province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UANG Xiulian1,WANG Bin2
(1.College of Arts 2.College of Geography,Fujian Normal University,Fuzhou,Fujian,350007,China)
Place names reflect how human societies have chosen and adapted to natural and social cultures,and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s in the process of evolution.Along the West River Corridor there accumulated a dense population which had never stopped increasing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The people lived in areas of plains,valleys,hills and low mountains.But limited by natur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s,village types had changes in accordance.Besides the names reflecting the na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ancient Yue language,there appeared a large number of ethnic languages and dialects,which fully mirrored the developments of ethnicities and dialects along the West Rive Corridor.
place names;characteristics of place names;West River Corridor;during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K928.6
A
1009-8445(2011)01-0038-06
(责任编辑:杨 杰)
2010-11-03; 修改日期:2010-12-19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0801055);福建省科技厅青年人才项目(2008F3034);福建省教育厅A类项目(JAO8038)
本文的广东西江是指广西梧州至广东三水思贤滘河段及其支流。根据曾昭璇先生的划分,西江从云南发源地至广西象州石龙三江口以上为上游,三江口至梧州为中游,梧州至广东三水思贤滘为下游,思贤滘到磨刀门为河口段。广东西江走廊即指西江下游干流及其贺江、罗定江、绥江(北江)、新兴江、悦城河等支流流域,包括今肇庆市(端州区、鼎湖区、四会市、高要市、广宁县、怀集县、德庆县、封开县)和云浮市(云城区、云安县、新兴县、罗定市、郁南县)。
黄秀莲(1976-),女,湖北随州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