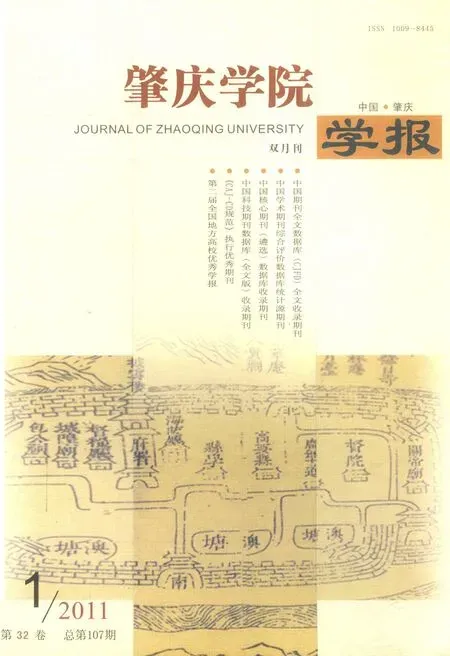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若干问题探究
肖本山
(肇庆学院 政法学院,广东 肇庆 526061)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若干问题探究
肖本山
(肇庆学院 政法学院,广东 肇庆 526061)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增设的意义主要在于适应打击当前贿赂犯罪以及诉讼证明的现实需要。“利用影响力”既是本罪的本质特征,也是理解本罪客观行为结构的重点。同时,“关系密切人”是理解和认定本罪行为主体的关键。此外,在界定本罪中相关人员刑事责任问题上需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客观行为;行为主体;相关人员刑事责任
为了适应严惩贿赂犯罪的现实需要,2009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第13条在刑法第388条①理论上称之为间接受贿罪或斡旋受贿罪,属于受贿罪的一种特殊形式。后增加1条作为第388条之一,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实施前款行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定罪处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9年9月通过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四)》将该罪的罪名确定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刑法修正案(七)》公布后,对于如何理解和适用第13条的规定,刑法学界和司法实务部门均产生了较大的分歧。本文拟就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若干问题进行探究,以期对本罪的正确理解和适用有所裨益。
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客观行为之探究
从《刑法修正案(七)》第13条关于本罪的客观行为方式的规定看,本罪的实行行为由两部分构成,即“利用影响力”和“索取或者收受财物”。②立法规定中的“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不是本罪的客观构成要件,而是行为人的行为动机。不过,在对“索取或者收受财物”的认识上,人们基本上不存争议,因此,“利用影响力”成为理解本罪客观行为的重点,也是刑法学界争议的焦点之一。
(一)“利用影响力”内涵之解读
1.关于“利用影响力”的含义。从理论上讲,影响力是指一个人在与他人交往过程中,能够影响他人的心理和行为的能力。[1]影响力可分为权力性影响力和非权力性影响力。前者指权力者所具有的与职务相关的影响力。后者是指来自行为者自身的因素,其中包括品格、知识、才能、情感、资历等个人因素,[2]这种影响力并非以强制性为特征,但它又能自然而然地起到影响人们思想与行为的作用。[3]从现实生活情况看,非权力性影响力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例如情感关系、亲情关系、地缘关系、事务关系等,不过,从深层次上看,它们均可归为情感或人情世故的关系。
对于本罪中“影响力”的性质,有的学者认为,本罪中的“影响力”仅指非权力性影响力,而不包括权力性影响力,即认为由于我国刑法将国家工作人员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规定为不同的犯罪,因此,本罪的影响力只包括非权力性影响力,而不包括权力性影响力,利用权力性影响力受贿的,构成我国刑法中的受贿罪而非本罪。[4]此看法对本罪中“影响力”缺乏全面的认识,故存在不足。在笔者看来,根据司法实践情况及立法的规定,本罪中的影响力既存在非权力性影响力,又有权力性影响力的情形。详言之,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直接“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而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在此情形下,该国家工作人员直接行使的是自己的职务行为,即在该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范围内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因此,在此节点上是不存在“利用权力性影响力”的问题。因为“影响力”只能存在于“关系密切人”与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既然本款规定的犯罪行为主体仅以“关系密切人”的身份出现,那么,该国家工作人员之所以直接行使自己的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正是受到了“密切关系”的影响,而这里的“密切关系”仅具非权力性影响力的性质。如果请托人请托的事项不在该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范围内,那就要发挥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作用。在此情况下,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必须“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这里的“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也是本罪中“利用影响力”的情形之一。不过,此种情形的“影响力”有别于上述“关系密切”,即其中具有权力的因素。因此,上文所讲的“权力性影响力”应包括两种情形,即权力制约性影响力和权力非制约性影响力。上述论者提及的“利用权力性影响力受贿”中“权力性影响力”应仅指权力制约性影响力,而不是指权力非制约性影响力。据此,本罪中“利用影响力”同样包括权力非制约性影响力的情形。此“权力非制约性影响力”就是2003年11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三条(一)所指的“行为人与被其利用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在职务上虽然没有隶属、制约关系,但是行为人利用了本人职权或者地位产生的影响和一定的工作联系,如单位内不同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上下级单位没有职务上隶属、制约关系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有工作联系的不同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等。”不过,此情形存在于“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即指被其近亲属或者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所利用的该国家工作人员与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的影响力。需要说明的是,“利用权力非制约性影响力”同样存在于本罪主体为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等实施犯罪的场合。
2.关于“利用影响力”的行为特点。对于如何理解本罪中的“利用”行为,有的学者提出“双重利用”说的观点,认为行为人的利用行为有双重性,即先利用了国家工作人员或者自己(主要指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对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影响,接着又利用了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行为。[5]笔者认为,论者的主张实际上是对第13条第1款规定的后一种行为方式的概括,但并没有顾及到第13条第1款规定的前一种行为方式。就第13条第1款规定的前一种行为方式而言,其中并不存在“双重利用”影响力,而仅存“单一利用”影响力的情形。因为,在前一种行为方式(即“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情形下,行为人利用的仅仅是其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具有“密切关系”的影响力,被其利用的国家工作人员只需实施本人职务上的行为即可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无需再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
(二)关于本罪的既遂与未遂问题
本罪的既、未遂标准取决于本罪的立法模式是行为犯还是结果犯。如果本罪是行为犯,那么,只要关系密切的人直接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或者间接利用了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请托人办理了请托事项,即意味着本罪的既遂;如果本罪是结果犯,那么,除了有上述行为外,关系密切的人还实际收受了请托人的财物或有了其他较重的情节,才构成本罪的既遂。从第13条的规定看,本罪采取的是结果犯的立法模式。①本罪之所以采取结果犯的立法模式,其立法理由除了受“计赃论罪”传统立法观念的影响、符合受贿的“权钱交易”的本质特征外,还有诉讼证据证明方面的考虑。其依据就是条文中规定有“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内容。既然立法将“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作为本罪的客观要件之一,因此,要构成本罪的既遂就必须符合“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这一要件的要求。那么,本罪的未遂标准就应当是没有收受到请托人的财物或者未出现其他较重情节。
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行为主体之探究
根据立法的规定,本罪的行为主体可分为两类五种人,即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其他与国家工作人员有密切关系的人、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以及其他与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有密切关系的人。不过,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以及其他与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有密切关系的人与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国家工作人员有密切关系的人的情形是一样的,因此,在理解和认定本罪的行为主体时,主要涉及的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其他与国家工作人员有密切关系的人以及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三种情形。
(一)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
一般认为,本罪中的近亲属不难理解。但是,近亲属的范围的界定也不是非常明确,原因在于我国相关立法和司法解释规定的内容不尽一致。例如,《刑事诉讼法》第82条第6项规定,“近亲属”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条规定,民法通则中规定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规定,行政诉讼法第24条规定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和其他具有扶养、赡养关系的亲属。依笔者之见,本罪中的“近亲属”应以刑事法律规定的近亲属来界定为宜。当然,对于本罪中的近亲属的范围,通过刑法的司法解释加以界定还是有必要的。
(二)其他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
对于其他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受贿行为,在我国一直是入罪的,只是在入罪模式上经历了共同犯罪到单独定罪的变化过程。
2003年11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三条(五)规定,“根据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伙同受贿的,应当以受贿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责任。非国家工作人员是否构成受贿罪共犯,取决于双方有无共同受贿的故意和行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向国家工作人员代为转达请托事项,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告知该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国家工作人员明知其近亲属收受了他人财物,仍按照近亲属的要求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对该国家工作人员应认定为受贿罪,其近亲属以受贿罪共犯论处。近亲属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有的,构成受贿罪共犯。”2007年7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七条规定,“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实施前款行为的,对特定关系人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特定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有的,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
关于“特定关系人”的范围,上述“意见”第十一条规定,本意见所称“特定关系人”,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在此司法解释中,“特定关系人”的属性是具有“共同利益关系”。
本罪第1款所规定的行为主体,如果从理论上将其表述为“关系密切人”,那么,其属性就是“关系密切”,其范围可分为两类,即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为什么立法未再沿用“特定关系人”这一先前已被司法解释所使用的表述,而是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这一表述呢?笔者认为,立法可能基于以下几点考虑:(1)“情妇(夫)”属于生活化的用语,不宜用在作为刑法典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修正案之中。(2)“关系密切”中的“关系”不仅指“利益关系”,也可包括“情感关系”,至少在外延可以包括司法解释中“特定关系人”中所列举的“情妇(夫)”和“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因为前者主要指“情感关系”,后者指“利益关系”),甚至在外延上比“情妇(夫)”和“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的范围更广,从而从行为主体的范围上可实现“严密刑事法网”的目的。(3)如果立法继续沿用“特定关系人”这一表述,那么,在其中的“共同利益关系”的认定上存在诉讼证据证明的难题,尽管在本罪中对于“关系密切”的认定上也会存在证明难的问题,但在证明难的程度上会小于前者。相比之下,本罪立法中使用“关系密切人”这一表述应当说是“利大于弊”。
(三)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
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在以往的司法解释中表述为“离退休的国家工作人员”。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指达到了退休年龄而退休,或是因各种原因而辞去公职,或是由于相应的法定原因而被免去公职的国家工作人员[6]。因此,在范围上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大于离退休的国家工作人员,因为前者除了离休、退休外,还包括辞职、免职等情形。不过,诸如“停职”、“调职”则不属于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从其内涵看,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应指“丧失职权”的国家工作人员。因此,刑法修正案(七)第13条未再沿用“离退休的国家工作人员”,而是使用“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不仅反映了我国国家工作人员“离职”的实际情况,而且此表述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立法的兜底性。
对于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行为,从我国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看,经历了从入罪到出罪再到入罪的演进过程。1989年11月6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三条(三)规定,“已离、退休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原有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在职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而本人从中向请托人索取或者非法收受财物的,以受贿论处。”而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发布的《关于贪污贿赂、渎职犯罪适用法律问题座谈会纪要(稿)》第三条(六)项规定,“离退休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原有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在职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索取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不以受贿罪论处。”《刑法修正案(七)》第13条再一次将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其原有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规定为犯罪。
我国相关司法解释之所以对于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行为出现从入罪到出罪的变化,其缘由乃坚持身份犯理论使然。在刑法理论上,通常将以特殊身份作为主体构成要件或者刑罚加减根据的犯罪称为身份犯。[7]我国刑法理论认为,受贿罪属于身份犯。虽然刑法第385条规定的受贿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但无论学界还是司法实务部门都将此条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解释为“现职”的国家工作人员,而不包括“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因此,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行为不构成受贿罪,应当说这是坚持受贿罪身份犯理论的结果。
我国立法最终又将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行为规定为单独犯罪,在笔者看来,其主要考虑以下两点:(1)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行为仍然存在,应当予以惩治,但立法不能存在漏洞,需要对此行为加以规制。(2)单独规定一个新的犯罪,而不囿于普通受贿罪,这样既实现了惩罚犯罪的现实需要,又不与身份犯理论相冲突,避免不必要的理论争议。
三、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相关人员刑事责任之探究
从立法的规定看,本罪涉及的相关人员较多,其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构成何罪,是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对于与本罪有关的人员的刑事责任问题,笔者认为应分为三种情况分别予以分析:
(一)国家工作人员的刑事责任问题
立法之所以将“利用影响力受贿”的行为规定为一个独立的罪名,是由此罪的本质特点决定的。其本质特点就在于行为人没有将自己收受或将要收受请托人的财物告知被其利用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被其利用的国家工作人员亦不知道行为人收受或将要收受请托人的财物。这也是行为人和被其利用的国家工作人员不构成受贿罪共犯的根本原因。不过,在本罪中,该国家工作人员对于行为人犯罪行为的实施实际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对行为人来说,利用影响力受贿可谓“借权取财”。但是,根据立法的规定,在行为人的行为构成本罪的情况下,被其利用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行为既不构成受贿罪,也不构成本罪,可以滥用职权罪论处。当然,如果有证据证明,国家工作人员知道自己的关系密切人受贿或者将要受贿的事实,或者关系密切人将自己受贿或者将要受贿的事实告知国家工作人员,在此场合,该国家工作人员的行为构成犯罪,而且构成受贿罪。不仅如此,该国家工作人员的关系密切人的行为不再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而是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因为在此情形下关系密切人的行为不再符合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构成条件,当然不能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论处。
(二)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刑事责任问题
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基于社会的有效管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责分工亦越来越细,这样,就为请托人请托事项的“归口管理”提供了权力基础。当请托事项不在国家工作人员职权范围内,并且必须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才能完成时,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在本罪中亦是一个重要的角色。在界定其刑事责任时,应分为以下两种情形:(1)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若收受财物的,以受贿罪论处,但不能与行为人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共同犯罪。(2)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若没有收受财物的,不能以受贿罪论处,可以滥用职权罪论处。
(三)请托人的刑事责任问题
在对修正案(七)第13条的立法规定给予肯定的同时,有的学者指出,此次立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要求还存在一定的距离,即我国立法只规定了影响力交易罪中的受贿行为,而缺少其中的行贿行为。笔者认为,从犯罪的对向关系角度看,上述看法所反映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因为,在我国现行刑法中,有关贿赂方面的犯罪,均具有犯罪的对向性特点,例如,我国刑法第385条规定了受贿罪,那么,刑法第389条就相应地规定了行贿罪;又如,第387条规定了单位受贿罪,相应地第391条就规定了对单位行贿罪。再如,2006年6月29日刑法修正案(六)第6条增设了单位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相应地刑法修正案(六)第8条规定了对单位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这次刑法修正案(七)第13条增设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却没有增设相对应的行贿罪。这是不是立法上的一个疏漏?或者说,立法者是否认为没有增设此类行贿罪的必要?笔者认为,这涉及现有的行贿犯罪能否“包容”本罪中请托人的行为问题。如果是肯定的话,那么,立法的这一“疏漏”就不成其为疏漏。在笔者看来,现有的行贿犯罪是不能“包容”本罪中请托人的行为的。其理由是:(1)本罪与受贿罪是有本质区别的,不仅本罪的主体不是国家工作人员,而且,本罪的主体也不是受贿罪主体的延伸。此外,本罪行为人的索取或者收受财物行为也不是受贿罪客观行为的延伸。同时,请托人请托的对象是国家工作人员的“关系密切的人”,而不是国家工作人员本人;请托人的财物给予的亦是国家工作人员的“关系密切的人”,而不是国家工作人员本人。笔者认为,本罪是一个独立的犯罪。正因为如此,本罪并不能与行贿罪形成对向关系。(2)本罪与刑法修正案(六)第6条增设的单位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也有本质区别,这不仅在于本罪的主体不是单位非国家工作人员,而且本罪的主体在实施受贿行为时并不存在利用自己的职权的情形,既然如此,请托人的行为也就不可能以修正案(六)第8条规定的对单位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论处。综上所述,由于刑法修正案(七)尚未规定与本罪相对应的行贿犯罪,因此,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即使“关系密切的人”的行为构成本罪,那么,请托人的行为也不构成犯罪。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只有立法上增加一个新罪,例如影响力行贿罪,以弥补这一立法漏洞。
不过,请托人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其行为都不构成犯罪。在笔者看来,如果请托人当着国家工作人员和其“关系密切的人”提出自己的请托事项,即使将财物只是给予“关系密切的人”。因为在此场合,国家工作人员和其“关系密切的人”的行为构成的是受贿罪的共犯,那么,请托人的行为应以行贿罪论处。此外,即使请托人只是向国家工作人员的“关系密切的人”提出自己的请托事项,并且将财物也只是给予“关系密切的人”,但“关系密切人”却将收受财物之事告知了国家工作人员,在此场合,国家工作人员和其“关系密切的人”的行为构成的是受贿罪的共犯,那么,请托人的行为也应以行贿罪论处。
[1] 李德民.非正式组织和非权力影响力[J].中国行政管理,1997(9):27.
[2] 谢钟.浅谈领导者的影响力[J].江苏教育学院学报,2000(4):58.
[3] 袁彬.论影响力交易罪[J].法学论坛,2004(5):81.
[4] 李山河.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M]//赵秉志,陈忠林,齐文远.新中国刑法60年巡礼.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1 553.
[5] 赵秉志.《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中国刑事立法中的转化模式评析[J].南京大学学报,2008(2):67.
[6] 张阳.论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3):48-50.
[7] 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M].3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07.
Study of Bribery Crime Committed with Personal Influencing Power
XIAO Benshan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Zhaoqing University,Zhaoqing,Guangdong,526061,China)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newly-added bribery crime committed with personal influencing power lies in attacking current bribing crimes as well as lawsuit proof.Using influence is not only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 of this crime,but also the focus of understanding its objective behavior structure.Meanwhile,the person of close relationship is the key in understanding and identifying the behavior subject of this crime.It needs concrete analysis and different dealings in defining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related people.
bribery crime committed with personal influencing power;objective behavior;behavior subject;criminal deeds of the related people
DF792
A
1009-8445(2011)01-0001-06
(责任编辑:杨 杰)
2010-09-13; 修改日期:2010-10-11
肖本山(1968-),男,安徽无为人,肇庆学院政法学院副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