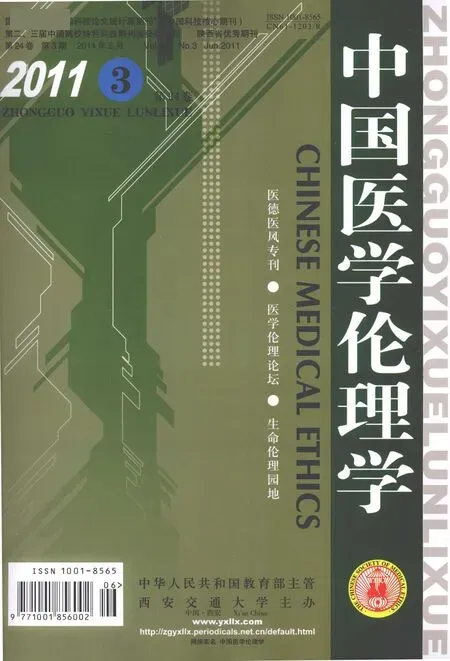“慎”在中国传统医业道德规范中的地位*
潘新丽
(天津医科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天津 300070)
在中国历史上,医学是最早独立的职业之一,在周代就已形成,《周礼·天官冢宰》记载:“惟王建国……设官分职,医师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并将医分为食医、疾医、疡医、兽医四科。以医为业的医学职业具有工作的内涵,通过参与医事活动用自己的劳动获取一定的生活报酬。医业是医事活动的社会化、职业化体现,医业道德反映的是医家在工作中的道德内容,也就是医家在职业生活中的道德。职业生活是医家参与医事活动的主要方面,是行医施治过程中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要求,其中的医业道德规范是传统医德最具体化的表现,反映着传统医德的特征。
传统医德包含内容丰富的道德规范,这些规范以“慎”为核心且有法、律、戒律、要等多样的表现形式。
1 传统医业道德规范以“慎”为核心
作为医家,患者以性命相托付,意识、思考、语言、行动必须要“慎”。在中国传统医德史上,医事要“慎”的观念源远流长。早在《易经·无妄》中有:“无妄之药,不可试也”,告诫医家在用药时必须谨慎;《黄帝内经》里也多次强调“慎”,《灵枢·禁服篇》记载,医术是上古贷季传至岐伯,岐伯授之黄帝,故贷季为先师也。在传授医术时,因为非其人不可授道,故须禁之,坐私传也,并且要先行“割臂歃血为盟”的仪式。在这种仪式里面,洋溢着神圣和严肃,表现的是谨慎的态度。后来,黄帝又将医术传授给雷公,割臂歃血之后,“黄帝乃左握其手,右授之书,曰:‘慎之慎之’”。正如张介宾所说:“医虽小道,而性命攸关,敢不知慎!”[1]
2 历代医家把“慎”的规范要求落实在行医施治的各个环节
首先是精确诊断。魏晋医学家褚澄在《褚氏遗书》当中就说到诊脉时“差其毫厘,损其性命”,因此要审证精微;孙思邈也强调:“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侯,纤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2]
其次是辨证治病,力求精确无误。“须明白开谕辨折,断其为内伤外感,或属杂病,或属阴虚,或内伤而兼外感几分,或外感而兼内伤几分。论方据脉下所定,不可少有隐秘,依古成法,参酌时宜、年纪与所处顺逆及曾服某药否。女人经水胎产,男子房室劳逸。虽本于古而不泥于古,真如见其脏腑,然后此心无疑于人,亦不枉误”。[3]
最后是用药审慎。在中国传统医德思想当中,“慎”的要求经常见于用药方面。褚澄说用药时要谨记“用药如用兵”,用药当“慎”。宋代医家寇宗奭比喻说:“用药如用刑”,甚至比“用刑”更为严重,因为“刑有鞫司,鞫成然后议定,议定然后书罪”;但是用药之后“盖人命一死,不可复生,故须如此详谨”[4]。在《医灯续焰》里面,针对用药,提出了“不可好奇而妄投一药,不可轻人命而擅试一方”的规范,因为“医为人之司命,生死系之”,在用药时必须抱有戒慎恐惧之心,兢兢业业,审慎小心。
为了倡导“慎”的规范,古代医家痛斥“粗工庸手,不习经书脉理,不管病证重轻,轻易投剂”[5]的草率敷衍的作风。作为医家,当记取黄帝传授医学时的谆谆之言:“慎之慎之”!
3“慎”的规范观念共同体现出了传统医家生命至重的思想,在以生命为本方面实现了统一
《黄帝内经》提出的“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生命至重至贵的观念奠定了传统医德生命价值观的基调,内在蕴含着“慎”的要求。在传统文化中,医术一直被视为特殊的技艺,根源就在于医术和生命密切关联。清代医学家黄凯钧在《友渔斋医话·橘旁杂论》中曾集中论说过这一问题,并提出“方技中以医术为要”的观点。他说:“古来方技,如天文术数,堪舆风鉴,卜筮医术数类。天文惟帝皇所重;术数若遁甲风角,惟为将所重;堪舆其应每远数百载,或数十载始验,真伪难知;风鉴即能先知预定人之富贵寿考,本各自具也。卜筮不过决疑,医则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不可废其术。”在各种方技的比较中,只有医术是为所有人所重视、所不可或缺的。因为只有医术能“疗疾病,决生死,望问切脉之次,必云因何而得,所属何脏,所系何经,当用何药,服后能见何效。”因而能使“危者复安,骨者复肉,能神而明之”,所以“实为方技中之最要者也”。医学自身在客观上就是具有善的意味,医学从来都是以促进健康、“起死回生”为终极价值追求的,在各种科学技术形态中,医学最为直接地体现着“善”的性质,最为典型地体现出对生命的关爱。
4 以“慎”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医业道德还具有丰富的表现形式
这些表现形式主要有法、律、戒律、要等。清代喻昌所著《医门法律》,将中医理、法、方药等内容,以法和律的形式逐条阐明,法就是正面的规范、律则是反面的规范,不仅从正反两方面提出了规范,而且将道德要求与行医诊治的各个环节相结合,很好地将德与术交融为一。此外,还出现了传统医家借用道家“功过格”以及具有佛教特点的“戒律”等规范形式,将医业行为细化,并逐条进行了评价。比如就有关取酬原则来说的:“医士贫富一体,细心审察定方,疗一轻疾,不取酬。一功。疗一关系性命重疾,虽取酬。准十功。不取酬者。准百功。若待极贫人,并能施药不吝,照钱数记功。虽一剂药不满十文,亦准一功。”[6]也有鼓励救济施舍行为的:“遇贫人危疾,助医药钱米。百钱,准一功。贫人偶为之者,虽十钱、五钱与百钱同论。疫疠设局施药施医。百钱,准一功。普施应病丸散膏药。百钱,准一功。倡募刻一济人善书。随缘乐助易,倡首劝募难,故特记五十功,刻施经验良方。百钱,准一功。”[6]这是以“功”的形式表现鼓励,并以“功”的大小衡量道德意义的大小。功过格同时还以“过”的形式批评了不良行为:“秘一经验方。二十过。为师就一人学业,品德兼全。准百功。误一门人。五十过。”[6]通过“过”的多少表现后果的严重程度。有过僧家经历的喻昌,还通过佛门戒律指出医家也应有“医门戒律”。他说:“尝羡释门,犯戒之僧即不得与众僧共住,其不退心者,自执粪秽杂役三年,乃恳律僧二十众佛前保举,始得复为佛子。当今世而有自讼之医乎?昌望之以胜医任矣!”。[7]从内容上看,这在医德史上产生了久远的影响。比如孙思邈说:“人行阳德,人自报之;人行阴德,鬼神报之。人行阳恶,人自报之;人行阴恶,鬼神害之。寻此二途,阴阳报施岂诬也哉。所以医人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但作救苦之心,于冥运道中,自感多福者耳”;[2]缪希雍:“人命至重,冥报难逃,勿为一时衣食,自贻莫忏之罪于千百劫”;[8]张杲:“乘人之急,故意求财,用心不仁,冥冥之中自有祸之者”;[9]吴楚:“夫人病不医,伤在性命。医病不医,伤在阴骘。性命伤仅一身之害也,阴骘伤乃子孙之害也”。[2]
在传统医德思想中,以“慎”为核心的医德规范是以“医乃仁术”为依据的,医乃仁术是传统医德的基本原则,[10]其精神实质在于对生命的关爱,这种关爱在医疗过程中生发出对生命的敬畏,这种敬畏贯彻在医业、医术的使用,激发出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传统医家怀着如履薄冰的态度,对待整个行医过程。所以,“慎”是“仁”的最具体化的表现。可见,医业道德规范是传统医德最具体化、最外在化的表现。以“慎”为核心的观念蕴含着生命至重至贵的价值观,反映着传统文化重生、惜生的特点,表现了医乃仁术的精神实质,说明传统儒、释、道文化思想都对传统医德产生了较深刻的影响。因此,医业道德规范是认识、理解传统医德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内容。
[1]张景岳.张景岳医学全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889.
[2]孙思邈.备急千金药方[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9:2.
[4]寇宗奭.重刊本草衍义[M]∥中国医学大成.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7:199.
[5]萧京.轩岐救正论[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83:518.
[6]顾世澄.疡医大全[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4:134-135.
[7]喻昌.医门法律[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2:3.
[8]缪希雍.神农本草经疏[M]∥缪希雍医学全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33.
[9]张杲.医说[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7.
[10]吴楚.吴氏医话二则[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