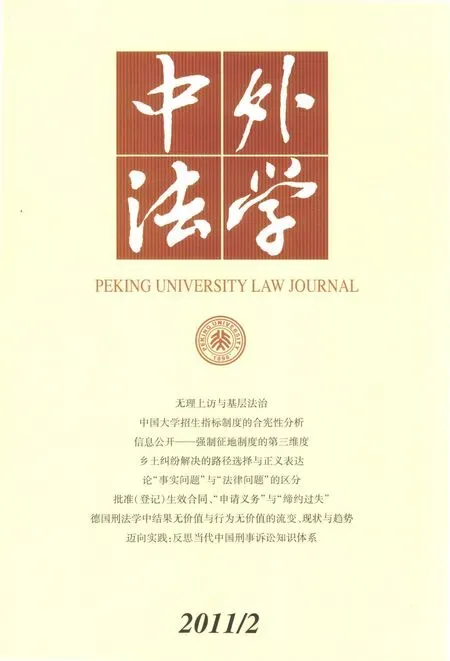权利不确定性与知识产权停止侵害请求权之限制
陈 武
知识产权是一种既能促进也能延滞国家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的制度。为促进技术创新和文化艺术繁荣,理想的知识产权制度应该是一个运行良好的“黑匣子”:它不仅需要一个设计良好的权利获取机制,也需要一个科学的权利执行和救济机制。〔1〕Jay P.Kesan&Andres A.Gallo,Why“Bad”Patents Survive in the Market and How Should We Change? -The Private and Social Costs of Patents,55Em ory L.J.61,69(2006).然而现实中的制度往往远离理想状态,在全球化和知识经济引发的新竞争生态中,各种商业主体对知识产权的倚重和策略性运用,使得知识产权权利的产生和运行偏离了正常的轨迹,而知识产权救济制度也在无意中推波助澜。由此,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兹评论说:“知识产权的基本经济原理是以更快的创新来弥补垄断带来的无效率损失。但是越来越明显的是大量错误形成并得到保护的知识产权实际上抑制了创新。”〔2〕Joseph E.Stiglitz,Economic Found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57Duke L.J.1693,1709 (2008).
“无救济则无权利”,在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强势话语和倡导自主创新的中国语境下,司法机关为知识产权主体提供了日益强化的权利救济。其中停止侵害 (禁令)〔3〕作为一种责任承担方式,知识产权侵权判决中的“停止侵害”与英美法中“永久禁令 (permanent injunction)”具有基本相同的功能。为了表述方便,若无特别指明,本文中的禁令是指“永久禁令”。救济在当前知识产权诉讼中得以广泛使用,但事情往往过犹不及,在目前的创新环境和司法实践中,法院在知识产权侵权判决中采用了近乎绝对化的停止侵害救济。这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技术创新的动力并对市场竞争带来负面影响。遗憾的是,目前这方面的理论研究较为薄弱,也难以指导司法实践,有鉴于此,本文从知识产权权利的不确定性出发,分析知识产权停止侵害救济的负面效应并提出限制性使用的建议,以求教于方家。
一、知识产权侵权纠纷中停止侵害救济的绝对化
知识产权不仅是法律手段,也是商业竞争工具,它是权利持有者为了不让竞争对手销售自己的产品而拥有的一种垄断顾客的权利。〔4〕参见(日)富田彻男:《市场竞争中的知识产权》,商务印书馆 2000年版,页 13。换言之,知识产权的价值实现需要知识产权的执行,而这建立在权利持有者行使排他权〔5〕知识产权的排他权是指在知识产权执行中,禁止其他人在商业上使用权利人被保护的特定知识。“IP enforcement is generally connoted with the enforcement of right holder’s exclusive entitlements to prevent others from using the IP protected subjectmatter”,See Henning Grosse Ruse-Khan,IP Enforcement beyond Exclusive Rights,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Com petition&Tax Law Research PaperNo.09-08.,Available at SSRN:http://ssrn.com/abstract=1445292.的基础上。但作为知识产权客体的信息并不能通过占有来实现排他性,因此知识产权排他权的行使通常依赖于“禁令”的颁布。尽管“禁令”是TR IPs协议和英美法上的术语,但由于 TR IPs协议对世界知识产权立法的影响,我国知识产权理论界和实务界也普遍接受这一称谓,〔6〕参见张广良:《知识产权侵权民事救济》,法律出版社 2003年版,页 52-61。只是正式立法表述上沿用大陆法系的术语:我国《专利法》、《商标法》和《著作权法》中的“诉前停止侵权”条款与英美法中的“临时禁令”在效果、适用条件上较为接近;而知识产权侵权判决中的“停止侵权”或“停止侵害”基本上等同于“永久禁令”。需要注意的是,“诉前停止侵权”与“停止侵权”有重要区别,前者更多的类似于一种程序性的临时权利保全措施,后者则是责任承担方式。本文侧重论述在知识产权侵权纠纷中“停止侵害”(永久禁令)救济的适用问题。
停止侵害作为一种责任承担方式,〔7〕以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为代表的传统民法将侵权责任承担方式限定为损害赔偿,同时认可独立于侵权请求权的物权请求权,而我国以现行《民法通则》为核心的民事法律体系确立了一种不同于传统民法的侵权责任制度。这导致在侵权请求权与物权请求权的关系上民法学界存有争议,焦点在于停止侵害、返还财产、消除危险是否是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参见王轶:“论侵权责任承担方式”,《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年第 3期,页 16-19。而现行《侵权责任法》界定的侵权责任承担方式不仅包括损害赔偿,还包括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等。在我国知识产权侵权纠纷中被广泛采用。若著作权、专利权或商标权侵权得以认定,则权利人获得“停止侵害”救济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这可以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报告中得到印证:“2002~2009年,全国地方法院共受理与知识产权有关的诉前临时禁令申请案件 808件,裁定支持率达到 84.18%。在认定侵权成立的情况下,一般都会责令侵权人立即停止侵害,同时确保权利人获得足够的损害赔偿,依法适当减轻权利人的赔偿举证责任。”〔8〕参见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 (2009年),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0-04/ 21/c_1246383.htm,最后访问日期:2011年 3月 1日。最高人民法院从未就判决“停止侵害”问题作过司法解释,各级法院也未感到判决停止侵权有什么不妥,因此只有极少拒绝停止侵权救济的判决。〔9〕迄今为止,中国法院在侵权判决中仅作出过二例不停止侵权判决:一是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01)闽知初字第 4号判决。该判决称:为平衡权利人利益及社会公众利益,原告晶源公司要求被告华阳公司停止侵权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二是珠海市晶艺玻璃工程有限公司诉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侵害专利权。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考虑到机场的特殊性,判决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可继续使用被控侵权产品,但应支付适当的使用费。参见(2004)穗中法民三知初字第 581号。究其原因,这种绝对化的停止侵害救济模式源于对知识产权的物权化理解和对知识产权排他权的错误认识:
首先,学术界通说〔10〕参见吴汉东:“试论知识产权的‘物上请求权’与侵权赔偿请求权”,《法商研究》2001年第 5期,页7;另参见王利明:《物权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页 152;崔建远:“绝对权请求权抑或侵权责任方式”,《法学》2002年第 11期,页 41。认为知识产权与所有权一样,是一种对世权、绝对权,可以准用“物权请求权”〔11〕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我国《侵权责任法》将停止侵害作为一种责任承担方式,“但就物权的保护而言,当以停止侵害作为请求内容时,实际上是一种被称为‘债权请求权’的‘物权请求权’”。王轶,见前注〔7〕,页 16。制度。物权请求权的内容包括返还原物请求权、排除妨害请求权、停止侵害和消除危险请求权及恢复原状请求权。但由于知识产权的特殊性,知识产权的物权请求权主要包括排除妨害请求权与消除危险请求权,这是一种请求停止侵害的物权之诉。〔12〕吴汉东,前注〔10〕,页 9。有学者指出对知识产权保护仅规定侵权请求权而无“类物权请求权”是“舍源逐流或舍本逐末”,并明确提出应设立知识产权请求权,其主要内容是停止侵害请求权,具有制止正在进行的侵害行为或者防止侵害行为发生的独特功能。〔13〕参见郑成思:《知识产权法:新世纪初的若干研究重点》,法律出版社 2004年版,页 132。这种绝对权请求权适用的条件是,只要侵权事实成立即可,不需要具备主观条件如故意、过失。〔14〕郑成思,同上注,页 124;另参见杨明:“知识产权请求权功能的解析与展开”,《烟台大学学报》2006年第 1期,页 16。这种学说对司法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法院在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颁发“永久禁令”,所秉承的原则是“绝对权——侵权——停止侵害”模式,即知识产权是绝对权,任何人违法侵犯,均应禁止,即对特定侵权人下达禁令。〔15〕参见张玉瑞:“浅析专利侵权禁令的限制(上)”,载《中国知识产权报》2月 24日,第 4版。
其次,人们通常将知识产权视为一种排他权,而且是排除他人实施其发明创造的绝对性权利,并由此将排他权和禁令保护划等号。其中专利权表现得最为明显。有法院甚至认为,既然专利法规定“专利权人有权排除他人使用、许诺销售、销售有关发明”,那么永久禁令,是原告的法定权利,原则上不属于法院根据衡平原则的自由裁量范围。〔16〕在 eBay案件中美国联邦上诉法院持这种观点;但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却认为:根据某种原则创造一种权利,和该权利的保护,属于两个不同领域,禁令应根据衡平原则做出。参见 eBay Inc.v.M ercExchange, L.L.C.,126 S.Ct.1837(2006)。这种观点曲解了专利权排他性的本质,专利制度并没有授予发明者排除其他人实施其发明的绝对权 (absolute right),相反,专利制度只是给予专利权人请求停止侵权的权利。〔17〕Mark A.Lemley and Carl Shapiro,Probabilistic Patents,19J.Econ.Persp.75,83(2005).著作权和商标权亦然。简言之,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并非一种绝对权,权利人享有停止侵害的请求权,而是否颁发停止侵害的禁令,则是法院的自由裁量权。
由于上述观念的影响,众多学者将知识产权作为普通的财产权、绝对权对待,知识产权的排他权被简单套用物权的排他权来解释。根据经典的财产权理论,对于非法侵害的适当救济便是通过禁令禁止对该财产的使用。〔18〕Mark A.Lemley and Philip J.Weiser,Should Property or Liability Rules Govern Information?85Tex. L.Rev.783,793(2007).由于财产权与禁令的关系非常密切,以至于法经济学者将禁令救济称为“财产规则”(property rules)。〔19〕Calabresi和Melamed在 1972年首次提出了财产规则 (property rules)与责任规则 (liability rules)的理论框架,并研究了二者在解决产权纠纷时何者更有效率。See Guido Calabresi and A.Douglas Melamed, Property Rules,Liability Rules,and Inalienability:One View of the Cathedral,85Harv.L.Rev.1089(1972).法院在知识产权侵权中也根据“财产规则”广泛采用停止侵害措施。然而,这种类比和借用忽略了知识产权特殊的权利属性,并对权利执行带来不合意的结果。
二、知识产权权利的不确定性
在 Calabresi和Melamed看来,选择不同的救济形式代表了执行合法权利的不同方式,财产规则提供了禁令而责任规则提供了非自愿方式的金钱赔偿。〔20〕See Guido Calabresi,supra note 19,pp.1089-1102.他们认为:当交易成本很低时,应采取财产规则来保护产权,而当交易成本很高时,责任规则是更为有效的保护方式。在Calabresi和Melamed以交易成本为核心要素对产权规则与责任规则进行选择的逻辑中,包含着一个重要假设——财产权的范围是清晰界定的。〔21〕See Lemley,supra note 18,p.789.但是该论证范例中的财产是不动产,却没有讨论知识产权。
与不动产清晰的权利边界相比,知识产权的权利边界高度不确定,这对于知识产权纠纷的救济方式产生重要影响。下面以著作权和专利权为例予以说明:
第一,从权利产生的角度考虑,著作权产生的重要前提是作品具有“独创性”;同时,著作权保护表达而非思想,它通过作品的文字表述,来确定可保护的权利种类和权利范围。然而,判断独创性的标准非常模糊,“表达”和“思想”的区分也并非泾渭分明。尤其对于地名册、电话本、计算机程序等功能性作品来说,作品的内容只是对事实汇编而已,具有很低的独创性,甚至毫无独创性,而计算机程序中的表达和思想也难以界分。实践中法院主要根据“思想与表达二分法”而非独创性要件做出判断,并依据个案逐一确定是否应受著作权保护以及保护的范围。〔22〕James Gibson,Risk Aversion and RightsAccretion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Law,116YaleL.J.882,897 (2007).从著作权的权利实施层面考虑,判断著作权侵权的标准是“实质相似性测试”,它在实践中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新著作的产生几乎总是从原有作品中有所借鉴,这从借鉴者角度来说提高了侵权的几率,虽然具有合理使用作为重要抗辩理由,但衡量合理使用的四要素测试,也在个案适用中才能明确。因此,著作权的权利边界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第二,专利权基于发明创造而产生,然而创造是一种抽象的思想和思维活动,需要借助有形的物体体现出来。从实体上说,授予一项专利权需要发明具有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新颖性和创造性的考察都需要与现有技术(prior art)做对比,囿于信息、检索技术等限制,作为参照的现有技术有限,因此授权难免出现错误;而且新颖性和创造性的判断又具有较大的主观性,专利法通过拟制“现有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person have ordinary skill in the art,即PHOSITA)”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仍然难以保证判断上的失误。在程序上,获得专利需要递交合格的专利申请书(包括权利要求书、说明书)等,并提供完整的实施例。由于专利权的范围以权利要求书为准,权利要求书是将发明思想转化为文字以表达,专利申请撰写人的水平、文字本身的模糊性等都决定了专利权具有内在的不确定性。同时,专利权排他性的执行通常需要解释其权利要求,以考虑侵权方的产品或方法是否落入专利权的范围。而等同侵权原则(doctrine of equivalents)的运用,让专利权人可以合法捕获后期非实质的发明改进活动,判断权利要求书所保护的发明与被控侵权物之间是否等同的标准是非实质区别 (insubstantial differences)。这又是一个抽象标准,因此在后的技术应用者和改造者承担诸多无法预见的侵权风险。
综上分析,由于作品和发明创造自身的特殊性,知识产权制度无法从权利创设和权利执行层面清晰地界定著作权和专利权的边界,这种不确定性合乎制度理性,〔23〕“专利自初审公告之日到获准授权后的专利存续期间,其权利一直是不确定的,而且这种不确定性有助于实现专利法促进创新与维护社会公益的双重目的。”谢铭洋:《智慧财产权基本问题研究》,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 1999年版,页 211。而且从经济效率上看,“清晰界定权利”并非总是有效率的。〔24〕Stewart E.Sterk,Property rules,Liability Rules,and Uncertainty about Property Rights,106M ich.L. Rev.1285,1292(2008).若不能清晰界定一项权利,便不能根据普通的“财产规则”轻易提供停止侵害救济,否则会事与愿违,本文第三部分将论述停止侵害救济带来的威胁 (以下简称“禁令威胁”)及其负面效应。但也许有学者追问,既然知识产权的权利边界不清晰,那么在适用“责任规则”时,是否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在特定的情况下,采用责任规则可以避免停止侵害救济的负面效果,原因首先在于责任规则是事后救济,它不产生搜寻不确定财产边界的动力;其次是知识产权侵权赔偿认定的特殊规则,而法院会根据原告损失的利润或者合理的许可费(在前者难以确定时适用后者)等方式确定赔偿数额。〔25〕关于赔偿数额认定的要素顺序和方法,请参见Mark A.Lemley,DistinguishingLost Profits from Reasonable Royalties,51W illiam&M ary Law Review655,663(2009)。
三、知识产权禁令威胁及其带来的不合理成本
(一)知识产权权利执行中的禁令威胁
知识产权权利人需要行使排他权来实现合法垄断,进而获取竞争优势。知识产权排他权的执行过程通常有两种情形:第一,权利使用方认可和尊重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的有效性,双方可以自愿达成许可协议,排他权可以在较低的交易成本中自然实现;第二,其他市场竞争者对权利有效性并不认可,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使用某项知识产权,则权利人可能以诉讼威胁促使所谓的侵权方实现和解谈判并获取收益;如果不能达成和解,可能最终通过诉讼实现权利的强制执行。
市场主体拥有一项专利或商标,仅代表排除其他竞争对手的可能性而非必然性,权利人还必须通过申请禁令去“阻止”竞争者或潜在竞争者的市场活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彼得·德霍斯说:阻止是知识财产法的额外功能。〔26〕参见(澳)彼得·德霍斯:《知识财产法哲学》,周林译,商务印书馆 2008年版,页 146。当前,知识产权的垄断性预期引发了市场主体获取专利权、商标权的热潮。以专利权为例,世界各主要国家的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急剧攀升,与此同时,这些授权专利的新颖性和创造性受到广泛的批评与怀疑,尤其在计算机、信息技术等行业出现大量没有价值的专利,但许多技术创新主体对这类权利标签并不认可,有学者甚至批评说:专利在创新发展的车轮中已经变成了“沙子”,而不是“润滑剂”。〔27〕参见(美)亚当·杰夫、乔西·勒纳:《创新及其不满》,罗建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页21。
在这种环境下,申请禁令是知识产权持有人常用的阻止策略,这对其他竞争者的创新活动造成了威胁。一些公司专门购买专利从事许可与诉讼,并以非法使用其专利技术为由,起诉研发活动集中的厂商以获取损害赔偿金,有学者将这种经营方式称为“专利敲诈 (patent trolls)”。〔28〕Markus Reitzig,Joachim Henkel and Christopher Heath,On Sharks,Trolls,and Their Patent Prey-Unrealistic Damage Awards and Firms’Strategies ofBeing Infringed.36Research Policy134,145(2007).专利敲诈使从事技术研发和产品制造的许多公司难以注意到小发明者的专利并可能落入侵权的陷阱,专利持有者一旦获得禁令将迫使下游的生产者将产品撤离市场。特别是在信息技术时代,很多产品被成千上万个不同的专利覆盖。例如在 3G移动通信技术中有数千项核心专利,而外围专利更是数以万计,处于行业下游的手机制造商面临专利侵权指控的风险巨大。在包含多个专利技术的产品上,如果某项弱专利覆盖了其中一个并不重要的技术细节,禁令的发布对产品制造者来说就是一项“可置信威胁 (credible threat)”。〔29〕MichaelMeurer,ControllingOpportunistic and Anti-Competitive Intellectual PropertyLitigation,44B. C.L.Rev.509,521(2003).在临时禁令或永久禁令的威胁下,很多公司愿意事前获取许可来降低风险。
简言之,禁令威胁反映了在权利边界不确定的条件下,知识产权权利持有人在获利动机下对禁令制度的策略性运用。禁令威胁促成了权利人采用知识产权要挟策略 (holdup strategy),要挟策略采纳者往往发布侵权警告函,以诉讼和申请禁令相威胁,如果在诉讼中胜诉的话,无过错的侵权人不仅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而且面临将产品撤离相关市场的被动局面。在专利权人与(潜在)侵权者的博弈中,以获取禁令为威胁极大提高了专利权人的谈判能力,并可能导致专利许可费的价格超出该专利技术的正常价值。〔30〕Mark Lemley and Carl Shapiro,Patent Holdup and Royalty Stacking,85Tex.L.Rev.1991,2003 (2007).
(二)禁令威胁带来的不合理成本
权利人对知识产权禁令制度的策略性运用不仅增加创新主体的搜索成本,也加剧了司法机关颁发禁令中的错误,下面分别予以阐述:
1.禁令威胁下搜索成本与许可成本的增加
许多财产权的边界不是不证自明的,潜在使用方也不完全清楚使用这些财产权是否会侵权,这对知识产权来说尤其明显。而获取必要的信息来解决这些不确定性需要付出一定的搜索成本,并可能带来无效率。〔31〕See Sterk,supra note 24,p.1288.然而,法律规则可以创造出潜在使用方搜索权利边界的动机,即使这种搜索是无效率的。潜在的资源使用方在财产规则救济下通常面临三种选择:(1)使用该专利或版权作品而不调查权利人和权利边界;(2)不使用该权利;(3)在调查清楚权利边界后再使用。〔32〕See Sterk,supra note 24,p.1308.
以著作权为例,著作权法的思想表达二分法、实质相似性测试和合理使用抗辩,导致了著作权范围的模糊性。这意味着利用已被著作权化的材料难以事前做出是否合法的判断,对于决定某种特定的使用是否符合著作权的范围,需要付出很高的搜索成本。例如,潜在的使用者如果试图利用某一受著作权保护的音乐作品或电视节目,他需要知道该作品是否仍在保护期内,该作品现行的权利人有哪些?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这些作品上有多个作者,即使知道了原始作者,但是取得所有权利人的许可就需要额外成本。而对于出版公司来说,作者对其所做的合法版权申明却没有对外的免责效力,而亲自查明一个音乐作品或电视节目是否侵权其他作品的版权又很困难。现实生活中作品使用人投入的人力物力越多,就会越关注并试图规避风险,倾向于“风险厌恶(risk aversion)”,为了满足先前的投资和下游发行人的利益需求,电影和电视节目的制片人会采取许可策略避免禁令威胁和诉讼赔偿带来的风险。〔33〕James Gibson,Risk Aversion and RightsAccretion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Law,116YaleL.J.882,905 (2007).例如,一部纪录片题材的电影拍摄和制作需要插播分属于其他两个作者的图片、音乐时,除非十分清楚其没有责任,否则一般会选择全部获得许可。如此一来,使用方的许可成本会大大增加。
同样,专利权范围的不确定性让使用方难以从事前准确判断一项专利是否覆盖了一件产品。为消除侵权带来的禁令威胁,当制造产品可能用到一项产品或方法发明时,制造商需要检索和分析该专利的权利要求以避免风险,但是清晰查明专利权利要求所覆盖的范围则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而且穷尽专利局的记录也不能保证使用该发明是否侵权。而“专利丛林”的存在,会进一步增加创新主体的搜寻成本,这抑制了创新主体从事研究开发的积极性,从而有悖于专利制度的初衷。
2.知识产权禁令救济带来的错误成本
一个权利若不能被清晰地界定,也就意味着禁令救济会带来一些错误成本。例如保护土地所有权的禁令可以根据所有权的边界而定,然而,一个针对不确定的财产权的禁令则会产生保护不足或保护过度的问题。当法院在界定不确定的权利边界犯错误时,作为财产规则的禁令倾向于禁止合法行为也禁止非法行为。〔34〕See Lemley,supra 18,p.803.
临时禁令 (诉前停止侵权)对权利人提供了强有力的保护,但在尚未认定被控行为构成侵权之前就禁止某些可能的合法行为,对于被控侵权人来说也具有相当的危险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对诉前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和《关于诉前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和保全证据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申请临时禁令的理由是:如不及时制止相关行为会使权利人或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损害的具体说明。在实体方面,司法解释要求申请人提供证明权利真实有效的证据及证明被申请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权行为的证据。司法实践中法院审查的重点是权利人“胜诉的可能性”,但有相当一部分裁定书在决定给予临时禁令时没有分析具体理由。〔35〕参见 9董晓敏:“论知识产权诉讼中的临时禁令”,《法律适用》2008年第 7期,页 2。最关键的问题是法院缺乏对权利有效性的审查,尽管专利权人在提出申请时应当提交证明其专利权真实有效的文件,包括专利证书、权利要求书、说明书、专利年费交纳凭证等,利害关系人应当提供有关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及其在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备案的证明材料,〔36〕参见《关于对诉前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 4条。但这些证据并不能充分证明权利的有效性。由于我国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的权利状态十分不稳定,而且法院无权作出权利有效性的裁决,实践中可能出现尽管法院发出了诉前禁令,但后来的程序中专利被宣告无效或权利范围的缩小。〔37〕此外,由于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体制的双轨制,《专利法》第 60条赋予专利行政机关责令涉嫌侵权方“立即停止侵权行为”的权限,这更容易造成临时禁令救济措施的滥用。上述问题会加剧临时禁令颁发中的错误。
即使在财产权利明确的知识产权案件中,法律也不能将禁令限制在侵权的范围内,这是由产品组合的物理属性决定的。假设你享有专利权的DVD解码技术用在我生产的 DVD产品中,在产品制造出来以后,一个禁止我侵犯解码技术的禁令同样禁止我销售产品中非侵权的部分,因此禁令范围就成为一个难题。法院要么不发布禁令来保护该部分产品专利,要么颁布禁令而使整个产品不能销售、使用,这种情形下颁布的禁令难免产生保护过度的错误成本。
如上文所述,在特定情况下,知识产权的停止侵害救济将对所谓的侵权行为人带来不合理的威胁,而权利人则可以通过停止侵害请求权成功地实施知识产权要挟策略,获取超额的许可费等垄断利益。要挟策略通常产生于某一产品上存有大量知识产权的领域以及具有累积性创新特点的技术领域。〔38〕参见梁志文:“反思知识产权请求权理论——知识产权要挟策略与知识产权请求权的限制”,《清华法学》2008年第 4期,页 129。知识产权要挟策略的采纳者获取与行使知识产权的基本目的不是为了生产、销售产品或者提供相关服务,而是为了获取超额的知识产权许可使用费,或者排斥竞争。而要挟策略的实施,主要借助于停止侵害救济的巨大威力,因此知识产权停止侵害的适用应有所限制。
四、知识产权停止侵害请求权的限制
从理论上讲,知识产权作为立法者创设的具有排他性的稀缺权利资源,强化甚至绝对化其排他性,将给予知识生产者更加强烈的激励,从而促使其生产出更多的知识。但是,这种停止侵害请求权一旦被绝对化,则意味着对知识的任何使用行为都必须事先取得权利人的许可,由此带来的巨大交易成本很可能抵消使用权利本身带来的效率。为了解决权利保护与知识利用之间的两难问题,对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停止侵害请求权进行限制十分必要。
停止侵害救济的普遍化和绝对化源于知识产权的强保护政策倾向,这偏离了禁令救济的基本功能。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曾在专利侵权案件中当然地适用禁令救济,而不进行衡平考量。〔39〕参见孔祥俊:“论裁判的逻辑标准与政策标准——以知识产权法律适用问题为例”,《法律适用》2007年第 9期,页 15。但美国最高法院在不久前著名的 eBay案中纠正了这种做法,强调了传统的衡平标准。〔40〕eBay Inc.v.M ercExchange,L.L.C.,126 S.Ct.1837(2006).该案中MercExchange指控 eBay使用的“立刻购买”交易方法技术侵犯其专利权。美国联邦地方法院认定 eBay侵权,判决 eBay作出 3500万美元的损害赔偿,但拒绝签发永久性禁令;而联邦巡回上诉法院(CAFC)则部分推翻了这一判决,认定 eBay侵权并签发了永久性禁令。2006年5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全体无异议地做出终审判决,否定了CAFC就 MercExchange诉 ebay专利侵权案的二审判决,认为其错误在于以近乎绝对的方式对待永久禁令。eBay案让禁令救济的适用回归衡平精神,它是法院采用禁令措施的重要拐点,并且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广泛影响。
为了让知识产权保护回归激励创新和促进文化艺术繁荣的出发点,知识产权保护应处理好禁令救济和损害赔偿的关系:禁令属于衡平救济的主要方式,而损害赔偿是普通法的主要救济形式。〔41〕DouglasLaycock,The Death of the Irreparable Injury Rule,103Harv.L.Rev.687,698(1990).在二者的关系上,衡平救济是普通法救济程序的补充程序而不是替代程序,当事人启动衡平救济有一个限制条件,就是只有当普通法救济不充分时才能申请并获得衡平救济,这被称为“不充分性”标准。〔42〕参见和育东:“美国专利侵权的禁令救济”,《环球法律评论》2009年第 5期,页 129。根据美国判例法,要满足禁令的“不充分性”标准,需接受以下“四要件”的检验:①原告有合法的权利请求;②未来侵害是逼近的而且损害赔偿是“不充分”的;③禁令给被告造成的困难并非不成比例地大于给原告的收益;④符合公共利益。〔43〕JamesM.Fisher,Understanding Rem edies,New York:Matthew Bender,1999,p.276.在我国知识产权侵权审判中,若有下列三种情形之一,应考虑限制停止侵害救济手段的使用:
1.复杂知识产权产品上的单一部件侵权。在信息技术和多媒体技术日益发达的时代,一件产品包含数百乃至上千项专利,或者由多个著作权人的作品组成。由于知识产权权利的不确定性,尽管制造商事前进行了合理谨慎的调查并取得了几乎全部的许可,但产品的某一个部件仍存在侵权嫌疑。如果法院颁发被告停止侵权的禁令,则被告前期投入的研发成本、制造成本、权利许可费将全部变为沉没成本,造成重大的社会福利损失。同时颁布禁令给被告带来的损失和颁布禁令给原告带来的收益将明显失衡,由此不宜颁布禁令。如果侵权给原告造成一定的利润损失,而且该侵权部件的替换成本较低,除了要求被告赔偿损失外,法院还可以要求被告在一定期限内重新设计产品以避免侵权。如果重新设计该部件的成本极高,则应要求被告对今后的使用支付合理的许可费。〔44〕See Lemley and Shapiro,supra 30,pp.1996-2003.
2.侵权造成低社会损害,但颁发禁令将带来高移除成本(removal cost)。假定侵权的社会损害用权利人的损害减去侵权人的规避成本衡量,在某些情况下,侵权对权利人的损害很小,因为权利人并不和侵权人开发同样的市场,或者根本不会涉及市场活动。然而侵权一旦发生,法院即判决被告停止侵权来对权利人提供救济,则被告的移除成本可能非常高。〔45〕See Sterk,supra note 24,pp.1328-1331.例如,在宁勇诉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北京北大华亿影视文化有限责任公司、英国联华影视公司等著作权侵权纠纷中,二审法院认定被告在影片《卧虎藏龙》中未征得原告同意而使用其音乐作品,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同时认定影片《卧虎藏龙》的国内版侵犯了原告的署名权。由此,二审法院维持一审法院作出的“停止侵权”判决,即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北京北大华亿影视文化有限责任公司、英国联华影视公司停止侵害宁勇《丝路驼铃》阮曲署名权,在以任何形式再版电影《卧虎藏龙》时应当署名“宁勇作曲”,并将“宁勇编曲”纠正为“宁勇作曲”;并新增判决要求被告赔偿著作权人宁勇经济损失人民币 2万元。〔46〕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6)粤高法民三终字第 244号。但该判决有两个重大瑕疵:第一,仅对被告侵犯原告音乐作品的署名权做出判决,没有对被告侵犯原告音乐作品复制权的行为作出判决;第二,尽管法院判决三被告“停止侵权”,但仅规定再版电影时应当明确署名,对于已经发行的侵权电影如何停止侵权不得而知。因为停止侵害只是民事责任方式的一种概括规定,就像其他民事责任方式一样,具体应用时尚需根据个案情况来加以明确,否则就不具有操作性。如此一来,该判决既没有达到充分保护原告权利的作用,又没有平衡、原被告之间的利益冲突。
其实在上述案件中,被告在影片制作中没有侵权之故意。相反,由于电影制作过程中音乐作品许可的复杂性,被告在明确相关权利人并取得许可过程中付出了较高的搜寻成本,而且侵权行为造成的社会损害较小,客观上也促进了原告作品的传播。若法院判决被告停止侵权,则被告需要召回前期发行的侵权产品除去侵权标识,而这会带来很高的移除成本,此时的禁令救济方式便会带来无效率。因此,法院在处理这个侵权纠纷时应持明确的态度,虽认定被告侵害原告的复制权、署名权,但并不对前期已经发行的电影颁发禁令,而是判决被告支付合理的金钱赔偿,赔偿额度可以根据每部电影的许可费乘以发行的数量予以确定。
3.权利人为专利非实施主体 (non-practicing entities)并故意设置陷阱实施专利敲诈,而被控侵权人出于善意使用涉案技术。专利的非实施主体通常有两类:一是专门从事专利许可与诉讼的公司;二是独立从事研究开发的专利权人及其创立的尚未生产制造产品的公司。其中前一类公司经常从事专利敲诈活动,它们首先选择购买具有经济价值的专利,这些专利通常属于商业上竞争激烈、具有累积性创新特点的技术领域并可以覆盖某些制造商的产品。其次选择目标公司并发出侵权警告函和专利许可费使用标准,旨在以提起诉讼和申请禁令相威胁,获取丰厚的权利许可收益。被控侵权人的善意如何确定,笔者认为被告若有证据证明自己通过独立的研发开发活动获得了使用中的技术,〔47〕See Lemley and Shapiro,supra 30,p.2001.或者在研发生产前进行了谨慎合理的权利调查和权利许可活动后仍无法确定权利人所主张的知识产权之存在,则可以证明自己的主观善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专利敲诈者作为原告提出停止侵害的诉讼请求,而被告的侵权行为成立,法院应当判决赔偿合理的专利许可费而不轻易发布停止侵权的禁令,因为此时金钱赔偿对专利权的救济是充分的。
五、结语:转向责任规则?
尽管知识产权在今天已经广泛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我们几乎还无法去把握它的实质;〔48〕参见易继明:“评财产权劳动学说”,《法学研究》2000年第 3期,页 98。因此我们经常借助物权法的基本原理来理解知识产权,借用物权保护的基本方法来保护知识产权,以至于出现南橘北枳、事与愿违的尴尬局面。知识产权已经到了成熟的年龄,它不需要通过借用其他领域的法律理论来寻求自身的合法性,而是需要重申自身特性。〔49〕Mark Lemley,Property,Intellectual Property,and Free Riding,83Texas L.Rev.1031,1053(2005).知识产权并非法律赋予权利人排除他人实施其发明创造的绝对权,而是权利持有者进入法院主张排他权的“入场券”。
在知识产权权利人和相关市场竞争者的利益博弈中,法院选择财产规则 (禁令)抑或责任规则(损害赔偿)来解决侵权纠纷,还是二者同时采用,将对权利人和资源使用方产生不同的成本影响,换言之,二者产生的界权成本不同。〔50〕关于界权成本的概念及其意义,参见凌斌:“界权成本问题:科斯定理及其推论的澄清与反思”,《中外法学》2010年第 1期,页 108。在财产规则下,资源使用方的成本和其造成的损害无关,而且一旦使用方落入侵权陷阱,判决“停止侵权”会给使用方带来很大的成本损失。因此在财产规则的救济规则中,权利使用方因惧怕禁令而往往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用于搜索权利边界,即使它产生很小的社会收益。而相反,责任规则不产生搜寻不确定财产边界的动力,因为赔偿成本和损害的程度有关。〔51〕See Sterk,supra note 24,p.1329.财产规则禁止任何非自愿的财产转移,是事前禁止;而责任规则准许一方按照法院规定的价格购入另一方的财产,属于事后救济,这种事后救济也可以对未来的市场交易产生事前激励,但与事前禁止不同的是,它留出了一定情况下进行权利调整从而增进社会福利的可能性。〔52〕参见凌斌:“肥羊之争:产权界定的法学和经济学思考”,《中国法学》2008年第 5期,页 183。
由于知识产权权利的不确定性和技术创新的日益复杂化,后续创新者面临极高的风险控制成本,而财产规则指导下的禁令救济会造就权利人的强者地位,这促成了权利人实施知识产权要挟策略,并形成“赢者通吃”的局面,进而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本文指出,当“财产规则”保护这种无形财产权的定势做法出现一系列问题时,我们需要反思采用禁令规则的合理性,并提出限制性使用禁令救济的条件。尽管选择有效率的知识产权救济方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需要重申的是,是否发布禁令,属于法院根据衡平原则自由裁量的范围。至于如何采用作为责任规则的损害赔偿从事后角度促进产权交易、提高创新动力,则是一个未完待续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