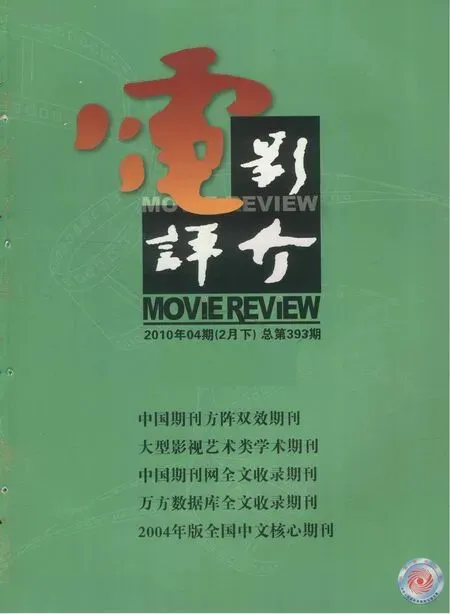楚歌的嬗变刍议
楚歌,一般指具有浓郁楚地特色的、体近屈骚的一种歌诗形式。它至少有两个指向:一是先秦时代的楚地民间歌谣;二是汉初文人及贵族的即兴抒怀之作及后代文人的拟作。所以,“准确的说,楚歌并不完全是产生于楚地的诗歌,而是指采用楚歌体制的一类诗歌。”[1]其体例包括以下几个基本特征:一是句中多用“兮”字,以“兮”为标志,楚歌句中之“兮”字,兼具节奏与句法的性质和作用。如《越人歌》中的“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因“兮”字用于句内,自然地形成了前后两个音节。二是句式长短错落,不拘一格,自由活泼。三是篇章短小。
楚歌在其历史发展中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是楚歌的萌生
“由于楚辞是楚地文学的成熟类型,因此楚歌常常被认为是源于楚辞的一种诗歌形式。”[2]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楚歌的产生要更早。最早见于《吴越春秋》记载的《弹歌》。其中载:春秋末年越国国君勾践向楚国的射箭能手陈音,询问弓弹的道理,陈音在回答时引用了这首民歌。当时是唱是诵,无从考证,但后人还是将词记录了下来:
“断竹,续竹;飞土,逐实。”
原始社会,先民们以狩猎为生。由于生产能力水平低下,刀耕火种,狩猎的手段也极为落后。弓箭这种复合武器出现以后,可以射鸟兽,很大程度上增强了人们应对自然界的能力。
“断竹,续竹”,指出的是弓箭的制作过程。这就是先将竹竿截断,然后用弦将截断的竹竿连接两头制成弓箭。有了弓箭,一场狩猎活动开始了:“飞土,逐实”。一只只箭头腾空射出,击中了一只只猎物,人们欢乐地追逐着,满载而归。“飞土”,指最初没射中,射入泥土中。“逐实”是说猎人们经过努力,追赶被击伤的鸟兽之类的猎物。“实”,古“肉”字。
此歌高度凝练地表现了从砍竹、制弓、攻击到逐兽的整个过程,语言简洁,节奏明快,富于跳跃感,体现了远古歌谣的质朴风格。
不过,它应当算不上什么正式的歌诗作品,较为普遍的看法是,楚歌由夏禹时涂山氏之女始作南音之始,逐渐发展而来。即出自《吕氏春秋》的《候人歌》,传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其妻涂山氏在等侯他归来时作此歌,歌曰:“候人兮猗!”虽为一句,“但‘兮’、‘猗’语助词的使用,已具有楚地民歌的语言特色。”[3]简短几字道出了心中的惆怅难言与诉不尽的绵绵幽思。这大概是中国古代最早的爱情诗和个人做品,并被认为是最早楚歌风格的歌诗。此外,《山海经》中的《神北行》,有人认为是楚地民谣,但它应当作为巫觋的符术咒语更为贴切。
二是《诗经》中的南音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分风(160篇)、雅(105篇)、颂(40篇)三大部分,计有15国风,但其中并没有“楚风”,而只有合称“二南”的《周南》与《召南》。《周南》即周公治地之南的歌诗,《召南》即召公治地之南的歌诗。所以,“二南”的歌诗实多为南方楚地民歌。其中,从诗歌的外在语言结构上来讲,《江有祀》等篇无“兮”字句,我们很难认定其为楚歌。《汉广》篇虽无“兮”字句,却有语助词“思”的运用,它与“兮”字有异曲同工之妙,因而唱出了一首荡气回肠的汉水恋歌。而《摽有梅》、《野有死麕》等篇,则有“兮”字句的运用,当为楚歌。如《野有死麕》: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
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
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
全诗描述的是男子向女子献猎物求爱的情景。有景、有情、有人、有物、有活动、有发展,在《诗》三百中别具一格。
三是《诗经》后逐步成型的楚歌
楚歌在最初产生之时,包括可供吟唱的歌词,也包括吟唱时特殊的节奏声调。可和辞而歌。句式亦复杂多变。及至后来,它与音乐逐渐疏离,更重吟唱的歌词和句式体制。体例亦逐步成型。主要采用“0000兮000”及“000兮000”两种句式。[4]
这时期的楚歌,散见于各种典籍。如《说苑》记载的《楚人诵文子歌》、《越人歌》,《新序》中的《徐人歌》,《吴越春秋》记载的《河上歌》、《渔父歌》、《申包胥歌》,又如《论语•微子》载:“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避之,不得与之言。”《史记•孔子世家》亦载此事,后边又说:“于是孔子自楚反乎卫。是岁也,孔子年六十三。”可见,这首歌是春秋时期孔子在楚国听楚人接舆唱的。意即:楚国的狂人接舆唱着歌从孔子车前走过,他唱道:“凤鸟啊凤鸟啊!你的德行为什么衰退了呢?过去的事情已经不能换回了,未来的事情还来得及呀。算了吧,算了吧!如今那些从政的人都危险啊?”孔子下车,想和他交谈。接舆赶快走开了,孔子无法和他交谈。从这里可以看出,楚狂是位“贤人”,但又“佯狂不仕”,连楚王请他去做官都不肯,他对于孔老夫子的那种积极用世的态度不以为然,并予以嘲讽。《沧浪歌》又名《孺子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灌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灌我足。”《沧浪歌》早在春秋时期已经传唱,据《孟子•离娄上》载也是孔子在楚时所闻,屈原《渔父》用为渔父答屈子之词。
并且,随着楚国疆域的进一步扩张,楚歌亦在这些新占领区流行开来,甚至有向中原地区扩展的趋势,如《左传•哀公十三年》载申叔仪《乞粮歌》,曰:“公会单平公、晋定公、吴王夫差于黄池,吴申叔仪乞粮于公孙有山氏,歌曰:‘佩玉蕊兮余无所系之,旨酒一盛兮余与褐之父脱之。’”,此歌是吴人所唱的楚歌。又如《晏子春秋•内篇谏下》载:“(齐)景公为长座,将欲美之,有风雨作,公与晏子人坐饮酒,致堂上之乐,酒酣,晏子作歌曰:‘穗乎不得获,秋风至兮弹零落。风雨之拂杀也,太上之靡弊也。’歌终,顾而流涕,张躬而舞。公遂废酒罢役”。
四是秦至汉初楚歌的风行及其盛极而衰
至秦汉间,楚歌演变成为一种正式的诗文体例,并在全国流行开来,从地域和时间看,“楚歌是《诗经》四言体之后,乐府五言产生之前中国诗歌主要的形式”。楚歌发展到秦及西汉前期趋于鼎盛,出现了不少优秀的作品,并非只有通常看到的项羽的《垓下歌》、刘邦的《大风歌》等少数几篇。尤其汉代,“有着庞大的作家群体,创作时间贯穿于汉代始终” ,“汉代楚歌由帝系楚歌、王侯及皇室成员楚歌、士大夫楚歌三部分构成。”[5]
汉高祖豪爽而不喜文学,但他的家乡沛地属故楚,故特别喜爱楚声。《汉书•礼乐志》曰:“高祖乐楚声。”其《大风歌》开创了汉代帝系楚歌创作的先河,当他欲废太子不能得、极端烦闷时,便对戚夫人说:“为我楚舞,我为若楚歌。”作为开国君主,汉高祖的爱好和习惯自然会受到人们的推崇和模仿。随之而下的汉代皇帝创作的楚歌作品有:汉武帝刘彻《瓤子歌》(二首)、《天马歌》(二首)、《秋风辞》、《李夫人歌》,汉昭帝刘弗陵《黄鹊歌》,汉灵帝刘宏《招商歌)),汉少帝刘辩《悲歌》。
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从之,汉代帝妃和王侯贵胄也创作了大量的楚歌作品,赵王刘友、城阳王刘章、广川王刘去、燕王刘旦等都有楚歌传世。计有:赵土刘友《幽歌》,燕王刘旦《归空城歌》、广陵王刘胥《瑟歌》、广川王刘去《幽歌》、城阳土刘章《耕田歌》、淮南土刘安《八公操》等作品;此外,乌孙公主刘细君《悲愁歌》、戚夫人《舂歌》、唐姬《舞歌》也属于此类。
受其影响,汉代士人也纷纷参与楚歌的创作。他们有的是故楚之人,有的深受楚文化影响,都能创作楚歌。李陵《别歌》、司马相如《琴歌》、李延年《佳人歌》、徐淑《答秦嘉诗》、蔡琐《悲愤诗》(楚歌体)等作品即是。另外,汉代的一些辞赋在创作时也穿插了部分楚歌,枚乘《七发》中有《麦秀歌》、司马相如《美人赋》中有《独处室歌》、傅毅《七激》中有《涉景山歌》、张衡《定情赋》中有《大火歌》、张衡《舞赋》中有《雄逝雌翔歌》、蔡邕《释悔》中有《琴歌》。
审视汉代楚歌,可以注意到,其作品具有率真自然、慷慨愁绝的抒情风格,之中蕴涵着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其中,“生命、生命精神及其价值意义是最为突出的特点。”[6]
上举的汉代楚歌,无论是皇家之作,还是士人之作,都能够说明这一点。刘彻的《瓤子歌》表现的是在自然的力量面前,个人力量的渺小与悲哀;戚夫人的《舂歌》、唐姬的《舞歌》、乌孙公主的《悲愁歌》是对自己不幸命运的悲哀与绝望;李陵的《别歌》是个体生命价值泯灭的呈现;司马相如的《独处室歌》是对自我生命压抑的反抗;张衡的《雄逝雌翔歌》则为个人身世漂零的感伤;蔡邕的《释悔歌》是士人遗世独立、孤芳自赏情怀的抒发。总之,汉代楚歌所展示和所歌唱的均为生命之歌。
汉代楚歌以其独特的文学精神与文学形式,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以后,随着时间的延续,历经后代文人的不断改造,楚歌渐失其清新活泼,句式结构不断规范化和程式化,且向四言、五言这类整齐划一的主体诗歌样式衍化。以后,虽有历代文人的拟作,但与前代相比,风采已全无。楚歌在人们的视野中渐渐淡去。
[1][2][4]蔡彦峰.论楚歌的体制特点及对汉乐府的影响[J].湖南工程学院学报,2006,(01).
[3]魏昌.楚国史[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2:235.
[5][6]周建江.论汉代楚歌的文学史地位[J].湛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