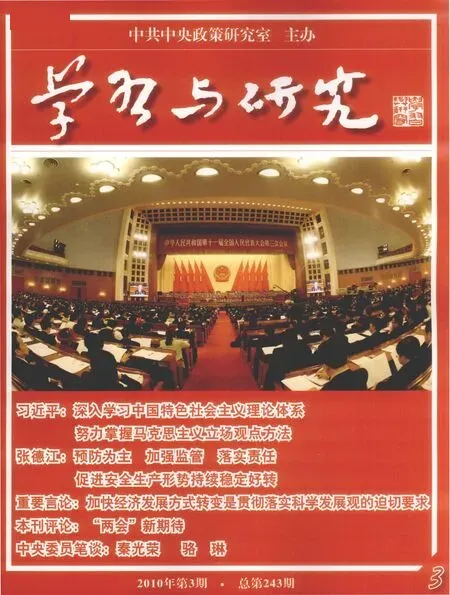农民工在城市融合过程中的社会认同“内卷化”分析
戴欢欢
农民工在城市融合过程中的社会认同“内卷化”分析
戴欢欢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湖北武汉430079)
农民工在城市融合的过程中,一方面,对城市的向往和渴求使他们不愿意再回到传统落后的乡村,另一方面,对乡村传统习俗的定势以及城市居民身份的不确定化使得他们无法获得对城市的归属感。他们的社会认同度正在下降,并且随着农民工内部的更新换代,第二代农民工更有内卷化加强的趋势,正因为如此,各级政府和社会要更多关注和重视这一特殊的群体,帮助他们健康良性的发展。
农民工;城市融合;社会认同;内卷化
一、国内外关于内卷化的阐释
近年来,内卷化一词被普遍用来解释中国历史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些现象,特别是在理解中国乡村社会发展的状态上,具有相当广泛的影响。国内外的许多学者很早就提出过“内卷”问题,最早的应该源于德国的古典哲学家康德,他在《判断力批判》一书中提出了与人类进化理论相对照的“内卷理论”,也称“锁入理论”,之后学者根据他的理论从不同角度阐释了“内卷问题”,被学术界普遍认可的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农业内卷。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是最早意识到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内卷”问题的,提出了“水稻生产的内卷化”,他在《农业的内卷化:印度尼西亚生态变迁的过程》一书中系统的运用了“内卷化”这个概念,通过爪哇地区水稻生产过程的研究,发现爪哇人很难通过现代化来达到经济的持久变革,而是内卷于原来的农业生产方式,这使得社会文化进步非常缓慢。[1]之后,黄宗智在他的著作《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以及《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提出了“农户生产的内卷化”,认为传统的小农经济既不是追求利益最大化,也不是追求剥削最小化,而是从生存的最基本需要出发,由于小农的生产只是为了满足消费而不是利润,因此这一时期就出现了“过密型商品化”的经济现状,即没有发展的增长。[2]
(二)国家内卷。美国学者杜赞奇在其《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9年的华北》一书中运用“国家政权的内卷化”概念。从财政权力扩张的角度指出,政权内卷是在财政方面最具有表现力,即国家财政每增加一份,都伴随着正式机构收入的增加,而国家对这些机构缺乏控制力。他特别指出,地方精英参与的乡村政权内卷化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国家税捐的增加引起盈利型经纪的增生;他们的增生反过来要求更多的税捐。[3]萧凤霞则是从国家与地方社会相互融合的角度,认为国家的内卷化不仅是国家的参与,而且是地方社会的共同参与,国家一旦陷入内卷化,经济的规则便会在一定程度上失灵。此外,费孝通曾经提出过基层政治无为而治的观点,与舒尔曼的“自组织”观点相对照起来,整个社会便呈现出国家的有为政治与基层的无为政治。在国家政治向乡村基层社会渗透的过程中,基层政权内卷化引起国家控制力的缺乏。
(三)制度内卷。国内学者韦森从制度变迁理论视角思考社会体制的“内卷”问题,使得“内卷化”的解释范围又进一步扩展。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博士后研究员张小军通过三个案例,提出“文化内卷”的概念,认为文化内卷化主要是指文化参与的社会复制(不是简单的复制)与精致地确定各种秩序。这一文化的参与不是固定的,文化内卷化也是文化的实践者选择何种文化,又何种文化可以作为行动的资源和手段,与习性和场域的共同作用有关。正是因为有习性,有场域的作用,任何新的制度或观念的实现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使得很多新制度新体系都难以形成。根据文化内卷的阐释,可以看出这里所指的文化并不是单纯的文化形式,而是与制度紧密相连的文化参与。[4]之后,李培林与张翼在《国有企业社会成本分析》中再次发展了“内卷化”的应用范围,认为国有企业功能的内卷化与人员过密化之间的矛盾,使得企业最终陷入负担过重,冗员过多,无发展的增长的困境。[5]
尽管各个学者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但该概念的基本所指还是能大致确定的,就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无法转化为更高形态的现象。我国传统的乡村社会正是在资源匮乏,技术低下,国家政权体制腐朽化,乡民习性传统化等现实中,形成了没有发展的增长,造成了社会发展的滞后。
二、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内卷化”分析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入到城市地区,城市建设过程中对劳动力的需求增长,涌现出大量的“离土又离乡,进城又进厂”的“农民工”群体,也正是从这时开始,“农民工”这一不同于农民和工人的第三重身份群体悄然壮大起来。据资料显示,1985-1990年,从农村迁出的总人数还只有约335万,1995年达到6600多万人,外出就业人口在十年翻了十几番,根据2004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在全国31个省(区、市)对6.8万农户和7100个行政村的调查,当年外出就业农民工约1.2亿人,占农村劳动力的24%左右。加上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 2004年全国农民工总数大约为2亿人,他们平均年龄28岁左右,绝大多数为初中教育水平,主要从事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工作。[6]农民工伴随着社会的转型而生产,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必然产物,他们作为社会的特殊群体,曾形象的被定义是“无法定位的边缘人”,有着社会身份和职业的双重结合,他们主要是指身份上属于农民而职业上属于工人的那部分劳动者,正是这样一个看似矛盾的概念定位,恰恰真实地反映了农民工的特征和尴尬处境。[7]而如今,农民工也经历着他们内部的交替换代,第二代的农民工正新生发展起来。所谓第二代农民工,是相对于80,90年从农村外出进入非农产业就业的第一代农民工而言的,他们主要是出生于80年代后,在90年代后期到城市务工的农民工群体。由于成长环境和接受教育的不同,这两代农民工有着不同的社会认同,从而导致他们不同的个人行为选择。[8]

表1 第一代与第二代农民工特征比较
第一代农民工被认为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工,他们具备传统农民的特征。他们对土地有着深深的眷恋,逼于生活的无奈才会选择背井离乡在异地漂泊,一旦他们有了生活上的保障,他们最终还是会选择回到自己的土地上来。与第一代农民工的恋土情节不同的是,第二代农民工对土地甚至是家乡的感情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慢慢的淡漠,他们希望能够融入城市的大环境中,但是很多方面又无法得到社会的认可,虽然他们在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心里层面都受到不同程度的不公平待遇,但是他们却不愿意再回到农村生活,宁愿继续在城市中寻找那片属于他们的土地。和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的发展可以说是停滞不前,无法转化为更高的形态,他们对社会的认同度下降,趋于“内卷化”的倾向。
(一)对农民身份认同的内卷
在我国,农民工被广泛的确定为身份和职业的双重结合,对于农民身份的认同反映了他们心里层面的感受,而对于非农职业这一定位则表现出他们应当在法律层面上理应享有权利和地位。泰勒认为,认同不仅应该有自我的观点而且还要包括别人的看法,因此,农民工在他们的身份认同过程中,不仅要经历自我的确认与肯定,而且还要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
首先,社会大众的态度。农民工希望在城市中能够得到肯定,被社会认可,在他们眼里,周围人对他们的态度将决定他们的生存状态,然而,学术界至今还未能给农民工一个明确的界定。他们只能对这一特殊群体达成基本的共识:首先,他们来自于农村,属于农业户口;其次,他们的社会身份虽然是农民,但他们的主要时间是在从事非农生产活动;再次,他们的非农活动不限于工业领域,还包括商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活动。这样看来,他们的职业已属于非农性质,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另外,他们被看作是城市化的边缘人,尚且无法享受到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待遇。比如在大多数城市对外来人员进入都设有如下的门槛:
城镇居民(非农业户口,享受本市市民待遇)
回迁居民(非农业户口,部分享受本市市民待遇)
被征地人员(农转非/非农户口,部分享受市民待遇)
农民(农业户口,不享受市民待遇)
这样一来,农民工在城市社区就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尽管国家对农民工问题越来越重视,许多政策都提出要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改革户籍政策也频频被提上日程,但是和第一代农民工境遇一样,第二代农民工仍在这样的环境中挣扎着。
其次,农民工自身的态度。依照张小军对文化内卷的解释,正因为有文化和场域的作用,尽管农民工的生活工作环境有了变化,但是他们仍然保留有旧有的生活习性,适应城市的制度环境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尽管研究者的调查时点和测试方式不尽一致,但这些实证调查数据显示:明确认同农民身份的农民工虽然占多数,但比例在下降;只有少部分农民工摒弃了农民身份;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对农民身份呈模糊认同的状态。可以预见,随着流动的加速,农民工主体模糊认同趋向将会加剧。[9]而在这点上,第二代农民工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们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是城市中的一员,应该得到城里人同等的社会地位,对农民的身份认同趋于内卷,特别是农民身份的制度性意义在减弱。在刘传江等的调查中显示,认为“农民工还是农民”的,第一代农民工占26.97%,第二代农民工占18.94%,认为“农民工不宜务农谋生,应该得到城里同等的社会待遇”的,第一代农民工占40.13%,第二代农民工占56.82%,很显然,第二代农民工比第一代农民工更多了自主和自觉意识。并指出,第二代农民工是最有市民化诉求也是相对容易市民化的群体。[10]

表2 关于农民工身份认同的调查结果比较
(二)对乡村社会认同的内卷
农民工外出务工实际上也就是为了追求比以往种地更高的经济效益,这也是他们最初的目的和预期,如果外出务工的收益要高于在家种地,那么毫无疑问他们会理性的选择外出务农,如果外出务工的收益低于或者和种地差不多时,那么他们是不是愿意回到乡村务农呢?从王春光对温州、杭州、深圳的调查中反映,第一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的态度是有些差异的,在第二代农民工中,有72.3%的人认为,即使在家乡务农收入与外出务工经商的收入差不多,他们也选择外出务工经商,只有27.7%的人选择“在家乡务农”。其他相关的研究表明,年龄越轻,越是倾向于长期在外发展。“相关分析发现,年轻的外出者希望长期在外发展的意愿更浓厚。在同一年龄组中,表示‘继续在外面干’的,16-25岁者占14.5%,26-35岁者占20.4%,36-45岁者尚占19%,46岁以上者便下降到12%”[11]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对于第二代农民工来说,他们对未来的期望是更愿意长期在外发展。这点可以用经济学家达·凡佐(Da Vanzo)的迁移收益理论来解释,他在探讨农民向城市迁移所带来的收益时指出,迁移的收益不仅包括收入的提高,一生额外福利的增长,而且包括非工资的收入(更高的福利及农业补贴)及更好的环境(令人更加愉快的气候;更好的文化设施;更加便利的健康诊所;更好的学习或培训机会;与朋友、亲戚更紧密的接近等)[12]第二代农民工认为在城市中能够获得更大的内心满足感,这使得他们对外部有着强烈的向往和留恋,他们本能的认为务农没有出息,有的人说,‘在家没事干出来’、‘村里年轻人大都出来了,我不出来,别人会说我没有出息’”[13]这种价值观深深影响着二代人,以至于有些农民工即使在城市里找不到工作,也不敢回家。当然第一代中也有一些人不情愿回到农村,但是他们大多是有家小的人,家庭负担比较重,一旦找不到工作,或者一旦家里有困难需要他们回家的时候,他们自然会回到农村,他们将这称为“回乡务农是没有办法的事”[14]
相比之下,第二代农民工外出务工不单单是为了生存、养家,更重要的是为了过好日子,追求生活的质量,他们喜欢城市的繁华与喧闹,不愿意再回到农村生活,就连平时都回去得比较少,大量的调查也都显示出,外出的农民工离家近的逢年过节回去一下,离家远的一年就只有春节回去几天,而这其中第二代农民工回乡的次数更是少之又少,他们回家乡更多的并不是出于内心强烈的思念和期盼,而是为了完成做子女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城市的繁华和更多的机遇深深吸引着这一群体,也使他们逐渐失去了对乡村社会的认同,他们对家乡的感情随时间在慢慢的淡漠,趋于内卷化,而这又将会直接影响到他们对自己未来的预期。
(三)对城市社区认同的内卷
当农民工满怀憧憬和希望来到繁华的都市重新开始他们的人生经历时,他们却意外地发现自己很难融入新的环境中,被当作是城市的边缘人,他们徘徊、迷茫,这样一种特殊的身份让他们在社会交往、组织参与等过程中频频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近些年来,“打工妹”、“民工”这样一些带有排斥性的身份定义将他们无形排除在城市居民范围之外,并且甚至有专家宣称,“是外来人口尤其是素质低的农民工延缓了深圳的现代化进程”。[15]然而有关调查显示,来自城市社会的排斥,对农民工子女的影响比他们自己更大,使他们对城市社会有许多不适、不满和不认可。这些孩子面临着与城市孩子无法整合的困境,他们不能形成相互的认可,正如北京一位打工子弟学校校长所说的:“外来打工子弟与城市孩子不好整合,他们的经济条件、生活习惯、学习基础、语言以及地域情结等都不一样,正如水与油一样,不相容。外来子弟在公办学校,就有被歧视的感觉,心理比较脆弱,或者自卑,或者逆反,心理障碍导致他们不适应公办学校”。[16]
农民工在城市社会中历经的种种不愉快的经历,然而却很少看到他们为了争夺基本权益而合理的申诉,仅有少数为了征讨拖欠以及重要事故而产生的纠纷,对于来自社会的大部分不公正,他们选择的往往是沉默,采取的基本上是不表达、不申诉的态度。有人称他们是“沉默的群体”,仿佛是与世无争,但内心又充满了种种无奈和伤感。然而在李培林、李炜对全国28个省市区进行的大规模问卷的分析中意外发现农民工因其经济地位遭遇的不公,表现出更加突出的社会不满情绪,反而呈现出积极的社会态度。对此,他们解释说这首先是和农民工对自身境遇的归因有关,要改变这种境遇,就只有依靠自己的勤勉努力和知识技能的提高。其次是和农民工的生活期望与权利意识有关,受教育水平较低,生活需求层次较低,期望也低使得他们对社会的评价更积极,社会参与度低使他们对社会群体利益冲突的严重性不敏感。第三是和农民工的比较参照体系有关,他们更容易与家乡的农民相比较,与自己的过去生活相比较,由此对未来的发展也抱有更加乐观的态度。[17]
城市社会的排斥使他们无法对城市产生归属感,得不到家的感觉,他们的业余生活单调乏味,除了吃饭、干活、睡觉之外,几乎没有可以支配的闲暇时间。在工棚内三五成群地聊天、打牌也是他们打发漫漫长夜的普遍方式。第二代农民工由于普遍希望得到公平对待,自我意识强,合作精神较弱的个性特点,在受到歧视的情况下,更少会与城市居民交往沟通,仅限于自我封闭的狭隘群体。有相当多的第二代农民工意识到与城市居民的关系比较疏远,接触不多,并且总觉得自己与当地人不属于同类人。尽管这样,他们心中对社会仍抱有积极的态度,正因为如此,我们就更应该促进和保护他们的积极社会态度,努力把这种积极性转化为他们对城市发展的动力和信心,把农民工作为城市的一员来看待,取消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生活的体制性门槛,加强他们对城市社区的认同。
三、结语
显然农民工在城市融合中的社会认同度正在下降,并且随着农民工内部的更新换代,第二代农民工更有内卷化加强的趋势。一方面,对城市的向往和渴求使他们不愿意再回到传统落后的乡村,甚至于在第二代当中有相当部分农民工对自己仍是农民的身份表示模糊不清。另一方面,对乡村传统习俗的定势以及城市居民身份的不确定化使得他们往往受到社会的排斥,游离于城市社会的边缘,无法获得对城市的归属感。尽管他们生活在城市的大环境中,然而无法融入城市社会让他们的社会交往只能局限于自我封闭的小群体里,这样一个群体就在无形之中自我发展并不断壮大起来,面对如今2.3亿农民工的庞大群体,他们对社会的认同度将会直接影响到这一群体的行为逻辑和态度取向,因此,西方有不少学者对中国大规模的民工流动可能造成的社会后果表示担忧,中国也有学者把农民工视为对社会稳定的一种威胁。但是庆幸的是我们发现了农民工在大量的社会不公正待遇下仍然对社会持有乐观积极的态度,这点无疑让许多人感到欣慰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就应更多的去关心和帮助他们,借助政府的力量和社会的制度,使他们得到合理的地位和应有的保障。
[1]格尔茨.农业的内卷化:印度尼西亚生态变迁的过程[M].1963:82
[2][英]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M].北京:中华书局,2000:77.
[3][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185.
[4]张小军.理解中国乡村内卷化的机制[J].二十一世纪.1998年2月总第45期.
[5]李培林,张翼.国有企业社会成本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23.
[6]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编,《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3-4.
[7]崔丽霞.“推拉理论”视阈下我国农民工社会流动的动因探析[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53.
[8][10]刘传江,徐建玲.第二代农民工及其市民化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7,(1):8.
[9]翟秀海.制度视角下农民工身份认同困境问题研究[J].农业经济2009,(4):62.
[11]赵树凯.纵横城乡[M].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29.
[12]杜鹰、白南生主编.走出乡村[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43.
[13]赵树凯.纵横城乡[M].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24.
[14]杜鹰、白南生主编.走出乡村[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337.
[15]艾君.对外来人口,政府不仅需要观念的改变[N].新京报,2004-11-27.
[16]王春光.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6,(5):118.
[17]李培林,李炜.农民工在中国转型中的经济地位和社会态度[J].社会学研究,2007,(3):6.
(责任编辑 刘华安)
C913.2
A
1008-4479(2010)03-0055-05
2010-01-09
戴欢欢,女,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制度经济与政府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