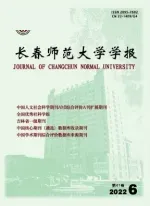论美国后现代派小说中的道德缺席现象
陈彦旭
(东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吉林长春 130024)
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琳达·哈茨恩在她2002年出版的著作《后现代主义的政治学》(Politics of Postmodernism)一书中“扣上了后现代主义的棺材盖,宣称‘一切都结束了’”[1]。那么,如果后现代主义真的已经终结,继它之后又出现了什么样的艺术与文学思潮呢?学术界普遍认为,答案就是出现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新现实主义。而新现实主义为何可以取代后现代主义,成为时代的新宠呢?笔者认为,这两者之间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新现实主义小说家与后现代派小说家对“道德”的态度上:前者致力于重建道德意识,并藉此来解决当代人文精神危机;而后者对“道德”抱有一种明显的漠视甚至否定的情绪。本文就美国后现代派小说中的道德缺失现象进行描叙、探讨并归因。
一、“上帝死了”与“人死了”
众所周知,西方的基督教思想对人们道德观念有着深远的影响,它所宣扬的博爱、宽容、牺牲、公平等思想在神的光环的笼罩下有着不可撼动的震慑力量。“可以说,没有宗教信仰就没有道德信仰,没有宗教,道德就失去了根基”[2]。我国著名宗教学家吕大吉进一步指出,“一方面,宗教将道德抬高为宗教的教义、信条、诫命和律法,把恪守宗教关于道德的诫命作为取得神宠和进入来世天国的标准;另一方面,宗教的教义和信条又被神以道德诫命的形式强加于整个社会体系,被说成是一切人的行为之当与不当、德与不德、善与不善的普遍准则。”[3]据此,西方世界禁不住发出这样感慨的声音,“如果没有宗教信仰,人怎么可能成为真正‘有道德的人’呢?如果不相信上帝是道德的前提,我们怎么可能发展美德,怎么可能有责任感呢?……如果没有上帝,人类是否全变得贪得无厌而不能善待同伴?如果没有上帝,我们是否能够保证人世间的博爱、公正和兄弟情谊?如果没有上帝,人类是否会放弃道德生活,倒退到茹毛饮血的诸多形态之中?”[4]
然而,哲人尼采在《快乐的智慧》这本书中,借一疯癫之人所发出的那一声长长的哀叹奏响了为上帝而谱写的挽歌,“上帝死了”这一残酷的现实标志着以基督教信仰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分崩离析,其所承载的道德信念也随之而轰然倒塌。失去信仰的人生命被物化,精神空洞,灵魂无家可归,流离在这个充满喧哗、恐惧、孤单、嘈杂、无意义的世界里,以至于继尼采之后,思想家福柯再一次语出惊人,宣布“人死了”,实指在后现代人文精神的消亡。
面对着如此的生存窘境,生活在这个时代的美国作家们显得无所适从。目睹了二战后血迹斑斑的战场、国内疯狂的麦卡锡主义的横行、热核战争的恐怖及东西方冷战、不断挑起矛盾与分裂的越南战争、英雄偶像人物如肯尼迪、马丁·路德·金的暗杀事件、罪恶不公的种族歧视,以及每况愈下的生态环境,他们作为文人所特有的敏感脆弱的心灵不再有勇气去直面这个混乱无序、不可理喻的世界,而普遍采取了一种隐退消极的态度:他们不再关注外部的世界,而转为对自我内心世界的审视,认为人的内心深处的直觉与潜意识更为可靠,并开始肆无忌惮地用文字宣泄自己的失望、迷茫、混乱、痛苦等负面情绪。因此,暴力、色情、吸毒、信仰危机、道德沦丧和人性崩溃等主题与情节在后现代派小说中屡见不鲜。
我国学者许汝祉教授曾将美国自由派理论家丹尼尔关于后现代派小说创作主题的论述总结为以下几点:宣扬暴力与残忍,作品中充满着嗜血的细节;宣传性反常,如对同性恋、异性模仿癖、口交行为与鸡奸的描述;宣扬荒谬的虚无主义情绪,情节古怪;宣扬污移,像吸毒、描写人体排泄细节等。[5]
二、“破碎的镜”与“昏暗的灯”
后现代派作家的这种极端的写作倾向显然是不妥当的,因为他们忽略并否定了文学作品反映现实与道德教化的基本功能。西方文论家艾布拉姆斯曾形象地将这两种功用比作“镜与灯”,如果非要把这个比喻生搬硬套地放在后现代派小说头上,我们看到的至多只能是“破碎的镜”和“昏暗的灯”。
所谓“破碎的镜”,是指后现代派小说并不能够真实地反映现实,多数情况下是对现实丑恶现象的夸大、虚构与极端的描写。“在小说创作领域,后现代主义作品以‘真实地虚构和冷漠地抒情’为最明显的特征,明目张胆又故做麻木不仁地向读者宣告作者是在那里‘胡编乱造。’”[6]著名后现代理论批评家欧文·豪也指出,“后现代作家的创作完全摒弃了英雄与英雄人物的冲突,他只能虚构他所生活的世界上的那些‘极度畸形’和他那‘极度飘忽不定’的经历之‘病态’”[7]。综上所述,后现代派小说所描写的多是夸张的、病态的与畸形的个别人物,这明显违背了现实主义小说中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一中心创作原则。因此,后现代派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反现实主义的,这也说明它与新现实主义之间也必然存在着天生不可调和的矛盾。
而“昏暗的灯”则是说后现代派小说无法照亮人们的心灵,洗涤人们的灵魂,弘扬伟大的精神,从而实现文学作品所肩负的道德承担。而后现代派小说中对于种种肮脏、丑恶、龌鹾事物的刻意的、赤裸裸的思想以及场景描写无法带给读者任何道德上的愉悦与启迪。主人公对其自己反道德、反伦理的行为非但丝毫不加掩饰,反而沾沾自喜,引以为荣。
举例来说,在约翰·霍克斯的著名后现代小说《血橙》中,主人公毫无廉耻地向他人炫耀自己糜烂的性史:“众神创造男人,就是让我们去分开女人的双腿……我曾经跟无数的女人发生过关系,包括我的妻子、我妻子的朋友、我朋友的妻子,还有其他形形色色的女孩和女人,从豆蔻少女到半老徐娘,再从半老徐娘到豆蔻少女。只要时机适当,只要爱神的歌声响起,我就会毫不犹豫地成就一番风流韵事”[8]。这番无耻的自白实在使得每一个有良知、有道德的人们震惊不已。
再举一例,美籍俄裔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是后现代作品中的经典之作,其主人公亨伯特是个心理与性取向都有些变态的成年男子,对“每一个从身边经过的快要进入青春期的小姐姑娘欲火中烧”,却对自己的结发妻子冷讽热嘲,极尽挖苦丑化之能事:“那个新婚之夜,我享受到了无限的快乐……可是,残酷的现实很快就暴露了,染过的卷发显出了黑色的发根;茸毛变成了剃过的下巴上的硬刺;那个灵活湿润的嘴唇,无论如何使劲地用爱去喂它,仍是不光彩地露出它与那幅宝贝肖像里故去的、癞蛤蟆一般的母亲嘴唇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亨伯特手里是一块骨骼粗大、脸庞浮肿、两腿短小、乳房硕大、呆头呆脑的奶油蛋糕。”[9]这本书由于充斥着反伦理的思想与露骨的性爱描写,触犯了社会所能忍受的道德底线,早期在寻找出版时屡屡碰壁,在法国遭到短期的封杀,在澳大利亚也被视作禁书。据说有的出版商建议纳博科夫将两个主人公角色换位,即把洛丽塔换成一个年青男子,把亨伯特变为一个土里土气的农妇,并安排后者去勾引前者,这样“能给读者与出版商增加一点道德上的安全感”。
类似的令人尴尬甚至反胃的描写也出现在巴塞尔姆的《白雪公主》中,在他的笔下,代表着圣洁、纯真的白雪公主变成了一个高个子、皮肤黝黑的女人,“身上长着很多美人痣:一颗在乳房上,一颗在肚子上,一颗在膝盖上,一颗在脚踝上,一颗在臀部上,一颗在脖子后面……”[10],而且她着迷于淫秽诗的写作,并在浴室中与七个侏儒淫乱,简直就像一头不知羞耻、性欲旺盛的母兽。就这样,扎根在每个读者童年记忆中的纯洁无瑕的、象征着真善美的少女形象被彻底地颠覆与摧毁,两个截然不同的形象之间的巨大反差也对读者的道德观与伦理观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三、反英雄
后现代派作家们将这种对文学经典作品所进行的扭曲的模仿、嘲笑以及戏谑称为戏仿,这是他们在写作中经常使用的手法,表达了他们对传统历史价值观与文学精神的蔑视与否认。这也恰好印证了杨仁敬教授在《美国后现代派短篇小说选》一书的前言中所提及的观点,“从本书所选的25篇小说来看……它们大多数描写的都是‘反英雄’”。
那么,何为“反英雄”呢?《郎曼20世纪文学指南》(1981)中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反英雄’成为金斯莱·艾米斯、约翰·奥斯本、约翰·布雷恩、哈罗德·品特等作家所写的小说和戏剧中的人物。反英雄否定行为的准则或先前被视为文明社会基础的社交行为。有些人故意反抗那些行为规范,把现代社会看作是非人的社会;有些人则根本无视那些行为准则”。王岚教授进一步指出,“他们可能卑微琐碎,对社会政治和道德往往采取冷漠、愤怒和不在乎的态度,甚至会粗暴残忍……反英雄走向了英雄的反面,它的出现是对传统理想中英雄人物的解构,或者说是这些理想概念的破碎和丧失”[11]。
我们知道,“英雄”是正义、理想、道德等一系列美好事物的化身,他们的所做所为也因此往往被当作典范与规矩为人们所效仿。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英雄,他们身上所独有的品质也同时体现了他们所处时代对道德的最高要求与向往。而在主张推翻“中心”、“典范”与“规矩”的后现代,不可能存在一个普遍认可的价值观,英雄的形象也因此被消解,社会的道德典范难以确立。在一片追逐所谓“道德个人化”和“道德自由化”的嘈杂声中,英雄人物被赶下圣坛,黯然退场,最终踪迹难觅,而反传统英雄品格的“反英雄”则在后现代的文学作品中左右逢源,逐渐站稳了脚跟,像《五号屠场》中的毕利·皮尔格里姆与《第二十二条军规》中的尤索林都是反英雄的典型人物。
另外,透过以上作品中文字所勾勒出的混乱、荒唐的画面,我们感受到的是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弗洛伊德所提出的“本我”中所包含的、受到压制而时时刻刻燥动不安的“利比多”。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人格结构共分为三个层次:本我、自我与超我。本我基本上由性本能组成,没有价值观念,没有伦理道德的观念,按照“快乐原则”活动;而超我“代表社会道德准则,压抑本能冲动,按‘至善原则’活动”[12];而自我负责协调本我与超我之间激烈的矛盾与冲突,遵循现实原则。
结合上文关于“反英雄”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由于同样“代表社会道德规范”的英雄的缺席,直接导致“代表社会道德准则”的“超我”的不在场,从而造成了“本我”的力量无约束而迅速膨胀,这种趋势发展到顶峰时人便被物化,亦可说兽性压倒了人性,道德的观念消失殆尽,人性也变得暗淡无光。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后现代派的作家在面对现实社会的种种困境时,采取的对策并不是积极地应对,去反映、去揭露现实的种种问题从而指出解决问题的途径,相反,他们回避现实,转向自己的内心世界,用凌乱破碎的意象与文字来倾诉自己个人的困惑、压抑与不满。这样的作品完全失去了文学“疗伤”的功能,只会强化读者的迷惑与伤痛心理。而美国大众在经历过二战、越战、国内麦卡锡主义、经济萧条等种种磨难后,期冀看到反映真实问题、解决现实问题的小说。在这样的情形下,新现实主义小说的兴起与后现代主义小说的衰落似乎也成了一种历史性的必然。
[1]Neil Brooks,Josh Toth,The Mourning After,Attending the Wake of Postmodernism,Amsterdam,New York,2007:15.
[2]魏长领.道德信仰与自我超越[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113.
[3]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768.
[4]于文杰.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文主义[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248.
[5]许汝祉.对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评估[J].外国文学评论,1991(3).
[6]陈刚.后现代的生存[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96.
[7]王潮.后现代主义的突破[M].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6:146.
[8]约翰·霍克斯.血橙[M].姜薇,孙全志,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2.
[9]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洛丽塔[M].卢炳瑞,译.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2001:11.
[10]唐纳德·巴塞尔姆.白雪公主后传[M].虞建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21.
[11]赵一凡,张中载.西方文论关键词[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108.
[12]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