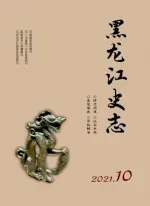论清后期黑龙江地方政权由军府制向行省制的过渡
李 慧
(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有清一代,黑龙江地区因其特殊的政治、军事以及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地方政权的设置形式不同于内地的行省制,而是一直实行以将军为主体的军府制。直至清末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黑龙江行政体制改革,裁撤将军,设置行省,黑龙江地方政权形式才发生了重大变革。但这种变革并非一朝一夕所完成,而是经历了由军府制向行省制过渡的漫长时期,并且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
一、军府制下的黑龙江地方政权
清军入关后,黑龙江所在的东北地区由盛京总管镇守,大量的八旗官兵开始在此驻防,并逐步形成盛京、宁古塔、黑龙江三将军驻防体系。一种以将军为主导,对旗、民分治的军府制政权形式逐渐在黑龙江地区形成。
清初在黑龙江地区实行军府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宁古塔将军的设置。顺治九年(1652年),清政府为抵御沙俄的侵扰,“命镶蓝旗梅勒章京沙尔虎达等统率八旗军驻防宁古塔地方”。[1]“顺治十年,置昂邦章京及副都统二人镇守宁古塔”。[2]康熙元年(1662年),改称宁古塔将军,所辖范围已大致包括今黑龙江流域的广大地区,“西起贝加尔湖以东的鄂嫩河源,东包库页岛,北抵外兴安岭山麓(包括乌第河流域),东南达日本海”。[3]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宁古塔将军“正式改称吉林将军。”[4]
黑龙江将军的设置,同样是为了防御沙俄。“康熙二十二年征罗刹,始设镇守黑龙江等处将军及副都统驻江东岸之爱浑城”[5],萨布素任黑龙江将军。此时,“原宁古塔将军管辖的亨滚河上源支流哈达乌喇河、黑龙江北岸的毕占河以及东流松花江等河流以西的地方划归黑龙江将军管辖。这样,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中上游的广大地区由黑龙江将军管辖,黑龙江下游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包括库页岛在内由宁古塔将军管辖。”[6]而黑龙江真正作为一个独立政区建立地方行政机构也正是由此开始的。
清朝“于各省分设八旗驻防官兵,以将军、副都统为之董辖,虽所司繁简略异,而职任无殊。”其中特别指出,“惟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俱以肇邦重地,俾之作镇,统治军民,绥徕边境,其政务较繁而委任亦最为隆钜。”[9]
黑龙江将军自设立起,即担负着“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均齐政刑,修举武备,遂徕部族,控制东陲”[7]的重要职责。作为黑龙江地方最高行政长官,承担辖区内各项军事以及行政管理事务,掌管所有旗务、民刑、赋税、兵备、防务、官学、学堂等事宜。为了更好地防御和抗击沙俄,巩固屯垦戍边政策的实施,进而加强内部管理,在将军之下,“黑龙江地区先后设立了黑龙江(瑷珲)副都统、墨尔根副都统、齐齐哈尔副都统、呼伦贝尔副都统衔总管、呼兰城守尉、宁古塔副都统(归吉林将军管辖)、三姓副都统(归吉林将军管辖)、阿勒楚喀副都统(归吉林将军管辖)等行政管理机构,将所属区域的各族人民编入八旗,进行管理。”[8]这些行政机构均为辅助将军治理政务设置,而将军的职权与中央六部并立,且直接听令于皇帝。这种以将军为主导的地方政权对于稳定边疆、抵御外患发挥了重要功效。
二、黑龙江地方政权由军府制向行省制过渡的原因
清代黑龙江地区的军府制实行了200余年,在此漫长的历史时期中,社会政治、经济以及军事情况都在不断变化,因此最终导致行省制取代了军府制。而黑龙江行省制之下的府、厅、州、县,并不是在清末改革之后才出现的,早在同治年间,清廷即对在黑龙江地区汉人较为集中的区域“实行州县制度”[10],相继设置很多府、厅、州、县,开始了由军府制向行省制的过渡。而引发这种过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其一,移民实边,汉民涌入。清政府在东北地区所实行的移民实边政策经历了招垦、封禁、开禁等不同阶段,其重要影响即是引起了人口数量的极大变化。虽然吉林、黑龙江一度成为封禁的重点区域,但仍有大量汉族人口从内地迁来。尤其到咸丰十一年(1861年),黑龙江部分地区实行开禁放垦政策,更有大批汉人涌入,致使黑龙江地区人口由清初至中叶的45万人发展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时,已达到2 577 380人。[11]随着汉人数量日增,民事渐繁,急需建立民事机构。而当时军府制下的八旗将官多是旗营出身,除了较为重视武功之外,在遇到旗民纠纷时又不免有偏袒旗人的现象。因此,黑龙江将军多次上奏请设民官,以加强对当地民人的全面治理。同治元年(1862年),清政府在呼兰地区设置呼兰厅同知就是最好的例证。咸丰十年(1860年),黑龙江将军特普钦奏请在呼兰地区开垦事宜获批后,不仅土地得到有效开发,呼兰地区人口也在大幅增长,佃民日众,烟户渐繁。由此造成民事增多,“案牍繁增,倍于往昔”的复杂局面,而“听讼诘奸,均非武职所长”[12],遂增设一名理事同知,专门负责赋课及旗民交涉等事件,以此来加强对该地民政事务的管理。
此外,在黑龙江东部地区所设置的绥芬厅、依兰府,同样是因为人口原因而增设的。“随着边防的巩固,土地的开发和人口的增加,三岔口这一垦荒的中心地带,逐渐地形成市井,而发展成此地的政治、经济中心。光绪二十八年即由招垦局改为绥芬厅。”[13]吉林将军达桂也曾在奏请中指出:“三姓地方为吉江门户,又为松花、牡丹两江汇流东下之区,多沃壤,户口殷繁,拟于该城设知县一员,名曰依兰府。”[14]这些都是行省制建立前,因受到移民实边政策及民人增加的影响而在黑龙江地区设置的民事机构。
其二,边疆危机不断升级。19世纪以后,清王朝深陷于内忧外患的危机之中。沙俄将黑龙江并入自己版图的野心继续蔓延,多次派考察队刺探有关黑龙江航运及当地的地理情况。而“吉林和黑龙江的将军很少注意到满洲边地的发展事务”,[15]加之为镇压国内太平天国运动,大批的黑龙江八旗被调离,边患危机不断升级。《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使我国东北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侵蚀,沙俄不仅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建村、移民,还蓄意向中国内地种地、盖房,“仅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四年,沙俄移民在黑龙江南岸八、九个地方,就非法种地达几百垧”。[16]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再一次使我国边疆领土遭到蚕食,沙俄继续在这些土地上广建村屯,大力发展基层政权,从而便于将更多军事力量进一步向我国边疆转移。与此相比,清朝在黑龙江边疆的基层政权建设起步晚、发展慢。人口规模小,则无法为边疆军事提供必需的人力、物力、财力;边患空虚,则更助长了侵略者的占领野心。因此,此时黑龙江将军、副都统的军事管辖已无法满足民政建设的需要,而巩固边疆实力、加强边疆地区的民政建设则逐渐被清政府提上日程。因为,不断完善民政机构建设并使黑龙江地方政权形式向行省制过渡,不仅能有效管理当地人口,还可以拉近黑龙江地区与内地行政机构之间的差距。只有边疆人口富庶,机构健全,才能有效的提高防御能力。
三、黑龙江地方政权由军府制向行省制过渡的进程
由于上述内、外两方面原因的影响,黑龙江地方政权发生了重要变化。在军府制下设置的府、厅、州、县加大了对黑龙江地区民事管理的力度。其设置的进程大致如下:
(一)黑龙江将军管辖范围内设置府、厅的情况
同治元年(1862年),清政府在呼兰城内设呼兰厅同知,两年后,呼兰厅同知迁往巴彦苏苏(今巴彦县城)。光绪三十年(1904年)呼兰厅升至为府,治理呼兰城。呼兰厅是黑龙江地区最早设置的厅。
此外,清政府在黑龙江地区于“光绪十一年,设绥化厅……三十年升厅为府。”[17]光绪三十年(1904),在海伦围场之地设置的通肯副都统升为海伦直隶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齐齐哈尔地区设黑水厅抚民同知,这即是改革后所置龙江府的前身。
(二)黑龙江东部地区吉林将军管辖范围内设置四厅一府,即宾州厅、五常厅、双城厅、绥芬厅、依兰府
“光绪六年,建城苇子沟,置宾州厅。二十八年直隶”;[18]光绪七年(1881年),设五常厅;光绪八年(1882年),设双城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改招垦局为绥芬厅。而依兰府为“光绪三十一年改置”[19]
(三)州、县设置情况
清末黑龙江地方政权改革前设置的州,除光绪“三十一年,置临江州”[20]以外,因“黑龙江将军达桂等奏:江省属境辽阔,非添设地方各官,不足以资治理”,于是在“巴彦苏苏地方,另设知州一员,名曰巴彦州,并设吏目一员”。[21]
黑龙江地区设县较晚,雍正四(1727年)年十二月曾设置泰宁县,后因不便管理,于雍正七年(1729年)裁撤。此后,长寿县(今延寿县)为光绪“二十八年改置,隶宾州直隶厅”[22]。隶属于吉林依兰的县为大通县和汤原县,均为光绪三十一年置。而黑龙江地区设置的县自光绪三十年(1904年)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主要有:兰西县、木兰县、青冈县、余庆县以及拜泉县。[23]这些州县的设置,在汉人及地方的管理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日后黑龙江地方政权的全面改革奠定了重要基础。
四、清末行政改革与黑龙江地方政权由军府制向行省制过渡的终结
黑龙江地区军府制下设置的府、厅、州、县,不仅使黑龙江地区的行政机构得到了逐步完善,而且在卓有成效地管理当地人口的同时,也推动了黑龙江地区土地的开发及地方经济的发展,使黑龙江地方政权逐渐走上行省制的轨道。正是因为这种过渡时期治理民事的机构普遍设置,才使得清政府更加意识到,在复杂的政局形势下,在黑龙江地区乃至东三省实行行省制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开始了清末黑龙江地方政权的最终变革。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4月,清政府准奏《东三省督抚办事要纲》及《东三省职司官职章程》,拉开了东三省行政体制改革的序幕。改革中废除了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将军,建立奉天、吉林、黑龙江行省,巡抚成为一省最高长官。黑龙江地区在原有行政建置的基础上设置的道、府、厅、州、县规模逐渐扩大,至清末共有瑷珲兵备道等五道、黑河府等十四府、瑷珲直隶厅等九厅、巴彦及绥远二州、长寿县等十四县,由此完成了黑龙江地方政权由军府制向行省制的彻底改革。
纵观黑龙江地方政权由军府制向行省制过渡的历程,府、厅、州、县的相继设立为最终的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而过渡的终结——清末黑龙江地方政权改革,不仅改变了黑龙江地区以往单一的八旗管理体制,而且形成了有利于地方管理发展的政权体系,初步实现了军事与民政的分离,提高了政府的行政职能,加强了政府对地方的治理,在维护社会稳定、开发和保卫边疆上也起到重要作用。同时,加速了黑龙江地区地方政权的近代化进程。
[1][4][6][8]周喜峰.清朝前期黑龙江民族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107-108.
[2][18][19][22]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五十六.志三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7.
[3]黑龙江省地方志编审委员会.黑龙江政权沿革[M].黑龙江省政府办公厅史志办公室,1924.
[5][17][23]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五十七.志三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7.
[7](清)高宗敕.清朝通典:卷三十六[M].商务印书馆,1935.
[9](清)长顺等.吉林通志:卷六十[M].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10]魏光奇.管治与自治——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县治[M].商务印书馆,2004:20.
[11][14]石方.黑龙江区域社会转型研究(1861-1911)[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35、62.
[12][21]柳成栋.巴彦州志辑略—巴彦州志资料类编[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176、238.
[13]邓清林.黑龙江地名考释[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106.
[15](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364.
[16]佟冬.沙俄与东北[M].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165.
[20]李沭田等.吉林纪略[M].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4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