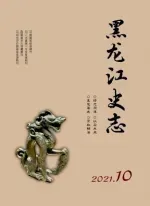原始森林的植树者,乡邦文化的著书人——《饶河百年拾记》代序
柳成栋
2009年8月,借饶河百年县庆之际,我再次应邀来到祖国东北边陲乌苏里江畔的饶河县,与老友姚中晋先生重逢,格外亲切。姚公以80高龄,瘦弱身躯,陪同考察县内重要历史遗址,自然风光,原始森林,赫哲风情,唯恐落下一处,并亲自陪同游览了四十年前因中苏边境冲突而发生一场激烈战斗的珍宝岛,弥补了四十年中几次到饶河、虎林而未能去珍宝岛的遗憾。三十年交往历史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一、潜心修志重肩担
我1980年步入志坛,在1981年4月5日至15日庆安县举办的全省地方志编写研讨会上,认识了颇有几分仙风道骨、素有饶河郭沫若之称的姚中晋先生。参加研讨会的绝大多数人员都是县志的主编或主要负责人,这些人大多数都是县里的“秀才”、“笔杆子”或中学语文教师。当时的我只是一个刚过而立之年被姚公称之为胖娃娃的“小青年”。由于我在大会上就如何搜集整理地方志资料和县志篇目的拟订问题作了两次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共鸣,给姚公留下较深的印象。1985年我调入省地方志办公室工作之后,与姚公接触机会就更多了。
说起姚公,真是有说不完的话题。姚公祖籍山东文登,我是山东莱阳,论起来同属登州府。我与姚公因编县志相识,到县志审定出版相知。说到县志编纂,当有四难。
一曰选拔人才难。饶河地处祖国东北边陲,人烟稀少,开发建设较晚,文化相对落后,适合修志的人才奇缺。只读过两年私塾和四年小学的姚公,便挑起了编修县志的重担。我国历来有编史修志的良好传统,对从事史志编修的人员也极为重视,要求很高。自从唐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几提出才、学、识为史才三长的著名理论以后,历代都奉为圭臬。如明代学者范蒿曾说:“志与史体虽稍殊,而作史者每于志采录焉。则志是亦史也。昔人谓作史有三长,而志亦不可缺一。则志岂易言哉”(见《重修建宁府志序》)。然而,无论何代,具备才、学、识三长的人都是不多的。尽管如此,为了保证志书的质量,历代对修志人员的身份、学识都很讲究。特别是明、清时期,修志常常由进士、举人等地方饱学之士担任。本地无胜任的修志人才还要从外地聘请。而1980年饶河县志办成立时调进和后来陆续调进的人员中,当时无一人具备大专学历,大都是抄写、打字等工作人员。真正能够独挡一面,负起某卷或全书编写责任的,除姚中晋外,别无他人。后来县志办人员最多时,也不过五人。很多年只是二三人或三四人而已。以如此单薄之人力,完成如此艰巨之任务,其中艰难,可想而知。然而姚公义无反顾,认为这正是自己大有作为,成一家之言的好机会。于是他一人力挑千斤重担,一百余万字的《饶河县志》从收集资料到编写几乎出自姚公一人之手。几乎创造了首轮修志的奇迹。
二曰征文考献难。史无志书。饶河境内,自古向为少数民族聚居之地,自夏商至周朝时期的肃慎到近世的赫哲等,大都以渔猎为主,尚武轻文,故而文字资料几不可考。自清中叶以来,屡遭俄患,烟匪横行,致使社会动荡日益加剧。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初始,又遭日寇蹂躏,战乱频仍,生灵涂炭。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原有典籍,也将荡然无存。对于饶河,有关记载,尽散见于零篇断简之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因此,即使左丘明、太史公再世,也会说到,修饶河志何其难也。然而“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姚公除石室阅档,上林翻书,史海钩沉,征文考献以外,则是风餐露宿,深山访古,阡陌踏查。凭着他在担任农工部副部长、乡长、分场副场长、林业科副科长、县联社副主任、县科协主席等职的漫长岁月里,跑遍了饶河的所有村屯,结交下不少乡友的便利条件,搜集了大量的口碑资料。姚公凭着一颗强烈的爱土爱乡之心,对乌苏里江中的岛屿一个一个地踏查,详究其形成过程,变化经过,名称来历。对饶河境内已考知的植物凡167科,1050种,经常可以辨识者达400余种。对其中的许多特殊品种,他都搜集过标本或画过图形,而且写了大量的文字资料。如果没有这些经历,他撰写县志时记述山水,记述物产资源,就不会进行得那样顺利。上上下下的几十年,使他熟悉自1947年以来饶河县委、县政府等机构的主要人员变化,熟悉饶河数十年来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主要演进变化情况,这实际上为他撰写县志的历史沿革、政治、文教、卫生、科学、计量、产业等部分,提供了方便。他在县联社做过经济工作,这也在实际上为他撰写财贸金融部分提供了便利。如果他不是自幼就生活在饶河,也很难写出人文部分中的民俗、宗教、庙宇等。正如姚公自己所说,每当他执笔写作时,饶河的山川、物产、人物便都不断地在眼前浮现。所以《饶河县志》才叙事清楚,人物鲜活,风情浓郁,可读性强。
三曰创新体例难。饶河史无志书,缺少依据,此次修志,不属续修,必须把志书所列项目,从古到今勾勒一番,以使后人明了各方面的沿革梗概。尽管详今略古是现代修志原则之一,但对于“古”无论怎样“略”,也须句句有来历,事事有根据。要想把数十年、数百年乃至数千年间的事情简明扼要地叙述清楚,谈何容易!尽管《饶河县志》在结构体例上、篇目设置当中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姚公在继承传统方志体例的基础上,结合饶河实际情况大胆创新的精神是值得肯定和学习的。全志分为地舆、建置、人文、历史沿革、政治、教育、文化、卫生、科学、产业、财贸金融、生物资源、杂记、人物传、艺文、要事简记16卷。如此,也就为国家、为社会在一定区域内建立了一处地理、政治、经济、人文、历史的宝贵资料库,以准确实际做标格,向世人全方位、立体的介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属下这片6 765平方公里土地的自然地理、人文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四曰考证史实难。县志编纂贵在史实考证。在史实考证方面,姚公是下了很大功夫的。纠正了许多历史事件或人物传的讹传,尤其是抗日斗争伪满洲国时期误传的人和事件尤多。首先是1946年2月22日西风沟土匪叛乱事件,一直误为“2·15”叛乱,经姚公追忆和查阅公安局叛乱头子贾绍堂的审讯供词,证实“2·22”确凿无误。二是对抗联七军军长陈荣久牺牲墓地的考查。原来依据抗联七军军需处长杨洪义提供在大顶子山后新开屯西屏岭山地方,前后两次均无所得。1982年5月12日,经过由13人组成的考查组的深入考查,终于查清了陈荣久牺牲墓地。(见《饶河县志》(五)《陈荣久烈士墓葬寻探记》)遂上报黑龙江省人民政府,陈雷省长亲自题词为之表彰。三是通过查考文献、访问满语专家、实地踏查等方式对饶河境内的山川河流、古代遗址详细进行考证。并撰写了《乌苏里江沿岸满语地名诠释》分别发表在1982年第三期《黑龙江地名通讯》和1983年《黑龙江史志》第六期上,后来收录在《饶河县志》卷二建置篇中。将乌苏里江沿岸上百个包括山名、河名、古民居遗址的满语地名的全部涵义译释出来。并找出了明代“失儿兀赤卫”、“苏穆噜河卫”的准确地址。同时撰有《明代失儿兀赤卫遗址考实》《明代苏穆噜河卫故址见证》等文章,分别发表在1984年第五期《黑龙江史志》和1985年第四期上。
说到史实的考证,不能不提姚公的固执。他自己也承认“个人生来有某种怪癖性,好固持己见”。有时固执得几乎别人的意见听不进去。这也是姚公的可爱之处。正因为有了这种几乎近于固执不轻易信奉他人意见的执着精神,才使他在史志领域和地方文化建设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二、原始森林植树者
说到原始森林的植树者,使我想到了姚公“林泉野人”这个别号。这不是退隐林泉之谓,乃爱惜山林、爱惜大自然之意也。更是对“天人合一”精神境界的追求。几十年的文化积累、生活积淀,使得姚公重新焕发了青春,可谓厚积薄发,连同他的整个人生感悟,一起涌入笔端。首先,他完成了科普随笔《原始森林的植树者》一书的创作。创作该书,是其二十余年农林工作实践的结晶。姚公长期观察体验,目睹了我国原始森林即将走向覆灭,而自己却有话无处倾诉,有言无人聆听,因而凑成了这个“小册子”。全书分为“森林家族”、绿叶撷趣、兽禽鱼觅踪三辑,共计67篇文章。纵观全书,不论是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水里游的,还是山上生的,地里长的,都属于作者的选题范围,又常常写出自己的一些独到见解。丰富的内容与精辟的见解的有机结合,深入浅出,雅俗共赏,趣味盎然,是这本书的显著特点。我看过书稿后,爱不释手,介绍给黑龙江科技出版社的好友范震威先生,由科技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嗣后,姚公又一发而不可收拾,又写了一些谷蔬考据、人文保健杂谈,与《原始森林的植树者》所余篇章仍涉及自然生态、山川草木、鸟兽鱼虫者汇为一编,1997年结集出版,名曰《山原拾趣》。二书互为补充,相互映衬,堪称姊妹篇。2004年,二书合印,仍称为《原始森林的植树者》,另一名称为《山原散论》。姚公这些涉及自然生态、山川草木、鸟兽鱼虫的科普随笔小品形成的动力,是出于他对祖国山河的每一寸土地的无比热爱,对故乡一草一木的无限珍惜,对生态环境的无尽忧虑而写下的。如果说身居东北边陲的姚公处于多年从事农林工作的职业敏感性,倍加关注边疆的生态环境变化和水土流失,不如说姚公强烈的爱国心使然。自1982年以来,他多次上书、写信给省长、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黑龙江省林业厅、林学会,就国境地带的水土保持、森林资源的管护、封护原始林区等等提出多项合理建议,献计献策。在《加强国境地带的水土保持工作是迫在眉睫的任务》中,面对我国北部边疆被沙俄鲸吞蚕食猎取的不下三百七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一针见血地指出:“世界上很少有像中国人这样不珍爱自己的国土和封疆的,以致造成不可收拾的地步。”真是发聋振聩。这是丧权辱国所致。而自然的水土流失更是骇人听闻。姚公语重情长地指出,“不要以为我们国家还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小小一点水土流失算得了什么……‘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祖国的疆域再大,也是由一颗颗微小的土粒组合积聚而成的,因此,对国土来说,就应该微尘不让,寸土必争。这就是每个具有爱国之心的中国公民所必须持有的态度和信念。”1987年大兴安岭的火灾,已经向我们敲响了如何保护原始森林的警钟。但这只是在少数人的心目中鸣响。1991年6月6日姚公明确地向国务院提出了《关于封护原始森林的建议信》,应该说,这一建议比1998年大水过后国人觉醒,国务院提出封山育林的决策早了7年。
三、自传人生三部曲
姚公在修志之余,又完成了《东大山传》《乌苏春秋》《那丹风雨》三部120余万字的自传体长篇小说。这三部书是以作者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形象地描绘了饶河县几十年的世事沧桑和风土民情。有些篇章和叙述的描写,宛如一幕幕话剧,一幅幅画卷,引人入胜,爱不释手。当我们打开三部书时,便会被书中的人物、情节、事件以及奇特的东疆风土民情所吸引,心灵的震撼如乌苏里春潮澎湃。三部书如同三部曲,是作者人生经历的真实写照。小说的第一部《东大山传》是一部内容丰富多彩、气势恢弘、容量庞大的乡土小说。尽管小说的文本还稍嫌粗粝,可它还是让我想起了沈从文的《边城》,想起萧红的《呼兰河传》,想起骆宾基的《混沌初开》。然而,沈先生的湘西的边城缺少东大山背景的广阔;萧女士的呼兰河边的小城或生死场,没有乌苏里春秋的野迈与僻远;骆宾基先生笔下图们江北岸的珲春,也比不上那丹哈达拉岭下多民族杂居和混血儿生存的境界与多重苦难。可以说姚公的乌苏里乡土三部曲,为读者展示了东北边疆风云的历史长卷,为多姿多彩的当代文学画廊,增添了一道独特的地域风景,是北乌苏里江左岸的一部有关汉、满、赫哲、朝鲜及中俄混血儿边地生活的风俗史。
边地的早年生活凄凉悲惨。小说的前两部发生在20世纪,叙述了地方官腐败无能,日本鬼子的凶恨残暴,伪警察的狐假虎威,跑腿子光棍的群困潦倒,边民的痛苦挣扎,妓女的斑斑血泪……抢劫、强奸、绑票、酗酒、谋杀、赌棍等等,可以说家家有血,事事有泪。
古典道德哲学认为,“善是人生的最高目的”(苏格拉底《高尔吉亚篇》)。可是哲思的命题却常常为生活的实境和文学的观照所颠覆。文学最动人之处是它的悲剧力量(尼采语),而悲剧源于罪恶和苦难,但罪恶与苦难却又可以煎熬忍耐和磨练意志,它可以把人性的某些特质推向极致。姚公的乌苏里乡土三部曲,其东大山下犹如一座炼狱,乡民和移民的原生状态便充满了贫穷与罪恶,充满了人性的变形与扭曲。因此有人说,姚公的三部曲实际上是贫困求生的三部曲,其实它更是20世纪前半叶数百万闯关东人的生活缩影!
《东大山传》写的是作者的幼年和童年,以孩子的视角来看待移民们的拓荒生活,但这生活很快便被日寇的铁蹄所践踏,他们刚刚站定了生存的脚跟,立刻又跌入亡国奴的深渊。作者展示了自家的乡邻人的许多苦难,在展示苦难的同时也不忘进行善与恶的形象对照,相比之下作者更钟情的是父子情、母子情、手足情、邻里情、师生情,作者在颠覆善的同时又重塑新的人性善与人性美。同时,作者更描写了北乌苏里和东大山的自然美,那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树林草甸,野兽飞鸟,无不打上东疆自然生态的烙印。
三部曲中的第二部《乌苏春秋》,继续以《东大山传》的叙事手段,回过头来补述主人公“我”父祖两代人居于山东老家的家史。他们这支姚氏家族,可以追溯到唐代的名相姚崇,姚崇的后代姚矶,他们由河南迁居山东文登,最后因参加乡民暴动失败远逃乌苏里。至此,一二部小说的情节再次汇合,继续朝前发展。小说虽然发生了时空交叉,却更细腻地展现了边陲小镇及其周围拓荒者们生活的艰苦卓绝。
日本鬼子垮了,生活依旧,乌苏里江的涛声与烟泡大雪亦依旧。新政权建立初期,鱼龙混杂,生活的脚步踌躇的趔趄,伪警长们的暴乱、屠杀,世态炎凉,命运逆转,许多荒诞的故事也在这里上演,宛如一幕幕的短剧,一幅幅画卷,读之叫人不禁拍案称绝,爱不释手。
第三部《那丹风雨》紧接着土改后几年,进入20世纪50年代,作者参加革命工作以后,曾担任县委农工部副部长,工作认真勤恳,但因一位姐夫案件的株连,由此而沉冤(此案“文化大革命”后才平反)。第三部小说的生活画卷展示了新旧社会的交替,泥沙俱下。农村的社会主义合作化高潮涌起,三江平原与北大荒的垦区开发,使作者的生活脚步加快。1958年4月,作者因“包庇罪”被处分,行政降级。但作者并没有因此而消沉,而是在生活的底层,撷取原生态的生活中的真善美,找到文学这个友伴,用文学来解读生活,诠释命运。
“三部曲”出版之后,好评如潮。首先是张超在《鸡西日报》1993年11月23日发表了《东大山人斑驳多姿的生活画卷》,对《东大山传》进行评述。鸡西《雪花》杂志社的编辑王文莉,专门致信给姚公,言其读过《东大山传》激动得在火车上落泪,使同车乘客流露出不解的眼神和家中女儿听得入神,直嚷“快念,快念”。并决定在刊物上选刊独立成章的一篇,以飨读者。《那丹风雨》出版之后姚公老友原副省长杜显忠撰文指出:“三部传记的表现手法虽然以自叙的表现形式出现,但他所反映的史实,远远超出了个人和家世的范畴,它记载的是社会风貌和历史的变迁,却折射出时代的光环,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范震威先生读过“三部曲”后写道:“北大荒沃土的开发是近一二百年的事,清末禁垦令的废止和农垦的推行,为这片沃土的拓垦提供了可能。可是关于这些情况,用文学,特别是用小说的形式来反映它,实在是太少了,本书虽不是第一部却是最重要的一部,它的雄浑、厚重、香醇成为这美丽而神奇土地的历史长卷。从这一点上说,姚先生无疑也是一位带有双重意义的拓荒者,而他所依托的背景,正是东大山、那丹哈达拉岭和乌苏里江!乌苏里江日夜奔流,不舍昼夜,它的故事也是说不完的!”“三部曲”是闯关东作品的代表作。电视连续剧《闯关东》热播后,编剧卖关子,说跑遍了东北三省图书馆竟未发现一部描写闯关东历史的文学作品和专著。可以肯定地说,姚公主编的《饶河县志》和他的“三部曲”他是没有读过的。
四、乌苏里江唱新歌
姚公自幼生长在乌苏里江畔。对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无不怀着深刻的感情。他一个岛屿一个岛屿的勘察、一寸江岸一寸江岸的踏查,一座山峰一座山峰的登攀。除完成百余万字的《饶河县志》和一百二十余万字的自传人生“三部曲”以外,姚公还写下了江河史话类《话说乌苏里江》,散文随笔《向古山房散记》《东疆风情》(与人合著)《赫乡散记》(与人合著),另外还创作并与人合著出版了新诗集《乌苏里江放歌》,旧体诗集《翡翠洲诗抄》《塞北情》等诗(诗词)集五六部。部部地方特色突出,篇篇(首首)地方风土浓郁。这些书中有对恢复喀尔喀山名字的考证,有对翡翠洲的命名,更多的是对饶河壮丽山河的描述,对乌苏里江的歌唱。其中《我爱饶河小南山》《挖参记》《挠力河畔话鱼舱》《大顶子山》等文章分别发表在《黑龙江日报》《上海文艺》《北大荒》《地理知识》等报刊上。姚公不仅是小说家、散文家,而且还是一位乡土诗人。《乌苏里江放歌》分“乌苏里江放歌”、“完达山中”、“赫家风貌”、“抗联的足迹”、“北边风情”、“渔歌”、“边地杂咏”、“塞北山歌”“自然生态之歌”等九辑。可以看出,这是一部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边疆人民的劳动赞歌。其中《乌苏里江畔》《渔舍炊烟》两首诗曾发表在1959年6月号《诗刊》杂志上。随着形势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文艺百花园春天的到来,姚公的诗歌创作又开始了由新诗向古典的转变或者说是回归。写下了几百首从体式到意境,从语言到风格的“旧体新诗”。与人合著的旧体诗集《翡翠洲诗抄》《塞北情》,以及收录在《饶河山水歌》中的姚公诗作都是这类仿古体诗新作。如《大带河口春游》:“大带河边木桥横,岸草初绿柳青青。洲渚三五游凫过,汊里渔舟如云轻。”完全是绝句形式的“旧体新诗”,或称“古绝”,后来均汇编在《东疆吟草》诗集中。而收录在与人合著的《双梦集》中的《奇遐的梦》291章,则全部是富有哲理的散文诗。关于人生、关于社会、关于自然、关于心灵、关于宇宙,姚公都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使人耳目为之一新,心灵为之一震。试举几例:如“当你需要时,痛苦也是幸福;当你厌倦时,幸福也成了痛苦。”对不同精神状态下的人对幸福与痛苦作出了鞭辟入里的精警分析。又如:“向日葵把头长大了,他就觉得太阳是无用的了。”在普通的生物现象中、在司空见惯的生活事物中,发现了引起人们感叹的哲理,将抽象寓于形象之中,令人过目难忘。
姚公不仅能文擅诗,是一位早已成为东北边疆乌苏里江畔的知名学者和作家,驰誉四方。但却很少有人了解他又是一位美术爱好者,他喜欢绘画,更早于文学。还是他在读小学的时候,他的绘画课程在班内都是名列前茅的。辍学以后,在家务农期间,每逢阴雨农暇,常以绘画以遣雅兴。虽然没有名师指点,只是一种托物寄情的自我慰藉。但是,作品的艺术手法之高,画面意境之深,无论从写实的角度,还是从审美的角度,都具有一定的艺术鉴赏价值。出于对边塞风光、自然景物的热爱,姚公常常以写生或素描的方式将其记录下来,勾勒成图,存于箧中。在饶河县政府领导的关怀与重视下,《姚中晋书画习作集》得以出版,不但可窥姚公绘画艺术一斑,饶河自然风光、山川风物也历历在目。对于已经消失的景物,更显得其有重要的存史价值。
五、重情重谊广结友
姚公重友谊,讲感情,广结各地朋友。2009年8月,我应饶河县委县政府的邀请有幸参加了饶河建县百年庆典活动。与其说是县委县政府的邀请,不如说是应姚公的盛邀,是他向领导力荐的结果。这和姚公在县里的声望和地位,以及它为饶河地方史志工作和文化事业发展所作的贡献分不开的。一起邀请的还有姚公老乡山东文登市史志办原主任《文登市志》主编初钊兴先生。在姚公看来,百年县庆,不能只是歌舞升平,吃吃喝喝,蹦蹦跳跳,还得要有县情发展历史的回顾,经验的总结。在姚公看来,这一点只有请到了史志办的专家学者,这个百年庆典活动才有声有色,才能够富有历史文化内涵,同时也可以借此机会老友重逢,旧雨叙旧。
因《饶河县志》的审定、出版发行,不算百年县庆我曾两次到过饶河。除了政府接待以外,好多次是姚公的朋友出面接待。这是因为姚公是饶河文化界的旗手,是饶河文坛的盟主,是饶河县的郭沫若,饶河地域文化的带头人。最难忘的是1993年1月《饶河县志》出版发行会之际,姚公的朋友曾倡议并亲自带头集资捐款加印《饶河县志》2 500册的县医药公司林基彧经理,又于雅达利酒廊设宴招待参加《饶河县志》出版发行的有关人员,祝贺《饶河县志》出版发行。从中可以看出姚公的朋友遍及饶河。
姚公之所以受到大家的尊重,是他的道德文章、人格魅力所致。姚公宽怀大度、雅量容人。莫逆之交王吉厚、望年之交于洪江、布衣之交陈景胜,以及官至副省长的杜显忠都有密切的交往,诚挚的合作,这主要缘于文章、缘于学问,缘于共同的理想和道德情操。仅以于洪江为例,与其合作共同出版的诗集就有《双梦集》《塞北情》《孤寂的心园》《翡翠洲诗抄》等。于洪江对姚公可以说是恩重如山,帮助校勘《饶河县志》并作长跋。同时与其舍妹于爱华合著了《姚中晋和他的作品》一书,全面阐述了姚公200多万字的写作经过,洪江认为姚公的这些著作“是饶河这片古老的土地真正摆脱蒙昧,开始走向觉醒的标志。”并对这些作品的创作过程、思想内容、艺术成就,以致缺点不足等进行了全面的阐述与评价。此书出版于1996年,虽然未能包括1996年以后姚公的著作,但基本反映了姚公的著述生涯和学术成就。姚公投桃报李,对洪江关爱倍加,帮助他出版《〈三国演义〉散论》,并对他的诗词创作倍加关注。2005年9月9日,在洪江病逝前三天,姚公看望洪江时见其案头放有百十首诗稿,劝其整理付梓,以便传世。洪江淡然一笑,对姚先生言道:“你已经76岁,我才55岁,你比我大21岁,应多考虑自己的著作的出版,不必为我这几首小诗费心劳神。”这是何等高的境界,何等深的友谊。洪江55岁,英年早逝,姚公不胜哀痛,写下了《于洪江先生永远活在我心中》1.2万字的悼念文章。
俗称饶河县“四大才子”之一的王吉厚是姚公又一好朋友。几十年来风雨同舟,相濡以沫,惺惺相惜,密切协作,携手并进。无论是在饶河共同工作的日子里,还是到虎林任政协主席之后,二人的协作始终没断。共同出版的著作就有散文集《完达山狩猎记》《东疆风情》,随笔集《赫乡散记》,江河传记《话说乌苏里江》,诗集《乌苏里江放歌》等等。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难舍的一对文友。
姚公最大的特点是对朋友坦诚,不计前嫌。仅以笔者为例,因审定《饶河县志》,我们曾因观点不一致而产生过“摩擦”,但双方都能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求同存异,因此成为了诤友。而又是姚公在饶河县庆百年之际真诚地邀请我去做客。本来官方的县庆结束之后,我与初钊兴先生就应离去,姚公偏苦苦地挽留多呆几天,好好在饶河走走转转,真的令人感动。
正因为姚公有对朋友的真心无限,更产生了对自己的父亲的孝心倍加。姚公之父,名学珍,字镜溪,号镜溪先生。是清朝废除科举制度前的最后一届秀才。在山东时,曾以教书为生,1929年因参与渔民反税暴动,失败后逃到饶河,后半生一直务农。镜溪先生的道德文章对姚中晋影响颇深。三十余年乌苏里江畔的生活使得镜溪先生写下了不少歌颂第二故乡饶河的秀美诗篇。姚公将其编为《姚镜溪先生边荒诗存》连同《姚镜溪集》《姚镜溪楷书千字文》《姚镜溪先生诗文杂抄》等其先父遗著陆续出版,这不仅是其孝心的结晶,更是对乡邦文献无比热爱和竭尽全力保护的具体体现。
六、《百年拾记》留后人
《饶河县志》出版后,姚公一天也没休息。从花甲到古稀,直至耄耋,犹不停地总结经验,梳理残稿遗编,埋头著述。姚公认为第一部《饶河县志》尚存在许多舛误和漏失的地方,他不顾自己年高体弱,甘愿为饶河县的史志工作再尽一把力气,将使这些误讹和缺失得到补正。在县志出版以来的十几年中,始终在马不停蹄地四处搜寻着边疆及饶河县一带的史料。一方面深入挖掘整理地方历史文化资料,深入挖掘历史档案,2006、2007年又曾两次前往吉林、长春档案馆查阅清及中华民国时期有关本县的文档,并搜集整理了相当数量抗日时期的史料,以及包括农林产业、人文等方面史料,一方面深入实地调查研究,采访口碑,对《饶河县志》进行拾遗补缺,纠谬正误。于是便形成了这部百余万字的《饶河百年拾记》(以下简称《拾记》)。《拾记》共分为舆地概述,政事沿革(1909~1917),文史拾记(1909~1917),抗日时期纪事,新政权建立后政事文牍,产业,人物(简传、特写、吊祭),赫哲族纪事,谱谍寻踪,杂记,艺文11卷。
《拾记》的编纂是一件非常艰巨的工程,是饶河县史志工作的又一项新的成果。对于百年的饶河,人们既熟悉,又陌生。凭一部《饶河县志》有些问题可以一清二楚,对于好多问题,由于受志书体例的要求和字数的限制,又显得语焉不详。诸如,饶河县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经过一些什么样的程序才确定建立县治的?饶河县建县以来疆域都发生了一些什么变化?是何原因,有无地图佐证?饶河县境内山脉属系;古代居民遗址考据;县内各时期居民集住地,村屯名称变化及分布;山河名称考据与命定;本世纪初县境内与俄罗斯边界的划定与变化,界标号数及位置;政事沿革,各任县官所经政事;各时期上级对本县所采取的重大举措;清季及中华民国时期本县各任县官任期的错讹与漏失;饶河县治所两次迁移的原因是什么,等等这些在《拾记》中都有详细的记载。就方志而言,黑龙江有《黑龙江外记》,吉林有《吉林外记》,《饶河百年拾记》又何尝不是《饶河外记》也。
《拾记》是一部纂辑类与著述相结合的地方志。纂辑为档案史料汇编,著述而成一家之言。其最显著的特点首先是资料翔实,内容丰富,很多内容来自于原始档案,其中部分卷次实乃政书体档案类编的志书。其次是考证与叙述相结合。《拾记》注重订正史实,注重事物发展变化的记述。起到了“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修湖北通志驳陈赠议》)纠史之缪的特殊作用。三是注重逐本溯源,又坚持与时俱进,述历史,尽量追溯到事物发端,写现实,尽量记到搁笔时为止。四是注重人物记述。古今方志半人物。《饶河县志》如此,《拾记》也是这样。读《拾记》之人物有血有肉,一批批洒热血与汗水在饶河这片沃土上的革命先烈、劳动模范、党政干部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激励我们去为这片热土而献身。这也正是姚公编纂《拾记》的目的。《拾记》是姚公献给饶河的又一份厚礼,也是献给志苑的又一束鲜花。姚公——原始森林的植树者 地方文化的著书人——在完成《饶河百年拾记》之后,又在思考什么呢?我们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