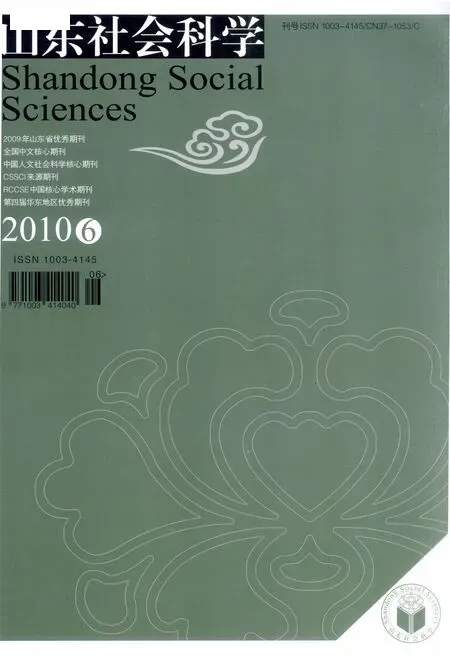唐诗中“草”的隐喻认知解读①
林丽君
(山东广播电视大学,山东济南 250014)
唐诗中“草”的隐喻认知解读①
林丽君
(山东广播电视大学,山东济南 250014)
当代隐喻理论认为,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修辞现象,更是一种认知方式。人们往往通过具体的、熟悉的、有形的概念去认知和体验抽象的、复杂的、无形的概念。隐喻与诗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诗歌重要的表现形式,隐喻在诗歌中普遍运用。唐诗中关于“草”的隐喻可以说比比皆是,并且隐喻丰富;与其它时代诗词中“草”的隐喻相比有其自身特点。
唐诗;草;隐喻;认知解读;时代特点
中国是一个讲究语言艺术的国家,尤其善于运用隐喻来含蓄地进行语言表达。俗语有“听话听音,锣鼓听声”,即指语言中有言外之意,文人讲究说话含蓄,不能太直白,其实就连村妇吵架也有“指桑骂槐”,这其中都有隐喻在起作用,可见隐喻是多么普遍地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而我国古诗词更是把这种隐喻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从《诗经》到楚辞再到唐诗宋词,几乎每个时代的诗歌中都大量存在着隐喻现象,而“草”的隐喻就占了很大比例,在古诗词中俯拾皆是,且隐喻丰富。本文仅对唐诗中“草”的隐喻现象进行简单分析,以期对“草”在唐诗中的隐喻规律及特点进行简单归纳,文中涉及的语料均来自 1983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唐诗鉴赏辞典》。
一、隐喻的本质与内部结构
人类对隐喻的研究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修辞学中隐喻一直被理解为辞格——比喻的一种,是“比明喻更进一步的比喻”。①陈望道:《修辞学发凡》,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3页。对隐喻比较系统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他在《诗学》和《修辞学》中最早提出隐喻,认为这种语言手法是用一个词替代另一个词表述同一种意义,并形成一种对比关系。所以,长期以来传统的隐喻研究把隐喻作为语言中的修辞手段来研究,人们使用隐喻就是为了制造特殊的修辞效果,增加语言的表达力。
但随着语言学研究的迅速发展,人们对它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学者们从哲学、逻辑学、语言学等角度对隐喻做了大量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解释隐喻现象的理论,隐喻在认知语言学中发生了质的变化。1980年,美国两位学者莱考夫 (Lakoff)和约翰逊 (Johnson)通过对英语中大量隐喻表达的调查和分析,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明确指出,隐喻是一种思维方式,是不可缺少的认知工具,存在于人类的思想行为中。此时的比喻不仅被看作一种修辞现象,而且更重要的是被看作一种人类的认知现象。由此看来,普通语言学的隐喻和修辞学的隐喻并不完全相同,修辞学关注的隐喻是一种临时性的有意识的创新,即打比方,其更加关注的是语言的表达效果,是一种语言手段;而认知语言学中的隐喻更多关注的是作为思维方式存在的,强调它的认知功能,是认知手段,这是两者的根本区别。
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是由两个域构成的,一个是相对清晰的始源域(sour domain)和一个结构相对模糊的目标域(target domain)。隐喻就是将始源域的图式结构映射到目标域之上,让我们通过始源域的结构来构建和理解目标域。这阐释了隐喻的内部结构,即始源域和目标域之间是跨域映射的,形成这种映射的基础是始源域和目标域的相似性。隐喻的这种认知机制同样适合于诗歌现象。
诗歌和隐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华兹华斯在《〈抒情歌谣集〉序》中说:诗歌所能表达的根本对象是某种情感体验,所以说抒情性是诗的本质属性,诗歌情感能得以生动地体现,主要是通过隐喻的功能。可见隐喻是诗歌非常重要的一种表现形式,是诗歌的基本构成方式。就像画家用颜料在画布上绘出美景一样,诗人则是通过隐喻创造诗歌的优美和深远。
中国是东方文化的代表,是历史上的诗歌与哲学王国,中国诗歌蕴含的优美和深远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思想的根基。至今我们仍在赏析古人不朽的诗篇,不断与古人进行精神交往,从中体验诗歌带给我们心灵的愉悦与哲思。作者通过隐喻进行表达,读者通过隐喻来理解的诗歌大量存在于古诗词中,如在《诗经》时代就出现了隐喻,即比兴手法;我们解读李商隐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解读刘禹锡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就是在解读其中的隐喻,尽管理解有所不同,但其中的隐喻从来未被否认过。
二、唐诗中“草”的隐喻解读
草是无处不在的,几乎是人们最早最多接触的植物,对其特性的了解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成为关于“草”的隐喻的经验基础。自古以来由草而产生的联想大量存在,仅从由“草”构成的词语中就可见一斑,如草率、草包、草莽、草寇、落草、草草了事等等,无不是“草”的隐喻的体现,正因如此,“草”的隐喻也自然而然地大量存在于古诗词中。当我们联系更多的唐诗中的有关“草”的诗句时,我们发现,唐诗中“草”的隐喻不仅大量存在,而且有规律可循,并被人们正确地认知和解读。
通过对《唐诗鉴赏辞典》的查询,共收集到涉及“草”的隐喻的诗歌达 58首之多,对其隐喻目标即目标域的分析归纳后发现,这些诗歌的隐喻可大致分为以下几类:隐喻生命力旺盛和希望不灭;隐喻衰败、际遇凄凉、失望的;隐喻战争悲壮、悲凉;隐喻离情别意、友情爱情;隐喻高洁情怀等几类。
(一)“草”隐喻旺盛的生命力和希望不灭
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一诗中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两句诗,历来为人们所熟悉,并经常用来比喻生命力的旺盛和希望的不灭,当人们在遭遇挫折、困难、不幸时总是拿此诗来自勉或鼓励他人,可见此诗是诗人通过“草”生命力的顽强这一特点来进行了隐喻表达,人们在诵读此诗时已完成了对此隐喻的正确解读。此时的野草是作为一个喻体存在的,它有“一岁一枯荣”、即使遭遇野火 (隐喻灾难、困境),来年依旧发芽的特点,具旺盛的生命力,即使历尽苦难希望仍在前面。诗人在诗中把野草作为源域,向希望不灭这一目标域投射,而人们对诗的理解基于对草的自然特性的认识而自然地产生了隐喻联想,完成了诗句的隐喻解读。
隐喻在唐诗中很多,如杜甫《绝句二首》中的“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是诗人经过奔波流离之后暂居草堂的安适的表达,是通过“花草香”来隐喻喜悦、充满希望的情怀;李益的“绿杨着水草如烟,旧是胡儿饮马泉”(《过五原胡儿饮马泉》)和“燕歌未断塞鸿飞,牧马群嘶边草绿”(《塞下曲四首》之一)都是用草在春天回绿来映射诗人喜悦的心情。前者写收复五原,旧地失而复得就像春回大地、草儿回绿,令人欣喜,叫人充满希望;后者用生机勃勃的绿草来隐喻西北高原上征人们蓬勃向上的生气和豪情,是希望的象征。
而韩愈的“新年都未有芳华,二月初惊见草芽”(《春雪》)、“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都写早春景色,写出了严冬过尽、春天来临的喜悦。生机勃勃的春草就是希望的象征,故而作者说草色“绝胜烟柳满皇都”。
司空图的“惜春春已晚,珍重草青青”(《退居漫题七首》)更是直接把草青青与希望等同起来。暮春时节,春意阑珊,虽然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却也不乏碧草青青啊,要珍重!用春草来隐喻诗人突破重重失望萌发的希望,使本是伤春的诗的意境有了希望的亮色,表明诗人寄希望于前程,虽身处乱世却自保高洁、不甘无所作为的风骨。
(二)“草”隐喻衰败、际遇凄凉等
从收集到的 50余首诗看,有接近一半的诗句是用“草”来隐喻衰败、失望、际遇凄凉等内容的。
1、用“草 ”来隐喻世事衰败
杜甫著名的诗歌《春望》中有“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用“草木深”这一衰败荒芜的景象来隐喻国都沦陷、城池残破的凄凉境况,流露出对安史之乱带来的山河破碎、满目凄凉的无限感慨。他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器行》一诗中也有“金粟堆南木已拱,瞿塘石城草萧瑟”的诗句,诗人用白帝城中萧瑟的秋草来隐喻安史之乱后社会的衰败萧条。用同样手法的还有刘禹锡的“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乌衣巷》)和“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台城》)都是用野草的荒僻气象来隐喻世事的衰败,曾经的繁荣如今全都败落荒芜了。
韩偓的“古都遥望草萋萋,上帝深疑亦自迷”(《古都》)、吴融的“他山叫处花成血,旧苑春来草似烟”(《子规》)、李白的“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古风》)、“昭王白骨萦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行路难》其二)等诗句都是用草来隐喻世事巨变之后的衰败景象,令人伤心失望,传达的都是不胜今昔的感慨。
2、用“草 ”隐喻际遇凄凉
盛唐时期,诗人们普遍具有积极进取精神,但仕途的不顺、国家的巨大变故都给诗人带来心理上的阴影,因此唐诗中多有写际遇凄凉的诗,而用“草”来隐喻的也不乏其例。
杜甫在《日暮》一诗中有“石泉流暗壁,草露滴秋根”的诗句,就是用秋露滴在草根上来隐喻自己老弱多病的晚年。杜甫居蜀十年,晚年老弱多病,济世既渺茫,归乡又无期,秋草的隐喻流露出诗人迟暮的悲凉情怀。他的“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佳人》)中的“草木”也是隐喻了自己身世的凄凉,是诗人经过安史之乱之后前途无可凭依的窘境的映照。
(三)“草”隐喻边塞战争的悲壮凄凉
战争总是残酷的,古人对战争的描写总传达出悲壮凄凉的况味。而战争多在边塞,尤其多在北部边疆,大漠穷风,边草萋萋,漫无边际,令人心生悲壮凄凉之感,即使是春草,在“景语即情语”的规律中,也总让人产生悲凉的联想。草的漫无边际、自生自灭、无人怜惜等特点此时凸显出来,正好来隐喻战争不知何时结束、归乡遥遥无期的困苦心境。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创伤,让人凄凉悲哀,所以唐诗中多有用“草”隐喻战争悲壮凄凉的诗句。
高适的《燕歌行》即是此类诗歌的代表,其中的“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落日孤城,衰草连天,且是“大漠穷秋”时节,是边塞典型的肃杀、悲凉的阴惨景象。此时战争重围难解,力竭兵稀,秋草恰是边塞战士悲凉心境的写照,隐喻意义鲜明。
李白《古风》中“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寇缨”,写寇兵占据洛阳一带,人民惨遭屠戮,野草的乱和荒凉也正是对战争惨状的隐喻;李白的《战城南》中还有“士卒涂草莽,将军空尔为”,写士兵在战争中无谓的牺牲,草莽的低贱隐喻了士兵生命的低贱,写尽战争的残酷。
岑参的“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更是突出了边塞百草尽折,生命衰竭的冷酷和肃杀,让人感到“愁云惨淡万里凝”的沉重与悲壮。杜甫的“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兵车行》)也是用百草隐喻战场上男儿命贱如草的现实,是对战争残酷的无情控诉。
(四)芳草隐喻高洁情怀
孟浩然在《留别王维》中有“欲觅芳草去,惜与故人违”的诗句,“芳草”出自《离骚》,正因为芳草在《离骚》中即是高洁情怀的象征,所以此处借来隐喻高洁情怀。“寻芳草去”意即寻找理想家园,“芳草”的低姿态、脱俗的特点,正是诗人高洁精神境界的写照。
李白《送杨山人归嵩山》一诗中也有这样的隐喻,“尔去掇仙草,菖蒲花紫茸”,用仙草隐喻理想的境界,高洁之地,表露了诗人对高洁精神的追求;韦应物则用幽草来隐喻安贫守节的恬淡情怀,在《滁州西涧》中有“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的诗句,诗人独爱自甘寂寞的涧边草,对隐喻仕途世态“深树鸣”的黄鹂却置之陪衬角色,是诗人自甘寂寞的高洁情怀映射。
(五 )“草 ”隐喻友情、孝心
草有漫无边际、柔长缠绵的特点,正好可以借以隐喻友情、亲情等感情的绵延与长久。罗隐的“芳草有情皆碍马,好云无处不遮楼”(《绵谷回寄蔡氏昆仲》)即是用了比喻和拟人手法,写连绵柔长的芳草好像友人一样,对自己依依有情,似乎有意绊着马蹄挽留自己不让离去,隐喻着蔡氏兄弟的友情如芳草般情意绵绵。
(六 )“草 ”隐喻离愁别绪
离愁别绪是唐诗的一个重要主题,用“草”来隐喻离愁别绪的诗句也不少。“上有无花之古树,下有伤心之春草”,这是李白《灞陵行送别》中的诗句,与友人离别的愁绪,连春草也伤心,拟人也是隐喻的一种,写出与友人离别时依依难舍的情谊。“苏溪亭上草漫漫,谁倚东风十二阑?”,是戴叔伦《苏溪亭》中的诗句,暮春时节,青草漫漫,绵延无边,正如倚阑人对游子的思念之情,离情别绪漫无边际;韦应物《寒食寄京师诸弟》中则有“把酒看花想诸弟,杜陵寒食草青青”的诗句,它与王维《山中送别》诗中的“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一样,都是用绵绵春草隐喻对友人、亲人的思念之情。
韩琮的“春青河畔草,不是望乡时”(《晚春江晴寄友人》)则是用春草寄寓了对故乡的思念之情。卢纶的“故关衰草遍,离别自堪悲”(《送李端》)则是在用秋草寄寓离别之情外,更着意用郊外野草的苍茫凄凉隐喻友人离别时凄凉的心境。
(七 )“草 ”隐喻时光易老
草生命短促,“一岁一枯荣”,由春到秋仅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诗人由此而体验到生命的短促、时光易老的现实。王维在《秋夜独坐》中有“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的诗句,诗人在独坐沉思中,发现无知的草木昆虫同有知的人一样都在无情的时光消逝中零落哀鸣,因而有了嗟老的忧伤;岑参在《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中也有“花门楼前见秋草,岂能贫贱相看老”的诗句,此二句前接“故人别来三五春”一句,是说时光倥偬,又到秋天草黄的季节了,把草的易衰老的特点映射到人生易老、时光易逝上,是隐喻的体现。
(八 )其它
另外,由于草还有低贱、渺小的特点,可以借此来隐喻小人。如杜荀鹤的《小松》中有描写小松的诗句:“自小刺头深草里,而今渐觉出蓬蒿”,就是借松草喻人,是说小松树从小淹没在深草里,被百草踩在脚下,所以此诗中的“草”明显用来隐喻心胸狭窄的小人,传达了对小人的鄙视与批判。
杜甫在《琴台》一诗中,用蔓草来隐喻卓文君的罗裙,“野花留宝靥,蔓草见罗裙”,是说琴台旁的野花彷佛卓文君当年的笑靥,一丛丛的蔓草则像卓文君昔日所着的罗裙,是抓住了蔓草柔曼、绿意盎然的特点来映射碧罗裙的美丽、妙曼,具浪漫气息。
三、唐诗中“草”隐喻的特点
归纳上述“草”的隐喻现象可以发现,唐诗中“草”的隐喻有其自身特点。
(一)唐诗中“草”隐喻的目标域多为抽象的情感
在收集到的 58首含有草的隐喻的诗歌中,仅有杜荀鹤的《小松》和杜甫的《琴台》是用“草”来隐喻具体的人和物体的,其它均隐喻了抽象的情感等概念。是用具体形象来描述抽象概念,使复杂感情形象化或委婉表达,作用在于通过简明生动地描述“草”这一源域,使人通过联想更深入地理解的域。
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植根于日常生活当中,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是运用语言和思维的基础。隐喻既是人类认识新事物的需要,也具有组织人类概念和发展人类认知的功能,莱考夫和约翰逊指出:隐喻的基本功能是由近及远、由浅入深、由具体到抽象、由已知到未知,而这个过程总是伴着隐喻,进而达到认识和揭示事物的目的。在隐喻的认知推理过程中,人们总是先从始源域中提取反映事物规律的概念结构,然后把它投射到目标域的概念结构中去,从而形成二者的映射关系,而这种映射的基础是相似性。
而保罗·利科更进一步对诗歌中的这种相似性进行了阐述:“如果隐喻丝毫不增加对世界的描述,至少它会增加我们的感知方式,这便是隐喻的诗歌功能。后者取决于相似性,但这是情感层次的相似性:通过用一种情境来象征另一种情境,隐喻将情感融入了被象征的情境,而这些情感与起象征作用的情境联系。在情感的这种转移中,情感间的相似性是由情景的相似性引发的。”①保罗·利科:《活的隐喻》,上海译文出版社,汪堂家译,2004年版,第260页。
通过分析唐诗中的“草”的隐喻发现,唐诗中的“草”的隐喻是诗人们从“草”这一始源域中提取了以下概念结构投射到目标域的概念结构中去的:“草”在春天发芽转绿,也即草的萌生意味着春天的来临,它的生生不息意味着新的开始,因而春草带给人们的喜悦心情与事业成功、前途有望带给人们的喜悦心情相似,所以诗人们多用“草”来隐喻希望;“草”在秋天衰败,意味着肃杀的秋冬来临,给人以颓丧感,与事业不顺、前途无望、战争失败等带给人们的败落心情有相似之处,故而秋草可以隐喻衰败和失望;“草”的连绵不断,不论是秋草还是春草,都有细长绵软的特点,与人们萦回缠绵的亲情友情相似,所以诗人用“草”的这一特点作源域向的域——亲情友情、离愁别绪映射,形成隐喻;“草”生命短促,因而用这一特点作源域来映射生命短促、时光易逝这一的域,从而体验到悲愁;“草”是一个泛指的概念,诗人们提取草中具有芳香高贵特点的一类,来隐喻高洁情操;“草”的低贱渺小与小人的渺小相似,所以可以隐喻小人。
由以上分析可知,唐诗中“草”的隐喻都是以草这种植物体现出来的不同的特点为始源域,以相似性为基础,向目标域投射,并且目标域大多是抽象的情感概念,所以唐诗中“草”的隐喻大多是由具象到抽象的映射,在“草”中融入了被隐喻的情感,达到形象地认识事物和揭示事物的目的。
束定芳在《隐喻学研究》中总结道:“从科学思维的角度来看,人们为什么总是用隐喻呢?黑格尔认为,因为人们需要利用‘感觉’现象来表达‘精神’现象,所以产生了隐喻。”①束定芳:《隐喻学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00页。也正是对这种现象的阐释。
(二)唐诗中“草”的隐喻具有时代性
语言是社会的一面镜子,隐喻作为语言中的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反映了社会的历史环境、时代风貌和一定社会历史背景所包含的特定的阶级关系以及相应的政治、经济制度等因素。在特定语言环境中产生的隐喻往往是当时社会历史背景的反映。
“莱考夫曾经预言:隐喻映射在普遍性上有差异:有的可能是普遍的,有的是分布广泛的,还有的可能是某个文化特有的。一方面,人类的理解和思维都植根于人类基本的身体经验,而基本的身体经验应当是人类共有的,因此我们有理由假定普遍性的概念隐喻的存在。另一方面,身体经验又离不开特定的物理、社会和文化环境,而这些环境是各处不同的,因此我们同时也有理由预测不同文化的概念隐喻体系之间应当是存在差异的”。②转引自蓝纯:《认知语言学与隐喻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版,第129页。这说明隐喻因文化的差异也存在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应不仅仅存在于不同的民族之间,同一民族在不同的时代因文化的发展变化也会发生变化的,所以文化是有时代特征的,所有的文学作品无不打着时代的烙印,体现着时代的特点,因此唐诗中“草”的隐喻具有时代性也是必然的。
在中国古代诗歌创作中,历来都有关于“草”的比喻,如《诗经》中多用花草等来起兴、比喻,楚辞中更是用芳草来比喻“美人”,宋词中则有较多“草”隐喻缠绵爱情的。可见用“草”来隐喻表达感情、认知事物、达到写作目的,在我国诗歌创作中是古已有之的了。但稍加注意不难发现,各个时代关于“草”的隐喻对象是不尽相同的,是与时代面貌息息相关的,体现出一定的时代性。
与上面举到的《诗经》、楚辞、宋词不同,唐诗中有关“草”的隐喻多涉及庄重、严肃、正统的内容,事关个人爱情、私情的隐喻很少,其隐喻的对象如上文所分析的都是与国家兴亡、战争成败、仕途穷达、亲情友情有关。大致看来,在收集到的 58首唐诗中,关涉国家兴亡、战争成败、仕途穷达的竟达 20余首之多,写离情别意、亲情友情的有 8首,而有关缠绵爱情和隐喻美人的竟然为零。由此可以看出,唐诗中“草”的隐喻目标多是正统、庄严的,反映出唐朝诗人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
唐朝经济繁荣,国力强盛,诗人们面对当时国势强大、经济文化繁荣、开疆辟土、军事活动较多的局面,大抵胸襟开阔,意气昂扬,希冀建功立业,体现出积极进取的精神,因此,唐诗表达的多是对祖国和人民命运的关注,在希冀建功立业、成就一番事业的同时,诗人也关注自己仕途的穷达,儿女私情反而不太关注了。所以唐诗中“草”的隐喻多为大气、庄重、正统感情的映射也就不难理解了,具有较强的时代特点。
另外,从表达的情绪看,在 58首诗歌中,竟有 20余首是用“草”来隐喻衰败和失望的,这同样是唐朝诗人精神风貌的体现。正因为唐朝的诗人们多是积极进取的,希望在事业上有所成就,但他们的仕途往往较多波折,如韩愈、李白、杜甫等事业多有不顺;又兼社会的动荡、战事的频繁,他们的诗歌中也体现出失望的情怀,衰败、失落的情绪在“草”的隐喻中较多出现也是正常的了。
当然,因个人的经历不同、性格的差异,唐诗中“草”的隐喻在不同的诗人之间也存在一定差异,此文不再赘述。
四、结语
隐喻是一种认知现象,是以相似性为基础由始源域向目标域的投射,唐诗中“草”的隐喻是这一机制的体现。诗歌与隐喻有着密切的联系,隐喻是诗歌重要的一种表现形式,是诗歌的基本构成方式。唐诗中“草”的隐喻大量存在,且隐喻丰富。由于时代的不同,唐诗中“草”的隐喻与其它时代诗词中“草”的隐喻有所差别,体现出比较明显的时代特点。
(责任编辑:艳红)
I207.22
A
1003—4145[2010]06—0097—04
2010-04-10
林丽君 (1962-),女,山东广播电视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