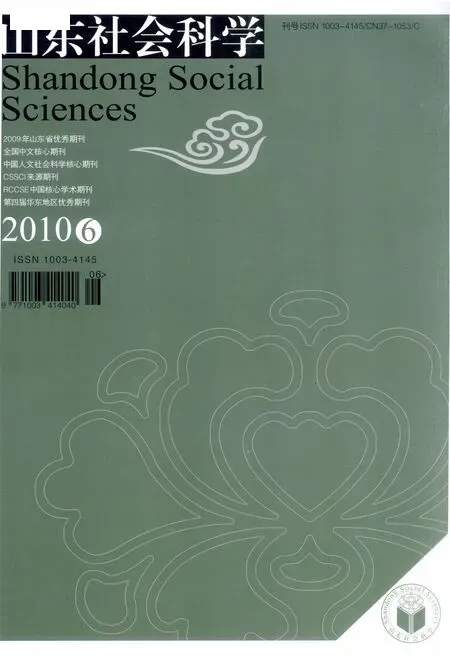艰难的过渡:1949—1978年“现代派”批评话语①
王洪岳
(浙江师范大学,浙江 金华 321004)
艰难的过渡:1949—1978年“现代派”批评话语①
王洪岳
(浙江师范大学,浙江 金华 321004)
现代派 (现代主义)文学及批评话语曾经在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盛行一时,在1949年之后现代派被当作资产阶级文艺思潮而被噤声。但在这种情况下,茅盾、袁可嘉等批评家一直在努力传达出他们对现代主义的矛盾看法;稍后文革中的地下潜在写作者们亦通过创作表达了他们对现代主义的认同。这一时期中国关于现代主义的话语呈现出一种艰难的过渡性特征,并为新时期现代主义文学的重新崛起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和艺术资源。
现代派;文学理论;话语方式;过渡性
一
当代文论发展的六十年,可以粗略地分为前后两个三十年:1949年至 1978年、1979年至 2008年。中国当代文论的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即构成一个不可割裂的有内在一致性的六十年。“现代派”在这六十年的遭际作为我们研究新时期三十年现代主义文论的前提和背景,特别值得在此进行一番深入探讨和研究。整体看来,前三十年“现代派”文学及其文论在中国的存在显得坎坷异常。1949年至 1978年,“现代派”基本上成了一个遭禁的或者横遭批判的术语。这与该世纪上半叶现代派诗学与文论流派争先恐后地出现的繁荣局面形成了鲜明对照。这个术语及其变相翻译如“现代主义”的使用,典型地代表了自 1949年后对来自于西方的各种学术话语、学术思想的禁锢状况。我们通过这期间的两个个案——茅盾和袁可嘉对于现代派的评论——来考察“现代派”在当代中国文论发展中的历史命运,以一斑而窥全豹,进而对当代中国文论家思维主体加以观照。
关于 modernis m或 modernist[汉译为“现代主义 (者)”或“现代派”]这个术语,在汉语语境中可追溯到1915年,陈独秀在这一年在中国最早提到了“现代主义”一词①陈独秀:《现代欧洲文艺史谭》,《青年》杂志第1期,1915年。。后来在 20年代初陈望道又正式运用了此术语进行文学批评。而关于“现代派”这个术语的由来,施蛰存先生有自己的看法,他在《〈现代〉杂忆·“现代派”的诗》一文中认为“现代派”这一术语与他主编的《现代》杂志有关,他指出了《现代》杂志和“现代派”诗的渊源:“原先,所谓‘现代诗’,或者当时已经有人称‘现代派’,这个‘现代’是刊物的名称,应当写作‘《现代》诗’或‘《现代》派’。它是指《现代》杂志所发表的那种风格和形式的诗。但被我这样一讲,‘现代’的意义就改变了。从此,人们说‘现代诗’就联系到当时欧美文艺界新兴的‘现代诗’(The Modern Poetry),而‘现代派’也就成为 TheModernists的译名。王瑶同志在他的《新文学史》中引用了我这一段解释,从而确定了‘现代派’这个名词的意义。”①施蛰存:《施蛰存文集·文学创作编》第二卷,《北山散文集 (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7-158页。《现代》是 30年代出现的标榜现代派文学观的杂志,但是“现代派”一词是否最早从此而来,还是令人存疑的。另外,徐迟在 30年代曾提出过“无产阶级的现代派”的概念,直接把现代主义文学和无产阶级启蒙文学、革命文学联系起来②吕周聚:《中国现代主义诗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这些论著都较早地涉及或提出了中国现代派 (现代主义)的课题。确定无疑的是,从陈独秀、陈望道等论及现代派起始,到二三十年代出现的“现代派”诗学,都为中国文学理论界大量运用“现代派”或“现代主义”来指称和研究这一文学现象和流派打下了初步的学理基础。
然而,“现代主义”一词在 1949年至 1978年的三十年间,几乎不再出现,而涉及到西文 modernis m或modernist的译文,大多以“现代派”表示之。而且在一般的文字表述中,如果不得不涉及到现代主义,也基本上用“现代派”代替之。即使大陆文论家提及“现代派”,也是持否定的姿态,但他们在否定的话语之中又含着十分微妙和复杂的内在认同态度。
二
当时中国学界普遍采取的态度是回避或躲避、漠视。茅盾先生的长文《夜读偶记》打破了这种鸵鸟策略,多次提到“现代派”,但在态度上基本是将之作为一种否定的对象来对待。他在文中即基本不用“现代主义”一词,而以“现代派”来指称那些“产生于资产阶级没落期”“抛弃一切文艺传统”的新文艺③《茅盾全集 》第25卷,第175页。。而这个“现代派”之“派”和后来一再出现某某派 (如走资派、保皇派等),都是在贬义上的运用。而“某某主义”的“主义”似乎含有肯定意味或褒义,那么是不能够用于带有贬义的、否定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文学思潮流派——现代派身上的。茅盾五四时期曾经大力介绍和翻译来自欧洲的各种新潮或现代主义文论,但后来他投身于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和文学创作,直到 1956年他写作《夜读偶记》,其背景是当时有人“认为现实主义已经过时,而‘现代派’是探讨新艺术的先驱者的人们”,“一九五六年忽然在欧洲又变得‘时髦’的调子”。当时中国整个国家追随老大哥一边倒,文论自然也从追随西方 (欧洲)到倒向苏联体制,这就是当时从政治领导人到批评家和文论家等都一再倡导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原则,而对产生于欧洲而且还有很大发展和影响的“现代派”则无疑持鄙视或全盘否定的态度。茅盾主要是将“现代派”放在现实主义乃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大背景下予以阐释的,他认为一部中国文学史便是现实主义和非现实主义或反现实主义相互斗争的历史。他认为现代派产生于西方 (欧洲),属于资本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因而是保守的、落后的;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产生于社会主义的苏联,是属于无产阶级的,因而是革命的、先进的。在这一点上,茅盾与当时的主流思想和评价标准并无多大的区别。
虽然《夜读偶记》是在这样一种学术氛围中写作完成的,但如果认为该书全面彻底地否定了现代派,并不符合实际。我们且看他的字里行间所透露出来的诸多信息,正是这些信息暗示或残留了早年他在五四时期接受和传播现代主义的积极态度和世界性视野。以前他借鉴象征主义等现代主义手法,对其评价也较高,虽然现在他称“现代派是彻头彻尾的形式主义”,是“颓废文艺”,“象征派是悲观主义者,又是神秘论者”,“象征派反映了‘世纪末’情绪”,等等。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给现代派定性,是把它完全限定在文艺思潮、文艺流派范畴之内,不轻易给现代派作家扣上“帝国主义殖民思想的传播者”、“反动、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的代言人”等政治帽子,通篇在论证“现代派是资本主义的批判者,不是资本主义的精神辩护士”。④张德林:《现代小说的多元建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9-310页。笔者在多年前就曾指出过,这样的文字论述反映了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在 50—70年代的复杂而矛盾的心理,一方面茅盾先生要顺应当时的政治形势,为当权者说话,对这种产生于西方的现代派思潮进行批判,而在批判的时候他把范围仅仅局限于西方的现代派,而非民国时期中国自身的现代派;另一方面,他又割舍不了在五四时期大量介绍现代主义以及现代主义本身所具有的创新意识和形式技巧对他的吸引力,他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现代派某些创作方法的可取性。所以就带来了茅盾此长文表述话语和表达方式上的隐曲委婉的矛盾之处。①王洪岳,刘绪才:《试比较茅盾与新时期新潮文学对现代主义的接受方式》,《茅盾研究——第七届年会论文集》,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
茅盾认为“超现实主义”可以大体概括现代派的精神实质。而在形式方面,现代派是区别于古典主义的“抽象的形式主义”和早期象征派的唯美形式主义。在给现代派戴上了一个资产阶级的“颓废文艺”的高帽之后,茅盾却将此分门别类加以概括分析。尤其是对于现代派的唯形式主义倾向并没有过多地进行批判,他只是按照现实主义和非现实主义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来立论,把现代派归于他的非现实主义,他还特别强调了非现实主义不一定是反现实主义;而大致看来现代派并不是反现实主义的,而是非现实主义的。他在这篇长文中一般不提“现代主义”,而基本以“现代派”表之。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已经经历了反右斗争,政治立场和党性要求不得不采取这样带有表态性质的表达方式。另一方面,笔者认为这是茅盾的写作策略使然。除了正标题《夜读偶记》,该文还有一个副标题——《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其它》。在篇幅上,当然关于现实主义包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字占多数,因为他拉拉杂杂写了较长时间,而且按照这种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或反现实主义之间斗争的线索从先秦开始写起,所以涉及到现代派的文字并不太多。然而我们不能忽略了这个“及其它”。这其中似乎包含着多种的意味。首先,作为一个党在文化领域的领导人,茅盾不能放开思维来大力地介绍、研究现代主义,更不能对此加以倡导、推崇。其次,作为一个学者和著名作家,作为一个曾经引领中国文学思潮的开拓者,他具备敏锐而超前的艺术眼光,他对现代主义其实抱有深刻的好感,所以这个《夜读偶记》的落脚点,笔者认为恰恰就落在了“及其它”的“它”上,也就是非现实主义的“现代派”身上。再次,在具体的小标题的设置方面,茅盾也是煞费苦心。如“四古典主义和‘现代派’”,提及古典文学的典型形态他谓之“古典主义”,而论及现代文学的典型形态时,他不能谓之“现代主义”,而只好用“现代派”,而且加上了引号。(他仅在两处用了“现代主义”,一处是在“五理想与现实”这一节中,写到“古典主义人物是反对中世纪的封建制度的,可是反古典主义的消极浪漫主义人物却不但不反对古典主义所反的中世纪,反而向往于中世纪。它们这个衣钵一直传到现代主义者手里”;另一处是在“从印象主义到超现实主义,大约已有五十年历史的现代主义运动,曾经流行于欧、美两大陆以及东方的一些国家”。)这个小标题与其他小标题一个很大的不同便是,仅有这个词在所有标题中加上了引号。而在内文中出现的“现代派”一词也几乎全部加上了引号。即使对属于现代主义各分支的象征主义、未来主义、表现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以及形式主义,和上述两处出现的现代主义等文艺思潮流派术语则都没有加上引号。我们对此不能不予以关注,从中可以看出当时作为一个著名学者和作家的写作心态和写作主体态度之微妙。其言外之意似乎是,“现代派”是加了引号的,乃引用他人之说法,而不是我茅盾自己的发明,在此囿于论题不得不谈论之,还请大家高人明鉴之。
茅盾当时的写作策略或说矛盾心理在《夜读偶记》就这样隐约而曲折地体现出来了。在批判地认为现代派是资产阶级的腐朽堕落的文艺之后,他对象征主义、印象主义和未来主义等还是持一种较为温和的态度,认为现代派“严肃地工作着”,虽然他们不要思想性,但可还注重形式的美,如“象征主义注重神秘美,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美等等”,“因而在艺术的表现手法 (即所谓技巧)方面有些新的前人未经探索过的成就”。而这种技巧上的新成就可以为现实主义作家或艺术家所吸收,可以丰富现实主义作品的技巧。这些话语则简直是在为“现代派”唱赞歌了。然而,他这部洋洋洒洒的著作也许写作的文气不顺畅,也许还有别的什么原因,总之,文本间杂混交织着政治意识形态的审判话语和严肃的学术话语,这两种话语之间无疑充满着矛盾。
所以,茅盾有时承认现代派的技巧和形式可以运用,甚至有的地方还对此予以充分肯定乃至赞赏;但有时又极力否认现实主义与现代派的综合的可能性,好像把握住现实主义就进了保险柜,而非现实主义就是临近危险之境,反现实主义就是反革命、反动的了。一个曾经在五四时期大力介绍和研究西方现代派的批评家、理论家,三十年后竟然变得神经兮兮,在下断语的时候犹豫矛盾,不想给那些现代派作家扣帽子,又不得不给他们扣顶帽子,给人家扣了帽子自己内心又不安,其文字又不免流露出自己作为现代文学批评家和小说家对现代派的某种特殊的兴趣和情味。因此他才写出了这样的句子:“然而毒草还可以肥田,形式主义文艺的有些技巧,也还是有用的,问题在于我们怎样处理。”所以,茅盾在行文中,在进行了一番带有大批判味道的议论,给现代派贴上了一系列逃避现实、鄙视群众、为资产阶级服务等等标签之同时,又往往会用其他文字来淡化这种批判意味。有时候加了括号来加以说明和补充,如“(当然,我们也不能把现代派文艺的倾向性和现代派的个别作家或艺术家的政治立场混为一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派艺术家其中有投身于革命行列的,有致力于和平运动的,为数很多……)”。有意思的是在这部评论的结尾,作者加上了如下的字样:“四月二十一日,首都人民围剿麻雀的胜利声中写完。”一个应该带有思想家气质的批评家,在那个严肃正经的时代竟然写下了如此的文字,这反映了那个荒诞时代的某些掠影,也算是一个有趣而带点喜剧色彩的小花絮。
三
60年代对于现代派感兴趣而且花精力写评论文章的是袁可嘉。60年代早期,袁可嘉写了三篇文章,对他很感兴趣的现代派发表了属于那个时代的文字。1960年发表的第六期《托·史·艾略特——美英帝国主义的御用文阀》是这样介绍和评价艾略特的:“托麦斯·史登斯·艾略特 (T.S.Eliot,一八八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美英两国资产阶级反动颓废文学界一个极为嚣张跋扈的垄断集团的头目,一个死心塌地为美英资本帝国主义尽忠尽孝的御用文阀。从本世纪二十年代起,他在美国法西斯文人庞德、英国资产阶级理论批评家瑞恰慈等人的密切配合下,在美英资产阶级理论批评界和诗歌创作界建立了一个‘现代主义’的魔窟。四十年来,他们盘踞着美英资产阶级文坛,一直散布着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思想影响和文学影响。”①袁可嘉:《托·史·艾略特——美英帝国主义的御用文阀》,《文学评论》1960年第6期。这段评价文字说明了袁可嘉在 60年代中国政治情势下,从社会政治学的角度去思考表达问题的思路,表达方式充满了论战和大批判的味道,而学术研究的成分甚少。只要把所论的对象放置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抑或现实主义和非/反现实主义等两相对照的思维模式之上,论者就可以做出自己鲜明的论断,如果被判为前者,那自然是革命的、进步的,如果被判为后者,那自然就是落后的、不革命的乃至反革命的。思维方式的非此即彼,思想内容的革命与反革命,简单的对立两极的评判模式往往只能导致这样的结论。
在《“新批评派”述评》一文中,袁可嘉首先考察了新批评派的由来和分支,接着又从政治意识形态角度进行论说,他指出:“‘新批评派’某些重要的代表人物不仅有一套形式主义的文学理论,而且有一套反科学、反民主、反社会主义的文化思想。其中有些人不止是深居学府的文人学者,而且是抛头露面的文化掮客。他们不仅撰写理论著作,而且通过具体评论打击资产阶级文学内部的民主进步传统,竭力维护古今反动流派的统治地位。”所以,它特有的“反动实质”需要加以解剖。接下来作者就以批判的口吻对此分析批判。但是,作者的评述文字并不能表明新批评派就是反动的,因为作者此处的分析还算客观,“象征主义为‘新批评派’提供了美学理论,文字分析则为它提供了批评方法,两者合起来,就构成‘新批评派’的形式主义理论”。②袁可嘉:《“新批评派”述评》,《文学评论》1962年第2期。再联系袁可嘉在 40年代大力提倡艾略特的象征主义“客观对应物”理论,他这里的分析大致是中肯和客观的。但是,为了达到自己事先设定的目标,他把艾略特的理论打入反动之列,他认为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中的诗学思想割裂了文学与历史传统的真正联系。其实,他这里不知是忽视还是有意忽略了艾略特所提及的传统实乃基督教信仰传统。艾略特有感于当时 (1917年左右,即一战期间)整个社会信仰丧失,人类尊严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完成此文。袁可嘉先生并没有重视这一点。
然而整体看来,袁可嘉对于艾略特“非人格化”、“客观对应物”等有机形式主义和瑞恰慈的字义 (语义)分析理论以及新批评派的贡献等还是较为尊重的,认为它作为理论基础,成为现代主义诗歌的根源。对自己的老师辈瑞恰慈则几乎没有只言片语的否定了。且不说他在 40年代关于现代主义的文论创造大多师出有源,他从艾略特等西方现代主义文论家那里汲取了很多的营养,仅就他在此文中的表述来看,他也深受艾略特及瑞恰兹等人的正面影响。他在该文中约有 90%的语言来客观描述新批评派的特点,用大约 10%的文字来抨击批判之。所以他骨子里的认同与表达形式上的否定,和我们在《夜读偶记》里所看到的情况非常相似,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些批判文字中,袁可嘉也有对“新批评”重视语言论转向的哲学背景有意无意的误读。他在该文中至少还没有意识到哲学及文学理论的语言学转向,而坚持语言工具论,反对语言本体论 (他称之为“唯语言论”),所以他在行文中说了不少行外话。另外作者在论及新批评关于“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对其坚持形式第一的观点基本持否定态度。这一点较之茅盾先生的观点则是一个后退。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更是充满了浓厚的冷战或意识形态意味——“它是帝国主义时期反映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典型的反动流派”。他的理论基础就是,新批评派为维护和巩固“现代主义”的统治地位服务,所以,它就是反动的。很显然,他的论证过程和结论存在着不能自洽的深刻矛盾。另外,他于 1963年《文学评论》第3期上发表《略论英美“现代派”诗歌》一文,还对英美“现代派”诗歌进行了评析,显示了作者较为广阔的学术视野,同时依然带有以某些政治话语来评判学术问题和文学理论问题的倾向。
四
而自 60年代中后期直到 70年代中期,也就是文革时期,“现代派”一词几乎成为一个文艺理论的术语化石,再也没有人敢去探究它。期间有一位诗人食指 (郭路生)曾经用现代主义手法写了一些诗,如《疯狗》、《烟》、《酒》、《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相信未来》等,后来出现的“白洋淀诗群”等。林莽在诗集《我流过这片土地》里这样提到白洋淀:“白洋淀有一批与我相同命运的抗争者,他们都是自己来到这个地方。他们年轻,他们还没有被生活和命运所压垮,还没有熄灭最后的愿望。他们相互刺激,相互启发,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文化氛围。一批活跃在当代文坛上的作家、诗人都曾与白洋淀有过密切的联系。那儿交通不便,但朋友们的相互交往却是经常的。在蜿蜒曲折的大堤上,在堆满柴草的院落中,在煤油灯昏黄的光影里,大家倾心相予。也就是那时,我接触了现代主义文化艺术思潮。”这些潜在阅读和潜在写作,由于受到了当时世界文学新潮——现代主义——的影响而显示出与当时主流的、显在的写作迥然不同的特性。路也在研究“白洋淀诗群”时,曾经写道:“白洋淀诗人们不仅仅像同时代的诗人那样只是从民歌和中国古典诗词里吸取养份,他们完全不同于当时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写作手法,他们更多地是从西方文学里吸取了对人类命运终极关怀的现代精神和多样化的现代诗歌写作技巧,隐喻、反讽、悖论、意象叠加和重合,以此来表现现实世界的荒诞和真实的内心向往,探寻人类的生存本质,这使得他们的诗歌不可避免地带有现代主义锋芒,更具有个人性,现代主义是这些青年人默认的共同的准则。这种现代主义特征以多多和芒克的写作探索最为突出,他们大量运用现代主义手法表达自己的感受、情绪与思考。”①路冬梅:《白洋淀诗群的文化地理学考察》,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第41页。在研究界、评论界一片肃杀、销声之际,是这批诗人在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是具有特殊的美学意义的。只是我们在认识和评价这段时间的潜在或地下写作的时候,不能评价过高。之所以说它是潜在的,就是它当时还未能对社会和文学发生多大的影响。由于当代文学的从业人越来越多,人们也有一种渴望挖掘和发现文革地下文学的冲动和心理补偿性诉求,所以使得此时期的潜在写作得到了挖掘和研究,这是应该做的工作,但是不能过高地评价那时的创作。
食指后来在与林莽、唐晓渡谈诗歌先行者的对话中,提到自己在文革前很喜欢西方的现代派。上述诗作所显现出来的风格无疑可以证明他深受现代派的影响。但这些诗当时只是在知青当中流传和吟唱,但无人去评论和研究它。文革地下写作、潜在写作和手抄本、油印本等写作—流传方式,现在想来就像中世纪般的遥远,可是那就是我们还不太远的过去的文学存在的实际状况。那个类似于中世纪的时代,恐怖、压抑、噩梦般的文学写作和文学阅读,终于在 90年代得到了人们的关注和研究,1993年杨健出版《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②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初步涉及到文革地下文学,其中特别提到了带有现代派色彩的诗人郭路生的创作,直到 1999年出版的《沉沦的圣殿——中国 20世纪 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③廖亦武主编:《沉沦的圣殿——中国 20世纪 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版。,在更细微的程度上回顾和整理曾经珍藏在一代青年诗人和文学作者心底的记忆。该书重点考察和记载了郭兰英之死、郭路生和赵一凡的诗、白洋淀诗群和北京的地下诗歌江湖,特别是民刊 (《今天》)的情况。这本书使我们的研究立足点不得不放在一个重要的民刊,即创刊于 1978年 12月 23日的《今天》,它上面发的大多是属于现代派的文字。在创刊号的“致读者”中作者引用了马克思的话剥离出文化专制的实质:“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唯一的色彩,每一滴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能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由北岛起草的这篇发刊词中还写到:“在血泊中升起黎明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五彩缤纷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属于大自然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开放在人们内心的花朵。”诞生于 1978年底的这个民刊,既是文革地下文学的总结者,又可以说是新时期文学的真正开创者,同时它还标志着关于现代派的话语从此由地下转向了地上,成了可以公开或半公开的现代主义的大本营之一。也因此,1978年不但是政治上的转折年份,而且也是文学尤其是现代主义文学发生重大转折的年份。在主流意识形态看来,它仍然是异类甚或异端的;但在新潮文学人看来,它是粗糙但充满旺盛生命力的新文学形式。所以,以纯文学姿态创刊的《今天》,则不得不以政治挑战者的姿态发声。风云际会的当代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文学理论,不能不在惊涛骇浪中前行。这个颇具现代派色彩的民刊,又是由一些具有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色彩的诗人创办的,这就昭示这一种即将到来的新时期启蒙的现代主义性质。这显然不同于西方的现代主义的反启蒙性。
现代派这个术语从 70年代末期开始又被大量使用,但基本上是在否定的意义上使用的。进入 80年代,“现代派”这个术语开始和“现代主义”一起运用,但使用前者则往往意味着话语主体依然囿于传统主流意识形态,抱持浓厚的怀疑和批判色彩;而使用后者则一般意味着承认该术语的客观存在,并有为之辩护的味道。到 80年代中期,两个术语被人们大量运用,使用机会也几乎平分秋色。其中钱中文先生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一书①钱中文:《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较早将学术研究的心态带入当时的学界,起到了很大的示范作用。然而在 1989年后的几年里,“现代派”一词重新获得某种宠幸,被某些极左人士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话语而大加挞伐。自 90年代中期以来,这两个术语交替使用,虽然还有人士在使用前者时仍然带有较为浓厚的意识形态批判色彩,但一般学人在使用时已经脱去了带有偏见的意识形态的批判色彩,能以学术的心态来做冷静客观的研究了。新世纪以来,后者 (“现代主义”)往往取代前者 (“现代派”)而获得了更多的青睐和关注,许多研究成果 (包括论文、专著)常常以此为标题或关键词。
围绕“现代派”或“现代主义”这个学术术语的争论、斗争,其实和 1949之后的六十年非正常的社会生活和学术活动有密切关系。本来,关于现代主义的讨论和研究不是什么政治问题,而是一个较为纯粹的学术问题,是一个文学批评、文艺理论问题,可是六十年来尤其是前三十年几乎所有的人文学术研究、文学理论和批评问题都被纳入到政治领域,由政治领导人来决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并进而决定学者的学术生命乃至肉体生命。由于较为长久的意识形态压制导致了写作的“政治的无意识”(杰姆逊语),由于外在意识形态的强势,学者和作家们在写作的时候往往会由这种外在的他律转变内在的不由自主的“自律”,根本无需他律的干预,自身就会设置一个过滤器来自行过滤掉不合时宜的思想。这种独语式的所谓写作其价值往往有限。正如福柯所说,专制的话语往往靠独语,它经不起推敲。1949—1978年的三十年中国文论关于现代派的观念及其表达形式正表现了这一点,其独语或独裁式话语表达方式及其对中国当代人文学术的负面影响至今仍显而易见。所以,我们把问题放在这个大背景来观照,自然会发现诸多见怪不怪的现象纷纷出笼。从上述茅盾和袁可嘉等人的文论中我们就会发现,他们无不以所谓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这些被官方政治领导人 (如毛泽东)钦定的“正确的”的一方,来贬低甚至打压“对立”的一方:资产阶级、资本主义、非现实主义或反现实主义。似乎这样做,就代表了自己是革命的、进步的。但是,他们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还是在一定程度上秉承了学者的良知和学术研究的科学态度,对现代派或现代主义进行了某些方面的具有开拓性的研究。这体现了杰姆逊“政治无意识”的两面性:一方面是被压抑的服从的集体政治无意识;另一方面是被压抑的独立的个体政治无意识。这两方面都在被压抑的文化或政治背景下以一种无意识的形式宣泄出来,结果就导致表达话语的复杂化、矛盾化。
总之,这样一种文论家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一方面含着很大的奴性意识,文论家的主体性也往往消弭在这种追随政治意识形态的行动当中,而不可能充分地得到张扬。另一方面,在当时东西方冷战和国内阶级斗争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尽量以隐曲委婉的方式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学术话语,从而又在某种程度上为我们留下了颇具参考价值和研究价值的关于现代主义方面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即使他们从贬义和批判的角度评论现代派,由于当时已经基本上没有在世的作家诗人从事现代主义文学的创作,而且他们所论的对象都是外国的或已死的文论家、批评家,其危害就相对来说较小。如果这种文风对准当时在世的中国批评家或文论家,那么他们的遭遇便更加危险了。处于 20世纪上半叶现代主义思潮和文论繁盛期和新时期现代主义文论新的繁荣期中间的三十年关于现代主义的批判话语,其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在显性的大批判话语当中,又不免在字里行间渗透了一种欲言又止、欲说还休的吞吞吐吐的肯定和向往,这种话语内容及表达方式也深刻地影响到了后三十年关于现代主义文艺理论话语运思方式及其文论家主体人格的建构。其经验和教训都很多,值得我们咀嚼和反思。
(责任编辑:艳红)
I02
A
1003—4145[2010]06—0085—06
2010-03-25
王洪岳(1963-),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