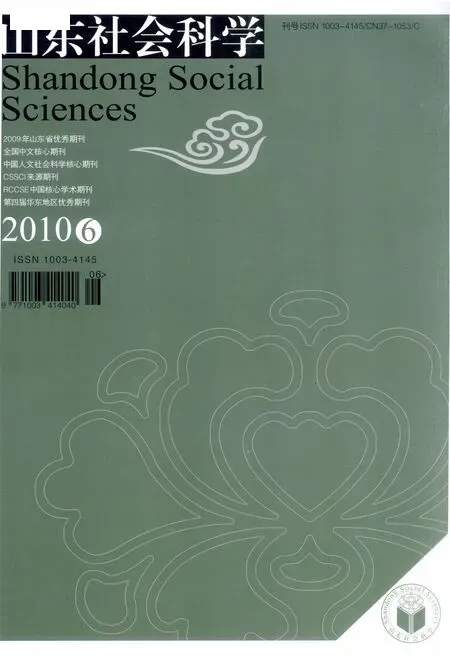商法规范的公法性与私法性、强制性与任意性辨梳①
张 强
(复旦大学法学院,上海 200438)
商法规范的公法性与私法性、强制性与任意性辨梳①
张 强
(复旦大学法学院,上海 200438)
公法性与私法性的对立,强制性与任意性的对立,是针对商法规范的两组不同分类标准。前者是法益保护的问题,后者是调整方法的问题,不能简单等同。商法强制性规范中既有私法属性的强制,又有公法属性的强制。前者重在实现交易便捷和交易安全的商法固有价值,是商法中原生态的规范,具有稳定性;而后者重在实现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是真正的“商法公法化”的产物,具有政策性和变动性。
商法规范;强制性;公法性;私法性
对于每一个重要的法学概念,定性研究是最为普遍的研究方法,同时也是阐释法律概念最为有效的一种方法。商法规范作为构成商法的最基本要素,对其做定性研究既是基础性的,又是不可或缺的。与作为一般私法的民法规范相比,强制性的商法规范占商法规范总量的比例要大的多,“应当”、“必须”、“不得”这样的表示强制性的用词,在商法中是经常出现的,这使得商法成为强制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相互对立,共生共存最为明显的一个部门法。除了商法强制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这样一组对立的范畴之外,学者们还提出了公法规范与私法规范这样一组对立的范畴。从商法强制性规范的研究现状来看,大多数学者直接将强制性规范等同于公法规范,或者将商法强制性规范理解为伴随“商法公法化”的产物。虽然提法有所不同,但普遍将商法规范的强制性与公法性等量齐观,将商法规范的任意性与私法性混为一谈。作为两组不同的属性范畴,强制性与公法性,任意性与私法性,只是在大多是情况下产生契合,它们始终属于两组相互分立的定性化研究方法。简单化的“公法强制,私法自治”在理论上远不够精细缜密,对两组分类的辨析、梳理有助于我们更为通透、科学地认识商法规范发展的规律性和存在上的特殊性。
一、商法规范的公法性与私法性
公法与私法的二元区分肇端于罗马法,继受了罗马法的大陆法系国家将这一法律传统保留并不断地发展。公法私法的划分在 20世纪以来,随着“私法公法化”趋势的形成和发展,又给法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挑战。在作为特别私法的商法领域,这种变化表现的尤为突出。具有公法性质的规范渗透到私法领域的现象,被称之为“私法的公法化”;“商法的公法化”,则是指具有公法性质的规范渗透到商法领域的法律现象。①邹海林:《中国商法的发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年版,第18页。
在研究“商法公法化”问题时,或者说研究商法规范的公法性与私法性问题时,必须要澄清的一个先见是,公法私法的划分最初是法律体系的划分问题,是宏观上的分类。从公法私法理论的历史发展来看,最初是针对“法律”、“国家法”这样的宏观概念,而不是针对法律规范这个微观概念设计的。它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将一国的法律体系划分为公法、私法二元对立的基本结构,以此在立法上宣扬不同的价值理念,完善不同的制度设计,在司法上建立不同的法院体系,发展不同的审判规则。
而我们现在讨论的商法规范的公法性与私法性的对立,则是一个微观问题,研究对象不是宏观的部门法,而是微观的法律规范。对于法律规范的研究,是分析实证法学的一大贡献。实证主义法学创始人约翰·奥斯丁的法律命令说被认为是一种初步建立起来的法律规范理论。一方面,这种理论非常接近常识观念,是普通人理解法律的重要模式;另一方面,后来许多法学家都在奥斯丁理论的影响和刺激下提出新的理论。①李旭东:《法律规范理论之重述—司法阐释的角度》,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7年,第71页。所以说,学者们经常提到的公法性规范、私法性规范,是将罗马法以来对于法律体系进行宏观分类的理论,与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兴起之后的法律规范理论相结合的一种分析方法。面对“商法公法化”的趋势,从法律规范的层面讨论公法性与私法性,比从法律体系层面讨论公法私法的二元对立要有意义的多,因为这种“公法化”的过程,是从微观的法律规范的层面开始的,而不是从整体上去否认商法的私法性。
对于微观的商法规范的公法性与私法性问题,要从宏观的公法与私法的区别标准谈起。美浓部达吉教授曾进行过学说概观:瑞士人荷灵加 (Hollinger)在其学位论文《公法与私法的区别标准》中举出十七种不同的学说;马尔堡 (Marburg)的私讲师华尔兹 (Walz)在就职演讲《关于公法的本质》中亦举出十二种不同的学说,即可知其复杂之一斑。②[日]美浓部达吉:《公法与私法》,黄冯明译,周旋勘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第23、24页。在如此之多的学说中,经过了时间的验证,在学说史仍具有解释力和影响力的不外乎四五种而已,即利益说、主体说、权利服从说、综合说。
根据利益说,判断一项法律关系或一条法律规范是属于公法还是属于私法,应以涉及到的是公共利益还是私人利益为准。隶属说认为,公法的根本特征在于调整隶属关系,而私法的根本特征则在于调整平等关系。根据主体说,如果某个公权载体正是以公权载体的身份参与法律关系,则存在公法关系。③[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 2001年 2版,第11、12页。而综合说,多为我国学者所采用,凡涉及公共权力、公共关系、公共利益和上下服从关系,管理关系、强制关系的法,即为公法;凡属个人利益、个人权利、自由选择、平权关系的法,即为私法。④张文显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 2007年第3版,第142页。以上各种学说,在区分公法、私法的问题上均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也存在一些缺陷,国外学者多以主体说作为通说,而国内学者更青睐于综合说。但是,从研究商法规范的公法性与私法性问题上,笔者认为利益说在各种学说中,是最具解释力的。
利益说虽然在宏观上区分公法与私法受到了不少的抨击,主要原因是公私两种利益在实际生活中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很难找到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公共利益是以私人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纯粹抽象的公共利益是不存在的;个人对私人利益的追求也有边界,只有不损害他人及社会公共利益时才受法律的保护。⑤孙国华,杨思斌:《公私法的划分与法的内在结构》,《法制与社会发展》2004年第4期。但在法律规范性质的层面,利益说并不应当受到这样的批评。诚然,现实生活中的利益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但是当一条法律规则被设计出来的时候,立法者并不会将各种利益交织在一起,而是有着明确的价值选择的,立法总是有“目的”的,这个目的的本质,就是某一种利益。
一部部门法中,往往会照顾到多方面利益,如民法、商法不会只顾及私人利益而放弃公共利益一样,所以在宏观上运用利益说,常常会有以偏概全之嫌,无法兼顾到每一条法律规范的利益追求。但针对法律规范这样的微观概念,利益说的解释力就大大增加了。“商法公法化”的动因,就是公共利益、国家利益不断地融入商法,利益的公共化、国家化是商法公法化的根本动力。如有的学者指出,“私法公法化”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在商事领域,即商事立法中越来越体现政府经济职权色彩和政府干预,调节个人与政府和社会间经济关系,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内容,这些内容体现了公法的明显属性。⑥赵中孚:《商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年第4版,第22页。因此,对于商法规范进行公法性和私法性的区分,主要看商法规范所要调整、保护的法益是商主体的个人利益、社会公共利益,还是国家经济利益,多种利益共生于商法体系内,是法律规范层面“商法公法化”的根本原因。
二、商法规范的强制性与任意性
从上文的论述中,我们看到了商法的私法性与公法性之间的对立是一个法益的问题,那么商法规范的强制性与任意性又当如何理解?法律所要保护的利益和法律保护该利益的方法,是“目的”和“手段”的关系。在“目的”层面上,因为保护利益的性质的差异区分为公法规范和私法规范,商法所要调整的利益,以商主体的私人利益为基础和主体,但是随着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涌入并与私人利益的不可剥离,使得商法规范呈现了私法性与公法性共生的状态;而在“手段”层面上,因为强制力的不同而区分为强制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商法也会在不同的场合下,分别运用到这两类规范。但是“目的”和“手段”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同样的“目的”可以用不同的手段来实现,同样的“手段”可以实现不同的目的。
对于强制性与任意性的分野,考夫曼指出,法律规范尚可依其效力强度而区分为:强行法律规范;不能依约定而变更 (例如刑法或民法第138条);任意法律规范 (惟有当事人无相反之约定时,才适用此种规范,例如契约法、夫妻财产制)。①[德]考夫曼:《法律哲学》,刘幸义等译,法律出版社 2004年版,第155页。我国法理学界则认为,按照权利、义务的刚性程度,可以把法律规则区分为强行性规则和任意性规则。强行性规则又叫强制性规则,指所规定的权利、义务具有绝对肯定形式,不允许以当事人合意或单方意志予以变更的法律规则。此种规则与命令式规则、禁止式规则关联度相对较高。任意性规则是指所规定的权利、义务具有相对肯定形式,允许以当事人合意或单方意志予以变更的法律规则。权利规则一般都属于任意性规则。②张文显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 2007年第3版,第119、120页。
对于法理学提出的这样一组法律规范分类,私法学者往往比公法学者要重视的多。德国民法学这样表述:这些规定要么是强制性的,这里所说的强制性是指这些规定不可以被法律关系当事人现有的或计划中的协议所排除或修改;要么是任意性的,在这种情况下,只在当事人没有一致同意排除其适用或以其他规定取而代之的情况下,它们才适用于法律关系。③[德]迪特尔·施瓦布:《民法导论》,郑冲译,法律出版社 2006年版,第37、38页。史尚宽先生认为,强行法,指不问当事人意思如何,必须适用之规定,与任意法相对。公法多为强行法,民法总则、物权法、亲属法及继承法,多为强行法,反之,债权法则多为任意法。强行法又可分为强制规定与禁止规定。强制规定是指法律命令为一定行为的规定;禁止规定则指法律命令不为一定行为的规定。
商法规范作为特别私法,秉承作为一般私法的民法的基本认识,更接受作为法学基础的法理学在基本范畴上的界定。商法规范的强制性与任意性,如同上述法理学者和民法学者的认识一样,划分标准就是法律关系的当事人(此处为商主体)可否依据协议方式或者单方行为对商法规范进行排除和变更。商法的强制性规范,是在商事活动中,商主体不得以协议的方式或者单方行为进行变更的商法规范,而商法的任意性规范,是在商事活动中,商主体可以以协议的方式或者单方行为进行变更的商法规范。所谓的强制性,也可以从反面进行阐释,就是有没有给商主体留有自由的空间,它关注的是一个法律调整手段的问题,而不是所要调整的法益本身。我们认为,法益的性质,法益的重要程度及大小会影响调整手段的选择,而且是影响法律调整手段选择的主要因素,这也就是为什么公法规范往往采用强制性的手段,而私法规范更适合于任意性的调整手段。但是,法益本身并不等同于调整手段,“私法自治”、“公法强制”只是一个较为笼统的概括,不应当简单地等同,更准确的认识是,私法多为自治,公法多为强制。诚如史尚宽先生所言,在传统民法中,也是债法多为任意法,而民法总则、物权法、亲属法及继承法多为强行法。我们也不能说,民法中的这些强制性规范都是公法性的,因为它们保护的还是私人利益,是私法性的。作为调整更为复杂,技术性要求更高的商事法律关系的商法,其强制性规范一部分是保护公共利益、国家利益,是公法性的,但是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保护商主体个人利益,是私法性的。
三、公法性的商法强制与私法性的商法强制
上文从法理学的视角,区分了法律规范的公法性与私法性,强制性与任意性。就商法规范历史发展来看,既具有“目的”上的发展,也有“手段”上的演进,我们往往只看到在整体上商法规范发展到如今的面貌,却忽视了它在“目的”和“手段”两条线上,是如何分别发展演进抑或是嬗变转型的。就商法的强制性规范而言,既有私法属性的强制,也有公法属性的强制,这是两条不同的发展路向。
首先,私法性质的商法强制性规范是传统的、固有的、与生俱来的。从法律目的上看,这一类的强制性规范完全为了维护商主体的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国家利益无涉。具体来说,一是用建构的方式促进交易的便捷,二是用调整的方式保障交易的安全。
商法的强制性规范,强制功能之一就是通过法律规范的刚性,建立起一套法律规则,并且是先有规则,后有行为。票据法律规范作为一种传统商法,很好地解释了这一点。票据行为不仅必须以书面形式作成,而且必须按票据法规定的格式作成。即每一种票据行为应该记载票据法规定的法定的事项,并且其记载的文句、顺序、位置等都是固定的,不允许行为人任意取舍或变更。①董安生:《票据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年第3版,第58页。正是由于票据法律规范在方式和格式上的强制性,才建立起了具有汇兑功能、支付功能、信用功能和流通功能的票据制度。对于商主体来说,就是在商事活动的支付环节中,有更为便捷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商法规范的强制性就如同格式合同所起到的作用一样,主要是通过建构一套规则,减少磋商成本,从而提高交易活动的速率。这类规范不仅具有强制性,而且具有构成性,被法理学者称之为“构成性规范”。如果它失去了强制性的特点,其构成性也就随之分崩离析了。正是由于这类规范建构性的特点,使得它的“刚性”更强,往往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例如《票据法》第22条规定“汇票必须记载下列事项……汇票上未记载前款规定事项之一的,票据无效。”
私法性的强制性规范除了用构成的方式降低协商成本,促进交易便捷之外,还在于用调整的方式保障交易安全。商法规范的外观主义即是如此。所谓外观主义原则,是指立法上采取一系列强制性的规定,使交易的当事人确认相对人的主体资格的合法性和交易内容的确定性,以维护商事交易的安全。商事立法确立外观主义原则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交易安全。②陈本寒:《商法新论》,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第51页、第55页。外观主义原则在商法领域运用的很广泛,以表见代理为例,它是指无权代理人,具有代理权存在的外观,足令使相对人相信其有代理权时,法律规定本人应负授权责任的制度。③王泽鉴:《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第467页。表见代理与狭义的无权代理构成广义的无权代理,区别在于表见代理是有效的法律行为而狭义无权代理是效力待定的法律行为。《日本商法典》第504条规定:“商行为的代理人虽未表明为本人所为,其行为也对本人发生效力。”我国《合同法》第49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作为一部民商合一的立法例,我国合同法关于表见代理的规定在运用中,更应当适用于商事合同。有学者指出,在解释我国《合同法》第49条关于合同代理中的表见代理行为时,不区分民事合同代理与商事合同代理在效力方面的差异,随意扩大表见代理制度的适用范围,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④陈本寒:《商法新论》,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第51页、第55页。
可见,无论是出于增进交易便捷的目的,还是保障交易安全的目的,其初衷都是立足于商人自身利益的,是为了使商人在一个高效、安全的商业环境下实现利润。所以,商法中的部分强制是商人自律的一个结果,无关乎所谓的公共利益、国家利益。这一类私法属性的强制性规范常常在商事习惯法阶段,甚至更早的时期就已经形成了,它最初并不是依靠国家的强制力而推动建立起来的,而是一种私人之间的强制,商人之间的强制。它秉承了传统商法固有的价值理念。它们并不是“商法公法化”的产物,我们只能说它是强制性的,但是不能说它是公法化的。
其次,如果说私法性的强制性规范是传统的、固有的、是与生俱来的,那么公法性质的强制性规范则是现代的、派生的,随着新法益的产生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公法性质的强制性规范与私法性质的强制性规范促进交易效率、保护交易安全有所不同,它更多的是考虑独立于私主体的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正如罗伊·古德教授描述的那样:
“这一类法规最早用来保护公共健康和禁止,例如,销售腐烂的食物和掺假的啤酒。后来一个阶段,立法补充了普通法规则,以确保在公平的价格下,市场上有充足的货物供应。因此,它主要致力于打击囤积居奇 (以牟取暴利为目的购买大宗货物)、抢先垄断市场 (在货物运达市场之前购买或者诱使预期的出售者不将货物运达市场),转售囤积商品 (购买货物并在相同或邻近市场出售)或者其他形式的价格操纵。……在现代形式的市场管制中,最为广泛和复杂的是金融服务立法中的管制,以及证券和投资委员会和自我监管组织制定的规则中监管。”⑤Roy Goode,CommercialLaw in the NextMillennium,Sw5et&Maxwell,London,1998,p.44.
公法性质的强制性规范盛行起来,是因为除了微观上的个别的商事交易以外,一个更为宏观的概念成为商法规范必须面对的问题,那就是——市场。市场自古有之,但现代社会的市场与传统意义的市场有着极大的差别。首先,传统市场是最狭义的市场,是指商品交换的场所和领域,即买主和卖主发生买卖关系的地点或区域,因此传统市场主要是对个人具有意义,是为个人提供交易机会的。而现代市场是产品交换关系的总和,是不同商品生产者之间经济关系的体现。它反映社会生产和社会需求之间、商品供给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之间、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买者和卖者之间以及国民经济各部门和社会各种组织之间的经济关系。①赵林如主编:《市场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9年版,第276页。因此,现代市场对于社会公众利益,国家利益的影响,更为突出。在现代社会,无论是货物市场还是金融市场,出现危机的时候,利益受损的是谁?作为私法主体的市场参与者当然是利益受损者。但是,如果更为细致地分析,如同公司是属于个人一样,市场是属于社会的、国家的,公司破产的受害者是投资者,而市场的危机虽然会使作为参与者的私人利益受损,但最大的受害者,是国家与社会。换言之,市场成为社会、国家利益的载体,其危机与安定,颓废与繁荣都是社会和国家利益消长的体现。其次,现代市场看似庞大、精致、复杂,但复杂的事物未必是安全的。诚如罗伊·古德所言,银行为什么是监管最为严密的,并不是简单的因为它接受来自于公众的存款,而是因为他们日复一日的与其他银行发生大量的业务往来,在一个多边的网络体系中,一个主要银行因为债务而破产将给其他的参与者产生巨大的困难,并且引发广泛的信任危机。②Roy Goode,CommercialLaw in the NextMillennium,Sweet&Maxwell,London,1998,p.46.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市场如此,一般的货物市场、劳动力市场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这些问题。
现代市场的以上特点,使得商法所要保护的法益不再是单纯的私人利益,而必须兼顾到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所以,有学者提出商法的社会化趋势,认为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上升到垄断阶段,诸多经济关系亦更为复杂,反映在理论上则出现了社会利益优位的思想,如民法中即出现了对私权神圣、契约自由等原则的限制,而商法在这种理论趋势下也必然要向法律社会化方向发展,即商法在重视保护商人的个体利益时要以不损害社会利益为前提。③任先行、周林彬:《比较商法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第195页。除了保护社会利益不受损害之外,国家利益的思想也不断地渗透进商法理念中来,这主要关涉一个国家经济安全的问题,这种经济安全往往与一些特殊的市场与行业联系在一起,表现为市场安全、行业安全。我国商法立法中将行业监管立法与单纯的商行为法进行混合立法就是很好的例证,如保险业法与保险合同法构成保险法、证券监管法与证券交易法构成证券法。
随着商法的价值观不断融入社会利益、国家利益的理念,商法在法律规范层面也就有了新发展,为维护社会利益、国家利益而设计出的商法规范,都是强制性规范,而且是公法性质的强制性规范。例如,现代商法中的商事登记制度,虽然有着成立要件主义和对抗要件主义的区别,但从属性上讲都是强制性规范,成立要件主义下非经登记不得成立,是强制性的;对抗要件主义下,非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实质也是强制性的。由于对抗要件主义容易引起法律关系的不稳定并导致法律关系更趋复杂,所以多数国家采用成立要件主义。④史天涛:《公司法论》,法律出版社 2006年第2版,第90页。其实除此之外,将登记作为成立要件的强制性,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国家可以通过强制登记制度,了解相关的市场信息,如企业的组织形式、所有制形式、行业分布状况等等,这些市场信息与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和产业发展政策是直接相关的,是关涉国家经济利益的。再如,保险法中都有关于保险资金的运用必须遵循稳健、安全的原则,其运用形式无外乎银行存款、买卖有价证券及投资不动产等方式。这种对于资金运用方面的强制性规范,所要实现的价值理念,是保证具有社会性的广大投保人的安全与国家保险行业的安全。所有这些以保护社会利益和国家经济利益为目的的强制性规范,构成了商法体系中公法属性的强制性规范,与私法属性的强制性规范在发生发展,价值理念上都有根本的区别。
四、结论
从调整利益的角度看,商法规范有着公法性与私法性的区别;从调整手段来看,商法规范有强制性与任意性的区别。“商法公法化”运动,使得商法规范中公法性的强制性规范大大增加,但商法中还是存在很多固有的私法属性的强制性规范。两者的功能是不同的,一部分私法性的强制性规范重在通过构成性的方式将商事主体和商事行为的某些制度定型化,增进交易便捷,这类规范具有稳定性,不会随意的废弃变更;另一部分私法性的强制性规范通过调整性的方式保障交易安全,它们会根据情况对商事法律关系的不同要素进行强制,稳定性不及具有构成功能的强制性规范。公法性的强制性规范才是“商法公法化”产物,这类规范重在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经济利益。公法性的强制性规范往往具有一定的政策性,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立法者对市场认识的不同,这类规范也会表现出变动性。不过,随着此次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重创,立法者对经济自由主义的反思极有可能导致公法性商法强制性规范的再次高涨。
(责任编辑:亦木)
D913.99
A
1003—4145[2010]06—0080—05
2010-02-03
张 强,男,复旦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得到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经费资助(项目编号:B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