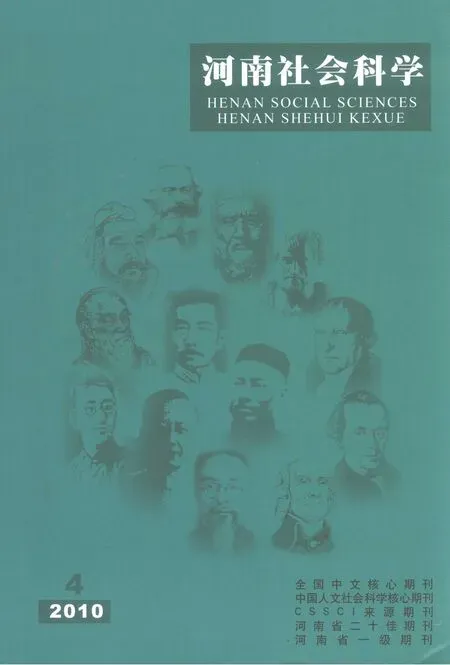招隐与遁世——“七”体和“设论”交映下的东汉文人心态
王允亮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枚乘创立的“七”体文和东方朔创立的“设论”文,是对后世影响比较大的两种文体。这两类文体不仅在形式上有鲜明的相对性,一为客人说服主人,一为主人折服客人,在思想主旨上也是如此。尤其是思想上的针锋相对,折射出东汉文人自豪和自怨兼有的矛盾心态,当这种心态集中到同一个人身上时,更显得突兀和令人瞩目。这种心态因何产生?它对于这两类文体的创作又起到了怎样的影响?这是本文所要加以探讨的。
一、汉代“七”体的创立及流变
汉代枚乘《七发》出现后,学习这一文体的代不乏人,南朝·梁卞景把这一类型的文章荟萃成《七林》一书十卷,《隋书经籍志》总集类也有《七林》三十卷。足见这类文体创作之多,影响之大。现存《文选》各本中把这一文体命名为“七”体,并选录枚乘《七发》、曹植《七启》、张协《七命》这三篇文章作为代表。在纷纭壮观的“七”体创作历史中,汉代是“七”体文创立和定型的阶段。“七”体文在汉代的流变,可以看出汉代文人意识形态上的变化。
对于汉代“七”体的创作情况,西晋傅玄的《七谟序》中曾有概括:
枚乘《七发》是“七”体的开创之作,同时也奠定了汉大赋的基础,其文载楚太子有疾,吴客拜问,以音乐、饮食、骑乘、游观、田猎、观涛六事启发太子,太子均加以推辞,最后客以要言妙道之美打动太子。在这篇赋中,作者采用的是欲扬先抑的手法,首先把要否定的感官享受之美极力进行渲染,最后才托出自己要肯定的圣言妙理,通过主人反应的对比来显出它地位的特殊。
就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作品来说,和傅玄在《七谟序》中所描述的相同,枚乘的《七发》出现后,在西汉并没有得到很大的响应。到东汉时期,这一题材的创作才蔚为大观,作者蜂起。在这一创作风气的盛行下,“七”体文章也在发生着变化。这一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章形式和题材方面,另一个则是文章思想主旨方面。
就形式上来说,《七发》里吴客和楚太子一问一答,贯穿全篇,稍显单调,到东汉张衡的《七辨》中,所发的七事分别由虚然子、雕华子、安存子、阙丘子、空桐子、依乔子、无子七个不同的人提出,虽然文章大体的结构并没有变化,但文中人物纷纷发言,却宛如一个小型的讨论会,明显比一主一客的问答显得活泼而富有新意。在文章题材方面,东汉的“七”体所写虽仍限定于七事,但描摹的对象,却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与枚乘首创时已渐有不同。如张衡的《七辨》就借依乔子之口,叙述求仙,这是《七发》里完全没有出现过的,借阙丘子之口描摹女色,这也是《七发》中着力不多的地方。
在文章主旨方面,东汉的“七”体创作完全不同于枚乘的《七发》,在《七发》中被拿来赞颂的要言妙道,到东汉的“七”体中,隐然被分为两个阵营,一个是主张归隐避世的老庄思想,另一个则是主张积极用世的儒家思想。而最后的结果,则往往是持儒家思想的客人占据上风,折服了信奉老庄哲学的主人。这一关键转变应该是从傅毅开始的,他在《七激》开篇就说徒华公子“托病幽处,游心于玄妙,清思乎黄老”,这显然是一个持有黄老避世思想的人物,这个时候客人玄通子出场来对他进行游说,通过妙音、滋味、骏马、游猎、游观几个方面来诱发他,但徒华公子均不为所动。这一点和《七发》的套路一样,但最后令玄通子取得胜利的却是儒家思想:“汉之盛世,存乎永平,太和协畅,万机穆清,于是群俊学士,云集辟雍,文质发。”最后引得公子瞿然而兴曰:“至乎!主得圣道,天基允臧。明哲用思,君子所常。自知沉溺,久蔽不悟。请诵斯语,仰子法度。”[1]可以看出,文章的最后是客人玄通子用东汉统治的兴盛打动了志在隐居的徒华公子,使他怦然心动,允诺出仕。
自傅毅的《七激》在思想主旨上定下这个基调以后,后此的文人多祖述此论。如张衡《七辨》写无为先生祖“述列仙,背世绝俗,唯诵道篇,形虚年衰,志犹不迁”,显然又为一老庄哲学的代表人物,这个时候虚然子述宫室,雕华子列滋味,安存子论音乐,阙丘子引女色,空桐子讲舆服,依乔子讲求仙,等纷纷出场,无为先生均不为所动,直到最后无子说:“在我圣皇,躬劳至思,参天两地,匪怠厥司,率由旧章,遵彼前谋,正邪理谬,靡有所疑,旁窥八索,仰镜三坟,讲礼习乐,仪则彬彬。”[1]这一番对东汉盛世气象的描述,引得无为先生慨然允诺入世用事。
东汉“七”体文主旨上宣扬王化,贬低避世隐居这一变化影响是比较深远的,不仅当时作者纷纷沿袭这一套路,此后的曹植《七启》、和张协《七命》以及到南北朝的大多数“七”体作者,也基本上遵循这一基调,借“七”体文为各自生活的王朝歌功颂德。可以说“七”体文至东汉时,已经出现了一个鲜明的招隐倾向,而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汉代“设论”的创立及流变
汉代自东方朔《答客难》出,这一文体的模仿之作也巍然成风,在《文选》中,这类文被归入“设论”一类。两汉创作“设论”文的作家继踵迭出,《文心雕龙》卷三《杂文》篇说:
自对问以后,东方朔效而广之,名为《客难》。托古慰志,疏而有辩。扬雄《解嘲》,杂以谐谑,回环自释,颇亦为工。班固《宾戏》,含懿采之华;崔《达旨》,吐典言之裁;张衡《应间》,密而兼雅;崔《客讥》,整而微质;蔡邕《释诲》,体奥而文炳;景纯《客傲》,情见而采蔚。虽迭相祖述,然属篇之高者也。[2]
这里所举的作家除了郭璞之外,全是两汉的文人,足见两汉时这一文体创作的兴盛。在这些人中,比较突出的有西汉的东方朔、扬雄和东汉的班固。
东方朔生活的年代,是汉代大一统的时代,这个时期战国时的游说之风尚有影响,但已经没有了生存的土壤。在他的《答客难》一文中清楚地反映了这个现实:“今则不然。圣帝德流,天下震,诸侯宾服,连四海之外以为带,安于覆盂。天下平均,合为一家,动发举事,犹运之掌。贤与不肖,何以异哉?”[3]而生活在这个新的时代,士人想要出人头地更加困难。《汉书》卷一四《诸侯王表》曰:“武有淮南衡山之谋,作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诸侯惟得衣食租税,不预政事。”服虔曰:“仕于诸侯为左官,绝不得仕于王侯也。”应劭曰:“人道上右,今舍天子而仕诸侯,故谓之左官。”师古曰:“附益者,盖取孔子云‘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之意也。皆背正法而厚于私家也。”[3]可见汉武帝时期,随着对诸侯王势力的打击,士人的生存空间也被大大压缩,这对于抱有游士之梦的汉代士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答客难》则是这种情况的集中体现。
到西汉末,扬雄又继《答客难》而作《解嘲》。《汉书》卷八七《扬雄传》载他“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3],由此可见,扬雄和东方朔不同,他本来就是一个胸怀淡泊的人。然而扬雄在《解嘲》中仍然表达了时移世易的现实:“当今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眉;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3]但在其中也分明有着全身远祸的思想。这种全身远祸心态和西汉末政治混乱的现实有很大的关系,文中虽然也有怀才不遇的牢骚,但主要表达的则是很有道家气息的知玄守默思想,《答客难》中的不平之气已经大大减弱。
东汉时班固作《答宾戏》则是“感东方朔扬雄自喻,以不遭苏、张、范、蔡之时,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复应焉”[1],他通过对东方朔和扬雄文中作为成功者典型的苏、张、范、蔡的批判,表明了推崇儒学的宗旨,“是以仲尼抗浮云之志,孟轲养浩然之气,彼岂乐为迂阔哉?道不可以贰也”,“慎所志,守尔天符,委命供己,味道之腴,神之听之,名其舍诸”[1]。这里所提倡的道主要是儒生遵守的道义,作为一个服膺儒学的人,班固对于东方朔和扬雄文中的异端色彩很是不满,虽然同样胸怀抑郁,但他采取的是崇信儒学、乐天安命的态度。
班固对“设论”文创作倾向的扭转,也对后世产生了影响。后此的东汉作家,在设论文中,大多以儒术作为安身立命之本,表达安贫乐道的思想。张衡《应间》中说自己去史官五载而复还,客以为非进取之势也。最后作者反驳客人的嘲讽,表达自己志向时也只是说:“姑亦奉顺敦笃,守以忠信,得之不休,不获不吝。不见是而不,居下位而不忧,允上德之常服焉。方将师天老而友地典,与之乎高睨而大谈。”[“4]奉顺敦笃,守以忠信”一语显示出儒家安贫守约的风范。崔在《达旨》中说自己“惧吾躬之秽德,勤百亩之不耘。絷余马以安行,俟性命之所存”[4],“惧吾躬之秽德”一语显示出儒家强调个人品德的特点。
随着时代的发展,东汉的设论文中也融合进老庄无为任真色彩。崔在《达旨》中说自己“独师友道德,合符曩真,抱景特立,与士不群”[4]。崔《答讥》中表明自己的处世思想为:“若夫守恬履静,澹而无求,沉昏睿壑,栖息高丘,虽无炎炎之乐,亦无灼灼之忧,余窃嘉兹,庶遵厥猷。”[1]毫无疑问,这些语言都具有鲜明的老庄特色。
可见设论文在东汉时期的流变中,日益朝遁世守志这一倾向发展。自从班固确定以儒家思想为指导,贬低纵横游说,提出新的处世方式之后,这一主旨便被继承下来,随着时代的变化,老庄的抱素守约思想与儒家的安贫乐道思想在这个系列里得以合流,使它成为士人自我隐遁的宣言之一。
三、“七”体和“设论”折射出的东汉文人心态
东汉“七”体和“设论”两类文体的创作都非常兴盛,各自有庞大的创作队伍,而两类作品的思想倾向则一个宣扬积极用世,一个主张遁世无闷,成针锋相对的两大潮流。它们鲜明地体现了部分东汉士人思想的双重性和矛盾性。最为具体的体现就是,有些东汉文人在“七”体和“设论”这两种文体上都有创作,比如崔既有《达旨》又有《七依》,张衡既有《应间》又有《七辨》,这个时候,士人思想的两面性便一下子集中到同一个人身上。以张衡为例,他在《七辨》中所持的是替汉家鼓吹的“招隐”思想,而在《应间》一文中却说出“方将师天老而友地典,与之乎高睨而大谈”这样的话,这里面体现的摆落尘世,潇洒任真的思想,和《七辨》所持的积极用世思想,又何其方枘圆凿格格不入?其实,张衡思想上的矛盾性,恰代表了东汉士人思想上的一个普遍现象,他体现出的是东汉这个大帝国下失意群体的共同思想状况。
(一)大帝国下失意群体的矛盾心态
然而,汉代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这一点他们自己也认识的很清楚,且看另一经历坎坷之士王充所言:
周时仅治五千里内,汉氏廓土,收荒服之外。牛马珍于白雉,近属不若远物。古之戎狄,今为中国;古之裸人,今被朝服;古之露首,今冠章甫;古之跣跗,今履高舄。[5]
在这种情况下,汉代文人思想上的矛盾性便开始显现:一方面自身仕途坎坷,自伤不遇;另一方面则又欣喜得逢盛世,深感自豪,这一矛盾思想奇妙的统一在这个群体身上。比较典型的代表人物则为王充。他一生屈居下僚,位不过州郡,观他《论衡》中的一些言论颇可以见出他的落落寡欢之情:“故夫临事知愚,操行清浊,性与才也;仕宦贵贱,治产贫富,命与时也。命则不可勉,时则不可力,知者归之于天,故坦荡恬忽。”[5]他在《论衡》开篇即对命逯、逢遇等问题进行讨论,可见他由于怀才不遇,也抱有很大的愤懑。然而即使如此,他对于自己所处的时代仍是大加赞扬,并创作《恢国》、《宣汉》等篇替汉室鼓吹。
可见,东汉士人间存在着一种自豪和自怜兼有的双重心态。一方面他们为自己生活的时代而自豪,觉得有义务要对它进行鼓吹;另一面,他们也不得不面对自己在这个伟大时代下失意的尴尬现实,努力消解自己心中的愤懑和不平。
(二)东汉文人对“七”体和“设论”的创作观念
在了解了汉人这种矛盾心态后,我们可以从“文体”创作的角度,对这两类文体思想背道而驰却同时兴盛的现象加以探讨。
东汉文人对于“七”体创作的热情是空前高涨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这一文体弹性极大的包容性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原因。主客问对的七段文字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可以自由挥洒,这为作者创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才情调整所要铺排的内容,就个人最擅长的方面进行描摹,只要保持“七”体结构的完整即可。以此为基础,“七”体的创作便成为文人炫耀才学的一种手段,故而作者非常热衷于这类题材的创作,这就使得“七”体的创作成为一种比较公开的文学活动。这一点和夸饰宫殿游猎的大赋是相通的,大赋的创作观念也由此得以进入“七”体的创作。以大赋润色鸿业是东汉人的普遍观念,这一点在班固的《两都赋序》中表现得最为典型。在和班固同期的傅毅《七激》中,大赋润色鸿业的创作观念已经被纳入“七”体的创作范畴,“七”体的创作主旨也从《七发》贬低物质享乐,抬高精神妙理转变为贬低老庄隐士思想,颂扬儒家入世态度。而且从这个时期开始,“七”体创作中招隐的主题也被确定下来,并为后世的作者所承袭。
反观“设论”文的创作,则多为抒发幽愤,表明独善其身的态度,偶尔兼以老庄思想自慰,这一点与汉代文人骚体赋中所述多同,可以说“设论”文承担了部分骚体赋的功能。如果以两类文章来进行类比的话,那么“七”体的创作主要体现的是兼济天下的思想,而“设论”更多的体现出的是独善其身的观念。然而,我们必须注意的是东汉文人思想中儒家思想影响的深远,即使在他们对现实不满时,也处处能体现出儒家思想的气息。
东汉是一个儒学极盛的时期。国力的强盛,声威的煊赫,加之以儒学的影响,使得东汉失意文人群体在思想上具有极大的矛盾性:一方面,出于儒家的积极用世态度,他们不自觉地为自己生活的伟大时代歌颂鼓吹;另一方面他们面临的不堪处境,也使得他们不能不悲怨愤慨,并勉力以儒家的乐天安命思想进行自我疏解。儒学的兴盛,进而影响到了当时的“七”体和“设论”的创作,无论是“七”体从推崇要言妙道向宣扬王化的招隐倾向转变,还是“设论”从渴盼纵横复归的用世之志向乐天安命的遁世态度转化,其间都少不了儒学的影响。当然就这两类文体来说,“七”体文更多的表现的是一种诉诸公众的态度,而“设论”文则显示出更多的个人感悟。因此同“七”体文创作中略显呆板的宏观表述相比,“设论”文则由于作者个人主体意识的渗透,显得更为灵动活泼。在这一创作现象兴盛的背后,东汉强盛的国势和儒家思想的兴盛是最为显著的成因,无论是主张招隐的“七”体文,还是主张避世的“设论”文,都显示出这两种因素的巨大影响,这是由东汉这个特殊的时代所决定的。
[1]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
[2]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5]黄晖.论衡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