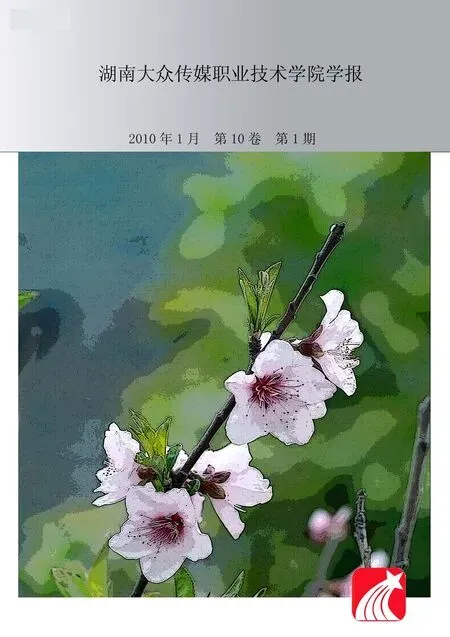陶渊明的生活状况与《桃花源记》
蔡建满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主持与播音系,湖南 长沙 410100)
一
对于《桃花源记》的写作缘由及内容的真实性,历来有各种不同的猜测:唐代有人认为陶渊明乃因受道教的影响,向往仙境而作斯篇。如王维《桃花行》就写到:“初因避地去人间,更闻成仙遂不还。”又说“当时只记入山深,清溪几度到云林;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刘禹锡《桃源行》也说:“桃花满溪水似镜,尘心如垢洗不去,仙家一去无踪迹,至今水流山重重。”但宋代苏轼明确反对神仙之说。“世传桃源事,多过其实。考渊明所记,止言先世避秦来此,则渔人所见,似是其子孙,非秦人不死者也。又云杀鸡做食,岂有仙而杀者乎?”他说到蜀青城山老人村,“道极险远”,认为桃源可能类似这种地方,世人不易找寻。“使武陵太守得而至焉,则已化为争夺之场久矣。”他在《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诗中说到桃花源:“桃花流水在人世,武陵岂必皆神仙。江山青云空尘土,虽有去路寻无缘”。他认为人世间会有桃花源的,不过桃源之路是无缘找到罢了。王安石也写过一首《桃源行》,他也认为桃源中人是避秦人后代。诗中说:“避时不独商山翁,亦有桃源种桃者。此来种桃经几春,采花食实枝为薪。儿孙生长与世隔,虽有父子无君臣。”
由苏轼、王安石所讲桃源人避秦之说,有人又附会为陶潜耻事二姓,如洪迈说:“予窃意桃源之事,以避秦为言,至云‘无论魏晋’乃寓意于刘裕,托之于秦,借以为喻耳。近时胡宏仲仁一诗,曲折有奇味,大略云:‘靖节先生绝世人,奈何记伪不存真,先生高步窘末代,雅志不肯为秦民。故作斯文写幽意,要似寰海离风尘。’其说得之矣。”将避秦说附会为影射刘裕。后来如清人孙人龙也说:“此乃寓意于刘裕,将托之秦以为喻。”清人翁同龢也说:“义熙十四年,刘裕弑安帝,立恭帝;逾年晋宝遂亡,史称义熙。潜征著作郎,不就。桃源避秦之志,其在斯时欤?”[1]近代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认为这是一篇“记实文字”,是陶渊明描述前代遗留下来的本族风光。他在《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一文中曾详细论证陶潜家世及陶侃的族属问题,考证出陶侃少时迁徙家的庐江郡原是溪族杂居之地,溪人多在水网地带,以捕鱼为业。陈先生又进一步考证出溪人原是《后汉书南蛮传》中的武陵蛮,此族以溪为名,与五溪之地有关,以捕鱼为业。[1]
以上对《桃花源记》的各种猜测都因证据不足而难以令人信服。笔者认为,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得把陶渊明还原为一位诗人来对待,把《桃花源记》还原为一篇文学作品来解读,舍此别无它法。正如中华书局《陶渊明资料汇编》中《历代陶渊明研究概况》一文所说的那样:陶渊明不是哲学家而是诗人,他的诗作不是哲学讲义,而是活生生的现实生活,经过诗人的选择、概括、构思,最后加以艺术的表现。[2]
二
笔者认为,《桃花源记》是陶渊明南村隐居生活的真实写照,是他以往田园诗的高度概括和归隐经历的诗意升华。根据李锦全先生的《陶潜年表》记载,陶渊明的隐居生活经历大致如下:义熙二年(公元406年),陶渊明42岁,年初自上京里移居田园居(古田舍);义熙七年,陶潜移居南村;义熙十年,陶潜还居上京旧宅;义熙十四年,陶潜作《桃花源记》,元嘉四年(427年)陶潜辞世,享年63岁。总计隐居时间约23年,其中在南村隐居的时间约为5年。[1]陶潜所隐居的这些地方大约都相距不远,因此本文为行文方便,把他的隐居之地统称为“南村”,把他的隐居生活统称为“南村生活”。 陶渊明46岁时由园田居移居到南村。对于南村,他特别喜爱,他有一首诗具体地叙说了南村情况: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敝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二首》)原来这里不仅多“素心人”——指心地纯洁的人,而且这些人大都有文化,不同于那些“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的农民,他们可以“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据此不妨可以进一步推测,这些人也多半和陶潜一样是隐士而不是地主或寻常的农民,因为他们平日“农务各自归”,是参加劳动的农民,只是在闲暇时才披上衣服聚到一起“言笑无厌时”。陶渊明与他们情谊深厚,经常“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总之,陶渊明在南村的生活过得十分舒畅。细看《桃花源记》,其主要情节都可以从陶渊明的其他诗中找到影子,试举例如下:
(一)“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试看他的《归园田居五首》其一:“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这首诗写于义熙二年(406年)陶渊明42岁,这是他写的《归园田居五首》中的第一首。可能是初住不久,满怀新奇、兴奋之感,对屋舍描写得非常具体:“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从屋前遥望远方,则看到“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此外还可以听到“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这副白描的乡村图画正是后来桃花源的雏形。
(二)“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试读《和郭主簿二首》(其一):“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凯风因时来,回飙开我襟。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这首诗写到他自己的文化生活和家庭生活,姑且不论其文化生活。家庭生活方面他写到自己在家悠闲地饮酒,小孩在他身边嬉戏,呀呀学语,大人小孩,各得其乐。这一图景与“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何其神似!再看《引酒二十首》(第十四):“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班荆坐松下,数斟复已醉。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你看:老朋友带着酒壶来相会,他们坐在松树底下,饮到有点醉意时,甚至胡言乱语,酌酒也不论什么行辈了,多么生动的一副老翁行乐图!其它如“命室携童弱,良日登远游”(《酬刘柴桑》),“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归去来兮辞》),陶渊明所描绘的南村幸福生活比起桃花源中的“黄发垂髫”的怡然乐趣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三)“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这种情形在陶渊明的田园诗中可谓比比皆是。如前引《移居二首》中的“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此外尚有“提壶接宾侣,引满更献酌”(《游斜川》);“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得欢当做乐,斗酒聚比邻”(《杂诗十二首》其一)。最为典型的要数《归园田居五首》其五了:“怅恨独策还,崎岖历榛曲。山涧清且浅,可以漉我足。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耕种归来,刚洗过脚,就端上新酿成的酒和一盆鸡招待客人为长夜之饮,主人热情好客的神态宛然如在目前。以上解析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历史真相:陶渊明坚决从上层社会的政治风云中隐退出来以后,把精神的安慰寄托在农村的躬耕、饮酒、作诗上,他的田园诗都是归隐田园生活体验的反映,他的《桃花源记》则是这种生活体验的总结和升华。
三
李锦全先生所著《陶潜评传》中有一句耐人寻味的话:“陶潜这个人有点怕远行,一旦奉有差事外出,就想到回归田园。”[1]李先生举他的《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为例进行说明,诗的最后陶渊明写到:“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田园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终怀在归舟,谅哉宜霜柏。”他坦言承担官差总觉得有点拘束,而自己生平的志向又不可移易,这种矛盾心态使他又梦想回到田园生活,就像严霜下的柏树能够坚持志节。像这样的诗句在陶诗中并不鲜见。如“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饮酒二十首》)。陶渊明之所以心念园田,据他自己的解释是“少小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这里至少应当包含两个条件,一是他在家乡有“园田”,二是他的家乡应该比较平和。如果那里连年征战不休,人命如草,陶渊明是没法“爱丘山”的。陶渊明家乡在江州寻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据逯钦立先生考证,江州地处荆州、扬州要冲,一直是封建军阀必争之地。在频繁的战争骚乱中,这一地区扫遭受的苦难比其它地方更为深重。史称:“自桓玄以来,骄蹙残败。至乃男不被养,女无匹对。”“州郡边江,百姓寥落,而役调送迎,不得止息。”(《晋书刘毅传》)。令人奇怪的是,陶诗中极少反映这方面的内容。尽管他的后期诗中不乏啼饥号寒之音,如“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乞食》);“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饮酒二十首》)。但陶渊明诗又曾经明确地告诉人们,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是天灾而不是战火。
据此可以推测,尽管陶渊明生逢乱世,但他所处的南村由于偏僻的地理位置和古代落后的交通条件,曾经有过相当长一段时间难得的和平与安宁。联系前面苏轼所说的蜀青城山老人村事例,这种推测当不为妄言。另据史载,宋元嘉元年(424年),陶渊明的好友颜延之出为始安太守,路过浔阳,送钱二万给陶渊明,陶渊明将这笔钱全部交给酒家,零碎向酒家取酒。这件事至少向我们透露了一点信息:这里曾经有过一段较长时间和平安定时期,且人民比较富裕。否则,陶渊明是不会如此放心地把钱放在酒家的。
再说他在家乡有无“园田”的问题。逯钦立先生曾认为陶渊明是一个“田园迷”,批评他出仕当官时对园田别业迷恋不已,辞官归隐时对园田别业更是喜爱备致,学术界多不同意逯先生这种在特殊时代背景下提出的观点。笔者认为陶渊明虽不一定是大地主,但他身为陶侃后人,又曾当过多年小官,那么“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属于他自己则是毫不足以为怪的。所谓“秋熟靡王税”(《桃花源诗》)也大抵是可信之言。另据〈宋书隐逸传〉载:“潜以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招主簿不就,躬耕自资,遂抱羸疾”。“躬耕”而能“自资”,可见陶渊明的归隐园田生活过得也还滋润。
如前所述,《桃花源记》平时交往的南村“素心人”多能“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他们的身份应该是隐士而非普通的农民。关于隐士,鲁迅先生有过一段著名的论述:“凡是有名的隐士,他总是有了‘优哉游哉,优游卒岁’的幸福的。倘不能,朝砍柴,昼耕田,晚浇菜,夜织屦哪有吸烟品茗,吟诗作文的闲暇?”[3]即使不能如此,拥有几亩薄田当属情理中事,也就是说这些人都和陶渊明一样过着自食其力的,没有多少苛捐杂税的宁静生活,这也正是陶渊明笔下的田园生活趣味良多的原因。
当然,陶渊明的隐居生活也并非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历过许多波澜曲折。开始他有一种解脱的喜悦,后来遇到火灾、疾病、灾荒,感受到生活的艰难。但在他看来南村之乐远远大于“尘网”(官场)之苦。《桃花源记》作于义熙十四年,这一年陶渊明54岁,已经过了13年的隐居生活。他参加农业劳动,与农民朋友共话桑麻,与南村隐士共赏奇文,写下了大量反映隐居生活的优美诗篇。《桃花源记》正是他晚年对南村生活的诗意总结和生动写照,是他对南村生活的一次集中的艺术反映而不是道家仙境或乌托邦的空想。
黑格尔曾经指出:“艺术作品形成内容核心的毕竟不是这些题材本身,而是艺术家主体方面的构思和创作加工所灌注的生气和灵魂,是反映在作品里的艺术家的心灵,这个心灵所提供的不仅是外在事物的复写,而是它自己和它的内心生活。”[4]这段话启示我们,文学虽然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但这种反映决不是简单的复制或机械的模仿,而是一种能动的反映。毋庸讳言,陶渊明的南村生活和《桃花源记》必然还存在某些方面的差距,因为《桃花源记》既是他归隐生活的写照,又寄托着作者的理想,更是他以隐士心态和诗人情怀来处理人生的一个经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