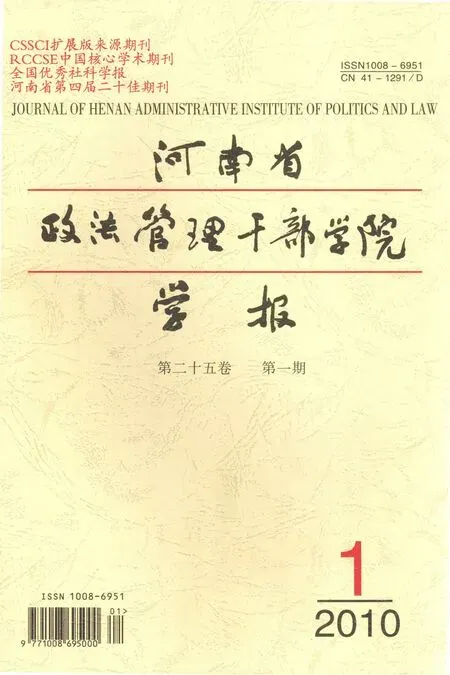中美现有技术抗辩制度之比较
雷艳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湖北武汉 430073)
作为专利侵权抗辩制度之一,现有技术抗辩制度建立的不仅是一种抗辩规则,其实施还牵动着专利制度中的许多其他重要方面。我国《专利法》第三次修正案中现有技术抗辩制度的引入对于合理确定专利权的保护范围,维护社会公正具有重大意义。从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到《专利法》的明确规定,现有技术抗辩制度在我国确立的时间不过数年,其中许多理论问题有待澄清,适用规则需要明确。下文将从各方面对中、美现有技术抗辩制度进行比较,以期加深对现有技术抗辩制度的理解。
一、中美专利无效宣告制度的比较
现有技术抗辩制度是专利侵权抗辩制度,其适用牵动着专利制度中的其他方面。其中,专利无效宣告制度与现有技术抗辩制度的联系最为紧密。专利无效宣告制度涉及的受理机关、宣告程序与现有技术抗辩制度运行的许多方面相互依存。分析中美现有技术抗辩制度之间的差异不得不先考察两国的专利无效宣告制度。中美专利无效宣告制度在受理机关和无效程序上存在差异。
在中国,审查专利申请并最终决定是否授予专利权的是中央专利行政管理机关——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从权力的属性看,授予专利权的权力属于行政权。基于行政权和司法权分立的基本规律,司法机关无权对是否授予专利及专利权是否有效做出判定。因此,申请人启动专利无效宣告程序后,只能由专利行政机关做出专利是否有效的判定。
美国实行严格的三权分立,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相互独立,同时相互制衡。其中司法机关可以对社会的各方面进行司法审查,尤其是 1804年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联邦最高法院确立了联邦司法审查制,开创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查国会法律的先例。首席大法官马歇尔阐述了宪法赋予法院的职权,明确宣称,“阐明法律的意义是法院的职权”、“违宪的法律不是法律”。从此美国司法机关对上至法律的合宪性的各种社会问题都有权进行司法审查,成为典型的司法国家①司法国家是指在一国行政权、司法权的对比中,司法权居于优越地位的国家。。具体到专利领域来讲,判断是否授予专利权是行政机关的职权,而审查专利是否有效则属于司法权的范围。因此,专利无效只能在专利侵权诉讼中向联邦法院提出,而美国专利与商标局只能在特定情况下对已授权专利进行重新审查 (reexam ination),而无权对已授权专利进行无效宣告①美国的重新审查包括单方重新审查和双方重新审查,仅当在先专利和书面出版物公开对专利授权的实质性条件产生影响时才可以提出。。重新审查程序不同于专利无效宣告程序:无效宣告程序,包括在美国司法系统中进行的专利无效程序的前提是专利权推定有效,提出无效申请的人必须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存在无效的理由;而重新审查程序中美国专利与商标局重新回到申请的时间点,将涉案申请看做新的申请案依照审查规程进行审查,并对符合专利性条件的进行授权。因此,尽管两种制度都可能最终导致专利权全部或部分无效,但在机制运行上存在根本不同。严格来讲,美国并不存在真正的专利无效制度。近年来,美国出现一些“问题专利”②“问题专利”一词由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在 2003年的报告《促进创新:竞争与专利法律政策的适度平衡》中提出,是指不当授予的专利,包括不符合现行专利法规定的授权条件,以及虽然可以授予专利权,但是权利要求范围过宽的专利。,专利质量饱受诟病,许多学者提出改革专利制度,在行政机关内部建立一个事后救济机制,即专利异议程序。根据美国 2007年的专利法改革法案,异议程序取消了专利推定有效这一前提,采用“优势证据”③优势证据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如果全案证据显示某一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明显大于其不存在的可能性,使法官有理由相信它很可能存在,尽管还不能完全排除存在相反的可能性,也应当允许法官根据优势证据认定这一事实。规则。该提案将会对美国企业界造成巨大冲击,迄今为止仍没有获得参议院通过。
可以看出,在中国专利无效宣告程序的唯一受理机关是专利行政机关,任何司法机关都无权直接对专利权的有效性做出判定。在美国授予专利是行政机关的职责,而判定专利是否有效则是司法审查的内容。无效宣告主管权的差异也导致了在处理确权诉讼和侵权诉讼时中美的不同态度。
中国法院体系中没有专门的行政法院,但是法院内部分为民事审判庭、行政审判庭和刑事审判庭。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存在许多共同点,但同时在诉讼程序、举证责任的分配等方面也存在差异。专利无效宣告申请经专利行政机关审查做出决定后,依据“司法最终解决原则”,任何一方当事人对行政机关的决定不服的,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诉讼中,司法机关只能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合理做出判断,从而做出维持具体行政行为的裁定,或者责令行政机关限期重新做出具体行政行为。在专利侵权诉讼中,如果被告对涉案专利的有效性提出质疑,申请宣告涉案专利无效,侵权诉讼的审理法院无权对此做出判定,而需要专利行政机关另案处理。由于专利的有效性是判决侵权案件的前提,根据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理,法院会中止侵权案件的审理,等待无效宣告程序完结。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不中止审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专利案件的司法解释,被告原则上只能在答辩期限内提出无效宣告请求;实用新型专利的原告在起诉时提供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的新颖性检索报告的,可以不中止;被告请求宣告该项专利权无效所提供的证据或者依据的理由明显不充分的,可以不中止;另外,被告证明其使用的技术已经公知的,可以不中止审理。从该解释可以看出,专利无效宣告程序中止专利侵权诉讼的审理是一般情况,不中止是例外。
美国各联邦法院都有权对专利权的有效性做出判定。尽管已授权专利应当被推定为无效,但在侵权诉讼中,如果被告提出涉案专利无效作为抗辩理由,受理侵权诉讼的法院有权在侵权诉讼中一并审理专利无效宣告的案件,从而一次性解决纠纷。由于有权初审专利案件的联邦法院众多,造成案件审理标准不一,当事人选择法院的现象,因此美国于1986年成立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统一对专利案件的上诉审,有效统一了专利案件的审判标准。另外,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 1971年的布兰德案中以重复认定一件事实消耗司法资源为由,规定了在一件侵权案中的无效认定对另一案同样有效[1],赋予了侵权诉讼中的无效宣告以对世效力。
二、中美现有技术抗辩制度地位的比较
中美在专利无效宣告制度上的差异导致现有技术抗辩制度在中美专利法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也决定了其在两国的不同地位。
在美国,现有技术抗辩制度是对等同原则的限制,其发展无法离开等同原则的发展而独立。在1950年的 Graver Tank&M anufacturing Co.v.L inde A ir Products Co.一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确立了一套检验等同侵权的“三步检测法”,即现在众所周知的“采用与专利技术实质相同的方法,实现实质相同的功能,达到相同的效果”。法院着重阐述了确立等同原则的意义在于防止侵权人利用替代物绕开专利人在专利申请中通过语言选择设置的字面保护范围,而使专利成为“空洞、无用的东西”[2]。
等同原则是专利制度内部紧张的产物。发明是一种无形财产,也有学者将其描述为信息、符号等。根据发明本身来确定无体财产是不可能的,专利法明显地依赖于登记程序[3]。正如欣德马什所说,如果发明要得到确认,就必须通过书面说明加以定义[3]。为了合理确定专利权的保护范围,给发明人提供充分激励,就必须寻找一种合理的方式对发明的书面记载进行解释。在这方面有两种做法,即中心限定主义和周边限定主义,两种方式针锋相对。周边限定主义能较好维持专利制度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但过于僵硬,其有效实施依赖于发达的专利中介行业和高素质的专业代理人员。为此,一些国家在采纳周边限定主义时,同时引入了等同原则,将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向专利申请书字面表述的范围外扩张,同时又限定在申请书字面表述的等同物以内。这样,专利制度的内部紧张情形得到部分缓解。
在 1990年W ilson Sporting Goods案之前,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通过一系列案例确立了判定等同原则的“三部曲”。即首先确定实质等同;其次适用禁止反悔原则;再次排除现有技术[4]。“三部曲”通过这三种途径限制了等同原则的适用,即首先确定了构成实质等同的客观检测方法,其次通过禁止反悔原则的适用防止权利人取得其在申请时没有要求的部分,再次通过排除现有技术防止专利人取得其在申请时无法获得的部分。等同原则检测“三部曲”的意义在于:第一,等同原则通过“实质等同”要件的适用赋予权利人在诉讼中“改写”(red raft)专利权保护范围的权利,同时禁止反悔和现有技术的排除要件又限制了权利要求的可能范围,排除了无限制“改写”专利申请书的可能。第二,“三部曲”调和了专利申请书两种解释方法之间的冲突。“实质等同”要件表明现代专利法应当更加注重实质而非形式,倾向中心限定主义的解释方法;同时,“三部曲”给中心限定主义的解释方法施加了双重限制,即“禁止反悔原则”给权利人施加了一个主观限制,“排除现有技术”给权利人施加了一个客观限制。
在W ilson案中,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对上述“三部曲”中的第三部分,即排除现有技术进行了详细阐述与分析。该案中陪审团判定被告生产的高尔夫球侵犯了原告W ilson的专利权。被告宣称其生产的高尔夫球同作为现有技术的Uniroyal球之间没有实质不同,判定被告行为构成等同侵权,就等于允许原告的专利覆盖存在于现有技术中的高尔夫球。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此案中确立了几个重要规则:1.再次确认了 Graver案中确立的等同原则“三 hi检测法”;2.创立了判定等同的“假想权利要求法”;3.宣称“现有技术的排除”是法律问题,而非事实问题。
在中国,现有技术抗辩制度在等同原则中发展起来,并逐渐独立于等同原则,成为合理确定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平衡公益和私益的重要制度。
我国最早确立现有技术抗辩制度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01年发布的《关于专利侵权判定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该《意见》明确规定,“已有技术抗辩是指在专利侵权诉讼中,被控侵权物 (产品或方法)与专利权利要求所记载的专利技术方案等同的情况下,如果被告答辩并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被控侵权物(产品或方法)与一项已有技术等同,则被告的行为不构成侵犯原告的专利权”。同时,该《意见》就等同侵权的判定也进行了规定,即“被控侵权物中的技术特征与专利权利要求中的相应技术特征相比,以基本相同的手段,实现基本相同的功能,产生了基本相同的效果”;“对该专利所属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说,通过阅读专利权利要求和说明书,无需经过创造性劳动就能够联想到的技术特征”。可以看出,《意见》对等同侵权和现有技术抗辩的规定与美国专利法如出一辙,是对美国判例的总结和借鉴。这些规定对我国完善专利法律制度起到过重要作用,但没有充分考虑我国国情,制度移植尚待本土化。实际上,我国在专利事后确权上采用的是单一的行政确权机制,现有技术抗辩制度在我国专利法中可以并且应该发挥比在美国法中更大的作用。
将现有技术抗辩制度适用于等同侵权,作为对等同原则的限制,在防止专利权不正当扩张方面的作用在上文已有详细论述。在我国,仅专利行政机关有权受理对专利权提出的无效宣告请求,进而对专利权的有效性做出认定。这一机制导致我国专利侵权诉讼和确权诉讼的交叉和冲突以及司法权和行政权的紧张①论及行政确权程序与民事侵权诉讼程序交叉问题的论文包括张红:《专利无效行政诉讼中行政、民事关系的交叉与处理》,载《法商研究》2008年第 6期;渠滢:《论专利无效诉讼中的“循环诉讼”问题》,载《行政法学研究》2009年第 1期。。将现有技术抗辩制度的适用从等同侵权扩及相同侵权意义重大:在专利相同侵权案件的审理中,现有技术抗辩制度的适用可以在不触及涉案专利的前提下,将被告从诉讼中解脱出来,既维护了诉讼正义,又实现了诉讼效益。基于这样的认识,在施特里克斯公司诉宁波圣利达电气制造公司及华普超市公司专利侵权案中②(2006)高民终字第 571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高院确认已有技术抗辩不仅适用于等同侵权,而且适用于相同侵权。同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九条指出,人民法院受理的侵犯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件……被告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其使用的技术已经公知的……可以不中止诉讼。2008年我国通过的新《专利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在专利侵权纠纷中,被控侵权人有证据证明其实施的技术或者设计属于现有技术或者现有设计的,不构成侵犯专利权”。虽然新《专利法》没有对现有技术抗辩制度的适用进行更为详细的规定,但司法实践的发展已经证明,现有技术抗辩制度独立于等同原则是我国专利法制发展的必然选择。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现有技术抗辩制度在中、美专利法中最显著的区别在于是否能脱离等同原则,取得独立的法律地位。现有技术抗辩制度在美国是等同原则的构成部分,仅适用于等同侵权,在相同侵权中不能适用。而在中国,现有技术抗辩制度脱离等同侵权在相同侵权中的确立赋予了该制度以独立的法律地位和法律价值。相同侵权中出现现有技术抗辩意味着涉案专利的有效性存在问题,此时被告可以通过无效抗辩或者无效宣告申请来实现救济。由于美国联邦法院在侵权诉讼中有权同时判决专利的有效性问题,因此,在美国法中,现有技术抗辩制度无法脱离等同原则而独立。而在中国,原则上法院无权审查专利的有效性,现有技术抗辩制度就给被告提供了一种很好的抗辩手段,既有利于迅速解决纠纷,又可以维护现行国家权力分配体系的稳定性。
三、中美现有技术抗辩制度司法适用规则的比较
现有技术抗辩制度的司法适用比较复杂,其中涉及对比对象、对比标准等问题。
美国法中现有技术抗辩制度表现为等同原则中的“排除现有技术”,这是一个法律问题,而非事实问题。在W ilson案件之前,美国联邦法院有两套适用现有技术抗辩制度的方法:Carm an检测法和 Ryco检测法。Carm an检测法确立于 Carm an Industries, Inc.v.W ah l案。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该案中指出,等同原则下对专利保护范围的解释应当以维持专利的有效性为前提[5]。总的来说 Carm an检测法中,如果专利人能证明专利技术和被诉侵权技术的差异仅属于等同物,则由专利权人对权利要求进行解释,以求在覆盖字面权利要求的同时也覆盖被控侵权技术。当覆盖了被控侵权技术的解释方案相对现有技术来讲是可以预料的或者是显而易见的,即不具有可专利性时,现有技术抗辩成立,不构成侵权;当上述权利要求相对现有技术来讲不具有可专利性时,现有技术抗辩不成立,构成侵权[5]。Ryco检测法最初确立于 Ryco,Inc.v.Ag-Bag Corp.一案,其理论是即使在等同原则下专利人也不能宣称被告侵犯了在颁布专利时已经存在于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6]。总的来说,Ryco检测法中如果专利人能证明专利技术和被诉侵权技术之间仅属于等同物,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被控侵权产品是否属于现有技术。如果被控侵权物没有落入 (in)现有技术,则侵权成立;如果被控侵权物落入现有技术,则侵权不成立[6]。但是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从未精确界定何为“被控侵权物落入现有技术”。在 Ryco案中,法院认定被告的转子(rotor)并非对现有技术的实施,因为比较而言,被诉侵权物更像原告专利的权利要求 1中的技术方案,而非现有技术[4]。这一判断方法在State Industries,Inc.v.M o r-Flo Industries,Inc.案中再次得到联邦地区法院的确认[4]。可以看出,两种检测法完全不同:Ryco检测法将被控侵权技术和现有技术进行对比,较为简单;而 Carm an检测法先对专利权利要求进行解释,覆盖被控侵权技术,然后判断这样的解释方案是否具有可专利性。
W ilson案在美国现有技术抗辩制度的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该案中发展出“假想权利要求法”。法院指出,如果原告主张的等同范围覆盖了现有技术,则侵权不成立。为了判定原告主张的等同范围是否覆盖现有技术,法院认为可以想象一个“假想权利要求”(hypothetical patent claim),该权利要求能够在字面上覆盖被控侵权产品。这样问题就变成“假想权利要求”是否具有专利性的问题:如果该权利要求不能被授予专利,则现有技术抗辩成立;如果该权利要求能够被授予专利,则现有技术抗辩不成立。可以看出,法院采纳了Carm an检测法,放弃了 Ryco检测法。Carm an检测法中覆盖专利方案和被控侵权技术方案的解释方案,在W ilson案中变成了法官脑中虚拟的“假想权利要求”。W ilson案后,联邦地区法院和上诉法院在不同的案件中又发展出了其他的检测法,但都没有脱离上述三种方法。其中,并且W ilson检测法直接以现有技术抗辩在美国专利法中的作用为切入点,受到学者和法官的追捧。正如专利法律师B ruceM.W exler对W ilson案中“假想权利要求法”所做的评价,当专利人诉请等同侵权时,他实际是要求法院将专利解释为覆盖权利要求字面含义以外的方案,权利人在诉讼中一直都在提出他脑海中的“假想权利要求”[4]。
在中国,尽管司法实践很早就确认了现有技术抗辩,但法院对该制度的适用非常谨慎,对其认识在很多方面含糊不清。《专利法》第三次修正案实施后,尽管仍存在一些混乱,但司法机关对现有技术抗辩制度的适用规则更加熟悉,同一法院内部对现有技术抗辩制度的适用规则基本能达到统一。
1.现有技术抗辩制度的适用范围。北京市高院在施特里克斯公司诉宁波圣利达电气制造公司及华普超市公司专利侵权案中确认现有技术抗辩制度在我国不仅可以适用于等同侵权,而且可以适用于相同侵权。随后最高人民法院以“驳回再审申请通知书”的形式确认了这一规则,认为:“公知技术抗辩的适用仅以被控侵权产品中被指控落入专利权保护范围的全部技术特征与已经公开的其他现有技术方案的相应技术特征是否相同或者等同为必要,不能因为被控侵权产品与专利权人的专利相同而排除公知技术抗辩原则的适用。”①(2007)民三监字第 51-1号。但下级法院在审判中仍存在一些相反认识。如上海市高院在建德市朝美日化公司与 3M创新公司侵犯发明专利权纠纷上诉案中指出:“被控侵权产品的技术特征经比对已完全落入涉案专利的保护范围,属于相同专利侵权,而非等同专利侵权,因此不适用公知技术抗辩。”②(2009)沪高民三(知)终字第 10号。
2.现有技术抗辩制度和侵权构成的关系。在新疆农业科学院农业工程公司与石河子市华农种子机械制造公司侵犯专利权纠纷案③(2007)新民三终字第 10号。和连展科技股份公司与东莞厚街新塘华宝电子厂等侵犯专利权案④(2006)粤高法民三终字第309号。中,二审法院新疆高院和广东高院都指出被控侵权物没有落入专利技术的保护范围,被告不构成侵权,也不需再对被控侵权物与已知技术进行比对。而在广州金鹏实业公司诉上海国东建筑装饰工程公司等专利侵权纠纷案⑤(2006)沪一中民五(知)初第 376号。中,上海市第一中院认定被控侵权技术与原告专利既不相同也不等同,未落入原告发明专利权的保护范围;继而又指出被控侵权产品的技术特征与现有技术相同,被告关于现有技术的抗辩理由成立。可见,多数案例中法院对被控侵权物是否落入专利权保护范围和是否成立现有技术抗辩进行同时认定。但也有一些法院在判决中指出,在侵犯实用新型专利权诉讼中适用现有技术抗辩时,“既可在先判定被控侵权技术与专利技术相同或等同的基础上进一步判定被控侵权技术是否属于公知技术,也可先行判定被控侵权技术是否属于公知技术”⑥参见(2009)高民终字第 1569号,(2008)高民终字第 1165号。。
3.现有技术抗辩的对比对象及对比标准。在西安高科陕西金方药业公司诉上海交大穗轮药业公司等侵犯专利权纠纷案⑦(2005)西民四初字第 136号。中,被告提出现有技术抗辩并举出三份现有技术的证据。一审法院西安市中院将现有技术与专利技术进行对比,以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在复审决定中认为该三个证据不能破坏原告专利权利要求 1和 2的创造性为由判决现有技术抗辩不成立。在佛山市顺德区杰晟热能科技公司与张黎光侵犯专利权纠纷案⑧(2006)粤高法民三终字第 276号。中,被告自认被控产品落入涉案专利保护范围。二审法院广东省高院指出,在判定现有技术抗辩是否成立时,应将被控侵权产品与现有技术直接进行比对,如被控侵权产品与现有技术相同或等同,则现有技术抗辩成立;如被控侵权产品与现有技术不相同或不等同,则现有技术抗辩不成立。在如何认定被控侵权技术属于现有技术的标准上,北京市高院在近期的判决中都以“被控侵权技术与专利技术相同或等同”⑨参见(2009)高民终字第 1569号,(2009)高民终字第 1574号。为标准,但也有一些法院在判决中并没有对此进行明确表述。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中美在现有技术抗辩制度的司法适用规则上存在很多差异,这些差异是由现有技术抗辩制度在中美专利法中的不同地位决定的。第一,适用前提不同。作为等同原则限制的现有技术抗辩制度旨在防止专利人通过侵权诉讼取得他在申请时无法获得的东西,因此,在美国,无论司法实践还是理论研究都认为在适用现有技术抗辩时首先必须确认专利技术方案和被控侵权技术之间的差异属于等同物,即存在等同侵权是现有技术抗辩制度的适用前提。在中国多数法院同时对是否构成侵权,包括相同侵权和等同侵权以及现有技术抗辩是否成立做出判定;也有一些法院认为实际侵权的认定并不是适用现有技术抗辩制度的前提。第二,适用范围存在差异。现有技术抗辩制度在美国只适用于等同侵权;在中国大部分案例确认现有技术抗辩也可以适用于相同侵权。第三,对比规则不同。目前中国大部分法院在适用现有技术抗辩时,将被控侵权技术同专利技术进行对比。在美国,现有技术除外是防止专利人利用等同原则不正当扩张专利保护范围的手段,因此在对比时先勾画出专利人在诉讼中寻求保护的专利范围,然后将描述此范围的权利要求同现有技术对比,判定其是否具有可专利性,从而解决现有技术抗辩能否成立。
四、中美现有技术抗辩制度比较之启示
美国是世界公认的科技强国,其技术发展离不开高水平的专利保护。近年来,美国在强调专利保护的同时,也开始注重提高专利质量,减少“问题专利”的产生。现有技术抗辩制度能有效防止专利人不正当扩张专利,合理界定专利范围,对平衡公益和私益具有重要意义。同美国相比,中国专利制度还很稚嫩,有待完善的地方很多。就现有技术抗辩制度来讲,其适用在我国还较为混乱,各地区和各级法院之间没有统一的适用规则。
在各国之间,现有技术抗辩制度的适用取决于专利制度的其他方面,无法做到一刀切。如上文所言,现有技术抗辩制度在一国专利法中的地位与该国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分立状况,以及专利无效宣告制度存在密切关系,而现有技术抗辩制度的地位决定了该制度的适用规则。由于历史原因,各国在国家权力配置和法律传统上都存在差异。制度移植能在短时间内提高法制建设水平,显现了制度的后发优势,但法律规则的本土化更为重要。正如孟德斯鸠所言,“每个国家的政治法律和民事法律应该是非常适合该国人民的……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竟能适合另外一个国家,那真是一个极大的巧合”[7]。实证研究也表明,不考虑社会背景,不关注人们的物质生活方式,而仅仅从需要或抽象“正义”出发的法律移植都失败了[8]。因此,美国的现有技术抗辩规则不能完全照搬到我国。美国在现有技术抗辩制度上选择以“假想权利要求”排除等同原则中的现有技术,由该制度在等同原则中的地位决定。在中国,现有技术抗辩制度既可以适用于等同侵权,限制专利权的不正当扩张;也可以适用于相同侵权,以排除诉讼中的“问题专利”。作为对等同原则的限制,现有技术抗辩适用于等同侵权在中美发挥相同的作用。因此,等同侵权中的适用可以借鉴美国成熟的对比方法,即先确定原告在诉讼中寻求的专利保护范围,然后将其同现有技术进行对比,判定是否具有可专利性。同我国目前普遍采用的将被控侵权技术同现有技术进行对比的做法相比,前者更为直接地切入原告诉求等同侵权的实质——寻求超出权利要求书字面范围的保护,也更符合现有技术抗辩在等同侵权中的作用——保证扩张后的专利权仍具有可专利性。而在相同侵权中,适用现有技术抗辩旨在绕过行政无效宣告,使无辜的被告从侵权诉讼中解脱出来,应当采用目前我国法院普遍的做法——将被控侵权技术对比现有技术的规则。
[1]专利无效抗辩与专利无效宣告的区别 [EB/ OL].2009/8/28.http://b log.ce.cn/htm l/23/ 330723-314951.htm l.
[2]Graver Tank&M fg.Co.,339U.S.
[3]布拉德 .谢尔曼,莱昂内尔 .本特利.现代知识产权法的演进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4]1991 Ann.Surv.Am.L.571.
[5]724 F.2d.
[6]857 F.2d.
[7]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1.
[8]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