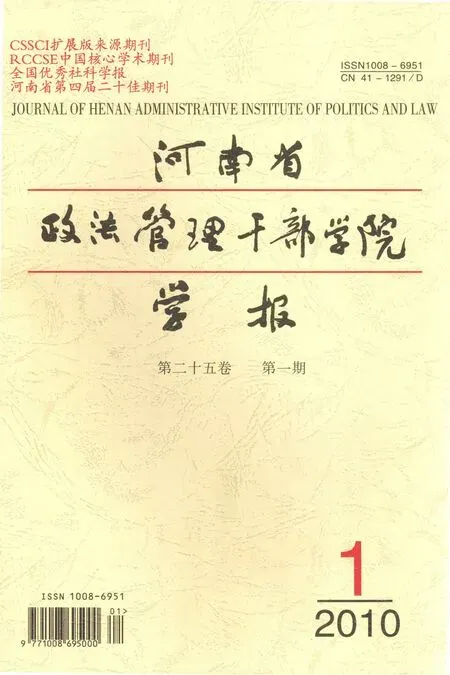由格鲁特布姆案透视南非住房权的司法保护
韩 敬
(东南大学法学院,江苏南京 211189)
由格鲁特布姆案透视南非住房权的司法保护
韩 敬
(东南大学法学院,江苏南京 211189)
南非宪法法院在格鲁特布姆案的判决中首次确立“合理性审查标准”,并对立法者科以即刻实现的积极义务,在绝对权利与相对权利的博弈中基于现实选择相对权利,在对住房权的政府积极义务进行审查时持妥协与退让立场。法院的做法虽然备受批评与指责,但却是在充分考虑了南非社会现实和法院自身能力后的明智选择,显示了宪法法院高超的平衡技巧,也为住房权等社会经济权利的司法保护提供了大量可资借鉴的经验。
格鲁特布姆案;社会经济权利;住房权;南非
宪法中规定的作为社会经济权利的住房权可由法院进行司法保护吗?这是一个支配对社会经济权利辩论并在世界各国引起激烈争议的问题[1]。令人欣慰的是,当国际社会还在为诸如住房权等社会经济权利的可诉性问题争论不休时,1996年才通过新宪法的南非,用司法实践向人们展示出如何保护备受争议的社会经济权利。“被视为证明社会经济权利具有可诉性的一个里程碑式判例”[2]——格鲁特布姆案第一次表明宪法法院在既尊重民主又顾及有限预算的基础上,是可以对住房权等社会经济权利提供司法保护的。
一、格鲁特布姆案之基本案情及南非宪法法院之判决
(一)格鲁特布姆案基本案情
格鲁特布姆案是南非共和国政府等诉格鲁特布姆案(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and Others v.Grootboom)的简称,基本案情为:一个由390个成年人和 510个儿童组成的原住在沃拉斯的穷人群体,因不堪忍受居住地恶劣的条件,而集中搬迁到一块由私人拥有的空闲区域,其中有一位成年人名叫艾琳·格鲁特布姆 (Irene Grootboom)。搬迁后不久,由于政府的强行驱逐,他们又不得不搬到同一区域的一个运动场。但是,应私人土地所有者的要求,政府又命令他们离开居住地,且在命令的最后期限届满前一天,用推土机强行铲平了他们的临时住所,所有家当被损坏殆尽,使得他们陷入居无住所的悲惨境地。于是,以格鲁特布姆为首,他们集体请求开普敦地区的高级法院发布紧急命令,要求政府立即向他们提供临时性住所,直到他们能够获得永久性住房为止。南非开普敦地区的高级法院根据南非《宪法》第 28条第 1款第 3项有关儿童社会经济权利的规定,判决政府应该给予那些有孩子的家庭临时住房。南非三级政府 (中央、省级和地方政府)因对判决表示不服而向南非宪法法院提出上诉。此时,南非人权委员会和社会法律中心两个机构作为该案的“法庭之友”①“法庭之友”即在南非宪法法院审查案件的过程中,法院允许任何相关或感兴趣的团体或个人,可以申请向法院提交一份法律意见书,并赋予该团体或个人享有口头辩论或者作书面笔录等权利。参与诉讼,并要求将格鲁特布姆等人的请求扩大到《宪法》第 26条 (即获得住房权)。他们认为,社会所有的成员,包括没有孩子的成年人都有权获得住房,因为《宪法》第 26条的规定使国家担负了最低限度的核心义务 (minimum core obligation)[3]。
(二)南非宪法法院判决的主要观点
在 2000年格鲁特布姆案判决中,南非宪法法院提出以下主要观点:
1.政府违反了消极保护义务。宪法法院认为,政府有义务确保驱逐行为以一种符合人道主义的方式进行,但是,政府实际的驱逐行动比原先通知的时间提前一天,而且被告所拥有的物品和建筑材料等都在驱逐过程中被毁掉,这种行为显然违反了南非《宪法》第 26条有关获得充分住房权所体现的消极义务。
2.第一次确立了合理性审查标准。宪法法院认为,判断国家是否履行了第 26条第 2款所施加之积极义务的关键问题是,国家采取的立法和其他措施是否合理。符合合理性审查标准的情形包括:采取的政策是全面而协调的;政策即使只能逐渐实现,至少也能够促进权利的实现;政策比较平衡、灵活并且没有把社会的重要部分排除在外;政策能回应那些处于绝望情形的人们的紧急需要[4]。
3.政府的住房政策存在不合理之处。宪法法院认为,政府采取的住房政策只关注了中期和长期的住房需要,却没有“在其可利用的资源范围内为开普敦那些没有土地、没有住房并且生活在不能忍受或者处于危机状况中的人们提供合理的帮助”[5],因而其是不合理的。故法院命令政府采取行动履行第 26条第 2款所施加的义务,主要包括设计、资助、实施并且监督临时性救济措施,从而保障那些处于极度困境的人们的合法权益。
4.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提出的“最低限度的核心义务”概念不适用于住房权。宪法法院指出,尽管“最低限度的核心义务”具有重大意义,但它有很多问题,为了确定任何特定情况下的最低核心义务,就必然要求法院获得大量的有关信息,而对于住房存在地区和城乡差异的南非,让法院来确定获得充分住房权的最低核心义务内容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宪法法院否认《宪法》第 26条第 1款包含国家应根据请求为权利人直接提供基本住处的最低核心义务,而认为,第 26条第 1款应该和第2款结合起来进行理解,即国家只负有在其可利用的资源范围内逐渐实现的义务。
二、绝对权利与相对权利的博弈——对格鲁特布姆案所适用《宪法》第 26、28条之解读
南非《宪法》关于住房权的第 26条规定:
1.每个人都有权获得足够的住房。
2.国家必须在其可利用资源的范围内采取合理的立法和其他措施,以逐步推进这项权利的实现。
3.在法院没有综合所有相关的情况作出判令之前,任何人都不得毁坏他人的住宅,任何法律都不得允许任意将人们从其住宅中驱逐。
第 28条第 1款第 3项规定:
每个儿童都有权获得家庭或父母的照顾,或在脱离家庭环境时有权得到其他恰当的照顾……并且有权享有基本的营养、住处、医疗保健服务和社会服务。
对于第 26条与第 28条的关系,牵涉到绝对权利与相对权利问题。从宪法条文上看,第 28条赋予儿童享有各种物品的绝对权利,即保证儿童在资源缺乏的情况下都能享受到“基本的营养、住处、医疗保健服务和社会服务”,那么,政府有绝对的义务来保证儿童有吃有住。而根据第 26条的解释,其对每个人所创设的权利都是有限制的,是“逐步实现的权利”,即相对权利。开普敦地区的下级法院即是按照这种思路理解的,他们亦认为第 28条为儿童创设了独立的、绝对的权利,儿童的权利不受“可利用的资源”或“逐步实现”条款的限制。
然而,审理格鲁特布姆案时,南非《宪法》法院拒绝对第 28条作出上述解释,与之相反,他们把第28条看成是对第 26条基本要求的补充。南非宪法第 26条第 3款不仅强调了政府的义务,而且对私有财产者也设置了义务。据此推断,个人如果没有得到法院许可,把他人从其住房中驱除出去或毁坏其房屋,就违反了宪法。也许制定此条的初衷是为保证穷人继续有房可住,但却给合法所有人留下种种担忧:如果不能把擅自在自己私有土地上搭建房屋的人赶走,那么建造住房的积极性势必消弱,私有住房的数量就会减少,国家本就住房紧张的情形只能是雪上加霜;另一方面,可能到处存在房东对租赁房屋的人进行严格的筛选审查,因为房屋所有者完全清楚,一旦房屋租赁关系成立,就很难终止这种关系,不得不承受某种来自宪法的义务。这也是宪法法院限制对第 28条进行扩张解释原因的一个方面。
宪法法院认为第 26条强调的并不是所有人都享有住房的权利,而是强调所有人都有权得到“逐步实现这项权利”的立法或其他措施的保护,同时,宪法要求国家、其他组织和个人“停止妨碍或侵犯拥有足够住房的权利”。更进一步来说,宪法法院根据个人的经济地位来区别政府的积极义务,认为要贯彻住房权,政府将面临两种责任:对那些买得起住房的人,国家的责任是放宽政策,提供住房供应及立法框架,通过制定法律和提供资金促进个人建造住房;对于穷人,国家的义务就是为“那些无法通过其他途径维持生存的人及其抚养者提供足够的社会援助方案”,在这方面,宪法权利指的是某种制度的建立,而不是指完全的个人保护。
对于儿童权利的保护,宪法法院强调为他们提供住处的义务首先应该由其父母或家庭来承担,然后才由国家承担。换言之,宪法并没有首先为国家设立任何义务,要求国家在儿童有父母或家庭照顾的情况下为其父母提供住处。有学者认为,“如果这样解释这一条款,就未免过于狭隘,这明显是出于实用的考虑”,“如果儿童被认为拥有获得住房的绝对权利,那么该法律文件对社会经济权利的限制就很难取消;‘如果处处要为儿童的权利让道,那么精心构建的逐渐实现社会经济权利的宪法蓝图也就没多大价值’。我想这才是宪法法院对要求把第 26条看做是创造绝对权利保持怀疑态度的关键所在。如果这样去理解第 26条,那它将超出即便是合理的先后顺序的设定,从而使国家无法决定在资源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哪些需求更加紧急”[6]。
因此,在绝对权利与相对权利的博弈中,宪法法院基于实用的目的选择了相对权利,而这种背离宪法文本的解释表明:南非宪法法院在处理住房权等社会经济权利案件时的法理和方法不得不被认为是一种“胆怯”[7]。
三、可以理解的、聪明的胆怯——案件背景分析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南非宪法法院在审理住房权案件时,面临着诸多困境与尴尬,既有国际的亦有国内的,既有历史遗留的亦有现实难以立即解决的,由此表现出一定的妥协与退让,难免令人同情与理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未必不是种聪明的做法,展现了宪法法院非凡的平衡技巧。
(一)长期种族隔离传统遗留的问题和住房短缺
20世纪 60~80年代,南非政府实行种族隔离制度,此制度是官方的种族隔离政策,包括在政治、法律和经济诸方面对非白色人种实行歧视,当时的法律成为压迫工具和执行政府政策的“警察”,陷入极度不光彩的境地。90年代初,南非完成国家转型,但其司法系统仍基本上由男性白人组成,为保护新宪法的实施,“一个希望不受历史污染的新法院——宪法法院在临时宪法下成立,其实其本身就是一个妥协产物”[8]。20世纪末,南非的失业率仍高达 33%(近 500万人),犯罪率也高居世界前列,平均每 12分钟就有一起谋杀或企图谋杀案件,每26秒钟就有一起强奸案件,而且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仍高达 53%[9]。格鲁特布姆案就是在此社会背景下发生的。
在住房方面,原来的种族隔离体制限制非洲人入住城区,政府试图赶走所有的非洲人,并把优先权留给白色人群。然而,非洲人继续流入这一地区寻找工作。由于没有正式的住房,他们就住进了“不正规的住宅区”,住宅区内搭起的都是一间间小屋,遍布整个半岛,没有水,没有下水道,也没有垃圾清除服务,只有 5%的房子有电,到 20世纪中期南非住房仍短缺 10多万套。此种境况下诞生的宪法法院,难免受到长达半世纪种族隔离传统所造成的根深蒂固的隔阂和偏见的影响,难免受到经济社会地位不平等及资源贫乏的限制,在作出判决之时要考虑诸多情况也是在所难免的。
(二)宪法法院自身生存的合法性及其所掌握信息的有限性
在南非这样一个刚刚完成转型的国家,如果法院发布一个有篡夺政府政策制定权之嫌的命令,难免会给反对者留下口实。在宪法法院成立之时反对者就认为,“司法介入将会导致政策分歧,并且包含住房权在内的社会经济权利与权力分立原则相悖而行,因为司法将会侵犯立法和行政的正当领域”[10]。何况,如果宪法法院真打算这么做,那将势必使自己处于一种无奈的管理者的境地,毕竟,法院又怎能去监督政府预算方面的偏好?如果政府对那些需要住房的人们帮助甚微,可能是因为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提供就业或教育等方面。此时,宪法法院聪明地适用迂回的“合理性审查标准”,既不会直接介入政府的预算安排,也不会对政府最初在宏观层面的分配决定作出指令,但是法院会审查政府措施的合理性,一旦法院作出政府措施不合理的判决,政府将不得不重新安排预算。从表面上看,法院自己重新安排预算和法院作出判决导致政府必须重新安排预算,两者之间的差别可能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后者允许法院在不对政府发出直接指令的情况下,在一定程度上介入政府的预算分配。这样,既可以通过间接的方式达到保护住房权的目的,又可以避免法院和政府的直接冲突。
因此,在南非这样一个贫困人口依然占多数的社会,在一个新的和脆弱的政体下,过于明显地保护弱势群体,对法院而言是不明智的,它将使法院不断地与政府对抗,从而形成一种不和谐的气候。同时,宪法法院“采取极端的、拒绝在社会经济领域为自己创造一个严肃角色的立场也是不合时宜的,这将引出宪法中社会经济权利条款及宪法法院自身的合法性问题”[11]。
另外,宪法法院是否应该对政府的项目进行全方位的监督以便保证国家把预算放在恰当的方面?宪法法院应该避免这么做,一方面由于权力分立体制的限制;另一方面,宪法法院在这么做之前又怎么可能获取足够必要的信息,从而作出准确的判断,这也是当年仅由“11名法官所组成的宪法法院”[12]精力与能力所无法达到的。
四、格鲁特布姆案对住房权司法保护的启示
没有救济的权利只是徒有其名,不能获得救济的社会经济权亦是如此。作为社会权典型的住房权,国际社会日益承认其具有可诉性,已有 50多个国家的宪法明确规定了住房权,几乎在所有的缔约国,国内法院都频频审视住房权问题[13]。其中,在住房权的宪法审查方面最为激进的当数南非宪法法院的做法,通过格鲁特布姆案,它正好做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曾经说过的“法院做不到也不应当做的事——推行社会经济权利”[14]。当然,学界对法院的做法亦褒贬不一,“批判意见认为,这种做法超过了司法审查权行使的界限,可能会带来干涉立法和行政的危险;赞赏意见认为,南非宪法法院通过司法审查模式对公民社会经济权利给予救济,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作为司法审查制度起源国的美国,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不能受理的案件在南非宪法法院得到了处理,实现了违宪审查制度本身和公民社会经济权利保护规则的创新”[15]。更有学者具体地列举了其积极意义,如西开普敦大学教授 Liebenberg指出,“Grootboom案力求在法院履行社会经济权利义务的宪法责任和立法与行政在民主社会制定和执行法律和政策的作用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从而发展一种负责任、透明和互动的司法、立法和行政关系”[16]。
(一)可学习与借鉴的经验
1.南非宪法法院确立了合理性审查标准。
这一标准的含义是:法院承认有关政策选择和资源分配的权力属于立法和行政部门,法院的职责仅在于审查立法和行政机关所采取方法的合理性,亦即如果立法和行政机关的方法具有合理性,法院就认为它们不违宪;如果它们的方法有明显不合理的地方,法院就会认为它们违宪。为了判断保障社会经济权逐步实现的立法或政策是否合理,法院提出了如下标准:“第一,立法或政策在可获得的资源限度内必须是充分的,以便于权利的逐步实现;第二,立法或政策必须是全面的、协调的、平衡的和灵活的,必须把责任分配给政府内不同层级的机构,必须考虑处于危急状态的人群的急迫需要,不能排除任何社会组成部分,尤其是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第三,政府必须为立法或政策的实施提供必要的资源;第四,立法或政策不仅应合理地被设计,也应合理地被实施,没有得到合理实施的合理计划不能被视为政府已经履行了它的积极义务。”[17]本案中,法院认定政府的住房计划没有达到“合理性标准”,主要是因为住房几乎没有满足处于困境人群的急迫需要。
在现代社会中,向弱者提供帮助的程度和数量可以被视为衡量社会文明的标尺。对南非《宪法》第 26条这种典型的社会经济权利条款,宪法法院虽然否定个人具有直接根据这些条款获得住房、食物和医疗等的请求权,但承认宪法赋予公民享有要求国家在其可利用资源的范围内设计合理的立法与政策的请求权。这意味着,立法者如果没有制定合理的立法与政策,公民就可以根据宪法中有关社会权条款请求立法者履行法定职责,以保障公民社会权的实现,保障公民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也许宪法法院的这种解释不能给予直接的救济,但却给予他们相对间接却同样重要的保护。“合理政策请求权”表明,人们通常认为的社会经济权利只是一种“政策性权利”的观念并不完全正确。因为个人对立法和政策具有了可以即刻行使的请求权,在社会经济权利方面享有的可控性得到了加强,使得此类社会经济权利的“权利性”得到显著增强,并且使它们向具有完全主观性的理想权利大大迈进了一步。如果没有这种政策请求权,那么这类“逐渐实现”的权利就只能寄希望于立法和行政机关的主观意愿,同时,法院适用“合理性审查标准”,缓和了反对者对法院能力和合法性的质疑,可以避免与政府的直接冲突,使法院有可能在不违背权力分立原则的情况下,实现对社会经济权利一定程度的保护。
2.宪法法院对立法者科以即刻实现的积极义务。
一个国家的资源是有限的,立法者需要在掌握大量信息的基础上,通过立法确定社会中不同层次需求的权利主体实现权利的先后顺序,根据不同的情况决定分配资源的时机和方式,对有限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因此,对可利用的有限资源进行分配在很大程度上是立法者的裁量范围,而立法裁量在很多国家是免于司法审查的,公民不能基于分配政策的不合理而寻求司法救济。在格鲁特布姆案中,宪法法院对《宪法》第 26条第 2款中的“逐步推进权利的实现”作出同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相同的解释,认为它对立法者科以即刻实现的积极义务。宪法法院的观点表明,国家对社会经济权利所负的“逐渐实现的义务”也具有即刻义务的内容。这就是说,目标可以“逐渐实现”,但是实现这个目标所需的行动却必须立即采取。如果立法者不履行即刻实现的立法义务,则公民可以基于“合理政策的请求权”请求立法者制定法律或采取其他合理措施;否则,公民就可以提起宪法诉讼,请求宣告立法者不作为违宪。因此,格鲁特布姆案判决的意义在于:“它第一次解释了国家在实现社会经济权利方面所负的积极义务的范围,它使公民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不再取决于立法者的主观意愿,而是通过司法审查的途径对立法者科以强制性义务,同时也使公民的权利获得了实质性的保障。”[18]
(二)判决对住房权保护所显现出的非凡平衡技巧
在格鲁特布姆案中,宪法法院拒绝接受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提出的“最低限度的核心义务”概念。宪法法院认为,《宪法》第 26条第1款“任何人都有权获得足够的住房”并不包含国家应根据请求为权利人直接提供基本住处的最低限度核心义务。不过,宪法法院认为《宪法》第 26条第 1款应结合第2款来理解。第2款规定:“国家必须在其可利用资源的范围内采取合理的立法和其他措施以逐渐实现住房权。”根据宪法法院的观点,该条款虽然没有赋予个人直接请求获得住房的权利,但是却赋予公民要求国家在其可利用资源的范围内设计合理政策的请求权,公民可以根据该条款请求国家合理立法或者采取其他合理的政策措施,以保障公民住房权的实现。
宪法法院之所以拒绝接受“最低限度的核心义务”,主要是因为,像充分住房权这种权利的最低核心义务是随着社会需要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法院不可能完全掌握确定这些最低核心义务所需的信息。其实,这种担心并非没有道理,最低水平的住房权应该享有什么条件的房子?哪些特殊人群和个人可以直接根据宪法条款行使请求权?对法院而言,这些问题都是不容易界定的。并且,在宪法没有直接确认社会经济权利最低核心义务的情况下,如果宪法法院对这些问题做出决定,将意味着直接对产生财政预算的问题做出了决定,其政治合法性可能异常突出。在南非《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必须在其可利用资源的范围内采取合理的立法和其他措施,以逐步推进这项权利的实现”的情况下,如果宪法法院界定了权利的最低限度的核心义务,那么“可利用的资源”就不再构成社会经济权利的内在限制。因此,这将使得法院的行为具有太强的立法意味,这也是为什么南非宪法法院始终不愿界定社会经济权利最低限度的核心义务的重要原因,从而展现出既间接保护住房权等社会经济权利,又竭力与立法权、行政权相平衡的非凡司法技巧。
五、结语
据联合国定期发表的数字估计说,“全世界 10亿多人没有适当住房,另有 1亿人根本没有居室,更糟糕的是,在许多国家,每年有数百万人被强迫驱逐出自己的住宅和土地,使全球住房权危机雪上加霜”[19]。直到 2000年的格鲁特布姆案,南非宪法法院才第一次在世界历史上启用了一项或许能成功对住房权等社会经济权利提供司法保护的崭新方法[20]。尽管提出的“合理性审查标准”由于过于笼统而受到很多批评,但其扩张性解释对于那些生活在极度贫困状态中的人们还是有帮助的,因为这毕竟给予他们在社会经济权利方面享有司法救济的途径。对长期陷于严重种族隔离与激烈种族冲突的南非而言,对公民社会经济权利作如此高调的保障,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和宪法理念的飞跃。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以前早就有路了,以后也该永远有路。”[21]弱者坚强,勇气与汗水亦能折射出前进的方向。
[1]See Henry J.Steiner&Philip Alston,International Himan Rights in Context:Law,Politics,Morals.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298.
[2]See JeanneM.Woods,“Justiciable SocialRights as a Critique of the Liberal Paradigm”,38Texas InternationalLaw Journal(2003),p.786.
[3]Se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and Others v.Grootboom and Others,2001(1) SALR46(cc).
[4]黄金荣.司法保障经济和社会权利的可能性与限度——南非宪法法院格鲁特布姆案评析[J].环球法律评论,2006(1).
[5]Se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and Others v Grootboom,2001(1)SALR 46 (CC).
[6][20][美]凯斯·R.孙斯坦.设计民主:论宪法的作用[M].金朝武,刘会春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268-270,257.
[7]郑贤君.南非宪法法院社会权救济的法理[A].燕京法学 [C].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6.
[8][12]胡建淼.世界宪法法院制度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382,386.
[9]韩大元.外国宪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424.
[10]See Lyun Berat,Constitutional Court Profil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titutional Law,Oxford Journals Press 2005.
[11]郑贤君.基本权利研究[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505.
[13][挪威]艾德.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权利[M].黄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73.
[14]SeeMark S.Kende,“The South African Constitutional Court’s Construction of Socioeconomic Rights:a Response to Critics”,19 Conn.J.Int’lL. 617(2004).p.617.
[15]郑书前.公民社会经济权利宪法救济之中国路径——以南非宪法法院判例为切入点[J].行政与法,2008,(10).
[16]转引自龚向和.作为人权的社会权[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77.
[17]张雪莲.南非宪法法院的“合理性审查标准”介评[J].河北法学,2008,(11).
[18]杨福忠.从南非格鲁特布姆案看积极权利对立法者的义务[J].山东社会科学,2008,(1).
[19]S.莱基.适当住房人权[A].[挪威 ]艾德.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权利[C].黄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71.
[21]鲁迅.生命的路[A].鲁迅全集(第二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87.
责任编辑:邵东华
A Perspective of Judicial Protection of the House Right in South Africa through the Grootboom Case
Han Jing
(Law School,Southeast University,Nanking,Jiangsu211189)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of South Africa has established the“reasonable investigation standard”principle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Grootboom Case.Moreover,it grants the legislator the obligation of complying their positive obligation,choosing the relative rightswhen facing the choice of absolute right and relative right,and compromising when facing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governmental positive obligation of the house right.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urt has been criticized and argued,but it is a wise choice to consider the reality in South Africa and the capability of the court.It is a result of the wise balancing strategy,and it also provides tremendous experience for the judicial protection of the house rights and other soco-economic rights.
the Grootboom Case;socio-economic rights;house rights;South Africa
D923.9
A
1008-6951(2010)01-0155-06
2009-10-22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会权的可诉性及其程度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07CFX010)
韩敬(1978— ),女,河南新乡人,东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宪法与行政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