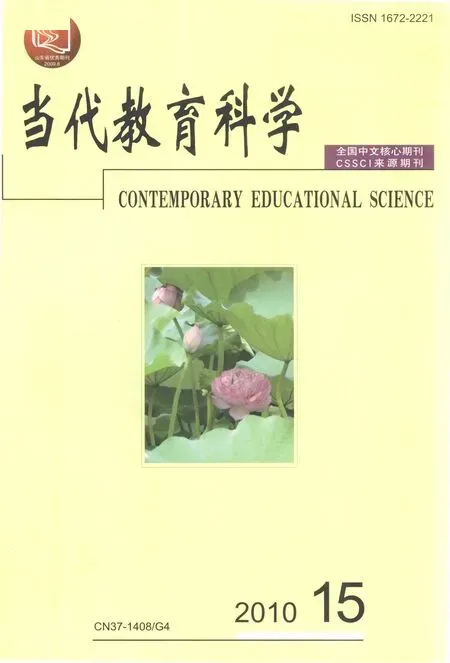布尔迪厄社会学思想的教育启示
● 王 军 查永军
布尔迪厄社会学思想的教育启示
● 王 军 查永军
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中含有大量的教育思想,对教育发展和教育研究有着重要的启发与引领价值。尤其是其论述的场域、惯习、资本等概念含有丰富的教育意义。资本尤其是文化资本量的差异造成了区隔,而现有教育将这些差异制度化、合理化。“场域——惯习”理论为教育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为实践层面的教育政策制定提供了理论依据。
布尔迪厄;社会学思想;教育
一、布尔迪厄提出的几个主要概念
布尔迪厄的社会学思想非常丰富,绝非一篇文章所能尽述。笔者觉得他所提出并作了较多论述的几个概念对学界的影响非常大,而且与教育理论研究及教育实践工作有着很大的关联性。
(一)场域
人们通常将场域与地域、区域等同。其实,这种理解违背布尔迪厄的本意。布尔迪厄在社会学研究中提出场域概念既受物理学中磁场论的启发(布尔迪厄在分析社会场域时就用过物理学中的磁场作比喻),也与现代社会高度分化的客观事实有关[1]。简言之,场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而不是一个地理空间。它是那种相对自由的空间,那种具有自身法则的小世界。“从分析的意义上来说,场域可以定义为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的网络或构型”[2]。所以,布尔迪厄的场域是由关系、网络构成的。
场域又由更小的子场域、亚场域构成,而且“每一个子场域都具有自身的逻辑、规则和常规”[3]。即,不同的子场域、亚场域之间具有相对独立性。在不同的场域之间,因为利益方面的原因常常引发争夺、冲突。“利益既是场域运作的条件,也是场域运作方式的产物。利益推动人们参与到特定场域的游戏之中,相互争夺。或者说,人们进入一个特定的场域,是因为相信其中存在着他们珍视的利益,比如在艺术场域是艺术感受,在宗教场域是宗教信仰”[4]。既然不同场域(子场域、亚场域)之间存在着相互争夺、冲突,那么,进行场域的划界就成为必需。然而,要做好这项工作决非易事。“场域的界限只能通过经验研究才能确定。尽管各种场域总是明显地具有各种或多或少已经制度化了的进入壁垒 (barrierstoentry)的标志,但他们很少会以一种司法限定的形式(如学术机构录取人员的最高限额——numerousclauses)出现。”用一句冠冕堂皇的话来说,“场域的界限位于场域效果停止作用的地方”[5]。
(二)惯习
布尔迪厄指出,场域不是一个“冰凉凉的”“物质小世界”,每个场域都有属于自己的 “性情倾向系统”——惯习(habitus)[6]。“惯习”是布尔迪厄社会学理论中的又一重要概念,它不同于“习惯”。“在布尔迪厄的心中,惯习至少有两层意思,即结构化了的结构(structured structures)和促结构化的结构(structuring structures)。所谓结构化了的结构,是指惯习源于早期的社会化经历,是结构的产物,为行动设置了结构性的限制;所谓促结构化的结构,是指惯习作为一种结构化的机制,是实践的生产者,为实践的生成提供原则”[7]。“习惯”只具有了第一层意思,即结构化了的结构,强调习惯是如何产生的,是一种结果。而“惯习”不仅是一种结果,同时还是一种促进发展、进步的力量。它主要通过家庭出身、学校教育、工作环境等因素,逐渐将个人所接触到的社会状况有意无意地内化到人的性情体系中,并长期持久地指导行动者的行为。
惯习是与客观结构紧密相连的主观性。惯习尽管是主观性的,但它绝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与客观外界接触、互动过程中逐渐形成并具有持续性、稳定性的一种主观性。与特定环境互动的主体既有个体也有集体,所以,惯习既是个人的又是集体的。即有置身于特定场域中的个体惯习,也有置身于相同场域中的集体惯习——各个个体共有的惯习。惯习具有历史性、开放性和能动性。“性情倾向在实践中获得,又持续不断地旨在发挥各种实践作用;不断地被结构形塑而成,又不断地处在结构生成过程之中”[8]。惯习就是一种社会化了的主观性[9]。“惯习”是人的主观心理状态,是人的社会行动、生活风尚、行为规则等实际表现及其精神方面的总根源。人们通过惯习的外在表现形式——气质、风格、个性、生活方式等,将自己与别人区别开来。场域与惯习关系紧密。惯习是场域中的惯习,场域是贯习的场域。惯习具有场域性,惯习只有在产生它的场域中发挥“如鱼得水”的作用。场域内没有与其他场域不同的性情倾向则无法区分,也不能构成独特的场域,不能保证自己的独立性。
(三)资本
资本原是经济学中最早使用的一个概念、术语,最初是指经济资本,随着其内涵的不断延伸,后来又有了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信息资本、人力资本等表述。布尔迪厄认为资本表现为三种基本形式,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还可加上符号资本。文化资本的概念源于布尔迪厄对教育系统的研究。最初提出这一理论假设,是为了解释不同社会阶级出身的孩子在学业成就上的差异。当然,布尔迪厄注重文化资本,更主要的是因为在现代社会,文化日益成为一种权力资源,投资者在文化市场中谋求利润的倾向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文化资本已然成为形塑和复制社会分层结构的关键因素[10]。在文字时代,文化资本是一种财富,是以教育资格的形式被制度化的。它可以转化为物质形态的东西;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借助于获得文凭等,拥有了符号暴力生产、传授的教育权威和文化专断。在布尔迪厄看来,文化资本可以三种状态存在,即:身体化的状态(the embodied state),表现为心智和肉体的相对稳定的性情倾向,比如言辞的流利、审美趣味以及通常所谓的教养,这种文化资本的获得往往是在耳濡目染中完成的,因而这种资本的传递要比经济资本的传递更为隐蔽和难以觉察;客体化的状态(the objectified state),表现为文化商品,诸如图书、工具、机器之类,它们是理论的印迹或实现,可以通过物质媒介来传递;制度化的状态 (the institutionalized state),表现为社会对资格的认可,特别是教育文凭系统所提供的学术资格[11]。文化资本的积累是处于具体状态之中的,即我们称之为文化、教育、修养的形式,它预先假定了一种具体化、实体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因为包含了劳动力的变化和同化,所以极费时间,而且必须由投资者亲历亲为,就像肌肉发达的体格或被太阳晒黑的皮肤,不能通过他人的锻炼来获得那样[12]。有关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少。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可以相互转化,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是以经济资本为基础的,同时,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繁荣与发展也在促进着经济资本的积累。文化资本有助于社会声望的提升,增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形成更强的社会关系网络。而强的社会资本能为文化资本的进一步积累提供机会和条件。
二、场域、惯习和资本对教育及教育研究的启示
(一)资本(尤其是文化资本)量的差异造成了区隔,而现有教育将这些差异制度化、合理化
家庭是文化资本生产的第一站,文化资本被有能力大量积累它的少数人垄断,凭借物以稀为贵的方式获得利润和效益。在不同家庭熏陶下获得的不平等文化资本,在学校教育中进一步受到制度化的保护。学校对来自不同家庭的学生一视同仁,从而默认了家庭传承的不平等文化资本的合法性。其实,文化具有区隔功能,不同文化背景、家庭背景、教育背景的人被划入不同组群之中,使得儿童的教育起点不在同一起跑线上。布尔迪厄认为,教育体制乃是文化再生产和社会等级结构得以延续的制度性基础。教育系统控制着文化资本的生产、传递和转化,因而乃是支配着社会地位、形塑着社会无意识的重要体制,也是再生产不平等社会结构的主要手段[13]。所以,教育系统不仅仅不是解放的力量,反而是将社会不平等合法化的工具,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保守势力[14]。教育是以合法(暴力)的形式生产和再生产着文化和社会的不平等。而教育权威是一种表现为以合法强加的权利形式实施符号暴力的权力[15]。实施一种教育行动的每一个当局(人或机构),强加的是一些集团或阶级的文化专断。只有当它根据这一专断确定的强加方式,以这些集团或阶级代理人的身份,即以受委托掌握符号暴力权力的人的身份的时候,它才具有教育权威[16]。
(二)“场域——惯习”理论为教育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
布尔迪厄的“场域——惯习”理论的方法论价值还没有引起教育研究者的关注。其实,“场域——惯习”理论对区分不同学科以及促进学科建设有着极强的适切性。学者非常热衷于用库恩的范式理论分析教育学及其分支学科建设等问题。范式理论是研究学科问题的一个视角,不过,它是一种静态意义上的方法论,而“场域——惯习”理论为研究教育学及其分支学科问题提供了更具动态的、充满活力的方法论。教育学及其分支学科建设更应关注该学术共同体内共同性情倾向的培养和共性话语系统的形成。此外,“场域——惯习”理论还为研究具体的教育理论和实践问题提供了方法论意义的指导。如教育系统内部不同分工人员和职责之间的关系和冲突的研究,完全可以用该理论来分析、研究和解决。譬如,大学系统中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的冲突研究,运用“场域——惯习”理论来分析,就可以发现大学学术系统和行政系统之间存在着惯习上的巨大差异,学者和行政人员有着差异极大的个体和集体性情倾向上的不同,如果仅仅从他们之间对利益的追求一个方面入手,对问题的分析就不够深入,最根本的是他们之间在文化(惯习)上的差异造成了彼此的冲突和矛盾。
(三)“场域——惯习”理论为实践层面的教育政策制定提供了理论依据
学校教育中占支配地位的是强势群体的文化,即在文化上占据主导地位的统治阶级 (阶层),以他们的思想和文化来要求全部的受教育者,这使得原本文化资本处于弱势地位的家庭的孩子处于更为弱势的地位,造成了教育的起点和过程的不公平,可想而知,教育结果必然也是不公平的。所以,简言之,文化资本的差异将导致社会区隔。人们往往认可文化资本的世袭传承,而不怀疑教育对文化资本等级的制度化再生产。
文化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有效而隐蔽地将支配与被支配的权力关系转换为社会成员甘心接受的自然现状。在现实社会中,某一类语言、文化类型,因其包含更多文化资本与符号资本,于是被社会行动者的“集体无意识”误认为更具有合法性、正当性。所谓文化正当性是权力者虚构和强加的,它本身绝不具备任何普遍价值与天然合法性[17]。其实,社会出身不同的个体在学术场的能力和获得的成果,与他们的出身状况是对应的。也就是说,一个出身于士绅门第的儿童和一个来自平民家庭的儿童,在最初的文化积累上是不平等的。教育(主要是学校教育)认同了文化资本的差异,并在强调教育公平的时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区隔,形成了符号暴力,即以强势阶级(阶层)的文化作为依据支配各个层次的受教育者。不同背景人员文化资本的巨大差异以及现实教育生活对强势文化资本的认同、接纳、强化乃至制度化,对文化资本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员是极其不公平的,也不利于多元文化的建设。因此,教育政策制定者可以运用政策手段对弱势者进行必要的、恰到好处的补偿,如美国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实施的 “肯定性行动计划”,尽管存在着争议,但这种补偿性政策有助于多元文化建设和提高少数族裔和有色人种的文化资本的质和量。
[1][6]毕天云.布尔迪厄的“场域-惯习”论[J].学术探索,2004,(1):32-35.
[2][4][7][10][11][法]皮埃尔·布尔迪厄.科学的社会用途[M].刘成富,张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13,15,20,17,17.
[3][5][8][9][法]皮埃尔·布尔迪厄,[美]华康德.李猛,李康译.实践与反思[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142,138,165,170.
[12][法]布尔迪厄.包亚明译.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13][14]朱国华.权力的文化逻辑[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84,89.
[15][16][法]P.布尔迪厄,J.C.帕斯隆.邢克超译.再生产[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1,33.
[17]张怡.文化资本[J].外国文学,2004,(4):61-67.
王 军/扬州大学旅游烹饪学院讲师,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查永军/扬州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大学教学和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责任编辑:刘丙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