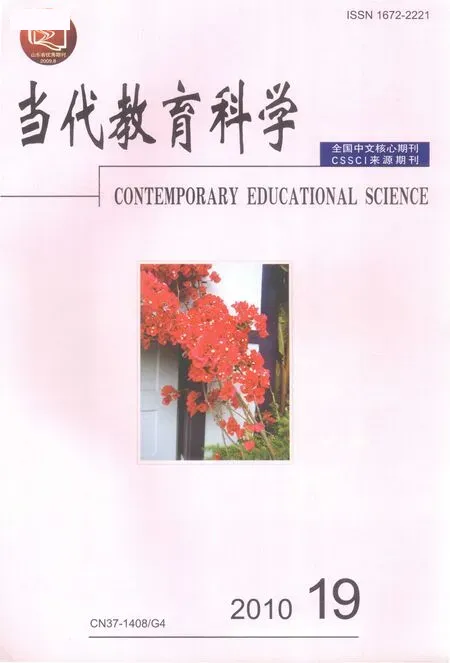美国“以科学为本的研究”评析
● 苏贵民 林克松
美国“以科学为本的研究”评析
● 苏贵民 林克松
2001年,美国联邦政府在所颁布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中公开提倡“科学为本的研究”,明确要求接受联邦政府资助的教育研究项目必须提供科学的研究证据以证明其有效性,并表态只资助那些实验研究和准实验研究。“以科学为本的研究”的推行引发了美国诸多教育研究组织及人员对它的争议性讨论,并对美国的教育研究趋势和方法产生了系列微妙的影响。
教育研究方法;美国;NCLB;“以科学为本的研究”
2001年,美国政府颁布了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以下简称 NCLB),其中有条款对教育研究重新提出了要求,即倡导“科学为本的研究”(Scientific Based Research)。这一由政府主导的政策,表现出希望教育政策具有科学依据的强烈愿望,希望能够接受联邦资助的项目和研究必须提供科学的证据以证明其有效性。“以科学为本的研究”这一政策并非出自美国教育研究者共同体的自然选择,且与当前教育研究的发展潮流明显抵牾。为此,探究这一政策的内涵、出台的背景及其产生的影响,有助于揭示美国政治与教育研究的微妙关系以及美国政治脉络下教育研究方法的发展走向。
一、“以科学为本的研究”的内涵
进行科学为本的研究是2001年颁布的NCLB这一法令对接受联邦资金资助的教育研究的要求。这一法令第一次将教育实践应当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这一理念变成联邦教育立法的核心特征。在NCLB法令中,“以科学为本的研究”这一术语总共出现了110多次,足见教育立法者对科学为本研究的渴求。NCLB的立法者将“以科学为本的研究”界定为“运用严谨、系统和客观的程序,来获取与教育有关的活动和计划的可靠有效数据。”随后,NCLB立法者用六条标准详细阐述了“以科学为本的研究”的内涵。这六条标准的内容如下:
1.运用观察和实验等经验、系统的研究方法的研究;
2.用严格的数据来验证假设和证明一般结论的研究;
3.运用测量和观察的方法提供可靠有效数据的研究。研究中同一评价者和观察者以及不同的评价者和观察者需要多次评价和观察来收集数据;
4.使用实验设计和准实验设计的研究。在这些设计中,个体、全体、机构或活动被分配到不同的控制条件下来评估研究者感兴趣的条件所引发的效应。这些实验设计中优先考虑随机分配的实验,或者其他包组内和组间条件控制的实验设计。
5,要充分、清晰地呈现实验研究,确保研究可以被重新验证,或者至少确保研究有助于系统建构其研究领域的发现。
6.研究能被运用同行评价的杂志或者独立的专家委员会,经过相对严格、客观和科学的评价后接受。
可以说,“以科学为本的研究”的内涵反映的是科学主义的立场,清晰地表达了美国政府希望将联邦的经费投入到那些“有用”的教育研究课题和项目上,以帮助学校和学生提高学业成就的“良苦用心”。“以科学为本的研究”明确地区分了“有用”和“无用”的教育研究,即符合上述6条标准的才是“有用”的教育研究,否则就是“无用”的教育研究。显然,“以科学为本的研究”倾向于认可那些涉及因果关系的问题和那些运用观察、实验和测量来收集数据、能准确识别因果关系的实证研究,而那些不明显具备这一功能的研究方法,诸如个案研究,人种志研究、历史研究、叙事研究等都被排除在外,且连一些属于实证主义阵营的方法,诸如调查和相关研究都未能幸免。
二、“以科学为本的研究”出台的背景
“以科学为本的研究”的政策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1998年出台的 “优异阅读法案”(Reading Excellence Act),从那个时候起美国联邦政府就开始增加对那些客观的、可靠的研究项目的资助。2002年,随着教育科学改革方案的通过,美国联邦政府明确表态只资助那些实验研究和准实验研究。[1]
美国国家教育法律中(NCLB)对“以科学为本研究”的强化,凸显的是教育政策制定和教育研究之间的微妙关系。对于教育政策制定者而言,作为教育研究结果的主要“消费者”,其往往会从党派或者自身政治利益出发,试图制定出让公众满意的教育政策,而这就需要教育政策制定者及其智库查阅和综合整理相关的教育研究文献,衡量和评估某些政策、学校和项目的效能,且尤其需要那些能揭示因果关系的文献,尤其需要“以科学为本的研究”这样的评价和比较标尺。而现实的情况是,作为教育研究成果的“提供者”,美国的教育研究由不同机构的人员来进行,主要有大学的研究人员、智库和公司、学校等,这些机构和人员的关注点和诉求都不一样,教育研究者往往强调教育研究背景的独特性和唯一性,不愿意做大规模的实验研究和验证研究,其研究的领域和成果与涉及公众利益的教育政策制定关系往往不是很紧密,研究者得出的结论往往不明晰,无法比较和验证,更不能揭示因果关系,这就导致了教育研究的成果不能顺畅地转化为教育政策。正是由于“供需双方”——教育研究和教育政策制定之间的不协调关系,才让美国国会通过倡导“以科学为本的研究”的新法令来刺激和推动教育研究向着立法者所希望的方向——科学为本的研究发展。
三、教育研究组织和人员对“以科学为本的研究”的反应
“以科学为本的研究”出台之后,引发了一些讨论和争议。一些专业组织和专业人员,纷纷从各自的立场和角度出发,对这一政策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和反应。
1.教育研究组织的反应
美国最大的教育研究专业组织——美国教育研究协会在2008年6月对NCLB中的 “以科学为本的研究”定义做出了回应,该组织认为国会近年来在运用“以科学为本的研究”时经常出现狭隘化和不一致,因此试图用自己的定义和框架来为国会立法中运用这些术语提供真正的指南。[2]该组织分别界定了科学研究的原理和“以科学为本的研究”两个术语,其对“科学研究”的理解与NCLB别无二致,分歧出现在“以科学为本的研究”究竟应该包含哪些研究类型这个问题上。与NCLB只认可应用研究、推崇实验设计和准实验设计的研究不同,该组织认为“以科学为本的研究”应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评价研究,除了实验设计和准实验设计等研究设计之外,还存在其他符合科学原理的实验设计,包括纵向设计,有控制的个案研究和时间序列设计等。美国教育研究协会委婉地批评了美国教育政策法规制定者不恰当地理解了“以科学为本的研究”,并将“以科学为本的研究”的内涵进行了适当的拓宽。
2.教育研究者的反应
教育研究者对这一政策的反应,根据其所持的价值立场和研究方法论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一些研究者试图超越具体研究方法的争论,认为方法本身没有什么好坏、科学和非科学之分,判断研究是否科学主要看研究者是否选择和运用了恰当的方法来研究特定的问题。那些坚持实证主义方法论和科学研究方法的研究者自然是乐于接受这样的政策的,其乐于看到联邦的教育政策支持和强化教育研究中大量运用科学方法;此外,那些强调教育研究情景脉络独特性的质的研究者,则对此表示出一些担忧和不满,认为这一政策是政治影响和左右教育研究学术自由的铁证,其缩小了教育研究的范围和领地,不利于教育学术研究的繁荣和发展,根本就不值得支持和提倡,他们担心立法者的好意以及对教育科学方法的狭隘理解会让“以科学为本的研究”走上歧途。[3]除了表明自己的立场之外,有研究者带着批判和怀疑的立场,对“以科学为本的研究”及其NCLB本身进行了审视和研究,从更加理性的角度探讨了这一政策。有细心的研究者用统计的方法发现NCLB在运用 “以科学为本的研究”这一术语中经常出现前后不一致,内涵和标准变换不定的情况,而且立法者在引用的参考文献中,并不总是引用那些符合“以科学为本的研究”的文献,研究者将这一问题的原因归结为美国两党政治利益的博弈与妥协。
四、“以科学为本的研究”对美国教育研究的影响
“以科学为本的研究”倡导科学为本的教育研究,按照立法者的预期,应该是推动教育研究向美国实证的方向发展,为决策者提供大量有用可靠的研究结果,以便立法者立法时参考和采用,进而大面积提高学生的学业成就,缩小不同族群学生学业成绩之间的差异。但是这些预期的结果是否发生,还需要深入探讨。
就“以科学为本的研究”对教育研究的影响而言,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考察:一是看政策颁行后教育研究者对于“以科学为本的研究”的关注程度;二是考察教育研究中运用科学方法的情况。
首先,NCLB颁行后以“以科学为本的研究”为题的论文数量明显增加。关于“以科学为本的研究”的相关政策颁行后,检测教育研究者对于政策关注程度的一个合适指标就是看相关论文的发表数量。有研究者统计分析了美国《教育周刊》(Bducation Week)和主要媒体上以科学为本的研究为主体的论文,结果发现2000年以前,《教育周刊》中以科学为本的研究为题目的论文均为零,而自从NCLB颁布之后,相关的论文大幅度增加,2002年就增加到16篇之多,之后每年一直稳定在15篇左右,而美国的主要报纸也是在2001年之后才开始关注这一问题。[4]可知科学为本的研究也是研究者和公众较为关注的话题,这一政策对研究者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其次,美国近几年来在教育研究中运用“以科学为本的研究”的状况并无明显变化。美国联邦政府的立法者希望通过拨款来引导教育研究者多运用“以科学为本的研究”来进行教育研究,但是实际的状况并不让立法者满意。“对教育研究相关的杂志和美国教育研究协会(AERA)年会中项目的粗略考察后发现,很多教育研究既没有什么结果,也没有运用那些支持因果关系推论的方法。尽管强调和重申随机抽样的研究设计和运用复杂的准实验方法的研究,但是在整个教育研究中,像别的研究领域那样符合严格科学标准的教育研究还是非常少。”[5]
出现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有三种:一个原因是美国联邦政府教育权比较有限,一般只能通过拨款的方式来调控教育研究,无法在更深层次上运用行政的力量,来控制和要求全美整个的教育研究朝着“以科学为本的研究”的方向发展;另一个原因是美国作为一个价值多元化的社会,一直在倡导和鼓励不同观点的存在和发展。反映在教育研究领域,表现为除了实证主义的科学研究之外,还存在众多价值取向的教育研究及其支持者。美国有众多的民间基金会,他们对资助教育研究也有兴趣,也不会像联邦政府这样限制教育研究者的专业自主权。美国联邦政府只资助“以科学为本的研究”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众多的研究者开始转向这些基金会寻求项目资助。此外,从具体的经费投入上来看,联邦政府所投入教育研究经费本来就有限,实际操作中又被分为两大块,一块是用于资助“研究”,包括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其中只有一半左右的经费被用来资助运用“以科学为本的研究”的应用研究,只有不到3.5%的经费被用于资助基础研究;另外一块就是“开发”,大约一半的经费则被用来资助“开发”——讨论新的观念,并将这些观点转化为某种有用的材料、设备,系统和方法等。由于限制众多,干预教育研究者的专业自主权,加上经费投入有限。导致“以科学为本的研究”对教育研究者的吸引力不够,政策的效果大大不如预期也就很好理解。
目前,NCLB还是法律,仍然有效。但日前传出消息,鉴于NCLB实施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奥巴马政府已经将修改布什政府任期内通过的NCLB提上了议事日程。就“以科学为本的研究”来说,其效果也不如人意。教育研究方法经过多年发展,早就过了实证主义方法一统天下的时代,而美国相关政策制定者和立法者从自己的需要和价值观出发,要求教育研究运用严格的实验方法来进行并提供有数字支持的研究结论,显然这与当前教育研究方法的发展趋势是背道而驰的。
五、对“以科学为本的研究”的审视
显然,“以科学为本的研究”所投射出的实用主义和实证主义的价值立场,大大地缩小了教育研究的问题领域和方法范围,其可谓深深地误解了教育研究。一方面,在教育研究中,不可能像其他自然科学领域那样运用严格的实验程序来进行真实验研究,而准实验研究的效度也是经常遭受质疑;另一方面,决定用什么研究方法的关键要素是看要研究什么样的教育问题。教育问题多种多样,不全是与因果关系相关的问题,故不可能要求所有的教育研究都采用实验设计或者准实验设计。事实上,在美国教育研究界,连那些鼓吹“以科学为本的研究”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立法者用科学方法作为推动教育政策和实践的关键因素,但是给出研究方法的处方和判断研究质量的标准多少都有点危险。[6]另外,美国的立法者最为关注的是社会公平问题,但是这一问题显然不能只依靠实验研究提供的有限结论来解决。
作为教育研究者而官,自主决定所要研究的问题和方法,而不需要法律来干预,这是研究者专业自主权的基本保障。因此,在考察教育研究和教育政策制定之间的关系时,不能用简单的线性思维和几个成功的个案出发来看待它们之间的关系。现实情况是,追求“理想”的教育研究成果很难渗入追求实际的立法系统,教育研究对于立法和政策的影响是间接和渐进的。教育研究者不可能为政策制定者提供简单明确的“处方”,教育研究者的使命是运用自己的智慧和实践,持续地推动教育研究领域的繁荣和深化。
[1]Fenwick W.English,Gail C.Furman.Research and educational leadership:Navigating the New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Guideline[M]s.Rowman and Littlefield Education,2006:62.
[2]AERA(2008)Definition of Scientifically based research.http://www.aera.net/Default,aspx?id=6790&terms=“SBR”.aprrl 20,2010.
[3][6]Michael J.Feuer.Scientific culture and education research[J].Educational Researcher,2002,31(8):4.
[4][5]Frederick M.Hess When Research Matters:How Scholarship lnfluences Education Policy[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8:198.
苏贵民/西南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课程与教学论、学前教育 林克松/西南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课程与教学论
(责任编辑:刘丙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