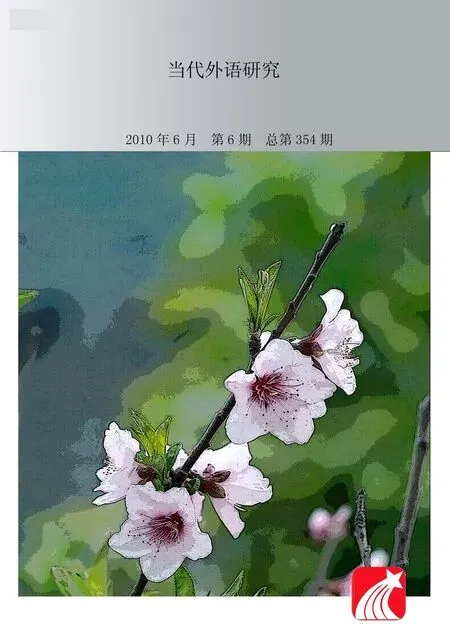驭生之力量,赴死之权利
——论《达洛维夫人》中的权力关系
陈润平
(江西财经大学,南昌,330032)
在《达洛维夫人》(Mrs.Dalloway)①中有两个主要人物,即克拉丽莎(Clarissa)和塞普蒂默斯(Septimus)。作者把他们平行并置,用一种精致而深奥的叙述模式构建这部小说。克拉丽莎沉湎于个人的生活——与彼得(Peter)的爱情,与理查德(Richard)的婚姻,而塞普蒂默斯则饱受战争和死亡的痛苦,尤其是埃文斯(Evans)——他的战友,也是他最亲密的朋友,死于战场。书中既展现了小说人物之间的权力关系,也展现了个人与现实之间的权力关系。“在整部《达洛维夫人》中,焦点不断地从外部世界转移到感受外部世界的人物内心世界”(Dick 2001:52)。其中主要的权力关系是爱情与婚姻之间的关系、外部世界与人物内心世界之间的关系。其中,情人或夫妻之间的关系是这部小说的重要元素。情人或夫妻遵循一定的权力关系生活在一起,相互影响。另外,在这部小说中,医生与病人之间,即霍姆斯博士(Dr. Holmes)、威廉·布拉德肖爵士(Sir William Bradshaw)与塞普蒂默斯之间,存在心智健全与心智异常的对立关系。在权力关系的较量中,克拉丽莎和塞普蒂默斯其实是在和生与死的冲突作斗争。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关于权力的观点主要聚焦在对权力的操控上。他研究了理性与疯狂之间、同性恋与异性恋之间的权力关系,“当它〔笔者注:权力〕凌驾于生命之上,在权力展现的整个过程中,这种权力建立起它的统治地位;死亡是权力的制约,是逃避它的时刻;死亡成为存在的最隐秘的东西,是最为‘私密的’”(1998a:138)。《达洛维夫人》作者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在该小说中展现了上述两类权力关系。通过对《达洛维夫人》中权力关系的福柯式分析,本文阐述该小说的深层意义,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主人公克拉丽莎和塞普蒂默斯怎样在生与死的冲突中挣扎和斗争。
1. 《达洛维夫人》中的权力关系分析
根据福柯(1998a:92)的论述,“对我来说,权力首先必须被理解为内在于一定范围内,实施操控的力量关系的多重性,并且构成它们自身的组织”。伍尔夫在这部小说中展现了异性恋与同性恋、理性与疯狂的权力关系和权力冲突,具体来说,前者涉及有关爱情与婚姻的社会规范,后者则是医生与病人之间“权力—知识”的关联。在现实生活中,爱情和婚姻的社会规范制约并影响着男人和女人彼此的生活与选择。通常,异性恋规范对同性恋行为实施权力制约和影响,同样,理性对疯狂施加权力制约和影响。由于权力“作为过程,通过不断的斗争、对峙、转变,使各力量得到加强,或转化为其对立面;作为支持,这些力量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作为策略,他们通过策略发挥作用”(同上),因此,该小说中主人公如何面对上述权力关系,并与之抗争,形成了他们在现实中的命运。当克拉丽莎和塞普蒂默斯在生活中遭遇权力关系冲突时,他们采取了不同的行动。塞普蒂默斯用自杀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以此作为他对强加于他的各种权力的抵抗,从而保留他对死的权利;相反,克拉丽莎维持着她的生活方式,继续忍受各种权力对她的控制。
1.1 异性恋vs.同性恋(爱情与婚姻的权力关系)
“性被小心翼翼地压抑着,它转移到家中”(Foucault 1998a:3)。福柯的解释是,我们倾向于认为我们的性能力被那些禁止我们性开放的社会力量压制着,“夫妻间的性爱曾被劝告和规定困扰,婚姻关系成了最强烈的制约焦点”(37)。谈及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权力关系,焦点就在爱情与婚姻关系上。生活中,人们面临着异性恋或同性恋的问题,“有两种西方人所确信的伟大制度来约束性:婚姻法和性欲禁令”(39-40)。这种现象常常向我们展现了夫妇或情人间的关系以及相应的权力行使。大多数人遵循异性恋的规范,并受这样的社会规范或惯例的支配。在《达洛维夫人》中,作者所展现的主要的权力关系之一是爱情和婚姻:一是克拉丽莎婚前与男友彼得的恋情;二是两对夫妇的婚姻,即克拉丽莎与理查德,塞普蒂默斯与雷兹娅(Rezia)的婚姻。另外,这两对夫妇情感上都受到了同性恋关系的威胁。在该小说中,作为权力关系,是彼得威胁着克拉丽莎与理查德的婚姻,同样,埃文斯威胁着塞普蒂默斯与雷兹娅的情感和爱情。
首先,爱情与婚姻相关的权力冲突支配着主人公的爱情与婚姻的选择和决定。譬如,克拉丽莎和彼得都受控于爱情与婚姻相关的权力冲突。由于社会偏见与习惯的影响,克拉丽莎拒绝了彼得的追求和求婚,这体现了她对爱情与婚姻的态度。尽管克拉丽莎与彼得彼此相爱,却最终难成眷属。“因为一旦结了婚,在同一所屋子里朝夕相处,夫妻之间必须有点儿自由,有点儿自主权。这些,理查德给了她,她也给了他……但要是跟彼得的话,一切都得分摊,这令人难以容忍”(Woolf 1964:10)②。克拉丽莎拒绝彼得而选择与理查德结婚,体现了她倾向于服从和遵循世俗对婚姻的考虑:让金钱与社会地位来决定对婚姻的选择,“萨莉(Sally)说,克拉丽莎骨子里是个势利鬼——谁都不可否认这一点,她是个势利鬼”(210)。她甚至瞧不起好朋友萨莉嫁给一个地位卑微的矿工的儿子,“克拉丽莎认为,她嫁给那男人有失身份”(同上),尽管她曾经挺喜欢萨莉——“回首从前,她对萨莉的感觉是那样纯洁、真诚”(39)。显然,克拉丽莎认为,嫁给政府职员理查德远比嫁给彼得有奔头。影响克拉丽莎的婚姻选择的另一个因素是恋人之间的权力斗争。彼得总在克拉丽莎面前耍弄小折刀,这一举动象征着他的男性权力和优越感。当这对恋人重逢,彼得突然感到“一阵窘迫……他把手插入裤袋,掏出一把大折刀,刀口半开着”(46)。当克拉丽莎在缝补她的衣裳时,彼得“将折刀斜向她的绿衣裳”(同上)。这一行为一方面透露出他对人或对某种局面的权力欲望;另一方面“总让人感到自己也变得轻佻;头脑空虚;只不过是个傻乎乎的话匣子,如他向来所说的”(49)。克拉丽莎很反感彼得耍弄小折刀的习惯,她当面反对他,并抑制不住愤怒地冲他喊:“看在上天的分上,改改你的恶习!”(52)。另外,克拉丽莎认为彼得总在对她指指点点,横加批评,所以她无法接受他和他的所作所为。“她从眼梢上瞥见彼得,站在那里,在那个角落里,显然对她不以为然”(185)。这对恋人知道彼此的近况——开始新恋情或步入婚姻之后,都显得矛盾而又心怀忌妒。那是怎样一份忌恨啊,“他恋爱了!可不是和她”(51)。不管怎样,克拉丽莎下意识地仍希望彼得能够出席她的晚会,她冲他喊道,“彼得!彼得!我的宴会!别忘了我家今晚的宴会!”(54)克拉丽莎或许认为彼得仍在对她施加某种权力和影响,她寻思着,“但他为什么只是为了指责批评而来?为什么总是索取,从不给予?”(185-6)。这对恋人的这种进退两难的情感,是他们无法逃避的惩罚。这是他们爱的权力斗争。
其次,在《达洛维夫人》中,克拉丽莎与理查德、塞普蒂默斯与雷兹娅两对夫妇的婚姻体现了异性恋施加给同性恋的权力影响。故事中,克拉丽莎和塞普蒂默斯都表现出同性恋情感倾向,但最后都放弃了,而选择了异性恋爱情与婚姻。这点表明这两位主人公无法回避婚姻和异性恋的社会规范。婚姻关系“时时受到密切的监视”(Foucault 1998a:37)。主人公处在异性恋与同性恋的权力斗争中。克拉丽莎与萨莉的友爱如此亲密,甚至让彼得产生了忌妒和仇恨:“她觉察到了他的敌意,他的妒忌;以及他要介入她与萨利之间的决心”(Woolf 1964:41)。对两位女性来说,克拉丽莎送给萨莉一件礼物——一枚钻戒是“无价之宝”,“那是神灵的启示,宗教的感情”(40)!克拉丽莎有一种冲动想和萨莉单独呆在一起:“萨莉停了下来;摘了一朵花;吻了她的双唇。整个世界宛如天翻地覆!别人都消失了,只有她和萨莉”(同上)。然而,克拉丽莎不能那样做,并且,“唯有她知道多么与众不同,多么互不相容,它们组合起来,以致这世界仅仅成了一个中心,一颗钻石,一个坐在客厅里的女人……”(42)。在现实中,克拉丽莎不能回避异性恋的权力影响,因为“异性恋法典排斥非异性恋的做法与身分”(Rivkin和Ryan 1998:347)。
作为克拉丽莎的丈夫,理查德爱他的妻子,但却对表达爱意感到别扭。他不愿表达对她的爱,“只是握住她的手。这就是幸福,他想道”(Woolf 1964:132)。作为一名政府职员,理查德必须经常外出,出席政务会、委员会等一些重要的会议。他给了克拉丽莎一个相对宽松、轻松的生活氛围。尽管他们已结婚,克拉丽莎仍保留着个人的空间与隐私。一方面,嫁给理查德满足了克拉丽莎的欲望和自我决断;另一方面,他们无法回避男女双方在婚姻生活中的权力斗争。理查德“在外意气风发,游刃有余”,并且见多识广,这点比他妻子强很多,因而他能够居高临下地“叫克拉丽莎别傻了”。对克拉丽莎来说,似乎“那就是她喜欢他的地方,或许——那就是她所需要的。‘喂,亲爱的,别傻了,握住这个——把那个拿来’”(83-4)。她很清楚她的婚姻处境,对此也保持了足够的理性。对她来说,“当然,有许多是达洛维的观点,诸如热心公益、不列颠帝国、关税改革、统治阶级的精神,所有这些在她身上潜移默化,熏陶颇深”(86)。无论如何,尽管克拉丽莎与萨莉甚为亲密无间,但她依然遵循异性恋和婚姻的社会规范,嫁给了理查德。
同样,对塞普蒂默斯来说,他对朋友埃文斯的爱与回忆,表现出和克拉丽莎与萨莉之间那种相似的同性恋情感。他的情感世界同样体现出同性恋与异性恋的情感斗争。塞普蒂默斯对埃文斯始终保持着一种情感寄托,以至于这份情感影响了他的生活。战争中埃文斯的死使他痛苦,精神恍惚,从此失去了爱的感觉。起初,塞普蒂默斯“长得很有男子汉气概;得到晋升;还受到上司埃文斯的青睐,甚至钟爱”(96)。后来,埃文斯的死让塞普蒂默斯深感震惊,使他精神崩溃。“当埃文斯死了,……塞普蒂默斯却显得无动于衷,或者意识到这是一份友谊的终结,反而庆幸自己能泰然处之,颇为理智”(同上)。塞普蒂默斯的痛苦挥之不去,埃文斯“这个死者与他作伴了”(103),“是啊,外面有个人,大概是埃文斯”(同上),他总是产生幻觉。自那以后的一切对塞普蒂默斯和他的妻子来说真是糟糕透顶,两口子再也没有了幸福的生活。尤其是雷兹娅,婚姻使她备受折磨,必须时时照看着丈夫。“但她自己没什么过错;她爱过塞普蒂默斯;她得到过幸福;她曾有个美满的家……为什么她要这样遭罪?”(73)当塞普蒂默斯“对她蹙眉,离开;又指着她的手,拉着她的手,惊恐地看着”,她甚至这样猜想:“是不是因为她摘下了她的结婚戒指?”(75)“他甩掉她的手。他们的婚姻完了,他想,带着痛苦,带着解脱”(同上)。虽然雷兹娅感到痛苦不堪,但一直爱着塞普蒂默斯,以妻子的责任悉心照看他,时时处处保护着他,“没有他,就没有什么能够使她幸福了!”(27)
1.2 疯狂vs.理性(外部世界与内心世界的斗争)
塞普蒂默斯与医生霍姆斯博士、威廉爵士之间的关系是典型的病人与医生之间的关系。通过这种医患关系该小说向读者展现了塞普蒂默斯与医生间的权力冲突和斗争。医生因拥有医学知识而显得自傲、武断,对病人采取绝对的控制权。塞普蒂默斯与医生间的权力对峙体现出一种疯狂与理性的权力斗争关系。
塞普蒂默斯患上了“炮弹休克症”(士兵因久战而患的一种神经病),再也不能感觉到现实中的一切。他似乎生活在幻觉中,而医生们则生活在现实中,充满理性。医生和病人形成了理性与疯狂的对峙,到底谁更清楚现实的真面目呢?塞普蒂默斯亲历了战争的恐怖和失去好友的悲痛。他会突然变得激动起来,“呼叫着说他知道真相!他知道一切!那个人,他的那个被杀死的朋友,埃文斯,来了!”(155)。然而,“霍姆斯博士和威廉·布拉德肖爵士都说对他健康最有害的是兴奋”(同上)。医生充满了理性看待病人,威廉爵士告诉塞普蒂默斯,“那是我办的一个疗养院,在那里我们将教会你休息”(108)。医生的判断和安排似乎不容怀疑。而塞普蒂默斯有他自己的判断:“你一旦失足,塞普蒂默斯反复告诫自己,人性就会揪住你不放。霍姆斯和布拉德肖都不会放过你的,他们搜遍沙漠,他们尖叫着飞越荒野……人性残酷无情哪”(同上)。他抵制医生对他的治疗。威廉爵士却享受着自己凌驾于病人身上的权力:“对这样一些病例,威廉爵士有着三十年的治疗经验,他以一贯正确的直觉得出结论,这便是疯狂,这种观念,他那平稳的观念”(110)。他的职业行为不无讽刺地表明,“威廉爵士完全能控制自己的行动,而病人则不能”(112)。正如福柯(1998a:142)所指出的,“生存的事实……其中部分成为了所控制的知识领域和所介入的权力范围的一部分”。医生制定心智健全的标准为“官能平衡”,而理性则是“关于不着边际练习的一套表演技巧或语言,在历史进化的知识统治方式中,在它们自身中间形成一致性规则,福柯把它叫做‘知识’(epistemes)”(Rivkin和Ryan 1998:336)。“约莫两三分钟(在粉红色卡片上写上问题的答案,谨慎地咕哝着)”,塞普蒂默斯就被威廉爵士诊断为“一种彻底崩溃的病例——身体与神经全面衰竭,每个症状都表明病情严重”(Woolf 1964:106)。威廉爵士行使他的权力,谴责说“他[笔者注:塞普蒂默斯]犯下了可怕的罪行,被人性判处了死刑”(同上),虽然塞普蒂默斯的妻子雷兹娅确信,“他压根儿没做错什么”(107)。
不管怎样,塞普蒂默斯经历了血腥的战争,他声称他知道真相,看见现实中的人性,“他知道他们所有的心思,他说;他知道一切。他知道这个世界的意义”(75)。他的疯狂象征着他想漠视人性的邪恶但却无法做到。他常常敏感、浮想联翩,深感恐惧。他无法抹去战争经历的梦魇。他在医生施加的权力支配下,努力挣扎,不让医生们帮他找回感觉官能,把他带回到现实中来。这种病人疯狂与医生的理性之间的冲突正是人物内心世界与他所在外部世界之间相互斗争的具体展现。
2. 对权力的反抗(生之力量与死之权利)
生活中,克拉丽莎和塞普蒂默斯都遭遇了权力冲突。“权力不是简单地作为职责或禁止对那些‘未享有权力者’来行使;它对他们投资,被他们传输,以他们为媒介;它对他们施加压力,正如他们自己那样,在与它的抗争中,反抗权力对他们的控制”(Foucault 1998b:465)。现实生活中,爱情与婚姻的社会规范深深地影响着每个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通常,人们用异性恋规范对同性恋行使权力支配,同样,理性对疯狂行使权力。“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反抗,甚而,或更加可能出现的,这种反抗从未处于与权力相关的外在性位置”(Foucault 1998a:95)。小说中主人公克拉丽莎和塞普蒂默斯以不同的方式面对和反抗施加在他们身上的权力关系,导致了他们在现实中不同的命运。在遭遇权力冲突时,塞普蒂默斯用自杀结束了他的生命,作为对强加于他身上的权力的反抗,保留了死的权利;而克拉丽莎则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忍受着施加给她的各种权力显示了一种求生的无奈。
在某种意义上,小说中克拉丽莎和塞普蒂默斯的生活际遇都涉及到现实生活中的人性。在时间和空间上,作者把塞普蒂默斯的生活与克拉丽莎的生活作为两条平行线索安排,前者经历了战争的残酷,对现实感到痛苦和绝望;后者在看似平静的生活中目睹真实生活的空虚和无意义,他们的命运有着内在的、异曲同工的一致性。塞普蒂默斯表现得神经错乱,但“当他将要死时,塞普蒂默斯看上去是心智最健全的”(Dick 2001:56)。他呼喊,“他落在他们手掌中了!霍姆斯和布拉德肖抓住他了!那长着红鼻孔的畜生把鼻子伸到所有的阴暗角落!”(Woolf 1964:163)克拉丽莎内心的沮丧就像塞普蒂默斯被什么人、什么事俘虏那样的情绪一样。当关于塞普蒂默斯的噩耗传来,“噢!克拉丽莎想道,在我的晚会进行中间,死神闯进来了,她想道”(203)。仿佛死讯提醒了克拉丽莎关于她与塞普蒂默斯之间的某种联系。“不知怎的,她觉得自己和他象得很——那杀死自己的年轻人。他那样做了,她觉得高兴;他抛弃了生命,而她们却依然活下去”(206)。塞普蒂默斯这个角色,“伍尔夫1928年在该书的介绍中说,是克拉丽莎的‘孪生型’”(Dick 2001:53)。他因内在的、扭曲的现实而痛苦,他的命运就好像是克拉丽莎命运的“孪生型”。但最后,塞普蒂默斯以结束自己的生命向他饱受折磨的灵魂投降,而克拉丽莎则无法逃离她的过去与现实生活,沉湎于回忆,抑郁寡欢。
3. 结语
米歇尔·福柯关于权力的观点聚焦在权力的行使上,他既研究了异性恋与同性恋间的权力关系,也研究了理性与疯狂之间的权力关系。伍尔夫在小说《达洛维夫人》中展示了异性恋与同性恋、理性与疯狂这两类权力关系。前者与爱情与婚姻的社会规范问题有关,后者体现“知识-权力”的内在和外在关系。权力关系方面的相似可以看作是在小说中平行展开的克拉丽莎和塞普蒂默斯的故事的联结点,使整部作品完整、有机地构建了起来。“而且伍尔夫感兴趣的是在他们彼此孤立的形式下,她作品中的各个人物具有的共性”(Briggs 2001:76)。这样的权力关系为该小说中平行叙述的克拉丽莎和塞普蒂默斯各自的故事在作品中联结与整合提供了基础,使小说故事情节和线索复杂多变,相互交错,引人入胜。通过分析《达洛维夫人》中的福柯式权力关系,能更好地帮助读者理解主人公克拉丽莎和塞普蒂默斯的人生遭遇和命运,以及他们怎样在生与死的冲突中挣扎、反抗。塞普蒂默斯以自杀作为反抗,保留了死的权利;克拉丽莎选择忍受,体现了生之力量。因此,这部小说向读者揭示了人性的堕落以及战争给普通人带来的不幸与毁灭。
附注:
①Mrs.Dalloway小说译名国内学界译法不一,有《达洛维夫人》、《达洛维太太》、《达洛卫夫人》、《达洛威夫人》等等,本文取国内较常见译法。
② 本文所引小说内容参考了孙梁、苏美译的《达洛卫夫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谨此致谢。
Briggs, Julia. 2001. The novels of the 1930s and the impact of history [A]. In Roe, Sue et al. (eds.).TheCambridgeCompaniontoVirginiaWoolf[C].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72-90.
Dick, Susan. 2001. Literary realism inMrs.Dalloway,TotheLighthouse,OrlandoandTheWaves[A]. In Roe, Sue et al. (eds.).TheCambridgeCompaniontoVirginiaWoolf[C].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50-71.
Foucault, Michel. 1998a.TheWilltoKnowledge,HistoryofSexuality,Volume1 [M]. Tran. Robert Hurley. London: Penguin Books.
Foucault, Michel. 1998b. Discipline and punish [A]. In Rivkin, Julie & Michael Ryan (eds.).LiteraryTheory:AnAnthology[C].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465-487.
Rivkin, Julie & Michael Ryan. 1998. Introduction: “The class of 1968-Poststrucuralismparlui-mêm” [A]. In Rivkin, Julie & Michael Ryan (eds.).LiteraryTheory:AnAnthology[C].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333-357.
Woolf, Virginia. 1964.Mrs.Dalloway[M]. Middlesex: Penguin Books.
——解析伍尔夫《达洛维夫人》的艺术构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