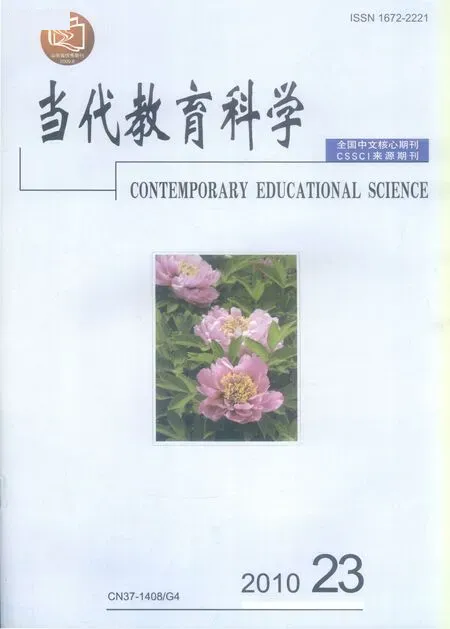认识论视野中课程理论与课程实践的关系*
● 苏贵民 林克松
认识论视野中课程理论与
课程实践的关系*
● 苏贵民 林克松
课程理论和课程实践之间存在非常复杂的关系,而不是简单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对于二者关系的传统认识主要源自实证主义的认识论。从实证主义、现象学—解释学和批判理论的认识论来考察,会发现课程理论源自具体的课程实践,具有多种类型,二者之间是一种平等对话和开放的辩证关系。
课程理论;课程实践;认识论;辩证关系
课程理论指的是具有一定价值立场,可用来认识、理解、预测课程现象和课程问题,并提供一系列概念、规则和规范的知识体系。“一种课程理论就是一套赋予学校课程意义的相互联系的陈述,指出课程各个因素彼此之间的关系,指导课程的开发、使用和评价。”[1]课程实践则是指在教育情境中,相关主体(学校、教师、课程研究者等)围绕课程问题而展开的一系列思考、决策和行动。一般认为,课程理论和课程实践的关系只能有一种,而且课程理论似乎总是高于课程实践,理论总是要求而且必须指导和改造实践。实际上,二者的关系并非如此简明。
早在1952年就有学者将课程理论与课程实践的关系分为逻辑的、运作的、问题解决的和辩证的四种。[2]前两种认为理论先于实践形成,理论一经形成,就可以也必须指导实践,二者是一种单向的决定关系;问题解决的认为课程理论可以从实践智慧中来,而辩证的则认为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是平等的和互动交流的。这一观点首次较为深入地解析了课程理论与课程实践之间的复杂关系,但是并没有从问题的根源——认识论的角度考察二者的关系。本文拟从课程改革的历史出发,从认识论的角度来深入探讨课程理论和课程实践的关系。
一、课程改革呼唤从认识论角度审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
课程理论一般都源自某种特定的认识论,相应的课程改革也会用这种认识论去约束和要求课程实践。当课程改革遇到挫折的时候,也就是反思和认识课程理论与课程实践的最佳时机。
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学科结构课程改革陷入困境,施瓦布开始思考和重新认识泰勒原理,最终得出如下结论:“课程领域岌岌可危。运用目前的方法和原理,它不能继续其工作,也不能对教育的进展做出重要贡献。”[3]追求普适性的泰勒原理并没有给课程实践带来繁荣,理论框范实践反而带来了诸多矛盾。于是施瓦布决定转换思路,“课程领域绝不会复兴,也绝不会对提高美国教育质量做出新的贡献,除非课程将其力量从主要对理论的追求转向另外三种运作方式……实践的方式、准实践的方式和折中的方式。”[4]施瓦布的这一转变不是不要理论,而是承认理论不能解释所有的课程现象,理论的主要任务是表述思想,需要从实践出发不断超越现有的理论。
施瓦布的观点站在新的认识论立场,凸显了源自实证主义的课程理论的局限性,也将人们对课程理论与课程实践关系的理解推进了一大步。随着概念重建主义的兴起,在新的认识论立场上,课程理论和课程实践的关系也被重新建构。课程改革的历史充分说明认识二者关系既取决于当时社会所面临的课程问题,更取决于研究者和决策者所持的认识论立场。
二、不同认识论视野下课程理论与课程实践的关系
从课程史的角度来看,影响人们认识课程理论与课程实践之间关系的认识论根源主要有实证主义、现象学和解释学的观点、批判理论。这些认识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分别占据主导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们对于课程理论与实践关系认识的角度和深度。
(一)实证主义的观点
最先影响人们认识二者关系的认识论是实证主义。实证主义产生于19世纪30年代。它不是去预先假设人类是如何得到知识的,也不提供关于知识的心理学或历史学的基础。它认为经验是构成全部哲学的基础,但是经验必须是按照实证自然科学的要求获得的,能够被科学检验和接受。[5]受实证主义的影响,课程研究者主要运用脱胎于自然科学的“科学”研究方法,从经验出发,在假设——检验的过程中通过观察、实验等等方法对“客观的”课程现象(“主观的”课程现象被排斥在研究的范围之外,也不是理论关照的对象)进行专门的研究,归纳和发现具有普遍性的因果关系,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套课程理论,然后用这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去解释、预测、控制、改造和评价课程实践。
在实证主义者看来,课程理论产生于对课程现象的实证研究,课程理论由于具有实证科学认可的经验基础而成为客观的、具有普遍性的原则和要求;课程理论一旦产生,由于有了科学性的保证,必然要指导实践,课程实践只能接受其控制和约束,只能尽可能努力达到课程理论的要求。课程理论一经产生,本身不会因为实践而发生任何改变,二者的联系是单向的和不对等的,理论自身的科学性和完整性高于一切,胜过了实践中的情境性以及历史、社会政治过程和主体的参与。
(二)现象学—解释学的观点
20世纪初期,现象学开始在欧洲兴起,也影响到了人们对于二者关系的认识。“现象学的基本特点在于把哲学研究变成没有任何前提的研究。”[6]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现象学及其后续的存在主义放弃了从事先设定的前提、概念等出发来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转而揭示现实生活和实践隐藏的意义。“(现象学课程论)所关注的不是视为理所当然的科层体制、社会背景和行为目标等议题,而是重视课程的生活经验与生活意义,透过语言和文本分析,将所有的象征系统,都视为生活世界中的层面,必须回归具体化的主体。”[7]
20世纪60年代以来,解释学开始发展起来。解释学的一个分支就是方法论解释学,代表人物是狄尔泰。狄尔泰虽然与胡塞尔一样都没有彻底摆脱实证主义的影响,但是为精神科学奠定了不同于自然科学的认识论基础。他认为“历史科学可能性的第一个条件在于:我自身就是一种历史的存在,探究历史的人就是创造历史的人。”[8]为此他提出在人文科学研究中使用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方法——理解。理解在这里既有认识论的意义,又有方法论的意义。狄尔泰提出的理解和重现文本原意的方法是,设身处地把自己“直接”置于文本当时的环境之中,重新体验和感受文本的意境、情境和作者的意图,以求最终领悟、重现和复制文本的意义。而哲学解释学的代表人物伽达默尔则反对狄尔泰“设身处地”的体验和重构,强调理解的历史性,承认成见在理解过程中的合法性,指出真正真理性的东西永远是过去和现在的综合,理解就是一种对话性的视域融合。
按照现象学和解释学的基本观点,不能事先假定一些概念和前提来推演出课程理论,接着再用理论去规范实践;课程理论是植根于课程实践,是从课程实践发展和成长起来的;理论和实践不是二元对立的,也不是理论必然高于实践,二者是融为一体的,理论是通过主体参与课程实践而获得的,“实践”才是理论的真正内涵,理论与实践在生活中合二为一才是生活中最真实的体验。
(三)批判理论的观点
批判理论的理论渊源主要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德国古典哲学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其核心观点主要是强调主体性、整体性和实践性。批判理论认为人类的理性植根于人类的实践,主体是在各种社会实践形式中行动的主体。
早期的批判理论批判了传统的理论,反对将理论体系化,主张理论不该以建立体系为最终目标,从而提出了“开放的辩证法”——主体与客体、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意识、理论与实践等等都处于永恒运动的状态中,其中的任何一方都不能被看成是绝对第一性或者原始性的因素。这就消解了理论的权威性,将处于特定社会情境脉络的理论和实践关系纳入到动态的运动过程中加以考察和把握,认为理论和实践统一于主体的批判行动。
批判理论的后期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反对将实证主义绝对化,认为实证主义忽略了人是意义的主体以及人所处的社会情境,不能用实证主义来认识社会现象。他认为一切科学的认识都是以主体的认识兴趣为前提的,将认识兴趣视为认识论的组成要素。他将认识兴趣分为三种:技术兴趣、实践兴趣和解放兴趣。[9]技术兴趣的目的是控制自然和积累客观反映自然的知识,实践的兴趣旨在达成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理解,解放的兴趣则是通过自我反思和批判来达到自我的解放。不同的兴趣发展出不同的科学,这些科学分别是经验分析的科学、历史解释的科学和反思批判的科学。
哈贝马斯的这种认识论架构,其实就是将人类的认识和理论分为三种相对独立的领域,这三种不同的认识各自有自己的基础、功能、特征和评判的标准。相应地,反映人们认识课程现象成果的课程理论也可以分为三种相对独立的类型——经验的课程理论、解释学的课程理论和批判的课程理论。概念重建主义的领军人物派纳对课程理论也有类似的划分。
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课程理论可以被分为三种相互平等的类型,基于实证王义的理论不再是绝对的和权威的;课程理论和实践都处于永恒的运动状态之中,二者都不是孤立、封闭和静止的,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情境中运动;理论并不是直接引导实践,理论和实践相互作用的中介是主体的社会行动。
三、课程理论与课程实践之间的多重关系
实证主义的认识论为人们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开了先河,而二者关系的认识历程就是一个逐步摆脱单一的实证主义认识论,走出单一关系,不断扩充认识论的视野以求得更为丰富认识的过程。
我们认为,结合认识论发展的脉络,从实证主义、现象学和解释学,以及批判理论等角度来综合认识二者的关系,才有可能获得接近真相的认识,走出非此即彼的藩篱。1981年派纳在与人合作编写的《课程与教学》一书中名为《课程研究的概念重建》的文章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我们并非面对一项唯一而排他的解释:是选课程领域的传统智慧,或选概念—经验主义,或是概念重建观点,它们每一个依赖另一个。为了使课程成为美国教育富有生命力及重要的领域,必须每一时刻都要提供营养:它必须努力于综合,对于课程提供一系列的观点——同时是经验的、解释的、批判的及解放的。”[10]
(一)课程理论和课程实践在地位上是相互平等的
课程理论虽然来源于实践,但是并不意味着理论就是对课程实践的客观“摹写”和描述,故不能先入为主地认为理论是第一性的,实践就只能为理论提供思维材料和接受理论的规范与约束。此外,课程理论和课程实践之间不是简单明了的决定关系,相互之间是可以转化的。这主要是因为作为社会理论之一的课程理论本身不仅仅是对实践的“客观”描述,只关注结果和目标,更是对课程实践的一种价值引导。理论产生后会作用于实践,将实践改造为符合或者体现某种理论的实践;而随着实践的深化,则会对理论提出更高更新更多的要求,迫使理论进行改变和更新。
(二)课程理论和课程实践发生关系的中介是主体的行动
事实上,理论与实践不是直接相互作用的。再伟大的理论都不可能抛开主体的行动直接改变实践。沟通二者之间的桥梁就是课程实践中的主体对于理论和实践的理解、反思、批判以及在此基础上采取的行动。课程理论要作用于实践,就必须经过主体在其特定经验背景支持下的反复理解、自我反思、批判和采取行动等诸多环节,才有可能产生真正的改变。
(三)不同类型课程理论与课程实践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
课程理论的类型是多样的,学校课程也需要不同类型的课程理论。基于某些可用实证主义方法研究的课程问题而建立的课程理论,是可以指导和约束与之对应的课程实践的,二者之间基本是单向的决定关系;而解释学的课程理论重在对实践中的主体、课程情境和课程问题的理解与解释,理论的合理性和解释能力就需要在与实践反复进行平等对话中才有可能实现,二者之间是对话和理解的关系;至于批判的课程理论则关注课程情境中不同主体的个人解放,而不是具体课程问题的解决,这种理论会和实践进行相互批判和改变,二者之间基本是带着强烈理想主义色彩的批判、启蒙的关系。
随着认识论的发展,人们对于课程理论与课程实践之间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实证主义一统天下,逐渐扩展到现象学、解释学与批判理论共存,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更加多元、开放和平等,理论的神秘性、权威性和普遍性遭到不同程度的解构,理论和实践呈现出一种双向建构的态势。这也预示着将来的课程理论和课程实践会整合新的认识论的观点,使课程探究涵盖和使用多样的探究样式。而不同课程探究的范畴,则要求必须与具体的课程实际有关。[11]
[1](瑞典)T.胡森,(德)T.N.波斯尔斯韦特.教育大百科全书(第七卷)[M].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海南出版社联合出版,2006.122.
[2]叶世芬.课程理论与实务的落差及其改善途径[J].台湾:教育研究月刊,2006(5):112.
[3][4]张华.课程与教学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19,22.
[5]Leszek Kolakowski,The Alienation of Reason:A History of Positivist Thought[M].New York:Doubleday&Company,Inc.1968:2-3.
[6][9]刘放桐等.新编现代西方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4,478-479.
[7]周珮仪.现象学课程理论之研究[J].台湾:人文及社会科学教学通讯,1999.10,(2):84.
[8]洪汉鼎.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99.
[10]转引自黄光雄.课程研究——回顾到展望[J].台湾:教育资料与研究,2005.67:163.
[11]钱清泓.在课程实际中开拓课程探究的新样式——从Short的观点谈起[J].台湾:教育资料与研究,2001.40:26.
*西南大学教师教育创新平台建设资助,系教育部“西南大学教师教育创新平台建设”子项目之一。
苏贵民/西南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课程与教学论研究 林克松/西南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为课程与教学论
(责任编辑:孙宽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