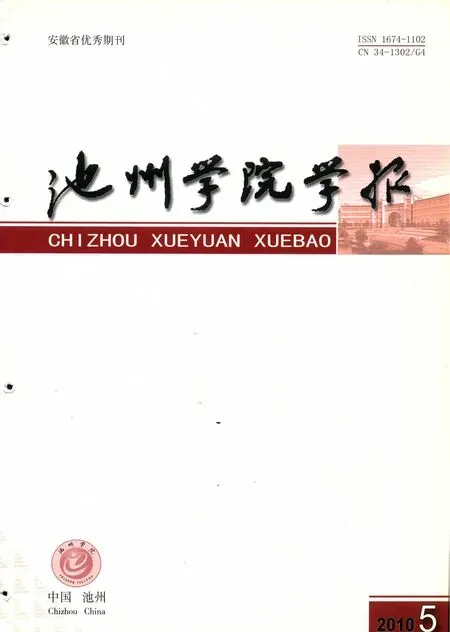古汉语词汇教学的两点思考
陈祝琴
(安庆师范学院 文学院,安徽 安庆 246133)
古汉语词汇教学的两点思考
陈祝琴
(安庆师范学院 文学院,安徽 安庆 246133)
古汉语词汇教学需要注意两个问题:字词关系的梳理和词汇学理论的应用。具体说就是分清字形义和词义的关系;掌握汉语构词法的发展;正确运用义位义素理论指导古汉语词汇教学。
字形义;词义;构词法;义位;词汇教学
词汇具有开放性,缺乏明显的体系。词汇的开放性表现在词语的流变上,它是最快最能反映社会历史变迁的语言要素,了解一定的词汇知识对于传承民族文化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就古汉语教学而言,古文献阅读的最大障碍缘于古今词义的差别,因而词汇的教学尤为重要。古汉语词汇教学之所以难,原因在于汉语词与汉字之间的复杂关系、词的意义的流变与词的同一性、词汇学理论难以贯彻等问题的存在。以下结合实际教学讨论两个问题:一是字词关系问题;二是词汇学理论的应用问题。
1 古汉语词汇教学中应当重视字词关系的梳理
语言是一套符号系统,文字是记录语言符号的符号。严格意义上讲,词和字不是同一个系统内的符号体系。正如霍凯特所言 “语言学家区分语言和文字,而外行人则倾向于把这两者混同起来……”[1]。“词”是语言单位中最小的能够独立运用的音义结合体,是以语音形式承载意义的符号;字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不仅有音义而且还有形。从耳治的角度来说的,词的形就是它的音;从目治的角度来说,词没有形,而字是形音义的结合体。
汉字是“音节-语素文字”[2],它所记录的意义往往有理据可循。古汉语中,词以单音节为主,基本上一个字就是一个词。因而,在古汉语词汇教学中,如何分清汉字形体与词义之间的关系,汉字形体的演变与词义的流变之间的关系对于古文献阅读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表意性是汉字的主要特点,某个词的意义从记录它的字的形体中多能找到一些提示,因而字形重要。独体的象形字、指事字姑且不说,合体的形声字、会意字的组成部件对于认识词义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形声字,一般认为形旁表意义,声旁表音读。实际上,形声字的形旁与声旁都有表意功能,甚至声旁在认识词义上更重要,因为声旁有示源性。词的本义从字的形旁声旁都能推导出来,如“页”,义与“首”同,均表[头](凡用[]处均指词),所以从“页”的字多与“头”部有关,如题、额、颜、项、颈、顶等。声符则显示词源义,如“戋”的本义是“残灭”,派生出“残、钱、践、刬”等,都有“残灭”义;从“残灭”义又可引申出“小”义,所以从戋的字又有“小”义,如“残、钱、浅、笺”等[3]。
字义与词义不是完全重合的。字义即字形义,指从字的形体构造分析出来的意义,如“逐”,从止从豕,字形显示“人追逐野猪”,但这是字形显示的意义。从甲骨文来看,“逐”专指“逐兽”,而不限于“追逐野猪”。 如:“贞:呼多马逐鹿,获? (合 10374)”徐中舒《甲骨文字典》:“甲骨文从趾于兽后,以会追逐之意,所从之兽,为豕、为兔、为鹿等”。甲骨文中“逐”的字形尚未固定,有从止从兔、从止从鹿等多种形体,从字义看,分别表示“追逐豕、追逐兔、追逐鹿”等;但从词义看,它们只是一个词的不同记录符号,表示同一个意义[逐兽]。
分析字形义与词义在古汉语词汇教学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不了解这一点在阅读古书时往往会产生一些误解。《周易·既济》:“亨小利贞。初吉终乱”。 《说文·刀部》:“初,始也,从刀从衣,裁衣之始也”。 《段注》:“衣部曰:裁,制衣也,制衣以鍼,用刀则为制之始。引申之为凡始之称”[4]。《说文》、《段注》都认为“初”的本义为“裁衣之始”。段氏还指出“开始”是引申义。由此观之,《周易·既济》例中之“始”当为引申义。这就错了。“裁衣之始”是从“初”的形体分析出来的字形义,而并非[初]的词义。词义具有抽象概括性,而汉字在记录词的时候总是通过一定具体可感的事物来体现,字义和词义既有联系,又不等同。宋代邢昺《尔雅·释诂》疏就已经指出:“初者,说文云:‘从衣从刀,裁衣之始也’……此皆造字之本义也,及乎诗书雅记所载之言,则不必尽取此理,但事之初始俱得言焉,他皆仿此”。“初”之本义即“开始”,《周易》例正作此解。古人造字,多从与自身生活环境有关,正如许慎所言:“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见鸟兽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4]。如“牡”字,甲骨文有从牛从羊等多个形体,原因是“牛羊”为古人常见之事物,而《说文》:“牡,养牛人也”。也只是字形义,[牡]的本义就是指“放养”。尤其是对于一些比较抽象的概念,更能体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如“進”表示“前进”义。陈独秀《小学识字教本》:“進从隹者,飞鸟不退行也”。古人正是抓住了鸟一般不后退的特点,因而用从辵从隹来表示“上升、前进”义。我们考察《段注》,凡称“引申之为凡某之称”例字369,有15例即属于错将字义当本义,将本义当引申义[5]。在古汉语词汇教学中应该明确,字形重要,字形是分析词本义的基础,但是也不要简单地将字形义等同于本义。
2 古汉语词汇教学中应当重视词汇学理论的应用
词汇学理论所含内容较广,下面从构词法和语义场理论在词汇教学中的运用加以阐释。
2.1 构词法
构词法既是语法的问题,也是词汇的问题。汉语构词法大体经历了从词义构词、语音构词到结构构词的发展:词义构词是指某词的义位从源词中独立出来,形成新词;语音构词是指改变词的语音形式(声韵调)构成新的词,即变声、变韵、变调构词[6];结构构词是指通过语法格式构成新的词,如主谓、述宾、偏正等。前两种是单音节时期的主要构词法,后一种是复音化的产物。学习古汉语词汇需要注意不同的构词法。如“田”:
(1)初,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见灵辄饿,问其病。(左传·宣2)
(2)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适而为之田,以为公族。(左传·宣2)
上两例“田”分别表示“田猎”、“农田”义,一为动词,一为名词。 《说文》:“田,陈也,树谷曰田”。 《段注》:“取其陈列之整齐谓之田”。《说文》认为“田”的本义就是指种植谷物的场所,《段注》进一步指出“田”当与“种菜曰圃,树果曰园”相并列。郭锡良先生指出许氏的说法是不确切的。根据社会的变迁,田猎社会在前,农耕社会在后,“田”的本义就是指 “田猎”,后来到了农耕社会,人们在先前田猎的场所进行种植,也就用“田”来指称“农田”了[7]。可见“农田”义是从“田猎”义派生来的新词。属于词义构词。
语音构词是单音节时期另一重要的构词法,在古汉语词汇教学中同样需要予以重视。试以变调构词为例,变调构词传统上称之为 “四声别义”,如“思”,本为动词“思念、思考”,平声。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另一个动词义“愁思”。如《史记·乐书》“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史记正义》“思音四,亡国谓将欲灭亡之国,乐音悲哀而愁思”。又鲍照《拟行路难之八》“还君金钗玳瑁簪,不忍见之益愁思”叶“治、意、置、异、思”,均去声字,说明“思”已有去声一读。又如柳宗元 《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从平仄规律看,诗中“思”必为仄,当读去声。声调不同,说明“思”产生了一个新的词义。变声构词、变韵构词可以各举个例子:史/事;见/观。《诗经》时代,史是山母之部,事是崇母之部。殷商时期,史的地位很高,主要是为王治事的人,因而与“事”在意义上有很大的联系,到《诗经》时期,通过变声由[史]产生了一个新词[事],表事情、事物义。见、观同源,《诗经》时代,都是见母元部字,区别只在两者的介音不同,“见”有/i/介音,“观”有/u/介音,分别表示[看见]和[观看][7]。结构构词是通过句法关系来构成新词的方式,是复音化后的主要构词法。如偏正式构词,系指两个具有偏正关系的语素组合成一个新的意义的词,它不能是其构成成分意义的简单相加,如:“门人治任将归”(《孟子·滕文公上》)中的“门人”并不是指“看门或守门的人”而是指“学生、门徒”。结构构词现代汉语中极为普遍,在此不多赘述。
2.2 义位理论
义位是词汇语义学中的术语,一般来说,一个单义词有一个义位,多义词有多个义位。从中观的角度来说,义位相当于义项,但又不完全等同于字典词典里的一个义项,尤其是对于一些不自由的语素义,在字典里虽然列为一个义项,但不能算作一个义位[8]。义位不完全等同于义项主要基于以下考虑:首先义位是对词而言的,与字无关涉,而字典词典中对字与词的划分并不严格;其次,字典词典中的义项之间的地位不是等同的。如《现代汉语词典》“兵”除姓氏之外列有四个义项:兵器:短兵相接;军人、军队:当兵、兵种;军队中的最基层成员:官兵一致;指军事或战争:兵书。表兵器与战争的“兵”都不能单用,只是语素义,列为一个义项是可以的,因为它们多是古汉语的遗留,但是不能算作一个义位[9]。义位是词义的下一级语义单位。而义素是义位的语义构成成分,它是词义的最小构成单位,又叫语义特征。
一个词的某个义位是从语言义来讲的。在古汉语教学中,要区分语言义与言语义,正确作好义位的归并。词义训诂的主要任务是揭示隐藏在言语义中的词义,归并义位的时候要因文定义,不能望文生义。正如王力先生所言:“我们只应该让上下文来确定一个多义词的词义,不应该让上下文来临时‘决定’词义。前者可以叫‘因文定义’,后者则是望文生义。……因文定义比较有客观标准,各家注释比较容易趋于一致;望文生义则各逞臆说,可以弄到‘言人人殊’,莫衷一是”。如:
(1)《左传·昭公十四年》:“分贫振穷, 长孤幼,养老疾”。杜注:分,与也。振,救也。
(2)《左传·哀公元年》:“在国,天有灾疠,亲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军,熟食者分而后敢食”。杜注:分犹遍也。
两句的“分”都是分发的意思,却不当“分”训,随意性比较强[10]。再如“小子”一词在先秦文献中习见:
(3)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尚书·君奭)
(4)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
陆忠发认为《尚书》中“小子”均系君主自称或尊称地位极高的人……春秋时代,孔子所说的“小子”就是指鲁哀公[11]。颜春峰指出《论语》中的“小子”不可能是指鲁哀公,依然是做“门人”解[12]。我们认为,上述文章对“小子”的解释都免不了有“望文生义”的嫌疑。“小子”的核心意义只是表示谦称或尊对卑的称呼,至于在具体的文中指称什么可以因文而异。上述诸文,没有严格的区分语言义与言语义,也没有将词义与词的指称对象区别开来。这种现象不仅在义位的归并上需要引起注意,在古汉语教学中也应明确指出来。
语义场理论告诉我们,一个词义不是孤立的,而是处在一个场中,场内成员的地位是不相等的,有不同的层级,比如区分上位义和下位义。词义的上下位关系在古汉语词汇教学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古今词义变化的教学上。从上下义的关系来看,词义的扩大和缩小是指某个词义在语义场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由下位义变成上位义,就是词义的扩大,如“河”,古义专指[黄河],现代演变成了[一般的]+[河流];“睡”,古义[坐着]+[打盹](坐寐),今义泛指[一般的]+[睡]。由上位义变成下位义,就是词义的缩小,如“臭”,本指[气味],后来演变为[难闻的]+[气味],乃气味的一种。
词义演变的教学还可以从义素分析法中得到启示。义素是词义的构成成分,也是联系同一语义场内成员的纽带。根据义素在词义中的所指不同,可以分为区别性义素、指称性义素和附加性义素[10]。具体词义的演变就是这些义素发生了变化。如“汤”,由[热的]+[水]到[水制的]+[食物],指称性义素发生了改变,是词义的转移。 如“爪牙”,由 [得力的]+[助手]到[坏人]+[得力的]+[助手],区别性义素发生了改变,是词义感情色彩的变化。需要注意的是义素的切分难以有统一的标准,往往会戴上主观随意性。如何找到比较一致的成分作义素,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问题,也是语义场理论遇到的主要困难之一。
[1]霍凯特.现代语言学教程[M].索振羽,叶蜚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裘锡圭.文字学概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3]曾昭聪.形声字声符示源功能述论[M].合肥:黄山书社,2002.
[4][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5]陈祝琴,史运林.《说文》段注“引申之为凡某之称”辨[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9(4):106-111.
[6]孙玉文.汉语变调构词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7]郭锡良.先秦汉语构词法的发展[C]//第一届国际先秦汉语语法研讨会论文集.长沙:岳麓书社,1994.
[8]张志毅,张庆云.词汇语义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9]张双棣,张联荣,等.古代汉语知识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0]张联荣.古汉语词义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1]陆忠发.《论语·先进》“小子”解[J].孔子研究,2007(4):122-123.
[12]颜春峰.《论语·先进》“小子”正解[J].孔子研究,2008(5):115-116.
G642
A
1674-1102(2010)05-0142-03
2010-08-26
安徽省教育厅教学研究项目(2008JYXM419)。
陈祝琴(1976-),男,安徽怀宁人,安庆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词汇史、语法史。
[责任编辑:章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