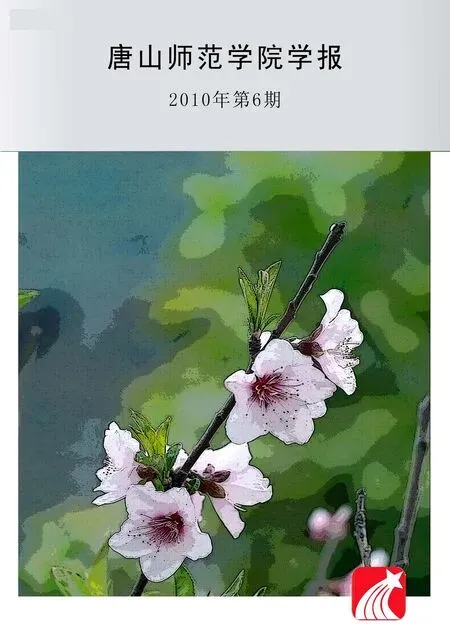从“仁礼”到“礼法”
—— 荀子之“礼”的再审视
董 春
(山东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先秦儒学的发展由孔子而及孟、荀,有学者认为,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仁学思想,发展了其内圣之学,荀子则发展了孔子的礼学思想,开创了儒家的外王之路。然而从两汉至宋明都主张孟子才为儒学正宗,而荀子则为儒家的变异之学,为儒学之旁支。实则不然,在战国末期,儒学的发展已陷入窘境,在这种情况下,荀子以儒学为主干,批判吸收了诸子百家的学说,提出了自己独特的以礼法为核心的外王之术,既是对儒学的一种继承,也是对儒学的拯救。
一、孔孟之“仁礼”
礼是最早的原始社会的宗教仪式,“礼者,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说文解字》)人们用礼来表示对祖先或者神灵的敬畏之心。礼在西周时期只是贵族所独有的社会制度,至春秋时期,孔子才将礼学与自己的仁学结合起来,用仁学来丰富礼的内涵,并将礼延伸为人人所应遵循的社会准则,“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经过这种改造,礼不仅是一种外在的社会准则,更成为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本质。在孔子以前,礼仅作为一种外在的规范,是一些僵硬的教条,而孔子将这种外在的教条拉回到人的内心之中,并将其扎根于人的生命之土壤之中,落实于人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中。李泽厚先生认为孔子这种“把‘礼’的基础直接诉之于心理依靠。……这就把‘礼’以及‘仪从外在的规范约束解说成人心的内在要求,把原来的僵硬的强制规定,提升为生活的自觉理念……,”的行为,“使伦理规范与心理欲求融为一体”[1,p21]。
孟子充分继承了孔子的“仁礼”的内在本质,且发明出仁义礼智四端,并围绕此建立起其“尽心——知性——知天”的理论体系,可以称得上是孔子学说的内在心性的充分发展。孟子从人生而所具有的仁义道德,建构了以“性善”为基础的“仁政”之说,他所主张的政治体系的构建都是以这种心理情感为基础的。孟子主张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只要依此而行则天下可运于掌上。
在孟子的仁义礼智四端中,仁义是中心,礼只是其外在的表现形式,而智仅为对仁义的认识和保证。孟子认为离开仁义而谈礼是空洞的,相比于仁义,孟子认为礼处于次要的地位,“恭敬之心,礼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这种礼只是一种仪式,“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孟子·离娄上》),礼只是仁义的外在的表现形式,依仁义而行的礼。那么这个“礼”的重要性就大打折扣了,孟子虽也主张以礼待人,循礼而行,他提出离开了礼的约束,仁义也会失去其具体的准则,而难以被人们所把握,但这种礼节仪式同仁义相比则是次要的[2,p341]。
二、孟荀的贯通之处
荀子思想在儒学体系中独树一帜,被后人视之为法家或由儒到法的过渡人物,人们关注的往往是其与孔孟的不同之处,但却忽略了其与孔孟的“一脉相承处”,而这个一脉相承之处才是最为基本的。“荀子可说是上承孔孟,下界易庸,旁收诸子,开启汉儒,是中国思想史从先秦到汉代的一个关键。”[1,p87]荀子亦是如孔孟一般“生乎今之世而志乎古之道”(《荀子·君道》)的学者,他的学术理路亦是如同孔孟一般以修身为本,而齐家而治国平天下的。
后人认为荀子讲性恶,与孔子、孟子在思想根本处就不同,并且荀子主张礼法并重,更是背离了儒家的基本治世原则。实则不然,荀子的思想虽受到了诸子百家的影响,但其与孔子之道的一以贯之之处是显而易见的,在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儒家类》评《荀子》书中曾说荀子“以性为恶,以善为伪,诚未免于理未融,然卿恐人持性善之说,任自然而废学,因言性不可恃,当勉励于先王之教”。荀子之性恶论是出于勉励人们致力于先王之教的目的而造的,韩愈评价荀子之说“大醇小疵”无疑是最中肯的。荀子只是将孔子的内在的仁之礼重新定位为外在的规范,在充分遵循孔子思想的基础上依据时代做出了一些变通。
荀子的思想中有着很重的孔孟思想之痕迹,如“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荀子·王霸》)与孟子的“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公孙丑章句上》)义同,李泽厚先生认为在《荀子·大略》等篇中掺入了不少孟子的思想,其中的“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从道不从君”(《荀子·臣道》)可与孟子的“民为贵”以及“天与贤则与贤”想比拟。郭沫若先生在其《十批判书》中也曾指出孟荀的一致处,他认为荀子的义荣势荣、义辱势辱的观念是从孟子的天爵人爵之说演变出来,孟子和荀子都很重视王道等等,都肯定了荀子思想的儒学根基。
三、荀子之法礼
人们往往依据荀子思想中“刑政”、“隆礼重法”等因素,便将荀子与儒家分割开来,此种做法未免过于武断。荀子思想中的这些因素,是其思想与时俱进的表现,他所主张的刑罚等思想仍是从属于儒学之根本——“仁”的。如其“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荀子·君道》仍遵循着儒家轨道。荀子所做的只是在此基础上提高了礼的地位,将礼作为修身之本、人道之极,故而在其《劝学篇》中提出了学应“始于诵经,终乎读礼”。他认为要想使国家得到治理,仅仅靠仁义说教是不行的,如果缺乏外在的礼仪的规范,那么就会陷于欲穷乎物,物屈于欲的状态之中。
1. 礼的缘起
荀子与孟子不同,他所关注的是人的自然之性,明确主张“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的性恶论。荀子的性是人生而有之的“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的自然之性,对于自然之性荀子强调应对其约束,这样便有了礼。“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在礼的基础之上形成的社会组织中,人们共同努力,如此人虽力不若牛,行不若马,但是却能役使牛马。
对于礼从何而来,一般认为荀子讲“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那么礼便是先王为治其乱的的产物,但是,先王也是生活于天地间的一个存在,其善性也是“人之所积而致”的,那么在制定礼仪之时,先王的这种礼仪、善性从何而来?蔡元培面对此种情形就提出:“荀子持性恶论,则于善之所由起,亦不免为困难之矣。”[3,p18]实则不然,在荀子那里,礼的存在有着先验性的根源,荀子曰:“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荀子·礼论》)这样荀子的礼首先有一个终极根基——天地,天地是礼产生的本源,礼是人们“制天命而用之”的产物。再者,荀子那里的性只是人的自然本性,性恶是由于任由这种先天本性发展而对其毫无节制的结果,先王清楚地看到了这种毫无节制的危害,用礼对其进行约束而已。这样,荀子的礼其实源于天时、地利、人情,先王只是发现并整理了已经存在并运行的礼,与其说“先王制礼论”是一个立法过程,不如说先王发现了长久以来人类共同生活的经验[4]。
2. 礼——道德与法的双重功用
与孟子不同,荀子更注重人的社会性。在荀子看来要组成一个社会,必须要有一定的社会规范,人们在这种共同规范下各司其职,各尽其能。作为“治辨之极”的礼便成为社会正常运行之本,荀子认为“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荀子·修身》)。
在荀子看来社会要稳定,就应该有社会分工,而礼所承担的是人为造就等级差别的任务,“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王制》)。在荀子这里,差别同“先王制礼仪以‘分’之”的“分”是一样的,即在社会结构中有贵贱、长幼、贫富的不同。荀子依据这种贵贱长幼之差进一步开显出君臣父子之等,而这种差等是不允许被打破的,因为“分均则不遍,势齐则不一,众齐则不使。……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荀子·王制》)。荀子认为在有限的社会财富下,不能搞绝对平均主义,应该有等级之差,这样才能促使社会体制正常的运行,如果没有“别”那么人们会因为财物的分配而陷入争斗之中,社会就会陷入强欺弱、众暴寡的混乱之中。只有“隆礼贵义者,其国治”,而“简礼贱义者,其国乱”(《荀子·议兵》。
作为维护社会基本秩序的礼,不再是一种僵硬的道德教条,而是作为人之生存的基本条件,为社会正常有序的发展提供保障。因为在荀子那里,“人”不再是孟子所讲的具有先验的道德本心的人,而是异于禽兽几稀的“人”,如果没有这种礼的外在的约束人就如同于禽兽一般。这样荀子的礼虽仍同孔子一样,以提高人的道德的修养为本,但其却具有了更多的含义,荀子之礼更注重于对社会成员的约束性,从而具有了“法”的强制性内涵。荀子将礼义称之为“治之始”,将法称之为治之端,礼与法便有了内在的相通性。在孔孟那里作为绝对的道德命令的“礼”,在荀子这里不再具有绝对意义,而是一种相对的伦理道德准则,更注重礼的强制性,他批评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便是从礼的强制性出发的。荀子的礼是人的行为的准绳,是规范群体秩序的准绳。
3. 礼——法之别
荀子虽一再将礼法并称,但并不意味着将二者看成一物,忽视它们之间的区别,荀子将礼法并称是以明确确定二者的界限为前提的。在《荀子·天论》篇中荀子提出“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将隆礼和重法分开来看,使用两种统治方式所导致的结果也截然不同。在荀子看来法只是礼的一个重要补充而已,法应以礼为本,“礼义生而制法度”,礼义是法度产生的前提,要想做到对法把握的极度精确,则需要对礼义之深刻的理解。荀子认为那些只知道条条框框的法律,而不知法之义的散儒,已经丧失了对法合理性的把握。
在礼与法的实际使用情况中,荀子“以善至者待之以礼,以不善至者待之以法。两者分别,则贤不肖不杂,是非不乱”(《荀子·王制》)。他认为礼与法有着不同的适用对象,“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荀子·富国》)。对于有着高度的价值自觉的“雅儒”、“大儒”不需要对其过分约束,他们能自觉地践行礼义,只以“礼乐节之”足矣。而处于社会底层的庶民,没有充分的自我价值明觉,对于礼义不能充分的把握,因而需要借助于法的强制性对其进行威慑。但同时荀子也提出“礼之生,为贤人以下至庶民也”(《荀子·大略》),他并没有将礼对庶民的教化作用一概否定,礼对于庶人同样有着适用性。
四、结论
荀子的隆礼重法的思想一直以来备受诟病,至于宋明理学之际,更是对荀子大加批判,后人以“孔——孟——朱——王”为儒家思想的发展主线,将荀子排除在儒家之外。这种观点略显偏颇,荀子对于儒学发展所作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其在儒学转型之际,将即将走入神秘主义深渊的儒学重新拉回到了现实之中,赋予儒学发展之新的张力。
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一种完善的理论,要应用到实践中去,有着一定的运行逻辑,在其展开的过程中,如依据理论套路来可能会实现其最完善之状态。但是从实际来看,这种理想的实施可能失去与现实状况之间的互动而陷入不可实行的尴尬局面之中。荀子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点而对儒学进行了适当的改进,提高了孔子仁学的实用性,使得儒学进一步向前发展。并且在荀子所生存的时代,儒家要实现其治国平天下之理想,仅靠其道德理想是不足以适应统治者的需求的,在其与现实的政治统治者合作时,必然需要其在理想和政治现实中寻找一个平衡点,来实现其政治抱负,而荀子寻找到了“礼法”来平衡理想与实际之间的差异,使得儒学从道德理论真正走向了实践。
荀子是儒学发展的一个关键点,离开了荀子对礼学的改造,儒学很可能会发展为一种神秘主义宗教,一种过分注重对于先验德行的追求,而忽视了对社会、对国家、对天下责任担当意识的道德宗教。荀子对儒学的这种改造可以称得上是对儒学偏差之补救,对儒学的进一步发展有着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