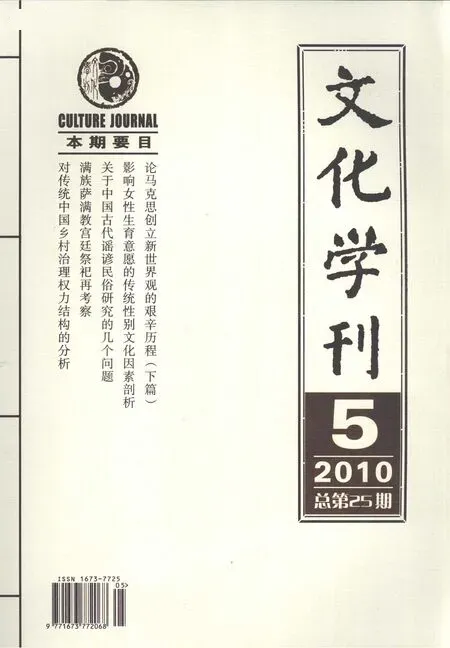论《悲愤诗》女性言说的主体精神
胡秀春
(首都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北京 100037)
汉魏乐府叙事诗中有一些感人的名篇刻画了女性的音容举止,她们发自肺腑的声音更令我们味之不倦、感触良深,诗歌塑造的女性形象不仅栩栩如生,而且深藏着某种文化意蕴。蔡琰的《悲愤诗》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文人创作的自传体五言长篇叙事诗,不仅为我们了解汉魏时期的政治、文化、社会风貌提供了生动有力的个案依据,其背后还涌动着女性言说的主体精神。
与《悲愤诗》同时期的叙事名篇如《陌上桑》、《孔雀东南飞》等生动地刻画了千古传唱的女性形象,有罗敷女的机智活泼,有刘兰芝的深情温婉,比《悲愤诗》中女诗人的自我形象更深入人心。然而,这些篇章中的女性都是男性目光注视下的女性,她们的所思所为都是隐藏在她们身后的男性在言说,唯《悲愤诗》是一部真正的女性生命史,是以女性目光注视的战争和社会写实,是女性主体在言说。
一、女性第一人称自述
全诗用的是真正的女性第一人称叙述,从开篇乱世场景的铺叙到篇末人生孤苦的忧叹,都是用女性的眼睛去看,用女性的耳朵去聆听,用女性自己的感观去感觉,这就超越了由男性掌控话语权的“代言体”文学传统。第一人称自述的表现手法而今早已司空见惯,但在女性没有参与社会话语权力的时代,敢于成为一名女性叙述者,这本身就意味着挑战传统、挑战男性社会秩序。传统社会已经习惯作者的声音由男性发出,由女性发出的自传体叙述难免与男性叙述产生冲突,而正是这种冲突的存在,才能让后人从另一角度去认识作者所处的时代。
同时代的《孔雀东南飞》又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显然是一种男性叙述话语,诗中的女性是缄默的,没有发言权,是男性主体在描述她。诗前的小序注明其产生的背景:“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没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陌上桑》中的女子更是男性目光注视中的美丽女子“: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紫绮为上襦。”这细致的装扮描述与南朝宫体诗的女性描述模式极其相似,是物化型女性形象的典型刻画手法。梁简文帝萧纲有一首《美女篇》写到女子的姿容:“约黄能效月,裁金巧作星。粉光胜玉靓,衫薄拟蝉轻。”《陌上桑》与《美女篇》两个文本的“第一关注”便是女性的服饰和身体,诗中的男性以背景形式出现,男性注视无处不在地充塞着女性的生活空间,无处不在地对女性的身体和精神造成压迫感。文本中的女性是被看的,并不是真正的女性,而是由男性立场、男性目光构筑的形象,因此是“第二性”。这是一种隐含的文化密码,是文化发展中沉积下来的一套思维方式的表现,也就是说,这种色相首位的关注方式是男性主体精神的表现。与这几首诗不同,《悲愤诗》是女性的自述,是女性的注视,以女性的目光和立场看社会,看男性,看到男性发动的战争,看到男性掠夺妇女,看到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遭遇和无以逃遁的生命困境。它张扬的是一种女性主体精神,作者兼叙述者的女性性别特征和不以色相为关注点的叙述方式使它有别于同时代的其他作品。
二、女性主体的人文关怀
对社会政治、家国命运的人文关怀向来都是男性的特权,他们以诗干预时政、教化百姓、抒发兴亡之叹,他们关怀宇宙、关怀人生、关注女性。《诗经》中有很多女性形象,有淑女、思妇、弃妇,等等,她们姿容美丽,命运可怜,被赋予男性目光下的同情与关怀,对女性形象的描述话语是以美色和情爱为主题的男性话语。与《悲愤诗》同时代的《陌上桑》和《孔雀东南飞》通篇流露的是男性诗人对女性的赞赏与同情,这是一种来源于男性社会对弱势性别的人文关怀。这些诗中的女性是作为男性诗人言说的对象而存在的,读者感知到的是印象式的“被看”的画面形象,色相评判标准是第一位的。而《悲愤诗》则是女诗人自述的综合形象,是集女儿、母亲、文人、难民于一身的真实立体的生活形象,是动乱史的代言人。这位女性的人生是与家国兴亡息息相关的,她的命运是“宏大”的,又是“私人”的。
诗的开篇写道“: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由一名知识女性喊出对黑暗政治的愤懑,她与男性一样平等地思考,平等地以诗介入政治,平等地承担起对社会的责任,这就是体现在蔡琰身上的女性主体精神。她发出对政治的价值评判,说出对百姓尤其是女性的怜恤与关爱,这是不同以往来自女性主体的人文关怀。可以说,汉魏之际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最混乱、社会最苦痛的时代,女诗人感怀于时政,不平则鸣,完全置身于士林风气之中。面对胡人“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的杀戮抢夺,诗人大声喊出“:彼苍者何辜?乃遭此祸!”她为天下苍生的悲惨命运深深不平,内心蕴蓄着强烈的民族正义,这是我们难以在其他两首诗作中读到的女性主体意识,它平等地融汇于男性主流社会的话语中。女诗人的返魏再婚无疑是曹操拉拢文人、收买人心的政治形式,战争中被劫掠的其他女性一个也没有被曹操救回,这一点,女诗人看到并且说出来了:“兼有同时辈,相送告离别,慕我独得归,哀叫声摧裂。”女诗人不拘于个体命运的描述,她的视野囊括了全体,覆盖到社会。
蔡琰以她的诗作维护着女性的写作权力,体现出难能可贵的女性主体意识。中国社会直至明清时代才有较多的女性参与写作活动,历来女性都是被剥夺写作权力也自认为没有写作权力的。《礼记》规定“男有分,女有归”,男性可以“立功”、“立言”,而女性的身份规定就是嫁人,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孝敬公婆、相夫教子、做饭织布,“农业社会中的男女两性有着鲜明的性别分工,男子负责家国大事,女子从事辅助的、琐碎的、次要的家庭事务。丈夫对妻子处于居高临下的位置,尊与卑、强与弱的对比极其鲜明。女人的职责是内主中馈,伺候公婆和睦处姻亲”。[1]“才思非妇人事”,她是物化的,没有任何话语权,否则就是僭越传统社会的性别角色规定。在蔡琰的时代,女性处于写作上的失语状态,甚至在明清时代还有很多女性作者在出嫁或临终前焚毁自己的诗稿,因为她们依然认为自己没有写作权力。男性社会的性别钳制已经内化到她们的心灵深处,她们已经丧失了追求平等的女性意识,更谈不上把女性的人文关怀投射到社会。“女性意识是女性在社会实践中觉醒的意识,包括自我意识(女性的自身认识)、主体意识(女性作为主体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的自觉意识)、平等意识(女性对现实生活中从属地位和一切歧视现象与行为的意识敏感性,以及对女性应该享受和男性同等的权利与地位的确切认知),主要表现在物质、精神、贞操方面的主观意志和能动选择上,有了突出的女性自主意识。平等是女性意识的重要内核”。[2]
可见,蔡琰在汉魏乱世能自述身世、评点政治,维护了女性的写作平等,体现了异于寻常女性的主体精神。“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在社会既定的男性传统和男性权威掌控之下,女性叙述的主体性只有在宏大叙事中才得以体现,蔡琰做到了,她以对国事、家土、黎民的关怀,使女性的言说在社会公共的话语领域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三、对传统女奴观的超越
在汉代的家庭中,妻子常常被当做生产奴隶和生育工具使用,从事繁重的家庭劳动,而且被丈夫及其家庭随意更换。汉乐府中有很多诗反映了当时年轻女性在家庭中所处的女奴地位。像《上山采蘼芜》中那位男性的前后两位妻子都是家庭中的重要女劳动力“,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馀”。评判两任妻子优劣的标准是“手爪”,即干活的质量和数量,“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陌上桑》中的美丽女子也是一个采桑、养蚕的劳动力:“罗敷喜蚕桑,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像《孔雀东南飞》中的年轻媳妇刘兰芝,“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从早到晚在公婆的监督下织布,一天也不能休息。从家庭生产层面上看,娶妻就是娶回一个女性劳动力。女孩从小就在家长的打造下自觉地接受了自己的女奴角色,刘兰芝就是其中的典型。“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勤勤恳恳地培养自己,准备为男性的家庭输送一名合格的物质生产者。除此之外,要当好一名妻子还得为男性家庭创造精神财富,得知书达理,颇通音律,像刘兰芝“,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更重要的是,她得在身体和精神上忠贞于丈夫,如,刘兰芝,“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刘兰芝切切实实够得上一名高级的家庭奴隶,与刘兰芝同命运的女性在汉代比比皆是。
在汉代,休妻之风极盛,夫家可以随时找借口让女子回娘家。《大戴礼记·本命篇》规定:“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3]刘兰芝就是不顺婆婆的心而被遣归的:“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传统社会的妇道要求为妻为媳者不仅要伺候好公婆与丈夫,而且要取悦丈夫家族的每个成员及其姻亲,年轻女性的地位不仅低于丈夫,也低于女性中的长辈。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女性从小就在自我意识和思想行为中烙上了深深的女奴意识,毫无自我的主体性可言。刘兰芝最后在身体和精神都不得自由的境况下选择了殉节,“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为男性的家庭生,为男性的名誉死,因而树立了古代诗歌史上一位杰出的女奴形象。殉节,就是一种屈从,就是对男性霸权的认同。这是传统的声音,是男性社会的主流话语,他们推崇这样的女性,也规范着其他女性。像《陌上桑》中的罗敷人见人爱。“行者见罗敷,下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怒怨,但坐观罗敷”。显而易见,这是一位男性心目中的理想女子,美色悦人,这样的女性形象体现了叙述者以色相评判为首位的男性立场。最重要的是,她只从属于自己的丈夫,富贵而不能淫,贫贱而不能移,威武而不能屈。罗敷机智地夸耀自己的丈夫“: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何用识夫婿?白马从骊驹;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她以男性价值观为自己的价值观,以男性言说为自己的精神主体,以依附男性为荣的价值判断申明了她作为一名合格的家庭女奴的地位。罗敷形象的潜台词就是女性附属于男性,女性屈从于性别等级秩序的男权意识,女性的身体和欲望被限定于仅仅属于夫主而不是本人。这种不平等的性别等级秩序,意味着不平等的社会等级秩序。这样的诗歌文本使用的是典型的男权话语,形式上的女性言说只是男性话语的伪装,因而存在明显的价值缺陷。
然而《悲愤诗》发出另一种真正属于女性的声音。女诗人被胡人掳掠,违心地生活在胡地,“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她终日思念故国家园,等待着归国重逢的机会,“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穷已”。这是一种理智的人生选择,虽然遭受凌辱,但始终珍视自己的生命,而不是简单地以死相抗。传统男性社会把女性当做物品、殉葬品,认为她们应该为男主人而死,为爱情而死,这是视女性为女奴的传统观念,《悲愤诗》却超越了这种传统的女奴观,体现了女性的自主意识。当曹操将女诗人赎回时,她并没有感激涕零,反而忧虑自己的命运:“流离成鄙贱,常恐复捐废。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她认识到女性的悲苦命运归咎于不安定的社会政治,希望能掌控自己的命运,这深沉的思索正体现出独立女性的自主生命价值观。
四、人格完整的弃妇形象
《悲愤诗》中的女诗人形象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弃妇形象。女诗人蔡琰“是东汉末年著名文学家蔡邕的女儿,字文姬,陈留圉县(河南杞县)人。16岁嫁河东卫仲道,不久因夫亡无子,归宁在家。董卓之乱时,被李、郭汜军中的胡兵掳去,流落在南匈奴12年,生有二子。建安八年(公元203年),曹操用金璧把她从匈奴赎回,归汉后再嫁陈留董祀”。[4]战争和命运把她抛到了荒蛮的胡地,她被故土所弃;政治又剥夺了她的异域家庭和子女,她被亲人所弃;而返魏再婚能否避免再次遭弃?女诗人非常清楚自己的命运,要求自己自尊自强“:托命于新人,竭心自厉。”这样一个自尊自爱的形象,完全不同于传统男性言说中的弃妇。
中国诗歌中源远流长的弃妇形象是无关乎女性主体人格的,她们被男性的意志主宰了整个生命。《诗经》的《氓》、《谷风》,汉乐府的《上山采蘼芜》等都有鲜明的、被丈夫抛弃的妻子形象。《上山采蘼芜》中被弃的女子遇到她的前夫不仅没有怨恨,反而还关心丈夫的生活:“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这就是男性社会塑造的理想弃妇,出之于男性笔端,蕴涵着男性霸权的主体精神。与这一诗学传统并行不悖的另一类弃妇形象是一个具有象征作用的经典符号,指向“士不遇”的价值内涵,其深层背景是不得志的男性诗人心中的弃妇情结。因为中国古代君臣与夫妇之间的关系比较类似,所谓“君为臣纲,夫为妻纲”,“被逐之臣和被弃之妻不仅完全没有自我辩解与自我保护的权力,而且在其被逐与见弃之后仍被要求持守单方面的忠贞,其内心怀有怨悱之情自可想见”。[5]因此,“逐臣弃妇”成为中国传统诗学的重要母题。屈原《离骚》首创以“美人香草”喻贤臣,喻有磊落君子情操的诗人自我的传统,表达“不遇”之感。建安时期的曹植有一首《七哀》诗就是用“愁思妇”、“宕子妻”、“孤妾”、“贱妾”这些被弃的女子形象喻壮志难酬的诗人自我,隐藏在被弃的女性形象身后的是渴望施展抱负的诗人。
而女诗人蔡琰却以崭新的女性叙事立场描述了自我形象,既不是男性目光哀怜、同情的传统弃妇,也不是男性诗人感怀于仕途的隐身弃妇,而是具有女性主体精神的人格完整的控诉型弃妇,她既不需要廉价的同情,也不必用隐讳的象喻,而是坦率地陈述。女性的命运女性自己来诉说,这在诗歌的艺术表现上和叙述者的文化立场上都是一种超越。
[1]张菁.唐代女性形象研究[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149.
[2]李丽君.魏晋女性亦风流——世说新语·女性形象透视[J].现代语文,2007,(8).
[3][汉]戴德.大戴礼记·卷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5.220.
[4]葛晓音.八代诗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7.60.
[5]叶嘉莹.迦陵说词讲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