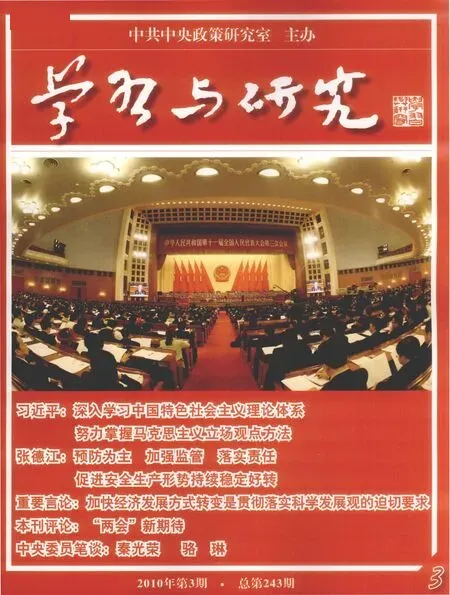近代中西法律文化交流的成功个案
——吴经熊与霍姆斯的交往
孙伟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 教学科研部,江西 井冈山 343600)
近代中西法律文化交流的成功个案
——吴经熊与霍姆斯的交往
孙伟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 教学科研部,江西 井冈山 343600)
吴经熊在第一次留学欧美期间,最大的收获可能就是结识当时的世界级法学泰斗——霍姆斯。他们之间的交往,大体上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一、对霍姆斯狂热崇拜(1921—1924),二、对霍姆斯重新审视(1924—1930),三、对霍姆斯敬仰有加(1930—1935)。两者之间的交往一时传为国际法学界的一段学术佳话,并成为近代中西法律思想文化交流中传奇式的成功个案。
吴经熊;霍姆斯;中西法律文化交流
吴经熊(1899-1986),浙江鄞县人,是二十世纪中国一位极为罕见的学贯中西、具有世界影响的法学大家,早年游学足迹遍及欧美著名学府,结识许多国际一流法学权威。奥立维·温德·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1841-1935),1902至1932年长期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他被公认为美国现代实用主义法学的创始人,也被看作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大法官之一。吴经熊在第一次留学欧美期间,最大的收获可能就是结识当时的世界级法学泰斗——霍姆斯。吴经熊小霍姆斯近60岁,一少一老,一中一美,结成忘年之交,一时传为国际法学界的一段学术佳话,并成为近代中西法律思想文化交流中传奇式的成功个案。
他们的交往从1921年第一次通信至1935年霍姆斯逝世,长达15年之久。两者主要通过充满热忱与睿智的书信进行,共计约106封。[1]这些书信是近代中国法制进程中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更是通向吴经熊和霍姆斯心灵世界的钥匙。这是沟通两种文化和四代人的通信,虽然他们一生只见过两次面,但我们可以从字里行间领悟两者深笃的情谊,它们记载了两者相识、相交、相知、相惜的过程。信的内容涉及对学术、人生、信仰、社会、教育、法律实务等问题的探讨,更是中美两种法律制度的对话。事实上,这段超越时空的友谊也被吴经熊视为“一生当中最有意义的一件事”。他们之间的交往,大体上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对霍姆斯狂热崇拜(1921—1924)
吴经熊后来承认自己与霍姆斯的友谊开始得非常偶然。1921年他在《密歇根法律评论》3月号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之前他曾多次听教授们以最褒扬的口吻提及霍姆斯大法官,知道霍姆斯对比较法学感兴趣,因而也许会乐于了解有关中国古代的法观念。于是年仅22岁的吴经熊心生向往之情,就主动把《评论》复印本寄了一份给当时誉满天下年逾八旬的霍姆斯,并随后寄去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告之此事,不久就得到了大法官的积极而认真的回应,这其中还有一段美妙的插曲。
霍姆斯先收到了信,在没有收到论文的情况下,草率地给吴经熊回复了第一封信:
我亲爱的吴先生:
你发表在《密歇根法律评论》上的论文尚未收到,但明天我会尽量在首府浏览它。我想,你想要的无非是一句同情话。但是,我只想进言几句你可能不大需要的忠告,这对有些观念丰富的年轻人是需要的。一个人不能一步登天。所以,我希望你不要逃避生活所提供的细节详情和单调乏味的活儿,而是去掌握它们,作为通往更大事物的第一步。一个人在成为将军之前,先得是个士兵。
谢谢你的好意!
你真诚的:奥·温·霍姆斯
1921年4月19日[2]P251
在接到这封信的次日,吴经熊却收到了霍姆斯的第二封信,这信是以道歉开始的:
我亲爱的吴先生:
昨天的信多有误会。我以为是写给一个初学者,因为你信的抬头是法学院。现在我已拿到了你的论文,并拜读完毕。我觉得自己是在对一个见识渊博的学者说话,他可能会唏笑我的建议。我相信你会把我的无知朝好的方面想……我极其赞赏你正在做的事,并衷心希望看到你取得更多的成果!
你真诚的:奥·温·霍姆斯
1921年4月20日[2]P252
可以说,霍姆斯对吴经熊的第一印象非常深刻,并迅速看出这位中国青年是个极堪造就的法学奇才,同时这也激发了吴经熊后来创造霍式法理学体系的雄心壮志。两人从此订交,吴经熊对霍姆斯开始了狂热的崇拜。在该阶段,霍对吴关怀备置的指导多表现在法学学术、人生与信仰等抽象方面。如霍一方面对吴在法学方面的洞察力和敏锐性非常惊讶,另一方面通过对一些共同感兴趣的法律哲学问题进行探讨,希望吴接受自己的法律思想,有时还对吴的学术旨趣进行善意的批评。如霍对黑格尔等德国哲学家的逻辑推理很反感,认为系统性的思考都是空洞的形式,系统性的思维只会扼杀洞见,只有洞见才是有价值的。所以,当吴经熊在柏林大学拜师施塔姆勒门下,潜心研究德国法律哲学思想的时候,霍生怕吴太受系统思维的影响,对施塔姆勒的观点不断进行批判,并寄希望于吴能在这个问题上接受自己的观点。
霍不仅在思想上对吴进行指引,还通过自己的影响对吴的学业进行直接的帮助。如当霍得知吴继续获得卡内基国际法奖学金的申请落空后,马上通过私人关系让吴能继续到美国做研究。另外,霍就吴对法律的热情给予了鼓励,并希望吴对法律哲学的兴趣不会致使自己过于远离具体的法律问题。霍对吴今后在法律实践中可能面临的困难也做了适当的提醒,没有忘记鼓励吴在面临困境时要有坚强的意志,要经得起逆境的考验,并隐含了吴今后在法律生涯中可能面对挫折时应采取乐观的态度,才能取得更大的成就。
1923年秋,吴经熊作为研究学者到哈佛大学法学院后,他们才有了第一次亲密会见,两人促膝而谈,并一起愉快地度过了圣诞节。此次会面在他们的心灵深处产生了共振,彼此间的关系更加亲密。吴在后来的回忆中记载了这短暂的美好时光:
霍姆斯和我继续有通信往来,我们的友谊不断增进。但直到那年12月我去华盛顿时才第一次见到了他。我在他那里度过了几个晚上,用他的笑话来说,“一起扭动宇宙的尾巴”。他的情绪极高。他把我带到他的书房里,取下一本书又一本书,偶尔也评论几句,但都妙趣横生。他向我出示他收藏的杜勒(Albrecht Durer)的木刻和铭刻。最后他说:“亲爱的孩子,我还没有向你出示书房里最好的书呢。”我竖起耳朵,问:“在哪儿?”他指着一个在上的角落;我看见那是一个空架子!我马上懂他的意思,大笑中说,“你可真是独具慧眼,总是望着前头!”他笑得可开心了。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逐渐达到了朋友之间所能达到的理解和爱。[3]P109-110
总之,从1921年两者开始通信到1924年吴经熊学成回国前,在吴的眼中,霍就是一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长者,对霍充满了崇拜与向往,且吴也时常能轻易地洞察与揣摩霍内心深处的“痒处”;在霍的眼中,吴就是一个世间罕见的少年天才与知己,且时常能给自己带来莫名的喜悦,常能让自己感受到人世间最真、最美的事物,爱惜之情溢于言表,所以对吴也循循善诱,使之有朝一日也成为大师级人物。
二、对霍姆斯重新审视(1924—1930)
1924年夏,吴经熊结束留学生活回到中国,此后他们通信的内容主要是围绕着吴在中国的法律实践活动及其法律思想展开。由于时空的距离,加上随着参与中国法制建设的深入,吴的思想变得成熟与复杂起来,对霍的观点开始重新审视。在此期间,霍对吴的指引多表现在社会、法学教育与法律实务等具体方面。如霍对吴在归国后的法律计划寄予了厚望,虽然也提醒吴今后的人生目标可能会随着归国后具体法律实践活动的开展而有所调整,但还是极大地鼓励吴大胆去闯、去体验,这样年轻的吴才能成长得更快。霍又对施塔姆勒等德国哲学家的系统说进行无情的批判,认为它毫无用处;看到吴经熊仍受它很大的影响,霍不厌其烦地对吴现在的思想进行了厘清,以免吴“误入歧途”而不能自拔。
当霍得知吴在中国的教学生涯比较顺利并有收获的时候,霍焦虑的心情才放松不少,并对吴的教学与科研进一步做了鼓励。霍希望吴不要受到当时中国的战乱或其他因素的影响,安慰吴希望他能振作起来,不求立竿见影之效,而是一点一点地通过自己的努力,使之有所改观;另外,还要积累更多的经验,耐住寂寞,坚持自己的理想,终有一天会有机会胜任祖国的伟大事业。霍还对吴在中国进行的司法实践和立法实践表现出喜悦与满意之情,霍更希望吴能到大量的具体法律事务中去驰骋,而不是只在抽象的思想中盘旋。
霍知道吴年轻气傲,比较喜欢寻求理想化,在回国后遇到的困难和挫折可能会使他心灰意冷,因此不断给予最及时的鼓励与指引。霍的担忧得到了应验,虽然吴的推事生涯非常成功,但他心中不觉安宁,想暂时脱离法律世俗的烦扰,重新回到美国进修,使自己的精神得到进一步升华。霍却不赞成吴的想法,希望吴能留在中国继续从事公共法律事务,通过法律的实施来真正将法律哲学思想及知识进行运用,体现真正的学术价值。但吴最终没有采纳霍的意见,执意于1929年冬再次来到美国。结果,这次访学吴过得不是很快活,且精神不振,心灵一片空白。1930年4月,吴经熊与霍进行了第二次会面。
这次会面与第一次不同,见面时当然彼此都很高兴,但吴不太自在,因为在自己的心灵深处,有一个想法,即应该接受霍的劝告,留在中国继续工作,却又不愿意向霍承认这一点。而此时的霍健康尚好,依旧激动,可是由于夫人的去世,触景生情而使庆祝略显凄凉。
总之,从吴经熊1924年留学归国到1930年再次出国访学,两者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随着接触复杂社会现实的增多,吴的思想有了较大的变化,而对霍了解的增多,开始对霍的某些意见不予采纳。但事后随着霍的许多话得以应验,吴逐渐对自己的思想与行为进行反思;而霍随着自己的变老,在自己眼中,让吴勇敢地接受社会现实的磨砺是非常有必要的,同时苦口婆心,最大限度地让吴接受自己的法律思想,对吴的精神依恋变得更加深了。
三、对霍姆斯敬仰有加(1930—1935)
1930年夏,吴经熊归国后因故没有返回美国,而是在上海开始了执业律师的生涯。[4]P78霍姆斯知道后,不仅没有责备反而表达了喜悦之情,建议吴能真正参与到祖国的法制建设中去。此后两者的通信由于霍的身体原因而减少很多,霍对吴的指引与社会现实问题贴得不是很紧,而更侧重于对人生和生活的体验。
在这个阶段,年迈的霍在给吴的一些信中,经常更像和一个老朋友在拉家常,倾诉着自己的近况,特别是自己的身体大不如前。可是平凡内容的背后却掩饰不住坚强的霍对现实生活的热爱、对复杂人际关系的从容应对、对吴的真心关爱,使得吴能对日后的工作与生活充满信心,遇到问题能够以积极的心态面对。从吴的一些回信中,我们也看到随着岁月的磨砺,吴逐渐变得成熟了,对现实的体味更深刻了,特别是更了解霍的良苦用心了,也在间接地就自己未曾听霍的忠言而道歉。虽然吴离霍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精神境界尚存距离,却知道从各种名誉诱惑中解脱出来,并向着自己的理想不懈奋斗。
1935年3月6日,94岁的霍姆斯与世长辞了。对于吴经熊而言,霍姆斯的逝世是一盏伟大明灯的熄灭。霍就是吴的精神支柱,霍以自己极强的人格魅力不断影响着吴,并推动着吴的事业不断取得更大的成功,然而这无价的精神财富,却要等到霍去世后才显得弥足珍贵。
总之,从1930年吴经熊再次归国到1935年霍姆斯逝世,两者的关系又有了新的变化:随着吴目睹社会现实的增多,思想也变得更加成熟,对霍又在另一个新的层次上更加敬仰了;而霍随着吴的自我改观,加上自己身体的力不从心,对吴的教诲更加人性化,而这背后却包含着巨大的智慧,有些良苦用心要等到逝世后吴才能慢慢地体会到。他们更像一对精神上的父子关系,经历了崇拜——叛逆——敬仰。
四、尾声
霍姆斯虽已逝世,但用吴经熊自己的话来说,“在我,友谊并未终结”[3]P144。他将自己保存下来的霍姆斯给他的来信,在自己创办的英文《天下月刊》(T’ienHsiaMonthly)1935年第1期上发表,共计50封;另外,他开始著文整理霍姆斯的法律思想[5],此后对霍姆斯思想的研究,始终是吴经熊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其中最重要的是《纪念霍姆斯法官》(InMemorian: JusticeOliverWendellHolmes)一文。该文在文末对霍姆斯进行评价后,最终的落脚点是将霍与伟大的文学家莎士比亚进行比较,并得出了精湛的结论:“他们的心灵属于同一等级……莎士比亚在文学上无人能及,霍姆斯在法学上领先群伦”[3]P144-145。
以下是吴经熊后来就自己与霍姆斯关系所作的总结,显得弥足珍贵:指出了双方吸引对方的魅力所在,以及年龄和经历差距如此之大的两者保持长久的通信和极强亲合力的根本原因——各取所需,即各自可以从对方眼中看到自己的优缺点,而两者身份的巨大反差以及时空的巨大距离反而使得这种精神交流变得畅通无阻。知霍莫如吴,知吴莫如霍!
对我,霍姆斯的最大魅力在于,他在智慧上是年老的,而在精神上是年轻的……
尽管我们在信仰和气质上不同,我们的友谊却一直增长,直到他最后的日子。他是如此之好,除了最初的几封外,他保留了我八十几封信,他死后,他的继承人将它们都还给了我。这一持续的友谊的秘密是什么呢?就我所能明白的,我们共有的最为基本的东西是,对宇宙之神秘的常新的惊异之感……
人罕有自知之明。故而我们需要真诚而智慧的朋友坦率地指出我们的优点和缺点。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鼓励;每个人都需要提高。好的朋友可以长久地满足这些要求。我感谢上主在我年轻时给了我一个像霍姆斯这样善良而又坦率的朋友……
他盼望我在抽象思维的领域能有好东西出来,我所需的只是自信,我应该在信仰中培养信仰,我灵魂里有热火要加燃料保持燃烧,他同意我的这个观点那个观点等等。另一方面,他在我身上看到了“为了确保普遍的而放弃个别的”的趋向、“见森林而不见树木、好远而厌近、近神而远人的倾向”。他的劝告很适合我的需要。[3]P148-150
可见,霍姆斯对吴经熊的生命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他为霍姆斯崇高的精神境界、宽阔的眼界、睿智的思维及其近似完美的人格魅力所深深吸引。吴在求学回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努力实现中国法制的“霍姆斯化”,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尝试,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当然,他们的尊重与信任是相互的,如霍姆斯对于吴经熊的法律生涯不断予以指引,并陪伴他成长,而吴则回报以对于霍法律哲学思想进行整理与建构。这两位法律泰斗之间的交往,作为近代中西法律文化交流的典型成功个案,无疑将永载史册。
[1]孙伟.吴经熊裁判集与霍姆斯通信集[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
[2]JohnC.H.Wu.SomeUnpublishedLettersofJusticeHolmes.T'ienHsiaMonthly[J],1935(1).
[3]吴经熊.超越东西方[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4]吴经熊.怀兰集[M].台北:光启出版社,1963.
[5]JohnC.H.Wu.TheArtofLawandOtherEssaysJuridicalandLiterary[M].Shanghai:CommercialPress,1936.
(责任编辑 梁一群)
K206.6
A
1008-4479(2010)03-0120-05
2009-11-17
孙 伟(1980-),男,江西德安人,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近代中国法制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