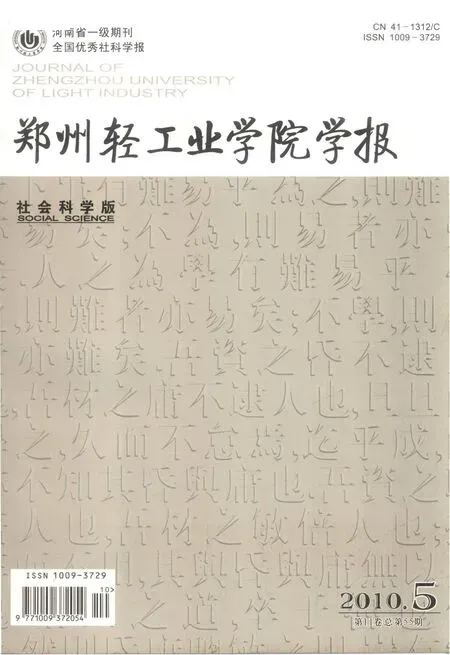帮助犯未遂研究
焦云娜
(郑州轻工业学院国际教育学院,河南郑州 450002)
帮助犯未遂研究
焦云娜
(郑州轻工业学院国际教育学院,河南郑州 450002)
根据共犯从属性理论,帮助犯未遂在正犯着手实行犯罪而未遂时成立,但帮助犯未遂与正犯未遂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在失败帮助和无效帮助的场合下,帮助者的行为不属于帮助犯未遂的范畴,应当比照教唆未遂的情况对帮助者以独立帮助犯论处。对于帮助犯未遂的处罚应限制在帮助犯参与重罪的情况,坚持以帮助犯的既遂犯而不是以正犯为参照标准的必减主义。
帮助犯;犯罪未遂;必减主义
帮助犯是指在共同犯罪中,基于帮助的故意,以非实行行为加工于犯罪,使犯罪易于实施或完成的犯罪参与形态。[1]帮助犯是从犯,其社会危害性较轻,帮助犯未遂的社会危害性更轻。帮助犯未遂作为一种特殊的犯罪形态,涉及共犯和未遂两个概念,实现了对基本犯罪构成的二次修正。在帮助犯的构成要件方面,德国、日本刑法学界素有“共犯独立性说”与“共犯从属性说”之争;在帮助犯的处罚根据上,又存在“起因说”和“责任参与说”之争。在中外的共同犯罪理论中,对帮助犯的研究较少。现阶段我国刑法理论界缺乏对帮助犯未遂的专门研究,《刑法》对帮助犯未遂也未作明确的规定。因此,有必要对帮助犯的成立条件及帮助犯未遂的特征、范围、处罚加以探讨。
一、帮助犯的成立条件
作为共犯的帮助犯的成立,首先要求在主观上有帮助的故意,在客观上有帮助的行为。帮助犯是犯罪分子并不直接实施犯罪的实行行为,而是通过为他人实施或完成犯罪提供精神或物质帮助而构成犯罪,这是帮助犯的典型特征。作为帮助犯的帮助行为有以下特点:第一,这种帮助行为本身是一种非实行行为,不符合犯罪基本构成实行行为的要求。第二,这种帮助行为通过加工于实行犯的实行行为对犯罪起到推动作用,即帮助犯的帮助行为必须使犯罪易于实施或完成。第三,帮助犯的帮助行为可存在于实行犯实行行为之前和实行行为之中,即存在事前帮助和事中帮助的情形。对于实行犯完成犯罪后的事后帮助除非基于事前的通谋,否则不成立帮助犯,是独立犯罪而非共犯意义上的帮助犯。在帮助犯的成立上存在争议的问题是:帮助犯的成立是否以正犯的存在为前提。在刑法理论上,由于对共犯性质的不同理解,存在着“积极说”和“消极说”的对立,即“共犯从属性”与“共犯独立性”的争论;成立共同犯罪是否以正犯的实行行为的存在为必要,是二者的根本分歧。
“积极说”从共犯从属性的观点出发,认为成立帮助犯必须有正犯的存在。坚持这一学说的多是客观主义的刑法学者,如德国的贝林格、迈耶、麦兹格和日本的小野清一朗、团藤重光等。我国台湾学者蔡墩铭也认为:“从犯既在于帮助正犯犯罪之实行,则正犯之成立为从犯不可或缺之要件。”[2]“积极说”认为帮助行为本身并不是犯罪的实行行为,只有借助于正犯的实行行为,帮助犯才有成立的可能性。“消极说”从共犯独立性的观点出发,认为帮助犯的成立只要求有帮助行为的存在,不以正犯的存在为必要。“消极说”认为帮助者的帮助行为本身已经具有了反社会的犯罪性质,即使没有正犯的实行行为,根据帮助犯本身固有的行为也可以成立独立犯罪。
笔者认为,帮助犯的成立是否以正犯的存在为必要,应从帮助犯的本质特征和处罚根据上来说明。第一,从帮助犯的本质特征上看,帮助犯是共犯,属于共犯的范畴。帮助犯的本质特征是通过非实行行为即帮助行为的实施,使行为犯的行为更容易实施和完成,即帮助行为的实施具有使实行行为更容易实施或犯罪结果更容易出现现实危险性。换言之,帮助犯的帮助行为能够使正犯更容易、更迅速、更有保障地实现犯罪。可见帮助犯实施帮助行为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加工正犯的实行行为,而非仅为帮助而帮助。因此帮助犯要实现其犯罪目的必然要依附于正犯的实行行为,即帮助犯的成立必然以正犯的存在为必要。第二,从帮助犯的处罚根据上看,帮助犯的帮助行为是非实行行为,之所以对帮助犯进行处罚,就在于帮助行为和实行犯的实行行为相结合具有造成社会危害的现实性。帮助犯的处罚根据就在于帮助犯的帮助行为显示出帮助犯主观上帮助正犯犯罪的犯罪意图,而且在客观上这种行为具有促进正犯者实施和完成实行行为的现实危险性。因为单纯的帮助行为并不会侵害到法益,帮助犯对法益的侵害只有通过正犯的实行行为才能实现。而犯罪的本质特征是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即犯罪行为对法益的侵害性。不具有犯罪的本质特征就不能成立犯罪,所以帮助犯要成立犯罪必须以正犯的存在为前提条件。如甲、乙二人约定某晚去盗窃物资仓库,该仓库保卫措施十分严格,基于共同犯罪的故意,仓库管理员丙故意未将仓库大门上锁,结果甲、乙顺利进入仓库并盗窃成功。在这个案例中丙的行为单纯来看不具法益侵害性,只有丙的行为和甲、乙的行为相结合才能造成盗窃结果的发生,从而危害到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因此应对丙的行为以犯罪论处。
二、帮助犯是否存在未遂
对于帮助犯是否存在未遂这一问题,中外刑法理论有“肯定说”与“否定说”之争。笔者赞同帮助犯存在未遂的观点。我国《刑法》第 23条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帮助犯是从犯,帮助犯的罪名和处罚从属于正犯,既然正犯存在犯罪未遂,帮助犯也应存在未遂的犯罪形态,又因帮助犯的成立以正犯的存在为前提,帮助犯的未遂在正犯着手实行犯罪而未遂时成立。一般情况下如正犯未遂,则帮助犯未遂。但是帮助犯的未遂和正犯的未遂并非一一对应,在正犯未遂的情况下帮助犯并不必然是犯罪的未遂。这种非一致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种情形:其一,帮助犯实施完帮助行为后,正犯在实行犯罪过程中自动中止犯罪,此时正犯成立犯罪中止,由于正犯自动中止犯罪是帮助犯意志以外的原因,因此帮助犯不是成立犯罪中止而是成立犯罪未遂;其二,帮助犯实施完帮助行为后,采取有效措施阻止犯罪结果的发生而使犯罪终于未遂,此时帮助犯成立犯罪中止,正犯成立犯罪未遂。[3]
三、帮助犯未遂的构成特征
第一,帮助犯实施了对实行犯的帮助行为。这一构成特征包括以下含义:其一,帮助犯的帮助行为可以在实行犯着手实施犯罪之前实施,也可以在实行犯实施犯罪的过程中实施,在实行犯完成犯罪后的事后帮助行为不是本文所讨论的共犯意义上的帮助犯,除非实行犯和帮助者事前通谋要求帮助者事后为其提供帮助。如我国《刑法》第 310条对窝藏、包庇罪的规定: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处 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 3年以上 10年以下有期徒刑。此为事后帮助独立成罪的规定。只有被窝藏、包庇的犯罪分子实施犯罪活动之前和窝藏、包庇者就犯罪完成后的窝藏、包庇活动进行谋议并达成和议的基础上,窝藏、包庇者对实行犯犯罪完成后实施的窝藏、包庇的帮助行为在刑法上才以共犯论处。其二,共犯意义上的帮助犯还要求帮助者和被帮助者之间有意思联络,帮助者在被帮助者不知情的情况下提供帮助行为的成立片面帮助犯,且被帮助者应具有刑事责任能力,虽然不要求是完全的刑事责任能力。帮助精神病人和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儿童实施犯罪的,不是帮助犯而是正犯。其三,正犯已着手实行被帮助的犯罪。正犯的着手是帮助犯成立的前提条件,正犯的着手即帮助犯的着手,因为帮助犯的未遂也只有在帮助犯成立的前提下才能成立。这样就把有些学者所称的预备犯的帮助犯也是帮助犯未遂的观点排除在帮助犯未遂的范围之外。[3]
第二,帮助犯的犯罪未得逞,即帮助犯未能完成犯罪。帮助犯的犯罪未得逞并不是说帮助犯的帮助行为没有实行完毕,因为作为共犯的帮助犯的犯罪既遂以正犯的犯罪既遂为标志,因此帮助犯的未遂就是正犯未使犯罪达到既遂状态。正犯的犯罪未完成包括正犯的犯罪中止和犯罪未遂两种情况,即帮助犯的未遂只在下列两种情况下存在:其一,正犯中止犯罪而使犯罪终于未遂情况。正犯犯罪的中止是帮助犯意志以外的原因,对帮助犯应以犯罪未遂论处,这也反映出帮助犯的未遂和正犯的未遂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其二,正犯未遂,帮助犯未遂。这是基于帮助犯和正犯两方面的意志以外的原因引起的犯罪的未得逞,对二者均应以犯罪未遂论处。
第三,犯罪未完成是帮助犯意志以外的原因。这包括两种情况:其一,共同犯罪因实行犯和帮助犯共同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遂。其二,帮助犯实施完帮助行为后,在实行犯自动中止犯罪的情况下,犯罪未完成是帮助犯意志以外的原因,因此帮助犯成立未遂。
四、帮助犯未遂的成立范围
帮助犯未遂的成立范围在刑法理论界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争论的焦点就在于帮助犯的未遂在无效帮助和失败帮助的情况下是否存在。“肯定说”认为帮助犯的未遂不仅在正犯于未遂的场合成立,在无效帮助和失败帮助的场合也存在。日本学者木村龟二认为帮助犯的未遂包括下列几种情况:一是被帮助者着手实施犯罪而未遂;二是强化了被帮助者的犯罪决意,但被帮助者还没有实施犯罪的实行行为(包括仅实施了预备行为及其他不可罚的行为);三是实施了帮助行为,但被帮助者的犯罪决意没有得到强化;四是实施了帮助行为,但被帮助者已经强化了犯罪决意。[4]“否定说”认为帮助犯的未遂只存在于正犯着手实行犯罪实行行为的场合,失败帮助和无效帮助的场合不存在帮助犯未遂。比如日本学者久礼田益喜认为,“承认加担犯 (指教唆犯和从犯)的从属性者不承认加担犯自身的未遂。其理由谓没有主犯罪,从犯罪就没有可能成立。狭义地理解从属性,以正犯的成立为加担犯成立的要件,与通说同样,我也不承认加担犯本身的未遂”[5]。
笔者认为失败帮助和无效帮助的场合是否存在未遂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帮助犯自身是否存在未遂的问题。肯定失败帮助和无效帮助的场合存在未遂的观点,是“共犯独立性说”在帮助犯未遂问题上的具体体现。依“共犯独立性说”,帮助犯独立于正犯而存在,因此帮助犯的未遂不依附于正犯的实行行为,可以在正犯的实行行为之外独立存在。“共犯独立性说”坚持帮助行为的着手即帮助犯的着手,因此在失败帮助和无效帮助的场合,帮助犯已经着手实施犯罪,被帮助者未实行犯罪只是帮助犯意志以外的原因,对帮助犯应当以未遂论处。可见“共犯独立性说”是失败帮助和无效帮助的场合存在未遂的理论基础。相反,“否定说”从共犯从属性的观点出发,认为帮助犯的成立以正犯实行犯罪的实行行为为前提,将正犯的着手视为帮助犯的着手,因此帮助犯的未遂只有在正犯着手实施犯罪的实行行为后、犯罪结果发生前这一时空范围内才能存在。在失败帮助和无效帮助的场合,因为正犯或尚未实施犯罪的实行行为,或帮助犯的帮助行为在实际上对正犯犯罪的实施或完成没有起到加工作用,因此帮助犯本身不存在未遂,帮助犯的未遂依附于正犯的未遂而存在。在失败帮助和无效帮助的场合下,帮助者的帮助行为对被帮助者不具有实质的意义,帮助者和被帮助者并没有形成共犯关系,因此也就不存在共犯意义上的帮助犯,帮助者的行为不属于帮助犯未遂的范畴,而是一种单独犯罪。在失败帮助和无效帮助的场合可以比照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的情形,对此种情况下的帮助犯应按独立帮助犯论处。[3]
在失败帮助和无效帮助的场合下,既然认为帮助者成立单独犯罪,那么对此种情形下的帮助行为该如何处罚呢?是否可以比照教唆犯的类似情况进行处罚呢?笔者认为,对任何行为是否是犯罪、是否进行处罚、给予什么样的处罚,都应当由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来决定,因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也是对犯罪行为进行处罚的根据。在失败帮助和无效帮助的场合下,帮助者在主观上具有帮助他人犯罪的目的,在客观上实施了帮助行为,具备了犯罪的主客观方面的特征,应当给以刑事处罚;但是,如果此种情况下帮助者的帮助行为不能现实地危害到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应根据我国《刑法》第 13条“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的规定,对失败帮助和无效帮助的场合下的帮助者的行为不以犯罪论处,即不去追究帮助者的刑事责任。这与我国只对未遂教唆犯作出规定而没有对未遂帮助犯的处理作出规定也是相符合的。[3]
五、对帮助犯未遂的处罚
我国刑法对帮助犯没有明确的规定,对帮助犯未遂的处罚也缺乏相应的规定,笔者认为对帮助犯未遂的处罚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第一,对帮助犯未遂的处罚只限于刑法分则对帮助行为未明文规定为单独犯罪的情况,因为并非所有的帮助行为都成立帮助犯。比如《刑法》第 320条对提供伪造、变造的出入证件罪和《刑法》第 321条对运送他人偷越国 (边)境罪的规定等,帮助者成立正犯,而非帮助犯。
第二,对帮助犯未遂的处罚应限制在帮助犯参与重罪的情况。根据我国《刑法》第 27条第 1款的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和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可见从犯包括次要的实行犯和帮助犯,即帮助犯是从犯的一种,从社会危害性上来说帮助犯轻于正犯,而在帮助犯未遂的情况下帮助犯的社会危害性就更轻了。因此没有必要对所有的帮助犯未遂都给以处罚,帮助犯未遂的处罚应当限制在杀人、强奸、抢劫等重罪的帮助行为上。轻罪的帮助犯的未遂因为社会危害性极轻,没有给以刑事处罚的必要。比如帮助犯帮助不满 18岁的未成年人实施数额不大的盗窃行为且未遂的情形,对帮助犯没有给以刑事处罚的必要,这也是刑罚谦抑性的表现。
第三,在对帮助犯未遂的处罚上坚持必减主义。我国《刑法》第 27条第 2款规定: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可见我国对帮助犯的处罚采用的是必减主义。又根据我国《刑法》第 23条第2款的规定: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此笔者认为对帮助犯未遂的处理应在比照既遂犯的基础上坚持必减主义,参照标准应当以既遂犯而非以正犯为参照对象对帮助犯予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这是因为帮助犯虽对犯罪结果的发生起到帮助或促进作用,但并不能直接导致犯罪结果的发生,在帮助犯未遂的情况下因犯罪结果未发生,帮助犯理应承担更轻的刑事责任甚至不承担刑事责任。[3]
[1]刘凌梅.帮助犯研究 [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8.
[2]蔡墩铭.刑法争议问题研究[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1999:310.
[3]焦云娜.共同犯罪未遂问题研究 [D].郑州:郑州大学,2007.
[4]张明楷.未遂犯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207.
[5]赵秉志,魏东.论教唆犯的未遂 [J].法学家,1999(3):28.
DF6
A
1009-3729(2010)05-0061-04
2010-07-14
焦云娜 (1979— ),女,河南省周口市人,郑州轻工业学院助教,硕士,主要研究方向:刑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