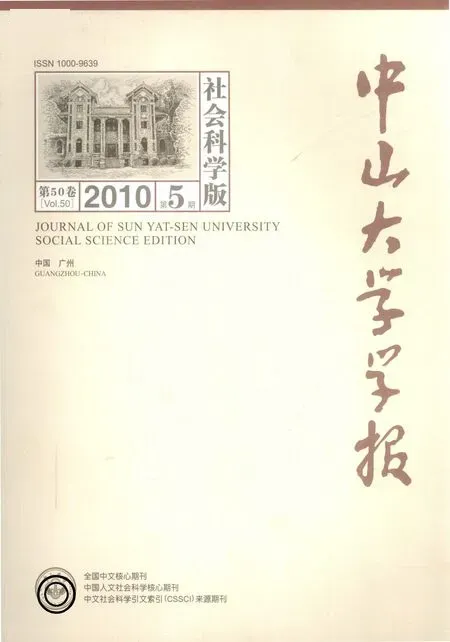梁宗岱和他的象征诗学*
李青果
梁宗岱(1903—1983),广东新会人,现代著名诗人、诗论家、翻译家。虽出身行商之家,却天资聪慧,自幼得览四书五经唐宋八大家文章,并《水浒传》、《三国演义》等通俗作品。少富诗才,受新文学运动影响,开始走向诗坛,所作新诗激情饱满,意态深沉,有超于时流者,16岁即获得“南国诗人”称号,引起在京新文学主将郑振铎、沈雁冰的注意,并获函请加入文学研究会,成为该会最年轻的会员之一。1923年梁宗岱免试进入中山大学前身之一的岭南大学。1924年负笈欧洲,先后游学于法国巴黎大学、瑞士日内瓦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对欧洲古典文学、文艺复兴以至启蒙运动时期文学有通观的了解;与当世法国大作家保罗·梵乐希(现通译保尔·瓦雷里)、罗曼·罗兰等过从频密,深受其时新锐文学影响,形成他象征主义诗学的肌理。1931年梁氏回国,先后执教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等名校,尤以居中山大学讲席时间最长(1953—1970)。有诗论《诗与真》(1933年,商务印书馆)、《诗与真二集》(1935年,商务印书馆)、《屈原》(1941年,广西华胥社)、《非古复古与科学精神》(1942年,西南联大《学术季刊》第1卷第1期)、《试论直觉与表现》(1944年,《复旦学报》创刊号)、诗集《晚祷》(1924年,商务印书馆)、《芦笛风》(1944年,广西华胥社)及大量翻译作品行世。
通观梁氏一生,其诗人地位可谓牢不可破,而其诗学主张更见精彩纷呈,引人注目。近人评价他论诗是“以独特的禀赋,深厚的文艺涵养以及广博的学识,对古近中外文学娓娓道来,不仅是如数家珍,且都深掘和揭示其珍异精微,或找出得失端绪”①陈敬容:《重读〈诗与真·诗与真二集〉》,《读书》1985年第12期。。站在上世纪20—40年代“新诗纷歧的路口”,他的诗学主张既涉及诗歌的现代“本义”,也为其探骊古今中外诗学源流,复对“科学与诗”的沟通提出为人所忽视的观点。这些论述“为中国新诗通向现代化的正道推进了一步”②卞之琳:《人事固多乖——纪念梁宗岱》,《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1期。,对中国诗歌的发展作出独异的贡献,是为中国新诗理论的宝贵财富。
一、象征主义:本义和创作
象征主义文学发端于19世纪70年代的欧美大陆,至20世纪20年代进入后期象征主义阶段,梁宗岱赴欧游学之时所结识的法国诗人梵乐希,正是后期象征主义集大成的人物。当时梵乐希声誉日隆,其“纯诗”理论和诗歌创作所代表的文化精神几成挽救一战后西方文明衰落的一个标志。在他接到梁宗岱进献的法文诗和《陶潜诗选》法译本时,不禁惊讶于这位年轻的中国诗人在法国“巴拿斯派和象征主义之间”,所娴熟进行的“一种企图把极度谨严和极度自由协调起来的探索”,更在中法两国诗人的亲缘性上,称道梁宗岱“把粗糙的语言转化成精美工作的原料,从中提取出纯之又纯、美之又美的物件;把一个词变成稀有的宝石,把一句诗变成确定的结构”的能力①[法]保罗·梵乐希著,卢岚译:《梵乐希序言》,《梁宗岱文集》Ⅰ(诗文卷·法译卷),北京:中央编译社、香港:天汉图书公司,2003年,第140页。。这种归之于近世象征主义和“纯诗”理论的评述,超出了梁宗岱对陶诗属于“一种斯多噶式的乐观主义,却又胜于斯多噶主义”的古典判断②梁宗岱著,卢岚译:《陶潜简介》,《梁宗岱文集》Ⅰ(诗文卷·法译卷),第150页。。在梵乐希看来,梁宗岱著译的法文诗歌,具有纯诗的品质和会通中外古今的视野。这对梁宗岱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此后他的诗学建构即以此为肇端和基础。
其实早在梁宗岱亲与接触象征主义之前,这种诗学观念就已登陆中国文坛。五四文学革命的一代如陈独秀、李思纯、沈雁冰、周作人、田汉等人都对此作过介绍,后起的诗人穆木天、王独清、李金发对象征主义和纯诗理论更有自觉的建设③参许道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新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96页。。但在梁宗岱看来,这些介绍“直到现在还是片面而不正确的”,这些努力“又给一般无聊的诗人糟蹋得不成样子了”④梁宗岱:《诗与真·保罗·梵乐希先生》,《梁宗岱文集》Ⅱ(评论卷),北京:中央编译社、香港:天汉图书公司,2003 年,第11,15,11,8,7 页。;所谓象征主义,涉及“真之追求与美之创造”,“不特深思而且要建造”,重要的不是“熟悉”它的“名字”,而是要“把握”其“本义”⑤梁宗岱:《诗与真·保罗·梵乐希先生》,《梁宗岱文集》Ⅱ(评论卷),北京:中央编译社、香港:天汉图书公司,2003 年,第11,15,11,8,7 页。。
在1933年出版的诗论集《诗与真》中,梁宗岱集中精力从文学史及理论上解决何谓象征主义的问题。该著借名于歌德的自传 Dichtung und Wahreit(《诗与真》),“可是立名虽是蹈袭,命意却两样”⑥梁宗岱:《诗与真·序》,《梁宗岱文集》Ⅱ(评论卷),第5页。,其中隐含着梁宗岱梳理文学史的机心和智慧。他指出歌德的意思“是指回忆中的诗与真,就是说,幻想与事实之不可分解的混合,所以二者是对立的”,而他的追求,却是参透对象的两面:“真是诗底唯一深固的始基,诗是真底最高与最终的实现。”⑦梁宗岱:《诗与真·序》,《梁宗岱文集》Ⅱ(评论卷),第5页。这种幻想与事实的由“对立”到“同一”,被梁氏认为是欧洲文学从浪漫主义到象征主义的历史演变。在《保罗·梵乐希先生》一文中,他进一步追述浪漫主义之后,“自然主义也好,班那斯派也好,黄金中已现败絮,灿烂中已呈衰象”⑧梁宗岱:《诗与真·保罗·梵乐希先生》,《梁宗岱文集》Ⅱ(评论卷),北京:中央编译社、香港:天汉图书公司,2003 年,第11,15,11,8,7 页。,当此之时,整个世界文学的神话时代已经结束,“颂赞神底异象和灵迹的圣曲隐灭了;英雄底遗风永逝了,歌咏英雄底丰功伟绩的史诗也消歇了”,只有“人的灵魂却是一个幽邃无垠的太空,一个无尽藏的宝库……创造那讴颂灵魂底异象的圣曲,那歌咏灵魂底探险的史诗”,非象征主义莫属⑨梁宗岱:《诗与真·保罗·梵乐希先生》,《梁宗岱文集》Ⅱ(评论卷),北京:中央编译社、香港:天汉图书公司,2003 年,第11,15,11,8,7 页。。
从文学史的正本清源推出象征主义,是梁宗岱高于一般时流的地方;而指出象征主义是“讴颂灵魂底异象的圣曲”和“歌咏灵魂底探险的史诗”,则探入了它的本义。借为梵乐希造像,他认为诗人切入人生悲喜和宇宙万象,是为了经由“真之追求”“参悟生之奥秘”,并给诗歌“带来深沉永久的意义”⑩梁宗岱:《诗与真·保罗·梵乐希先生》,《梁宗岱文集》Ⅱ(评论卷),北京:中央编译社、香港:天汉图书公司,2003 年,第11,15,11,8,7 页。;通过和另一诗家朱光潜的辩驳,他指出朱氏所言“象征最大用处,就是把具体的事物来替代抽象的观念……象征主义底定义可以说‘寓理于象’”为根本错误,这种“以甲为乙底符号”来称谓近世以来的“象征”实属言不及义(11)梁宗岱:《诗与真·象征主义》,《梁宗岱文集》Ⅱ(评论卷),第60—61页。。在梁氏看来,象征属于生命诗学范畴,不是“反映”固化的“观念”,而是“表现”生命的“灵境”“真义”。在中国古典诗学领域它与“起情者依微以拟义”的“兴”近似;在近代西方哲学世界则与阿米耶尔“一片自然风景是一个心灵底境界”相仿佛,是把“心情印上那片风景去”,重视不相联的两物之间微妙的“暗示”关系,并具有“融洽或无间”、“含蓄或无限”两个特性①梁宗岱:《诗与真·象征主义》,《梁宗岱文集》Ⅱ(评论卷),第63、66,66—67,72,67—68页。。由“含蓄或无限”出发,他把象征定义为:“藉有形寓无形,藉有限寓无限,藉刹那抓住永恒,使我们只在梦中或出神的瞬间瞥见的遥遥的宇宙变成近在咫尺的现实世界……它所赋形的,蕴藏的,不是兴味索然的抽象观念,而是丰富,复杂,深邃,真实的灵境。”②梁宗岱:《诗与真·象征主义》,《梁宗岱文集》Ⅱ(评论卷),第63、66,66—67,72,67—68页。由“融洽或无间”出发,他指出“象征之道”在于心灵与万物互融的“契合”,达到形神两忘的无我境界:“在那里我们底心灵是这般宁静,连我们自身的存在也不自觉了……我们正因这放弃而获得更大的生命,因为忘记了自我底存在而获得更真实的存在。”③梁宗岱:《诗与真·象征主义》,《梁宗岱文集》Ⅱ(评论卷),第63、66,66—67,72,67—68页。在他看来,以具象代替抽象仍居于“反映论”位置,只有以有限寓无限的“创境”,才称得上象征正轨。诗人要以灵巧的心智参悟万物玄机,在澄澈的心境中映照出万象真义,“实因为它们包含作者伟大的灵魂种种内在的印象,因而在我们心灵里激起无数的回声和涟漪,使我们每次开卷的时候,几乎等于走进一个不曾相识的簇新的世界”④梁宗岱:《诗与真·象征主义》,《梁宗岱文集》Ⅱ(评论卷),第63、66,66—67,72,67—68页。。梁氏以“纸花”、“瓶花”、“生花”为喻,指称只有元气浑全、看不出作者心机和手迹的生花才是艺术的最高境界,非纸花瓶花的匠气所可比拟⑤梁宗岱:《诗与真·论诗》,《梁宗岱文集》Ⅱ(评论卷),第26页。;后来他又为诗人排列位次,说三流诗人借助写诗抒写苦闷,宣泄悲愤,二流诗人写诗可以驾驭强烈的感情,只有一流诗人通过象征“把他们所负荷的内在解放出来”,超越情绪情感,并“从这些情感底混沌创造出他们不朽的精神世界”⑥梁宗岱:《屈原(为第一届诗人节作)》,《梁宗岱文集》Ⅱ(评论卷),第242页。,从而把象征主义推向了诗歌的最顶峰。
梁宗岱服膺梵乐希“纯诗”理论,指认这一理论为象征主义的最新标尺。梵乐希认为纯诗是一种理想状态的“绝对的诗”,是与实际的秩序毫无关系的世界的、事物的秩序和关系体系,但因其理想性受制于实践方面的语言因素,实际上只能是一个难以企及的目标⑦[法]瓦雷里著,梁栋译:《瓦雷里诗歌全集》,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304、306页。。梁宗岱赓续其说,承认诗人永远追求“绝对”与“纯粹”,去创造现世未有或未臻完美的东西,但更致力于在“创作”上探索写作纯诗的法则。1935年出版的《诗与真二集》就是贯穿“‘诗与真’探讨的精神”,继续用心于寻绎“诗的技巧和内容”⑧梁宗岱:《诗与真二集·题记》,《梁宗岱文集》Ⅱ(评论卷),第83页。的成果。在《谈诗》中他为纯诗定义,就涉及创作方法:“所谓纯诗,便是摒除一切的客观的写景,叙事,说理以致感伤的情调,而纯粹凭藉那构成它底形体的元素——音乐和色彩——产生一种符咒似的暗示力,以唤起我们感官与想像底感应,而超度我们底灵魂到一种神游物表的光明极乐的境域。”⑨梁宗岱:《诗与真二集·谈诗》,《梁宗岱文集》Ⅱ(评论卷),第87,84页。他认为艺术的生命是节奏正如脉搏是宇宙的生命一样,节奏分明音韵铿锵的诗句“蕴藏着深刻的情感或强烈的思想”(10)梁宗岱:《诗与真二集·李白与哥德》,《梁宗岱文集》Ⅱ(评论卷),第103页。,故力倡新诗的格律化,强调诗人应仔细摸索语言文字和诗句组织的内在“节奏韵律”,用文字来创造音乐。只有把诗提高到音乐的纯粹的境界,才是象征诗人殊途中的共同倾向。而摒除客观的叙事说理及主观的感伤主义,实由于最高明的诗歌深入宇宙人生的真相,勾心夺魄,神思飞越,“使人起崇高的感觉”(11)梁宗岱:《诗与真二集·论崇高》,《梁宗岱文集》Ⅱ(评论卷),第123页。。梁宗岱其实把诗提升到哲学的高度,要求诗歌与纯真的哲学思想保持适当的关联。为达到这一境界,诗人写诗必备内倾和外向两种素质:“对内的省察愈深微,对外的认识也愈透澈……二者不独相成,并且相生:洞观新体后,万象自然都展示一副充满意义的面孔;对外界的认识愈准确,愈真切,心灵也愈开朗,愈活跃,愈丰富,愈自由。”(12)梁宗岱:《诗与真二集·谈诗》,《梁宗岱文集》Ⅱ(评论卷),第87,84页。梁宗岱虽高标诗歌的高妙境界,却同样重视对诗歌真义的有效传达,强调“最要紧的还是要能够把这灵象从私己的感觉变成大众可以欣赏的对象;把自己的体验变成公共体验的工具”(13)梁宗岱:《试论直觉与表现》,《梁宗岱文集》Ⅱ(评论卷),第338页。。这种对形式与内容、价值与传达的完整表述,显示他对其诗学主张有通盘的考虑。
梁宗岱论诗具有纵横流泻风姿,长于以诗化文字分疏理论,擅用感性思维处理抽象议题,文思畅宕,义理澄澈,触处成春而新见迭出,且“词意的谨严是迄今所仅见”①徐志摩为梁宗岱《论诗》所写“前言”,《诗刊》第2期,1931年4月。,以致获得同道交口赞誉,被评为“成色足,分量足”的“黄金文字”②李健吾:《读〈从滥用名词说起〉》,《大公报·文艺》,1937年4月2日第12版。,是用“博学深思”之笔,以“毫不苟且的思想家的态度”所作的“近年来文学论文中最认真最深刻同时也极美丽的论文”,足以在“时间上站得住”③朱紫:《读〈诗与真〉》,《大公报·文艺》,1937年7月25日第13版。,显示他是当时诗坛独特的“这一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象征主义现代派初登文坛,胡适的写实主义之风影响犹存,左翼革命诗风正风行一时,各路诗人“只知道用‘常识’或‘报章主义’来处理一切事物和现象”④梁宗岱:《诗与真二集·韩波》,《梁宗岱文集》Ⅱ(评论卷),第177,178页。,“教训诗”大行其道,重视人类精神活动、表现人生永恒意义的作品反被斥为“捣鬼”、“弄玄虚”⑤梁宗岱:《诗与真二集·谈诗》,《梁宗岱文集》Ⅱ(评论卷),第89页。,整个诗坛存在着破坏有余、建设不足,或热闹有余、沉淀不足的现象,因此梁宗岱论诗不仅属于创建,也是针对诗坛流弊而加以匡正,具有自觉的文学史意识和明显的实践性倾向。
二、传统资源:西方与中国
梁宗岱论诗意在革新,思想在中国诗坛激起新浪潮,开创新局面,但他创新的思路,却是充分利用文学传统资源,重视文学史的源流之辨。自五四以来,中国文坛偏重于取法西学“新声”,不甚措意于维护本国的文学传统,所以梁宗岱张大传统的力量,在当时文坛虽非独此一家(如周作人一派取法晚明小品,独张“言志”文脉),但因他对中西最新文学的论述都能重视其贯串传统、开源启流的一面,而显示出不同凡响的特色。
在他综理西方象征派时,虽然对它断代清晰,却是以“通史”之眼来考察的。如从理论一面,起自“柏拉图底《斐特儿》(Fhedre),《斐东》(Phedon)和《宴会》(the Banquet)尤其是来宾尼滋底《单元论》(Movadologie)和《人类悟性新论》(New Essays on Human Understanding)”⑥梁宗岱:《释“象征主义”——致梁实秋先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6期。,以至宗教家班扬的《天路历程》和达芬奇、莎士比亚、卢梭、康德、斯宾诺莎、帕斯卡尔、卡莱尔、梵乐希、里尔克、彭加勒等著述学说,范围涉及哲学、宗教、诗学、绘画、数学等领域,时间贯串古希腊、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迄现代。他论象征诗风,也是远推前代,搜寻诗综,对于之前的浪漫派如济慈的诗作,便称为有“深沉的意义”,更把哥德《浮士德》的《和歌》视为象征的典型⑦梁宗岱:《诗与真二集·李白与哥德》,《梁宗岱文集》Ⅱ(评论卷),第105页。,可作为象征诗风的样板,昭示前代诗人的灵光显现已伏有今世诗歌的慧根种苗。他指出象征诗人兰波的成功经验,就是对前代文学的认真吸纳,以致使他成为“许多文学史底摘要或菁华”⑧梁宗岱:《诗与真二集·韩波》,《梁宗岱文集》Ⅱ(评论卷),第177,178页。,并看到马拉美、梵乐希师徒二人从旧诗的格律和最古典的法文中创造出了一种新的文字,“不特能把旧囊盛新酒,竟直把旧的格律创造新的曲调,连旧囊也刷得簇新了”⑨梁宗岱:《诗与真·保罗·梵乐希先生》,《梁宗岱文集》Ⅱ(评论卷),第23页。。他进而论述道:“文艺底创造是一种不断的努力与无限的忍耐换得来的自然的合理的发展,所以一切过去的成绩,无论是本国的或外来的,不独是我们新艺术底根源,并且是我们底航驶和冒险底灯塔。”(10)梁宗岱:《诗与真二集·新诗底纷歧路口》,《梁宗岱文集》Ⅱ(评论卷),第157页。诗人浪费在“新旧之争”上其实是一种“短见”,对传统应保持严肃的敬意,惟“循”古——“采用那渐渐改良底系统”(11)[法]梵乐希作,梁宗岱译:《诗与真二集·哥德论》,《梁宗岱文集》Ⅱ(评论卷),第146页。——才能“创”新,甚而至于要在看不出连续性的事物中找到关系才能于文艺所有贡献(12)梁宗岱:《非古复古与科学精神》,《梁宗岱文集》Ⅱ(评论卷),第269页。。
从西方诗学转到中国诗学,他也要求破除“中外”之蔽,套用他翻译的梵乐希的话——“可是还有比受东方诱惑更是欧洲性底明证的么”①[法]梵乐希作,梁宗岱译:《诗与真二集·哥德论》,《梁宗岱文集》Ⅱ(评论卷),第151页。,他对西方诗歌的称道就同样是他表达中国性的逻辑和证据。这种“中外”逻辑也是“古今”逻辑,空间交接实寓时间的接榫。他尊古的取向一方面来自中国前代诗人的“复古”经验,一方面也受启发于西方的保守潮流。他引用勃莱克所说“所有的时代是相等的”②梁宗岱:《诗与真二集·新诗底纷歧路口》,《梁宗岱文集》Ⅱ(评论卷),第156,157页。,说明当时诗坛专事“打倒”的激进“革命”,其实是“一种玉石俱焚的破坏,一种解体”③梁宗岱:《诗与真二集·新诗底纷歧路口》,《梁宗岱文集》Ⅱ(评论卷),第156,157页。。
承认“旧诗体最大的缺陷(由极端的精炼和纯熟流为腐滥和空洞),是新诗惟一的存在理由”④梁宗岱:《诗与真二集·新诗底纷歧路口》,《梁宗岱文集》Ⅱ(评论卷),第156,157页。,但对前代诗学应“运用自己智力底源泉,从新的观点去研究新的应付或解决的方法”⑤梁宗岱:《非古复古与科学精神》,《梁宗岱文集》Ⅱ(评论卷),第269页。,方能进行“移花接木”,使传统变换新声,梁宗岱以回溯的方式推出他的诗学新观。他谈象征,多引类《诗经》《楚辞》、晋唐诗歌、北南宋词,显示新造必有旧端,并能掘微显象,分别高下真伪。如谈谢灵运、陶渊明诗,指出谢诗“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始终有一个旁观者,未得全喻,而陶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情景浑融,主客合一,才是真正的象征⑥梁宗岱:《诗与真·象征主义》,《梁宗岱文集》Ⅱ(评论卷),第64页。。他论诗受近世王国维的“境界说”影响很大,多用有我无我、隔与不隔标示象征的“境界”。王氏之说,在当时也已流出诗坛而归之于学术,位列“古典”,属于文学革命需要超越的对象,而梁氏上起古代传统下迄王氏之说,足见他总览远宗近源,别立诗宗的眼力。又如他谈纯诗,指出纯诗实起源于屈原的《九歌》,后世诗人宋玉、曹植、温李、姜白石、柳宗元等,“均各得其一体,便可成家”⑦梁宗岱:《屈原(为第一届诗人节作)》,《梁宗岱文集》Ⅱ(评论卷),第219,213—219页。;由此整理出中国诗歌的纯诗传统,并标示南宋词为其最高境界,在“言志”一派之外又新开一支文脉。他还提出文学发展的“树”型理论,以“树”型——枝桠的生长伸展——比喻作家所有作品的完整性、延展性,在这个一贯而完整的观念中,是传统“将随你的视域底广博和深远而增长”的意识。又如他在《屈原(为第一届诗人节作)》的文章中,反对当时学界有人认为《九歌》只是《离骚》的范本而非屈原作品的说法,指出《九歌》是屈原的早期作品。这种论说,是要引出他的新旧传统延续中的“支点”说——正是《九歌》这个看似不够分量的作品成为了《离骚》的“支点”;更进一程,他回溯到《诗经》,认为《诗经》是楚辞的“支点”,从《郑风·野有蔓草》到《少司命》,从《郑风·子衿》到《湘夫人》,从《卫风·硕人》到《山鬼》,从《邶风·击鼓》到《国殇》,使楚辞从“旧世界”来,又以新的情感方式和表现手法,创造出一个“新宇宙”,“不止灌注新的情感,并且创造了一种新的完美的诗体”。摸索梁氏文踪,其实隐含着“创作”来自于“改作”这一渐进改良的文学史的事实/逻辑。他还把这种创化视为西方文艺复兴大师们的手腕,屈原与《诗经》的关系如同文艺复兴画家创化《圣母像》一样,都是在“改写”中打破“因袭”而创造新境,从而推动文学的演进⑧梁宗岱:《屈原(为第一届诗人节作)》,《梁宗岱文集》Ⅱ(评论卷),第219,213—219页。。
梁宗岱谈的是中国新诗,但所用材料几乎全是“西典”和“古典”。重视“西典”,是“援西入中”,为中国新诗嫁接西方诗学资源;重视“古典”,是“守旧出新”,承接中国诗歌传统,为新诗固本培元,实现中国诗歌的现代化。但相对于引进西方诗学成就,他认为还是激活本源最为重要,因为学习他人,“即使做到亦步亦趋,而源泉不在自身,实无异于等天吃饭,终有匮竭之一日”⑨梁宗岱:《非古复古与科学精神》,《梁宗岱文集》Ⅱ(评论卷),第269页。。这种观点,在西方经典地位上升、中国经典地位下降的现代,含义十分明显。其平视中西、烛旧照新的态度,也是一种值得称道的“拿来主义”。他常用中西诗歌对举或互释的方法探索中国新诗的出路,证明中国自有现代诗学的原型,中国诗歌也有它永恒的意义和形式的基石,新诗试验无需彻底“革命”,打倒重来,现代诗人应该充分承认和尊重“古意”,实施转换而出以“新声”。梁宗岱甚至以“欢乐的源泉”比喻传统:“一个人和一个世代既经汲尽了他们底特殊关系所容许他们分受的它(传统)那神圣的流泻之后,另一个然后又另一个将继续下去,新的关系永远发展着,一个不能预见也未经想像的欢乐的源泉。”①梁宗岱在《屈原(为第一届诗人节作)》中所引雪莱《诗辩》文字,见《梁宗岱文集》Ⅱ(评论卷),第207页。把现代与传统的关系理解为一种永远的世代更新的关系,一种不停地发展着的“新的关系”。这在盛行“文化破坏主义”的现代,无疑具有补正纠偏的作用。
三、科学精神与诗
在常识看来,科学与诗,分属物质和精神两个领域,除非用科学作为诗的表现题材,两者的交集其实很少。可在梁宗岱眼里,认识宇宙万物真相,科学和诗具有异曲同工之处。科学探索世界的本原和普遍法则,诗也负有同样的使命,因为诗人的智慧“并不在于事事浅尝,事事涉猎,以求得一个浮光掠影的认识;而在于深究一件事物或一个现象到底,从这特殊的事物或现象找出它所蕴蓄的那把它连系于其他事物或现象的普遍观念或法则。一旦达到这‘基本态度’之后,正如俗谚所谓‘一理通,百理融’,万事万物自然都可以迎刃而解”②梁宗岱:《诗与真二集·哥德与梵乐希——跋梵乐希〈哥德论〉》,《梁宗岱文集》Ⅱ(评论卷),第152,150,150,152 页。。这个参透事物普遍法则的“基本态度”,就是诗人应该具备的科学精神。
这种观点来自文学史和科学史的相关史实,梁氏发现他所阅读、接触的大诗人如哥德与梵乐希,都是“以诗人而兼思想家科学家……属于全才一流的”人物③梁宗 岱:《 诗 与真 二集 · 哥德 与 梵乐 希— — 跋梵 乐 希〈 哥德 论 〉》 , 《梁 宗岱 文 集》 Ⅱ(评 论卷),第152,150,150,152 页。,在他们身上,科学探索和诗歌创作并无轩轾反而是两面一体。哥德精通植物学,探索的对象是外在世界,他“从森罗万象找出共通的法则,然后从那里通到自我底最高度意识”,创作出伟大的作品;梵乐希精通数学、几何学,把它作为探索心灵法则的实验科学的最有力工具,他“先对自身法则有澈底的认识或自觉,然后施诸森罗万象”④梁 宗岱:《 诗与真二 集·哥德 与梵乐希 ——跋梵 乐希〈哥 德论〉》 ,《梁宗 岱文集》 Ⅱ(评论 卷),第152,150,150,152 页。,写出了绝世的象征诗歌。梁氏由此指出“诗人是两重观察者”,对外物的掌握越准确,心灵就越自由越丰富;对心灵的认识越深入,就越能穷物力之变,探造化之微。这不仅涉及诗歌探索真理的主题和影响及于形式上“谨严”与“自由”的张力,还显示了科学和诗歌互相激发的促动。如他看到“梵氏是现代欧洲最大的诗人,但普氏(普恩迦赫)那被数学界公认为‘数学论证法底真正灵魂’的‘循环法’却得自他的暗示;反之,当我读普氏底科学论文的时候,除了不断地惊异他对于文艺的理解外,有些句子几乎使我疑心是梵氏底诗底前身”⑤梁宗岱:《非古复古与科学精神》,《梁宗岱文集》Ⅱ(评论卷),第271,284,262,269页。;他还引用《天演论》作者赫胥黎把哥德的散文诗《自然》当作英国科学杂志《自然》发刊词时说的一句话——“这篇《自然》是哥德年青的作品,写了若干年了。可是我觉得不独哥德本人在自然科学这方面的探讨赶不上它,就是未来自然科学底造诣也不能超出它的藩篱”⑥梁宗岱:《非古复古与科学精神》,《梁宗岱文集》Ⅱ(评论卷),第271,说明诗人探索真理、把握世界真相所具有的价值和前导作用。梁宗岱论诗贯串着求真的意志,科学对于世界的精密观察,无疑可作为诗的助力。
在作于1935年的《哥德与梵乐希》和1941年的《非古复古与科学精神》中,梁宗岱都用不少篇幅谈到科学精神对诗的重要性。对科学精神的持续关注,源于他对中国缺乏科学精神的判断。在他看来,中国自宋明以来虽有“格物”、“致知”的认识论,但均以伦理学为依据,“认识论不能脱离伦理学而独立发展”⑦梁宗岱:《诗与真二集·哥德与梵乐希——跋梵乐希〈哥德论〉》,《梁宗岱文集》Ⅱ(评论卷),第152,150,150,152 页。,“本体论和认识论等形而上部分却惊人地片段和零碎”⑧梁宗岱:《非古复古与科学精神》,《梁宗岱文集》Ⅱ(评论卷),第271,284,262,269页。,始终是科学精神无以张扬的一个主因,影响了诗人探索心物究竟的能力。他认为五四以来中国学界高标的“科学主义”,专力于对传统的“打鬼”,无甚科学可言,所倡导的科学,并未“溯本探源,根植于我们民族性底深处,以期达到一个独创的阶段”而修成正果⑨梁宗 岱:《 非古复古 与科学 精神》 ,《梁宗 岱文集》Ⅱ(评论卷),第271,284,262,269页。,相反对科学的“副产品”如飞机、电话、潜水艇等产生“恋物癖”,影响及于诗歌,便是以常识代替真知的惰性,流于表象而不能深入究竟。他感叹当时不少诗人的头脑“根本是‘加减式’或‘算术式’的”,“所能想像和欣赏的诗文,自然只限于一加一减,至多不过一乘一除而已。你和他们谈代数,谈几何,谈微积分不独等于‘对牛弹琴’,并且他们很少不目你为‘痴人说梦’的”(10)梁宗岱:《诗与真二集·诗·诗人·批评家》,《梁宗岱文集》Ⅱ(评论卷),第187—188页。。对于五四以来提倡科学精神的中坚胡适,他就蔑称为“一个以常识来处理和解决一切专门问题的思想家”,批评他“自认为代表作”的诗歌《飞行小赞》“古人辛苦学神仙,/要守千百戒,/我今不修不炼,/也凌云无碍”,正显示出“不修不炼”的懒惰①梁宗岱:《非古复古与科学精神》,《梁宗岱文集》Ⅱ(评论卷),第270,270、268,270、266页。,缺乏运用精神力量征服表象、探究物我关系的能力。梁氏一向批胡甚力,或有过甚之辞,而在诗学较量上,时有肯綮之论。梁宗岱虽断定宋明以来中国缺乏科学精神,但对先秦两汉诗哲对世界的探索却保持相当的敬意,注意发挥其潜德幽光,认为“孔老庄之所为孔老庄”,就是因为他们具有“抓住一切事理底核心或深层关系的灵机和洞见”②梁宗岱:《非古复古与科学精神》,《梁宗岱文集》Ⅱ(评论卷),第270,270、268,270、266页。。循此灵机洞见,孔子要求诗人多识草木虫鱼之名便具科学探索的内涵,孔子“逝者如斯夫”的感叹,由于“同时直接抓住了特殊现象和普遍原理底本体,是川流也是宇宙底不息的流动”,并且“表现方法暗合了现代诗之所谓‘具体的抽象化,抽象的具体化’底巧妙的配合”,“所以便觉得诗意葱茏了”。与之对照,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我们不能在同一的河入浴两次”,由于“是辩证的,间接的,所以无论怎样警辟,终归是散文”,无法达到中国诗哲的高度③梁宗岱:《说“逝者如斯夫”》,《梁宗岱文集》Ⅱ(评论卷),第126页。。他又举出汉代贾谊的《惜誓篇》与胡适的《飞行小赞》相对照,认为从贾诗“一举兮知山川之迂曲,再举兮睹天地之圜方”,“可以一目览尽其中每一个元素,以及它在整个系统中所占的位置”,而且“又是永无止境的,永远发展和扩大的,峰外有峰,真理外还有真理”;胡适的飞行诗只有“感情底自然的流露”,而贾谊的飞行诗却“所举愈高,所见亦愈广博而愈真切”④梁宗岱:《非古复古与科学精神》,《梁宗岱文集》Ⅱ(评论卷),第270,270、268,270、266页。,具有“穷天人之际”的深邃、气魄和不断追求“真理”的意志。梁宗岱如此论证科学精神与诗的关系,致力于“把准绳的科学与美感的直觉融在一起”⑤梁宗岱:《诗与真·保罗·梵乐希先生》,《梁宗岱文集》Ⅱ(评论卷),第15页。,打破唯物唯心的二分法,统一诗人内外探索的两条路,在当时中国科玄对立,诗坛缺乏探索力、感受力、表现力的背景下,起到了以科学精神的求真和精密激发“文艺的想像”的作用。
四、现代“畸人”的诗性意味
中国历来有“畸人”,其特征是独立特行,不合流俗,恣肆自我,诗文超迈有真气。《庄子·大宗师》云:“子贡曰:‘敢问畸人?’曰:‘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成玄英疏为“畸者,不耦之名也。修行无有,而疏外形体,乖异人伦,不耦于俗”。其行状如宋陆游《幽事》诗之二所述:“野馆多幽事,畸人无俗情。静分书句读,戏习酒章程。”其作诗如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高古》所论:“畸人乘真,手把芙蓉,泛彼浩劫,窅然空纵。”郭绍虞为其集解:“畸,奇异也……真……畸人乘真,谓畸人乘其真气而上升也。”可见“畸人”所涉实在“诗与真”两面。如以这些条例加诸梁宗岱,则他分明是一现代“畸人”,并饱具诗性的意味。
梁宗岱一生酷爱陶诗,如用“无俗韵”名之,是恰如其分的。当新诗运动风起之时,他创作的诗歌便被目为“与别的作家显有不同之处,喜欢研究新诗者不可不读”⑥引自黄建华、赵守仁:《梁宗岱》,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1页。。在岭南大学研习文学,他就阅读陶诗入迷,并在法国留学时把陶诗翻译成法文,进献于文豪梵乐希、罗曼·罗兰,后由巴黎Editions Lemaiget出版社于1930年出版。和许多专攻一艺、师从一门的留学生不同,他留欧七年,从不受“专业”、“学位”限制,游历于法国、意大利、德国、瑞士等国大学和名山大川,结交名士,淬炼新知,淘洗心灵,壮大胸怀意志。他的“留学”实为“游学”,他“游于艺”而不取学位,这一点与同属中山大学的陈寅恪教授最为近似。
因陶诗结缘的梵乐希和罗曼·罗兰对陶渊明其人其诗都充满钦敬,罗曼·罗兰对陶诗“少无适俗韵”更是沉吟再三,体味不已⑦梁宗岱:《诗与真二集·忆罗曼·罗兰》,《梁宗岱文集》Ⅱ(评论卷),第198页。。他们二人对梁宗岱都影响巨大。前者“纯思想纯美感底悦乐”,在“诗”的一面启发梁宗岱最深,后者提倡的“新英雄主义”要求“做一个‘人’,一个顶天立地一空依傍的好汉”,在“真”的一面对梁宗岱的“处世伦理”有更大的影响;罗曼·罗兰主张的一个人要用毕生精力征服痛苦完成工作和弃绝“领袖欲”、“奴隶性”,更是梁宗岱一生行事独张自我、坚持己见的精神之源①梁宗岱:《诗与真二集·忆罗曼·罗兰》,《梁宗岱文集》Ⅱ(评论卷),第194,194页。。如在与同道论学时,他从不掩饰自己的“不耦于俗”,甚而张大自己一空依傍的独立特行。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现代大学体制渐入正轨,学者多安于一家从事专门而系统的著述,可梁宗岱却甘于做野狐禅的狐狸型学者,自道“事事都爱涉猎,东鳞西爪,无一深造”②梁宗岱:《诗与真二集·论崇高》,《梁宗岱文集》Ⅱ(评论卷),第108页。。其原因在于他所研究的对象是活泼诗文而非灰色理论,是追踪天纵诗性而不限于理性学问。他作文虽有底蕴理据,却是发散思维,任由文思行云流水,非至于穷形尽相然后达旨得意而不止,同道对此或时有微词,他却坚持一生从未有任何改变。又如40年代他突然抛出诗集《芦笛风》,全用格律词体,被诗界视为“弃甲曳戈的逃兵”,招致广泛的批评。可他的“反潮流”,恰恰是要对新诗的“矫枉过正”再来一次矫正,为新诗施以“镣铐”,重建它的“纪律”和“规矩”。新诗发展二十余年,“诗体大解放”的形式革命导致新诗自由过度,讲究格律被看成汩没性灵、个性的举措,松散的自由诗成为新的一律,因此他的惊人之举也是找回诗人“个性”的象征方式③参单世联:《梁宗岱:诗人的戏剧生涯》,《南方周末》2001年12月20日。。他说:“就是词又怎样呢,如果它能恰当地传达我心中的悸动与眩晕?”④梁宗岱:《试论直觉与表现》,《梁宗岱文集》Ⅱ(评论卷),第297页。这是他一贯反对诗人“为人”写诗,主张“今之诗人为己”⑤梁宗岱:《诗与真二集·诗·诗人·批评家》,《梁宗岱文集》Ⅱ(评论卷),第187页。,弃绝浅薄凡俗,大胆抒写自我,保有纯真本性的表现。特别是《芦笛风》记录的是他和甘少苏的不凡爱情,甘是一个不识字的普通粤剧花旦,二人的结缡招致众人的不解和非议,但他自道“世情我亦深尝惯,/笑俗人吠声射影,/频翻白眼。/荣辱等闲事,/但得心魂相伴”,并不以为意。他的“逆流写词”和“抗俗结婚”也是他弃俗取真、不拘格套的性情流露。后来甘少苏在《宗岱和我》中回忆道:“在纵情声色、人欲横流的社会里,宗岱抛弃了世俗观念,用艺术审美的眼来鉴别人的品性,从社会的最底层发现了我,付出了很高的代价救我于水深火热之中,让我恢复了人的尊严,走出了苦海,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这种“乖异人伦”的“畸人侠客”⑥见郭希仁《从戎纪略》附《钱君定三传》。行为,实则又是梁宗岱“毫不犹豫地把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带到生活中去”的最佳证明⑦梁宗岱:《诗与真二集·忆罗曼·罗兰》,《梁宗岱文集》Ⅱ(评论卷),第194,194页。。鲁迅先生在论“清之拟晋唐小说”时曾说“畸人异行,出于幻域,顿入人间”⑧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11页。,则梁甘因缘中的诗情(幻域)和侠义(人间),庶几近之,其本身就是一部精彩的“传奇”。
写诗论诗,梁宗岱可谓“畸人乘真,手把芙蓉,泛彼浩劫,窅然空纵”,即使生活中留给人的印象,也是“修行无有,而疏外形体”的畸人形貌。学生称他“大模大样”,与其说他是文学教授不如说他是体育老师,他的几十个“老子天下第一”常常成为学生编排他是“自大狂”的生动资料⑨卢岚:《心灵长青——怀念梁宗岱老师》,《梁宗岱文集》Ⅰ(诗文卷·法译卷)“附录”,第233—240页。。对于“他摇着大蒲扇,精神抖擞,急促促地、甚至是雄赳赳地行走,脸庞满溢红光,笑起来像顽童”的姿容,北京大学同事、英文教授温源宁曾惊为独步寰宇的天人,认为他的诗人真趣可以补充书斋学问家欠缺的生活力:“万一有人长期埋头于硬性的研究科目之中,忘了活着是什么滋味,他应该看看宗岱,便可有所领会。万一有人因为某种原因灰心失望,他应该看看宗岱那双眼中的火焰和宗岱那湿润的双唇的热情颤动,来唤醒他‘五感’世界应有的兴趣;因为我整个一辈子也没见过宗岱那样的人,那么朝气蓬蓬,生气勃勃,对这个色、声、香、味、触的荣华世界那么充满了激情。”其实这种激情源于一种生命的“沉醉”,有时形成一种可爱的较真的“力”。在流传的一些关于他的故事里,最精彩的莫过于他因论诗衡艺而与人吵架,甚而至于上演全武行的生动案例了。如他自道:“朱光潜先生是我的畏友,可是我们意见永远是分歧的。五六年前在欧洲的时候,我们差不多没有一次见面不吵架。去年在北京同寓,吵架的机会更多了:为字句,为文体,为象征主义,为‘直觉即表现’。”①梁宗岱:《诗与真二集·论崇高》,《梁宗岱文集》Ⅱ(评论卷),第108页。他挖苦梁实秋:“我不相信世界还有第二个国家——除了日本,或者还有美国——能够容忍一个最高学府外国文学系的主任这般厚颜无耻地高谈阔论他所不懂的东西。”著名古希腊研究学者罗念生教授回忆:“1935年我和宗岱在北京第二次见面,两人曾就新诗的节奏问题进行过一场辩论,因各不相让竟打了起来,他把我按在地上,我又翻过身来压倒他,终使他动弹不得。我警告他,如再动手,我可以一拳送他回老家。”抗战时期在重庆北碚复旦大学,他和一位中文系长发老教授为一个学术问题争论起来,没几下便交起手,“两人从休息室一直打到院子当间,终于一齐滚进了一个水坑;两人水淋淋爬了起来,彼此相觑一下,又一齐放声大笑。这两位师长放浪形骸的潇洒风度,令一些讶然旁观的学生永远忘不了。”还是温源宁说得好:“宗岱喜好辩论。对于他,辩论简直是练武术,手、腿、头、眼、身一起参加。若一面走路一面辩论,他这种姿势尤为显著:跟上他的脚步,和跟上他的谈话速度一样不容易,辩论得越激烈,他走得越快。他尖声喊叫,他打手势,他踢腿。若在室内,也完全照样。辩论的题目呢,恐怕最难对付的就是朗弗罗和丁尼孙这两位诗人的功过如何。要是不跟宗岱谈,你就再也猜不着一个话题的爆炸性有多大。多么简单的题目,也会把火车烧起来。因此,跟他谈话,能叫你真正筋疲力尽。说是谈话,时间长了就不是谈话了,老是打一场架才算完。”②参李冰封:《想起了梁宗岱先生》,《读书》1991年第7期;杨建民:《争辩——梁宗岱的生活方式》,http://www.gmw.cn/content/2004 -12/14/content_123706.htm.
1956年,经历了“浮士德”式丰富生活——当然,除了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外,1944年蒋介石派人坐总统专车招见,他借酒醉不应,以伸诗人意气,不为权贵所熏灼——的梁宗岱,在阔别母校30多年后再次回到康乐园,任中山大学外文系教授。他独立直行的性情依然不改。当政治氛围紧张之时,他还敢于放言“违俗”之论,批评1958年之后的大学校园自由学术空气渐趋稀缺,是因为“现在大家都有戒心,怕抓辫子,受牵连,弄到‘比邻若天涯,老死不相往来’”。他不顾流言提携有天赋的学生,却指责热衷政治而疏于问学的青年:“你应该分一部分精力把法文学好,否则你将成为空头政治家!”他怀疑某种不顾规律的“团结论”,说:“团结要有一定的基础,和一些不学无术的假知识分子怎能搞好团结呢?”最为率性的是,文革中看到有人在校园刷写巨幅标语“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如果我们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便出言建议“‘所以’两个字不必要,删去更简洁些”。全然不觉这是领袖语录,不可妄评,更不得作一字修改,径以“诗家语”批改“政治经典”。而与此形成映照的是,梁宗岱在自己的红墙绿瓦小楼购置了三台电唱机,经常邀请同事、学生共坐,手把红酒,欣赏品味西方古典音乐③参黄建华、赵守仁:《梁宗岱》,第227—265页。。他在交响乐的流转飞扬中以酒为伴,沉酣不已,保持诗心常在,诗脉不坠,完成了重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浮士德》的重要工作。这种“畸人无俗情,静分书句读,戏习酒章程”的行为,与其说是表面可见的“抗俗”,毋宁说是体验生命底里的“沉醉”诗意。他说:“只有醉里的人们——以酒,以德,以爱或以诗,随你的便——才能够在陶然忘机间瞥见这一切都浸在‘幽暗与深沉’的大和谐中的境界。”④梁宗岱:《诗与真·象征主义》,《梁宗岱文集》Ⅱ(评论卷),第71页。这是生命世界最高的象征主义,梁宗岱完成了他生命诗学最华美的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