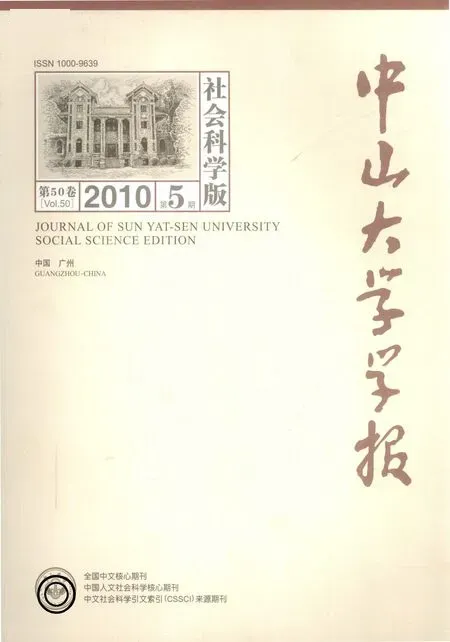婉约之“约”与词体本色*
杨 雨
一、引言:作为基本词学范畴的“婉约”
“婉约”与“豪放”是词学两大基本范畴,在词史的发展上,代表了两种不可偏废的艺术风格和审美趣尚。婉约与豪放的正变之争是词学史上聚讼纷纭、绵延不绝的问题。本文无意于辨析两者何者为正,何者为变。但是,就整个词史的客观面貌而言,我们必须承认,“婉约”词始终在数量和整体质量上占据着绝对优势,这也决定了词学界会将关注的重点不约而同地聚焦在“婉约”这一基本范畴上。这里需要廓清的是:婉约与豪放风格的区别,并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认定的婉约词派与豪放词派。词史上其实并不存在豪放派与婉约派的绝对分野,即便是公认的豪放词风的代表作家苏、辛,他们其实也有不少或“韶秀”,或“妩媚”,或“声韵谐婉”、“婉曲缠绵”,或“秾丽绵密”、“昵狎温柔”的词作。按照对“婉约”范畴的一般界定,苏、辛的这类作品也完全可以视为婉约风格的典范。因此,词史上的客观事实是:只有婉约或豪放的词作风格,却并不一定要截然划分婉约派词人或豪放派词人。假如将词学范畴体系看作一株枝繁叶茂的“大树”,那么“婉约”作为词学一大基本审美范畴,也许可以当成是这棵“树”上最重要的一根“树枝”,是词学范畴体系中的骨干部分,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他相关词学范畴的产生与延伸。
纵观上个世纪以来的词学研究,“婉约”无疑是聚焦程度最高的范畴之一,20世纪以“婉约”词为研究对象的论著约150来篇(部)①据王兆鹏20世纪词学研究论著目录索引。。不过,检阅大多数以“婉约”为研究对象的论著,基本上都旨在阐明“婉约”作为词的一种独特美学风格的表现:或从题材论②许伯卿:《宋代婉约、豪放二词派作品题材构成分析》,《江海学刊》2003年第3期。,或从语言的雅俗论③罗章:《语言与宋婉约词的雅俗个性》,《重庆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或比较婉约与豪放词风表现形态的差异①陈忻:《南北宋婉约词不同的表现形态及其成因》,《中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2期。,或视“婉约”为宋词的阶段性发展形态②许德楠:《宋词三阶段:婉约、豪放、醇雅》,《中国韵文学刊》2003年第2期。,或追溯婉约词之渊源③王力坚:《宋代婉约词与六朝诗风之关系》,《文学遗产》1996年第2期。……将“婉约”视为美学范畴,从范畴论的角度对其进行全面审视还需等到21世纪:华东师范大学2003届博士周明秀的博士论文《词学审美范畴研究》对词学的重要审美范畴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其中单列一章把“婉约”作为正体风格论(“豪放”为变体风格论范畴),探讨“婉约”范畴的本义及渊源,以及在词学理论中的内涵延伸,并以“阴柔”作为婉约词的主要风格美类型。朱崇才在《文学遗产》2007年第1期发表的《论张綖“婉约—豪放”二体说的形成及理论贡献》具体而全面地分析了婉约、豪放从一般概念上升到词学基本范畴的理论飞跃。该文根据张綖的另一重要词学文献——明黎仪抄本《草堂诗余别录》,并结合张綖多方面的词学实践,考察了“二体说”形成的思想脉络及其对词学理论的贡献,考论均很有说服力。通过这些研究成果,“婉约”作为词学基本范畴的面貌日趋明晰,其概念的界定也日趋规范和严谨,也为对“婉约”范畴的一步阐释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笔者在研读上述研究成果时也发现,对“婉约”这一范畴的理论认识仍有可以继续深入之处:作为范畴的语言载体,当“婉约”这一语词并提时,人们对它的认识已有一个基本公认的规范,但“婉”与“约”在各自的理论界定中却还有可以补充的地方。本文即拟从对“约”的重新认识出发,进而试图对“婉约”这一范畴进行更全面的梳理。
二、“淖约”与“隐约”:“约”的双重内涵
对“婉”的理解一般并无疑义。《说文》:“婉,顺也。”④许慎:《说文解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618页。从女,即“和顺宛转”⑤《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第1246页。意。“婉”既可形容人物(尤指女性)外貌的“柔和美好”,如“有美一人,清扬婉兮”(《诗经·郑风·野有蔓草》),以及性格的柔和温顺,如“妇德尚柔,含章贞吉,婉嫕淑慎,正位居室”⑥张华:《女史箴》,萧统:《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404页。;又从形容人物容貌性格的和顺美好引申为形容书法、诗文风格的柔美和顺,如钟嵘论诗曰:“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⑦钟嵘:《诗品》,何文焕:《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3页。其后“婉”更成为词学批评中最常用的范畴之一。如苏轼评黄庭坚词“清新婉丽”⑧苏轼:《跋黔安居士渔父词》,吴熊和主编:《唐宋词汇评》两宋卷第1册,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615页。,认为“微词婉转,盖诗之裔”⑨苏轼:《祭张子野文》,曾枣庄、舒大刚主编:《三苏全书》,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年,第427页。;关注评叶梦得词“婉丽绰有温、李之风”(10)关注:《石林词跋》,吴熊和主编:《唐宋词汇评》两宋卷第2册,第1206页。;贺裳认为“少游能曼声以合律,写景极凄婉动人”(11)贺裳:《皱水轩词筌》,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96页。;“宋人作词多绵婉,作诗便硬”(12)王又华:《古今词论》引毛稚黄词论,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609页。。“婉”还可用来形容声音的婉转缠绵,如姜夔自序《暗香》:“使工妓隶习之,音节谐婉。”(13)唐圭璋:《宋词三百首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23页。“婉”从“宛”声,又有婉转曲折之意,如《左传·成公十四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杜预注曰:“婉,曲也。谓屈曲其辞,有所辟讳,以示大顺,而成篇章。”(14)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65页。词,作为一种新兴韵文体,因其独特的女性气质,“她”从唐代一开始登场亮相就具备了女性化“婉”的各种意蕴:曲调的婉转和美,文辞的婉曲清丽,歌者姿容的婉娈和性情的婉顺,以歌筵酒席为主要传播场境的婉媚华艳……这种以女性化的婉美为主导的审美趣尚,一直贯穿在词创作的整个盛衰史以及词学理论的发展全过程中。
相对于“婉”而言,“约”作为另一审美范畴进入词学视野则要晚得多。“约”与“婉”并提始于南宋许:
近时僧洪觉范颇能诗,其《题李愬画像》云:“淮阴北面师广武,其气岂止吞项羽。公得李祐不肯诛,便知元济在掌股。”此诗当与黔安并驱也……又善作小词,情思婉约,似少游。①
考察此则诗话主要论洪觉范诗,并拟之黄庭坚,又以“婉约”评词,并拟之秦观。虽然许并未就“婉约”范畴作具体阐释,但在其意识中,显然是以“婉约”作为与豪放诗风相对的概念来解释词之柔婉情致的。那么,“约”作为特定范畴,到底该如何界定呢?
在探析“婉约”这一范畴的时候,学界或以“简约”来界定“约”的内涵,这固然有一定道理。如陆机《文赋》之“若夫丰约之裁,俯仰之形”,李善注引《广雅》曰:“约,俭也。”②陆机:《文赋》,萧统:《文选》,第770,776,770页。“铭博约而温润”,注曰:“博约,谓事博文约也。”③陆机:《文赋》,萧统:《文选》,第770,776,770页。陆机:《文赋》,萧统:《文选》,第770,776,770页。也是文辞简练的意思。《文赋》中亦有“婉约”并提:“或清虚以婉约,每除烦而去滥。”④陆机:《文赋》,萧统:《文选》,第770,776,770页。陆机:《文赋》,萧统:《文选》,第770,776,770页。此处之“约”仍可理解为“除烦去滥”,精炼文辞。但是“约”还有另一层涵义,即“隐约”。《说文》:“约,缠束也。”⑤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647页。运用在文字表现上则为隐微难明,将复杂的意蕴裹束在简洁的文辞中,非一语道破之义。《荀子·劝学》云:“《春秋》约而不速。”⑥荀子:《劝学》,《诸子集成》第3卷,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第8页。王先谦注曰:“文义隐约,褒贬难明,不能使人速晓其意也。”⑦王先谦:《荀子集解》,《诸子集成》第3卷,第10页。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以一字寓褒贬的“春秋笔法”了。司马迁评价屈骚“其文约,其辞微”,认为《离骚》文辞隐微曲折,微言大义,“其称文小而其旨极大”⑧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缩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629页。。总的来说,“约”的基本内涵应是“俭约”与“隐约”的集合:即以相对俭约的文辞将丰富的意蕴隐约其中,达到言简意深、言近意远的艺术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约”除了通常认为的“俭约”、“隐约”之意外,还有一层意思,即“美好”,而且是偏向女性气质的柔美。《庄子·逍遥游》:“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郭庆藩注引为“淖约,柔弱貌”,“好貌”⑨郭庆藩:《庄子集释》,《诸子集成》第4卷,第15—16页。。显然,“淖约”是用以形容女性体态的纤柔美好,“‘处子’在室女也”。因女性体貌的柔美又引申出性情品格的柔弱温顺甚至卑下。如《国语·吴语》:“故婉约其辞,以从逸王志,使淫乐于诸夏之国,以自伤也。”注云:“婉,顺也;约,卑也。”(10)鲍思陶点校:《国语·吴语》,济南:齐鲁书社,2005年,第291页。从这个意义而言,“约”便与“婉”基本同义,都可以用来表示女性美的柔顺特质。女性身体曲线具有独特的凹凸有致、婀娜柔婉、摇曳多姿的美感,引申到文学批评中则多用以形容文学作品委曲缠绵的美学风貌。如陆时雍评诗:“意态在于转折,情事在于犹夷,风致在于绰约,语气在于吞吐。”所谓“情事在于犹夷,风致在于绰约”,即“善言情者,吞吐深浅,欲露还藏,便觉此衷无限”(11)陆时雍:《诗镜总论》,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423页。。言情之诗的妙处在于朦胧委曲,含蓄缠绵,婀娜绰约,风情万种。沈雄《古今词话》引《柳塘词话》云:“孟载诗如西湖柳枝,绰约近人。”(12)沈雄:《古今词话》,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1024页。则是以“柳枝”般纤柔婀娜的体态拟诗词的婉转绸缪之风度。而“婉”在特定语境下也有俭约的意思。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杜预注曰:“婉,约也。‘险’当为‘俭’字之误也。大而约,则俭节易行。”①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第1100页。由此可见,在文学批评理论中“婉约”并提,至少有三种可能的涵义:其一是“婉”和“约”都解释为和顺美好,用以形容女性化的柔美委曲;其二是“婉”和“约”都解释为俭约、隐约,用以表达含蓄幽微的艺术风貌;其三是前述两者的融合,即文学作品形式的婉转和美,情意的俭约隐微,曲折蕴藉,“终不许一语道破”的意思。
三、歌者词婉转淖约之美与文人词隐约蕴藉之美
按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盖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抵词体以婉约为正,故东坡称少游为今之词手;后山评东坡词“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所录为式者,必是婉约,庶得词体,又有惟取音节中调、不暇择其词之工者,览者详之。④张綖:《诗余图谱·凡例》,《续修四库全书·集部词类》第1735册,第473页。
张綖婉约、豪放二体说的提出是在唐宋词经历了从萌生到全盛再由盛而衰的全过程后,因此张綖实际是用这一组对待性范畴对词体美学风格进行总结性的理论概括,并在此基础上对“婉约”进行进一步地理论阐释:“婉约者欲其词情蕴藉。”显然,张綖是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来理解“婉约”的,即形式的婉转柔美和内容的沉厚隐微。所谓“蕴藉”,意近“隐约”。蕴,积聚。《说文》:“蕴,积也。”⑤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40,42页。又有丰饶之意,还引申为事理深奥,如《正字通》:“蕴,奥也。”⑥《汉语大字典》,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年,第1385页。《说文》:“藉,祭藉也。”⑦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40,42页。本为祭祀时陈列礼品的垫物,引申为铺垫①《汉语大字典》,第1379页。。张綖以“蕴藉”释“婉约”,显见更加侧重其内容的内在蕴含,因此他并不认为豪放之词就绝对排斥蕴藉。如评陈与义《临江仙》(忆昔午桥桥上饮):“豪放而不至于肆,蕴藉而不流于弱。”但在对词的整体接受上,张綖却是更偏向婉约的。因此尽管婉约可能伤于纤弱,有妨气格,但对于词体来说,纤弱却正是其不同于诗的特性,也正符合了词体的淖约之美。如评欧阳修《浣溪沙》(小院闲窗春色深):“结语尤曲折。婉约有味。若嫌巧细,词与诗体不同,正欲其精工。”②以上张綖评语见黎仪抄本《草堂诗余别录》,详参朱崇才《论张綖“婉约—豪放”二体说的形成及理论贡献》(《文学遗产》2007年第1期)。基于这样的美学主张,张綖继承许的观点,尤为推崇秦观,以秦观词为婉约的典范,也就不难理解了③张綖“存乎其人”的说法倾向于认为“婉约”、“豪放”的美学风格是由词人的性格气质及其主观创作态度决定的,实则就苏轼的词创作来看“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的评价并非客观实际。但张綖确立“婉约”、“豪放”作为词体的两大对立美学风格范畴,仍不失为能基本反映词史客观面貌的中肯之见。。
“婉约”范畴一经提出,立即引起了词学界的关注和普遍认同。稍后徐师曾的《文体明辨序说》沿用了张綖以“词情蕴藉”论婉约,并强调了婉约为正、豪放为变的正变观,其后以“婉约”论词则绵延不绝。那么,既然词之“约”包含女性化的淖约之美和文人化的隐约之美,具体到词人创作的实践上,这两种美学风格又是如何各自发展又彼此交融的呢?
(一)歌者词之婉转淖约美
笔者曾以南渡为界,将词的传播史划分为“歌者之词”时期和“文人之词”时期。这一划分是基于词的传播性质的改变,并综合前人的词史阶段论而提出的:胡适将词在唐宋时期的传播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歌者的词——诗人的词——词匠的词”。他将歌者之词的界限划到苏东坡,认为苏之前是“教坊乐工与娼家妓女歌唱的词”;诗人之词的时代则止于辛弃疾、刘克庄;姜夔以下到宋末元初为词匠之词④胡适:《词选自序》,胡明主编:《胡适精品集》卷6,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第265页。。在胡氏提出“三段论”之前,王国维也曾在《人间词话》中提到词至李后主而一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无意中将词划分为两个阶段。胡氏的三段论实承王国维,其理论依据主要是从词的功能论出发,即词的创作是否承担了言志抒怀的主要功能。在“伶工之词”也即“歌者之词”的时代,词主要是应歌而作,目的是尊前侑觞,以娱乐功能为主;进入“士大夫之词”的时代以后,作为艳科之词逐渐从仅仅以资娱乐的功用上升到言士大夫之身世、家国感慨。如果说,胡氏和王氏的阶段论都是从词的功能论出发进行划分的,那么笔者的两段论则是基于词的传播实践活动:时间上以宋室南渡为界,之前的唐五代、北宋为第一阶段,词以口头传播为主,“歌者”词创作的中心,词人作词的对象、传播的媒介甚至目的就直接指向唱词的人。之后的南宋至清朝为第二阶段,词从以口头演唱为主要传播方式转变为以书面传播为主,词人作词的目的逐渐转向抒发个人身世、情感、社会的怀抱和文人之间的酬唱应和,传播媒介除了歌者,更大程度上依赖于纸质媒体的书面传播。这一划分并非将词的历史截分为前后互不相关的两段,歌者之词的时代以口头演唱为主要传播方式,但并不排斥书面传播;同理,文人词时代以书面传播为主,也不排斥歌者仍然扮演着口头演唱的重要角色,但其在词的传播活动中所占比重确实是有了较大的差异⑤详参拙文《歌者之词与文人之词》,《海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首先,词是作为口头演唱文学进入文学史的视野的。词自唐五代到北宋,基本上还是处于“歌者之词”的阶段,它的主要传播媒介就是唐代所说的“音声人”,即乐工歌妓。口头传播时期以歌者为中心的“面对面”的交流⑥参阅拙文《略论歌妓文化与词的兴起和传播》,《词学》第13辑,2001年11月。,直接促成了词的婉转淖约这一风格的形成。以女性为主体的传播媒介决定了词的生存和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女性传播的方式和特点:依靠面对面的视觉、听觉等感官刺激直接进行交流来获取传播讯息。从词的传播角度而言,这一阶段歌者在传播活动中主要依靠的技巧就是“性感”,即所谓“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娇娆之态”①欧阳炯:《花间集序》,《花间集》,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页。。
在传播学理论中,有4种技巧是经常运用在传播活动中,并且企图“说服”传播对象来接受相关信息的——图像、幽默、性感和重复。在这4种常用技巧中,“性感”说服在词的传播活动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②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著,郭镇之等译:《传播理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200,200页。。在词兴起的最初,边客游子、忠臣义士、隐君子、少年学子、医生佛子等等都能借歌曲各抒己怀,但正如王灼所说,词在后来的发展却是从“古人善歌得名,不择男女”到了“独重女音”③王灼:《碧鸡漫志》,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79页。的地步,流行歌曲在后来逐渐越来越集中到歌女身上,成为她们重要的生存技能。除了基本的技艺之外,“性感”是其最主要的谋生手段,而词又很快与这种“性感”资本配合,形成了天衣无缝的默契,并且终于在与歌者关系密切的文人那里获得了肯定的回应。文人在与歌者的交往中当然也会将产生的愉悦感觉转移到歌者所传达的消息——歌词上去,导致文人对歌词的态度由最开始的忽视、轻视慢慢变为重视。而在这一传播过程中,词作为传递的信息因歌者这一特定传播媒介而“变得性感化,或带有性感因素”④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著,郭镇之等译:《传播理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200,200页。,形成了词的“侧艳”与淖约的基本特色。
概言之,从题材看,词从产生起就与“儿女情长”结下了不解之缘。《花间集》几乎完全就是一个女性世界,以女性主人公为描写对象的词超过了总数的80%。即便是号称豪放之祖的苏轼,他的300余首词中,语涉女性或男女情爱的也占了一半强⑤据唐圭璋《全宋词》统计,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其“‘采索身轻常趁燕,红窗睡重不闻莺。’如此风调,令十七八女郎歌之,岂在‘晓风残月’之下”⑥贺裳:《皱水轩词筌》,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696—697页。。
就语言和意象而言,词也具备“语懦而意卑”⑦王炎:《双溪诗余自序》,施蛰存:《词籍序跋萃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302页。的特点,词中常用的意象如“泪”、“梦”等多与女性心理特点及柔弱的刻板印象相关。即便是写景的意象也以女性化的轻柔妩媚为特征。杨海明《唐宋词美学》在对《全宋词》排名前100的高频字进行统计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唐宋婉约词在‘色’的方面所给人的感受,也以那种女性化的风容色泽最为鲜明突出。”⑧参阅杨海明:《唐宋词美学》,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21—324页。
从创作态度上看,诗人填词最初大多是以“谑浪游戏”的态度为之,以是否能合乐歌唱,尤其是合“女乐”歌唱为主要评价标准。既然填词为“薄伎”,目的也只是为了“聊佐清欢”,那么,词人在抱着游戏笔墨的态度时并不会有意识像传统诗学要求的那样赋予词以言志载道的功用,词人的这种游戏心态也纵容了词之淖约风姿的继续发展。
对词之女性化这一客观现象的存在,词学界当然不可能视若无睹。因此古典词话论著中,遵循文学批评传统的感悟式、崇比喻的特点,对这类词的体认,常以女性形象比拟之。如张耒评贺铸词“盛丽如游金、张之堂,而妖冶如揽嫱、施之祛”⑨张耒:《东山词序》,吴熊和主编:《唐宋词汇评》两宋卷第1册,第750—751页。;周济评温庭筠及韦庄词“飞卿,严妆也。端己,淡妆也”(10)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1633页。;李清照评秦观词“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11)李清照:《词论》,吴熊和主编:《唐宋词汇评》两宋卷第1册,第679页。;郭麐评花间词人及晏欧诸公“风流华美,浑然天成,如美人临妆,却扇一顾”,秦周贺晁诸人“施朱傅粉,学步习容,如宫女题红,含情幽艳”(12)郭麐:《灵芬馆词话》,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1503页。;彭孙遹评周邦彦词“如十三女子,玉艳珠鲜,政未可以其软媚而少之也”①彭孙遹:《金粟词话》,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721页。。
可以说,在词的传播活动中,歌女与文人构成的传播关系决定了词以婉媚淖约为主要审美趣尚,而且这种审美趣尚一经奠定,就成为了贯彻词史始终的主流意识。
(二)文人词之隐约蕴藉美
南宋以来,词进入以书面传播为主的文人词时期,文人词之“约”又具备了哪些特点呢?
如果说,相对于歌者的口头演唱传播以风姿淖约、语娇声颤为感官的审美享受,那么文人词以纸质媒体为主要的传播媒介就有了新的优势——传载信息的稳定性与可复读性更适合传递内容复杂、阅读所需的背景知识比较艰深的信息,因此,用典、双关、蕴藉、言外之意等,就成为纸质媒介无与伦比的优越性。反映到文字表现力上,就是充分发挥书面语言含蓄、凝练的优长,使文字中蕴含的信息更加丰富,使用的符号单元更加俭省。词的隐约之美,正是应和了这种纸质书面文字的表达特质。
既然歌者之词的传播特点注重的是“面对面”的声色交流,其传播形式的娱乐性、即时性和随意性必然造成词在滥觞期的重“声”不重“辞”,看重的是音律的和谐婉媚和歌词是否合律。至于歌词是否清雅、内涵是否深刻倒并不重要:一则乐工歌妓的文学素养还不能将歌词创作提高到文学创作的高度,二则迎来送往、喧嚣热闹的职业生涯也使得他们(包括作为传播主体的歌妓和传播对象的文人和市人)尚无暇顾及雕琢歌词的内容。随着词的发展和日益受到重视,出现了一批将自己才情的精华部分都倾注在词创作中的文人,他们精通音律,着意辞藻,注重词的独特体性,并且出现了历史上第一篇有关词的专论——《词论》。李清照在《词论》中提出了词“别是一家”的主张,从理论上要求词从口头演唱的率意上升到文人创作的严肃。李清照虽然并未从理论上提出“婉约”这一范畴,但她的创作实践和系列理论范畴的提出,却实现了词从仅关注形式的妩媚淖约到更重意蕴的含蓄隐约的提升。从这一点上说,李清照被后人推为婉约词之宗祖是当之无愧的:
张南湖论词派有二:一曰婉约,一曰豪放。仆谓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惟幼安称首。②王士祯:《花草蒙拾》,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685页。
南宋文人词的特色表现得更为明显:文人结社、酬唱风气盛行,以学问为词、以议论为词、比兴寄托成为有意识的创作手段等等。这几大特点除了“以议论为词”尚属辛派词人所特有之外,其他几个方面均为南宋重要词人和重要词人群体所共有。尤其是风雅派词人,不仅继续稳固了词婉媚淖约的女性化特质,还大力发展了词之隐约深微的审美风尚,其用典使事、比兴寄托等创作手法的运用其实都是为了使作品在有限的容量里包含无限的内涵和联想空间。因此“约”在词创作中的内涵,不仅在于字句的凝练,无拖沓语,无累赘语,并且还须具备感发的力量,能于言有尽之外体味到意无穷之感,吟诵已尽而余音袅袅。例如陈廷焯评姜夔《点绛唇》云:
白石长调之妙,冠绝南宋,短章亦有不可及者。如“点绛唇”一阕,通首只写眼前景物。至结处云:“今何许。凭阑怀古。残柳参差舞。”感时伤事,只用“今何许”三字提唱,“凭阑怀古”下,仅以残柳五字咏叹了之。无穷哀感,都在虚处。令读者吊古伤今,不能自止。洵推绝调。③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3798页。
陈廷焯此评实质上就是指出了姜夔《点绛唇》一阕虽为小令,却做到了言约意远,触发人的“无穷哀感”,实是姜夔在词中运用了比兴寄托的创作手法之缘故。再如谭献评王沂孙《眉妩·新月》一词云:“圣与精能,以婉约出之。”④谭献:《复堂词话》,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3992页。而张惠言也认为:“碧山咏物诸篇,并有君国之忧。此喜君有恢复之志,而惜无贤臣也。”⑤张惠言:《张惠言论词》,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1616页。
南宋诸词人除了在用典使事、字锤句炼和比兴寄托方面深下工夫之外,由于他们多作长调,因而对作品的营章布局也极为讲究,在该煞住时煞住,该宕开时宕开,以此营造一种沉郁跌宕、缠绵反复的委曲之“约”的艺术效果。读南宋人词,在咀嚼其声律和谐、深厚蕴意之时,尚须兼味其章法结构的高妙。词评家在评点南宋词人作品时亦多对此予以足够的关注。如吴文英《齐天乐》词:
烟波桃叶西陵路,十年断魂潮尾。古柳重攀,轻鸥骤别,陈迹危亭独倚。凉颸乍起,渺烟碛飞帆,暮山横翠。但有江花,共临秋镜照憔悴。 华堂烛暗送客,眼波回盼处,芳艳流水。素骨凝冰,柔葱蘸雪,犹忆分瓜深意。清尊未洗,梦不湿行云,漫沾残泪。可惜秋宵,乱蛩疏雨里。
陈洵评此词曰:
此与《莺啼序》盖同一年作。彼云十载,此云十年也。西陵,邂逅之地,提起。“断魂潮尾”,跌落。中间送客一事,留作换头点睛三句,相为起伏,最是局势精奇处。谭复堂乃谓为平起,不知此中曲折也。“古柳重攀”,今日。“轻鸥聚别”,当时。平入逆出。“陈迹危亭独倚”,歇步。“凉飔乍起”,转身。“渺烟碛飞帆,暮山横翠”,空际出力。“但有江花,共临秋镜照憔悴”,收合。倚亭送客者,送妾也。柳浑侍儿名琴客,故以客称妾,“新雁过妆楼”之“宜城当时放客”,“风入松”之“旧曾送客”,“尾犯”之“长亭曾送客”,皆此“客”字。“眼波回盼”,是将去时之客。“素骨凝冰,柔葱蘸雪”,是未去时之客。“犹忆分瓜深意”,别后始觉不祥,极幽抑怨断之致,岂其人于此时已有去志乎。“清尊未洗”,此愁酒不能消,“凉飔”句是领下,此句是煞上。“行云”句着一“湿”字,藏行雨在内。言朝来相思,至暮无梦也。梦窗运典隐僻,如诗家之玉溪,“乱蛩疏雨”所谓“漫沾残泪”。①陈洵:《海绡说词》,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4847页。
在长达百余字的长调中,不光精妙的布局能给词营造出抑扬顿挫、含蓄蕴藉的艺术氛围,所谓“笔笔能留”、“运典隐僻”实际上也是指出在词之章法中既要可“放”更要能“约”(收束)的创作笔法。而文辞之隐约曲折、缠绵幽深又和词之雅化相辅相成。作为文人词的主要传播媒介——书简、印刷品等纸质媒体,其相对于面对面的口头传播,最大的特点就是:它不再是“一时高兴”的游戏笔墨之作,而是经过了文人的深思熟虑,再三推敲后的作品。同样,当这样的作品传播到其接受者(一般同样也是文人)那里的时候,接受者亦不可能仅凭“直觉”的感受,而必须也经过深思熟虑,反复品味,咀嚼作品的用典使事、营章布局、遣词工雅、协律与否等等多方面文学因素,深入发掘隐约于文辞中的丰富意蕴。正像论者评南宋词人时所云:
梦窗之词,丽而则,幽邃而绵密,脉络井井,而卒焉不能得其端倪。②冯煦:《六十一家词选例言》,吴熊和主编:《唐宋词汇评》两宋卷第4册,第3328页。
王碧山词,品最高,味最厚,意境最深,力量最重。感时伤世之言,而出以缠绵忠爱。诗中之曹子建、杜子美也。词人有此,庶几无憾。③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3808—3809页。
如果说,词之婉丽淖约的感官审美效应凭藉面对面的传播交流就可直观感受到的话,那么词之隐约深微之美则必须等到文人词时期,凭借纸质媒体,进行再三复读,不断在眼前重现,才能透过字句的表面,深味其含蓄无穷、言近旨远的韵致。
(三)推崇“隐约”是词体雅化的重要标志
“约”既然同时具有“俭约”与“隐约”的涵义,即文辞的简洁和内容的复杂丰富和隐微委曲,由此需要再辨析的就是:就词体而言,如果说以文辞俭约来界定小令的体制还可说得过去的话,那么南宋以后慢词长调成为文人词的主要流行体式,以铺叙为特点的慢词长调又如何体现“约”的风格呢?依笔者所见,在“俭约”与“隐约”两重义中,词学范畴对于“约”的体认与接受是更偏重于隐约的,也就是说,“俭约”并非针对词与其他文体(如律绝等诗歌的传统形式)的体式对比。事实上,词的体式又何尝比诗更为俭约?但是,就词所能容纳的意蕴而言,词之体式又确乎是俭约的。因此,词之“俭约”并非仅就体式而言,而是相对于其所蕴积的情、意而言。明晰了这一点,“约”这一理论范畴可同样运用于小令与长调就并不矛盾了。在“俭约”与“隐约”两者中,既然词体“调有定句,句有定字”,形式的“俭约”是已经规定好的,那么“隐约”理所当然就成为更为主要的理论要求。周明秀的博士论文《词学审美范畴研究》以“不说”、“不直说”、“层深地说”归纳婉约词达成“含蓄”的三种方法,所论颇有见地。“不说”以温庭筠《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翠翘金缕双鵣”等词)为例,整首词似乎都在铺陈女性的容貌服饰及其相关的纤柔意象,而主人公与作者的情感却是隐藏在文辞之外秘而不宣的。也难怪温词要被人批评:“谀之则为盛年独处,顾影自怜;抑之则侈陈服饰,搔首弄姿。”①李冰若:《花间集评注·栩庄漫记》,王兆鹏主编:《唐宋词汇评》唐五代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24页。陆时雍评温诗为:“有词无情,如飞絮飘扬,莫知指适。”②陆时雍:《诗镜总论》,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第1422页。这段话同样可以移用来评温词。但也正因为其意蕴的“莫知指适”,温词作为《花间》词婉约的正宗,因其“不说”而给后来的接受者留下了无限的阐释空间,才有可能依据诗学系统的香草美人、比兴寄托传统,被解读出“《离骚》初服”③张惠言:《张惠言论词》,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1609页。之意,被提升到“深美闳约”④张惠言:《词选序》,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1617页。、“全祖风骚”⑤吴梅:《词学通论》,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6年,第71页。的境界。这倒可能是温庭筠作词之初所未想见的。
“不直说”也就是“曲说”,即言在此而意在彼。“长短句名曰曲,取其曲尽人情,惟婉转妩媚为善。”⑥王炎:《双溪诗馀·自序》,施蛰存:《词籍序跋萃编》,第302页。例如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即被前人评价为“无限凄婉,却又妙在含蓄。短幅中藏无数曲折”⑦黄蓼园:《蓼园词评》,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3024页。;周邦彦《少年游》(并刀如水),妙在“言马言他人,而缠绵偎倚之情自见。若稍涉牵裾,鄙矣”⑧沈谦:《填词杂说》,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632页。。
“层深地说”则更契合长调慢词之曲折往复⑨相关论述可参阅周明秀博士论文《词学审美范畴研究》第7章《含蓄:词体表现方法范畴》。。长调慢词本因体式的扩充和笔墨的铺叙展衍而使“隐约”的难度更大,因而对词人的创作技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成为词之文人化和雅化的标志之一(10)长调慢词作为词的一种体式并不能成为区分歌者之词与文人之词的标志,但对长调慢词创作技巧的讲究却是文人之词的重要特质,这一重要特质正是通过对“隐约”的自觉追求来体现的。。前引吴文英《齐天乐》词就是典型范例,此不再赘列。反之,如果在长调慢词中浪费笔墨,尽情展衍铺叙,使词缺乏委曲、收束之美,则有失婉约之旨了。例如秦观《水龙吟》(小楼连苑横空)词,苏轼曾讥笑其首联“小楼连苑横空,下窥绣毂雕鞍骤”:“十三个字只说得一个人骑马楼前过。”张綖以秦观为婉约词宗,但在选评此词时亦认为“率易无甚思致”而被删去(11)详参朱崇才:《论张綖“婉约—豪放”二体说的形成及理论贡献》,《文学遗产》2007年第1期。。柳永的许多慢词之所以被目为俗,也是因为他在铺叙展衍中“备足无余”,把话都说尽了,没有达到“隐约”的要求。如宋征璧所云:“词家之旨,妙在离合,语不离则调不变宕,情不合则绪不联贯。每见柳永,句句联合,意过久许,笔犹未休,此是其病。”(12)沈雄:《古今词话·词品》引,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850页。当然,柳永并非不能“曲说”或“层深地说”。如郑文焯即认为柳词:“浑妙深美处,全在景中人,人中意,而往复回应,又能寄托清远。达之眼前,不嫌凌杂。诚如化人城郭,唯见非烟非雾光景。殆一片神行,虚灵四荡,不可以迹象求之也。”(13)郑文焯:《手批石莲庵刻本乐章集》,台湾:广文书局影印本。但部分柳词之所以有“意过久许,笔犹未休”的毛病,还是因为在某些特定场境下,他的创作目的仍是以歌者为中心,在刻意迎合以歌者及市井百姓为主要传播者和接受者的审美水平。
可见,文人词对“约”的美学追求中,在“俭约”的规范下,“隐约”才是其更高的理想境界。一方面,含蓄委曲符合传统的“温柔敦厚”诗教之旨,为词在创作上的雅化提供了实践依据;另一方面,深隐幽微之美也为以比兴寄托、香草美人为旨归的词之再阐释提供了无限空间,进一步为词学批评的尊体和雅化提供了理论基础。
四、淖约与隐约的理论升华:比兴寄托
张綖提出婉约—豪放二体说后,其理论在清代词学中兴期得到了更丰富的延伸,“婉约”范畴的内涵也更明晰和丰富,“约”和“婉约”成为词学批评论著中出现频次最高的范畴之一。如郭麐评女词人许庭珠《采桑子》词“婉约之情,一往而深”①郭麐:《灵芬馆词话》,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1523页。;欧阳炯“词大抵婉约轻和,不欲强作愁思”②冯金伯:《词苑萃编》引蓉城集,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1825页。;蒋敦复评周济词“缠绵婉约中,得深厚之致”③蒋敦复:《芬陀利室词话》,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3633页。。
相对于唐宋词而言,清代词创作与理论虽然有了再度的振兴,但此时的词,早已“物是人非”,不再与歌唱相倚伴,成为纯粹的“案头作业”。相应地,无论是“醇雅”、“雅正”、“清雅”、“骚雅”,还是“比兴寄托”,词之雅化几乎成了压倒一切的创作规范和美学标准。其实质就是希望改变词为小道的传统观念,推尊词体,将以艳情为旨归的唐宋词也打上“比兴”的烙印,从而达到“微言大义”的“隐约”的审美境界。这类理论的登峰造极者首推常州词派。到张惠言这里,词之婉约的标准更加明确化了:虽然词体“文小”“声哀”,却是借“风谣里巷男女哀乐”,来抒发“贤人君子幽约怨诽不能自言之情”,并且上攀“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④张惠言:《词选序》,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1617页。,有着深厚的感慨寄托。被他推崇备至的温庭筠,也不再是那个“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的浪荡公子,而是“其言深美闳约”的词坛“最高”之人。
在清代词学界,以各种词学理论和范畴为词之“约”作注解的并非张惠言一人。浙西派始祖朱彝尊的主要词学理论“醇雅”说主张的就是以词为文学载体,运以比兴寄托的手法:“词虽小技,昔之通儒巨公往往为之。盖有诗所难言者,委曲倚之于声,虽辞愈微,而其旨益远。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此尤不得志于时者所宜寄情焉耳。”⑤朱彝尊:《陈纬云〈红盐词〉序》,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3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91页。“假闺房儿女之言”,即是肯定了词体形式之淖约美的独特性;“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则是以比兴寄托发展了词之情意“隐约”的审美理想。
浙派自朱彝尊始普遍推崇姜夔、张炎等南宋词人,除了南宋风雅派词人的工于音律之外,另一主要原因即如王昶所云:
姜、张诸人,以高贤志士放迹江湖,其旨远,其词文,托物比兴,因时伤事,即酒食游戏,无不有《黍离》周道之感,与《诗》异曲而同其工,且清婉窈眇;言者无罪,听者泪落。⑥王昶:《姚茞汀词雅序》,《春融堂集》卷41,《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438册,第90页。
姜氏夔、周氏密诸人始以博雅擅名,往来江湖,不为富贵所熏灼,是以其词冠于南宋,非北宋之所能及。暨于张氏炎、王氏沂孙,故国遗民,哀时感事,缘情赋物,以写闵周、哀郢之思,而词之能事毕矣。⑦王昶:《江宾谷梅鹤词序》,《春融堂集》卷41,《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438册,第88页。
也就是说,不管南宋诸词人其词作于何种场境之下,“托物比兴”、“因时伤事”、“哀时感事”、“缘情赋物”甚至是“酒食游戏”之作,都是在“清婉窈眇”的文辞中蕴藉有深厚的家国之慨,因此他们的作品才能“与诗异曲而同工”,非为沉溺于花前酒下之“富贵”“熏灼”的北宋所能及。
浙派式微,常州派代而起兴,主张不一,且力革浙派末流推尊姜夔而导致的空滑之病,但在“比兴寄托”这方面,仍与浙派殊途而同归,甚至走得更远,如周济的“寄托出入”说和“诗有史,词亦有史”说。谭献的“折衷柔厚”说之重心也在强调利用词体独特的含蓄隐婉的表现形式,来阐发“比兴之义”:
愚谓词不必无颂,而大旨近雅。于雅不能大,然亦非小,殆雅之变者欤。其感人也尤捷,无有远近幽深,风之使来。是故比兴之义,升降之故,视诗较著,夫亦在于为之者矣。①谭献:《复堂词话·复堂词录序》,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3978页。
陈廷焯以“沉郁”说为其理论核心,对“沉郁”这一范畴,他有系统的理论阐释,这就是他在《白雨斋词话》卷1开章明义所概括的:
所谓沉郁,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写怨夫思妇之怀,寓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而发之又必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匪独体格之高,亦见性情之厚。②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3777页。
“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还是旨在阐明词的隐约委曲之美学理想。
以况周颐为代表的晚清四大家之词学理论更是彻底摈弃了词在口头传唱时期娱宾遣兴、宴嬉逸乐的基本娱乐功能,将比兴寄托说进一步推向深化。传统词学之“终结者”王国维在清代诸词派的理论之外,独拈出“境界”一说,但他的理论同样推崇比兴寄托,强调作词“观物之微,托兴之深”③王国维:《人间词甲稿序》,《人间词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6页。,应寓有“忧生”、“忧世”之意。
其实,无论是浙派还是常州派,或者两派绳墨之外的词学家,在崇比兴寄托以推尊词体这一大方向上是一致的。如刘熙载《艺概·词概》:
词之妙,莫妙于以不言言之,非不言也,寄言也。如寄深于浅,寄厚于轻,寄劲于婉,寄直于曲,寄实于虚,寄正于余,皆是。④刘熙载:《艺概·词概》,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3707页。
一言以蔽之,“意内而言外谓之词”,张惠言解词的深文周纳虽然有些可笑,但是清代词学家们努力想摆脱词为小道、卑体、末技的努力仍是值得肯定的。他们以比兴寄托为词创作与理论的旨归,甚至不惜“锤幽凿险”地挖掘词中可能蕴含之微言大义,更是为“隐约”的理论升华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至此,词之隐约委曲之美学范畴的成熟,使词从理论批评和创作实践上都摆脱了词萌生初期因偏重淖约之形态美而可能产生的柔弱纤靡之病,肯定了词之淖约柔婉的形态下,完全可以蕴含隐约的深厚情意,而像诗一样承载起言志抒怀的大任。“淖约”与“隐约”的组合实际上就是既承认词与诗体性的不同——诗如君子,词则美人也——但是又主张词与诗在文学基本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以微言承大义,同归于变风之义,骚人之歌:
两宋词派,推吾乡周清真,婉约深秀,律吕谐协,为倚声家所宗……尺凫之为词也,在中年以后,故寓托既深,揽撷亦富,纡徐幽邃,惝恍绵丽,使人有清真再生之想。⑤厉鹗:《吴尺凫玲珑帘词序》,《樊榭山房集》文卷4,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477页。
词家者流,其源出于《国风》,其本沿于齐梁。自太白以至五季,非儿女之情不道也。宋立乐府,用于庆赏饮宴,于是周、秦以绮靡为宗,史、柳以华缛相尚,而体一变;苏、辛以高世之才,横绝一时,而奋末、广贲之音作。姜、张祖骚人之遗,尽洗秾艳而清空婉约之旨深。自是以后,虽有作者欲离去别见,其道无由。⑥郭麐:《无声诗馆词序》,吴宏一、叶庆炳编辑:《清代文学批评资料汇编》下集,台北:成文出版社,1978年,第602页。
很显然,到了清代词论家这里,他们已经不能满足对词婉转淖约的形式美要求,而特别标举对“约”的内容要求,无论是“幽约”、“闳约”、“婉约深至”、“婉约深秀”、“婉约之旨深”,还是“寄言”、“意内言外”、“言近旨远”、“意在笔先,神余言外”等等,都是在强调词创作要超越其体格之小、之卑,遵循比兴寄托的香草美人传统,将“孽子孤臣之感”、“忠爱悱恻、不淫不伤之旨”隐约蕴藉于柔婉的文辞之中,深厚缠绵,含蓄隽永,典雅醇厚,归于词之雅正。“婉约”并提,即从特定的角度表达了在词学理想中,“约”的最高境界就是淖约缠绵的女性风致与隐约委曲的风雅气度的双美绾合。
五、结语:以婉约为正与词史之尊体
词从滥觞、发展期的以歌者为中心,到全盛期的以文人为中心,虽然词体的风格越来越多样化,但总的发展趋势却是明晰的——词的尊体雅化是一条不可逆转的主要潮流,而在雅化大潮中最主流的声音又是以婉约为正,以豪放为变。“婉约”因此成为词学的基本审美范畴。对婉约之“约”内涵的界定无疑也反映了这一主流的正变观:首先以淖约美的女性风致奠定了词区别于传统诗歌的“别是一家”的体性。传统诗歌非无淖约美,但淖约婉娈并非诗歌的基本特质。词学批评之所以以豪放为变,其原因之一还是豪放词部分地遮掩了诗词的差异,影响到词体的独立性,而使词成为“句读不葺之诗”。出于对词体基本特性的尊重与维护,词学批评史上以婉约为正是符合词体发展客观事实的。为了纠片面追求淖约婉娈可能导致的纤弱绮靡之弊,又以香草美人的阐释传统赋予词以隐约深微的比兴寄托之旨,并在实践上成为创作的理论指导。词之“约”就从淖约的形式美上升到淖约与隐约的形式美和内容美的浑成,并在“隐约”的基础上促成了词学批评向诗学体系的靠拢和交融,最终完成词的尊体目标——词之尊体的终极理想就是既坚持了词体独有之淖约美,又达到了词学批评向隐约蕴藉、温柔敦厚的诗学回归。
——评陈水云教授新著《中国词学的现代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