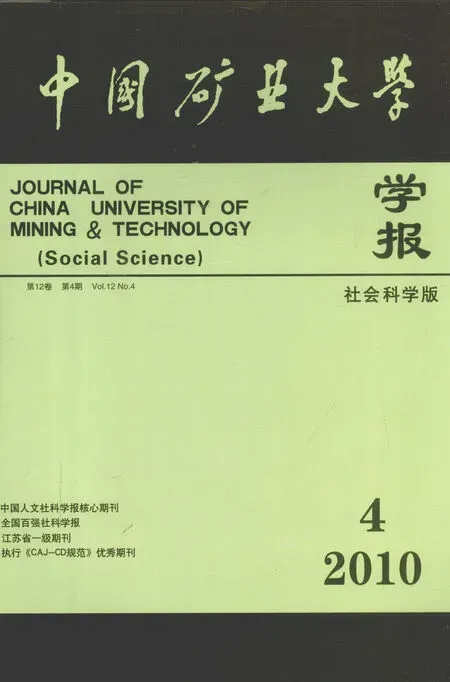从功能对等角度论英译汉中的“同构现象”
朱 哲,刘 优,郭 华
(中国矿业大学外文学院,江苏徐州 221116)
从功能对等角度论英译汉中的“同构现象”
朱 哲,刘 优,郭 华
(中国矿业大学外文学院,江苏徐州 221116)
“同构”在翻译实践中比比皆是,可视为一种归化翻译。在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看来,它属于功能对等的范畴。鉴于翻译在本质上是无法实现绝对或完全对等这一事实,本文主要论述了在尊重目的语读者的前提下“同构”在翻译中的运用及其作用。文章同时指出,“同构”翻译策略很好地体现了“翻译即交际”这一原则,最大限度地提升了目的语读者对源语文化的理解和吸收,该翻译策略是实现本族语文化与源语文化对话的有效方式,极大地促进了跨文化交际活动。文章还指出,运用“同构”策略翻译时所损失的信息可以通过使用各种补偿手段来进行弥补,从而尽可能多地传达出源语所包含的信息。
同构现象;功能对等;归化;跨文化交际
从功能对等角度探讨英译汉中的“同构现象”是目前译界成果较少的一个学术领域,除美国翻译学家尤金·奈达(Eugene A.Nida)等在其著述中有所论述外,“同构现象”在翻译领域鲜有提及。究其原因,其一是“同构现象”往往被简单地理解为“对等”;其二是当前翻译理论研究重点已经转向文化,从关注源语向关注目的语过渡,并潜藏着某种回归语言学范式的趋势。“同构现象”虽然不是奈达翻译理论体系中的核心问题,但其有重要的研究价值。首先,“同构”与功能翻译观存在思想上的一致性;其次,“同构”的核心要素即“类像性”(iconicity)符合交际翻译的需要和原则。更多地关注目的语读者,从功能翻译视角能给予其更多地解读,即运用功能对等理论解释翻译中的同构现象是可行的。需要指出的是,同构并不适合所有的翻译活动,它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即为了更有效地进行跨文化交际,它的指向是语用的,更多地关照目的语读者。本文重点从这一角度切入探讨同构在翻译中的应用。
一、同构、功能对等及相关理论和概念
同构是一个生物学或数学名词。根据美国普利策奖获得者、认知科学家道格拉斯·霍夫施塔特(D.R.Hofstadter)的定义:当两种复杂的结构能够互相影射时,它们就是同构的。通过这种方式,一个结构中的每一个部分在另一个结构中有与之对应的部分,这里的“与之对应”指的是在各自的结构中,两个部分所起的作用相似[1]。比如说,一副标准的、背面为绿色的52张扑克牌和一副标准的、背面为棕色的52张扑克牌,尽管它们有各自不同的背面颜色,但这两副牌在结构上却是同构的,即如果我们想玩牌,不管选择哪一副牌都可以。“同构”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辨别和讨论对等问题非常有效的策略。事实上,同构的概念只是符号学中类像性概念的一个延伸。同构现象广泛地存在于符号系统中,如阿拉伯数字1、2、3,罗马数字Ⅰ、Ⅱ、Ⅲ和汉语中的一、二、三,这些数字在各自的符号系统中尽管形式各异,但功能却是完全相同的。
奈达在谈到翻译的性质时,提出了“功能对等”的概念,这是对他早期提出的“动态对等”概念的一个完善。不同于后者的“以内容为主,形式为次”的思想,前者强调“不但信息内容的对等,而且尽可能地要求形式对等”[2]。受语用学的启发,以卡塔琳娜·莱斯(Katharina Reiss)和汉斯·弗美尔(Hans Vermeer)为代表的翻译功能派对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进行了发扬光大,使其灵活性和适用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他们认为,翻译是怀有具体交流目标的人所采取的一种行动,即“文本的目的”(the text’s Skopos)[3]。克里斯蒂安妮·诺德(Christiane Nord)甚至认为,Skopos原则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即“目的决定手段”(The ends justify the means)[4]。功能主义翻译观体现了语用学中一个重要的思想,即交际原则。功能派翻译家认为,译者根据受众/消费者的文化背景和需要,可以选择忠实于原文精神,或者选用一种逐字翻译策略,抑或增加、删除或更改他们认为适合的信息。正如埃德温·根茨勒所指出的那样,功能翻译理论打破了长期以来困扰译界的直译和意译的二元对立,使得译者在特定条件下能灵活地选用适当并且合理的翻译策略以实现跨文化交际目的。译者的地位不再是二流的和机械的,译者、作者、编辑和客户的地位是平等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功能翻译理论与“归化”翻译观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功能翻译理论并非一味地“归化”,排除异质。从语用学和交际学的角度看,功能翻译理论和奈达的“功能对等”一样,也强调译文的连续性、通顺性和自然性。总之,功能主义的翻译理论体现了现代翻译理论的一个发展方向:从“以原文为中心”向“以译文为中心”的理论转变。
同构现象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在各个领域都有很多的应用。在翻译理论与实践中,同构现象也是比比皆是。
二、同构在翻译实践中的运用
在翻译实践中,同构在拟声词、谚语、成语翻译等方面都有比较切合的运用。同构充分体现了现代翻译实践中“以译文为中心”的翻译理念,体现了“翻译即交际”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同构翻译能跨越文化的障碍,虽然译文中可能、而且经常有文化审美因素的损失,但较之于交际目的,这种损失则是一种相对的损失,并非使原文中的所有特定文化成分(cultural specifics)[5]湮灭于翻译的过程中。
(一)同构在英汉拟声词翻译中的运用
英汉两种语言分属不同的语系,在词法、句法或篇章结构方面差别极大,因此在翻译时译者必须进行相对应的调整,以使译文更符合目的语的表达习惯。在拟声词的翻译方面,同构原理的适用性很能说明这一调整的价值。英汉拟声词都是对事物自然声音的模拟。正确地翻译拟声词,“能够烘托气氛、显示意境、增强声势和实地情景感,使平淡的句子变得鲜活生动、富有情趣,创造出一种使人身临其境、如闻其声的氛围,达到传声达情和闻声解意的语用目的”[6]。奈达认为,最显而易见的语言同构体就是拟声词,如hiss,squawk,cluck和screech等[7]。奈达所列举的这几个拟声词既有直接拟声词(Primary onomatopoeia),如hiss和cluck,也有间接拟声词(Secondary onomatopoeia),如squawk和screech。笔者认为,这些词在汉语中都可以找到与之对应的拟声同构: hiss可译为“发出咝咝的声音”,squawk可译为“(鹦鹉、鸡、鸭等受伤或受惊时)发出粗厉的叫声”, cluck可译为“咯咯叫”,screech可译为“发出尖锐刺耳的叫声”。然而,从这些词的译文来看,汉语在模拟声音时有时显得力不从心,与英语对应的很多拟声词都要借助于“叫”再加上相应的描述词构成,这主要是因为英语中的拟声词要比汉语丰富,如:英语中表示狗叫的词有bark,yelp,yap,bowwow等,对应的汉语译文分别是“汪汪”、“短促的吠叫”、“狂吠”、“汪汪声”,但无论叫的程度如何,英国的狗叫声和中国的狗叫声不会因为国籍不同而有什么差异,即bark和“汪汪”是同构的。原文读者和译文读者在听觉感受方面是完全相同的。也就是说,英汉两种语言中的拟声词从功能上讲是对等的,是不负载文化含意的,是同构的。
鉴于英语中的拟声词数量众多这一事实,英译汉时通常采用以下三种方法:
1.直接译成汉语中的拟声词,如:The wolf howls.狼嚎。The lion roars.狮吼。The tiger roars.虎哮。The horse neighs.马嘶。The sheep bleats.羊咩。The donkey hee-haws.驴叫。
2.将英文的拟声词译为汉语中较为笼统的“……地叫,发出……的声音,……地响”,有的则直叙其动作。如:The frog croaks.青蛙呱呱地叫。The snake hisses.蛇发出嘶嘶的声音。The dove (cuckoo)coos.鸽子(布谷鸟)咕咕地叫。The hen cackles.母鸡咯咯地叫。The firecrackers cracked overhead.鞭炮在头顶上空劈劈啪啪地爆响。Tires screeched on the wet pavement.车胎在潮湿的路面上发出刺耳的声音。They splashed through the mire to the village.他们一路踏着泥水向村子走去。
3.为使译文更形象生动而增译拟声词,如: The logs were burning briskly in the fire.木柴在火中哔哔剥剥烧地正旺。
上述译例告诉我们,模拟创造或变通处理后的译文是原文的同构体。总之,在很多情况下,“英汉拟声词存在着缺省现象,但拟声词的缺省并非是思维的缺省,并非修辞功能的缺省,只是思维角度的不同。对于这类拟声词可以根据语言和思维的需要模拟创造或作变通处理。”[8]
(二)同构现象在英汉成语翻译中的运用
同构在很多情况下也负载着文化信息,这一点可以从英汉成语翻译中得以体现。众所周知,英语中的成语/习语不像汉语中的成语一样通常都是由四个字组成的。无论何种语言,成语都具有源远流长、约定俗成、言简意赅、思想丰富的特点。广义地说,英语成语/习语包括谚语(proverbs)、俚语(slangs)、俗语(colloquialism)、成对词(twin words)、三词词组(trinomials)、熟语(catchphrases)和习惯搭配(habitual collocation)等。由于语言的共性特征,在某些情况下英语成语在汉语中都有接近“自然对等(natural equivalent)”的译文,如:(as)firm as a rock(坚如磐石),(as)light as a feather(轻如鸿毛),sour grape(酸葡萄)等。但在更多情况下,由于中西文化差异和各民族生活经验的不同,对同一概念或事物存在着不同的表述方式。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中西方对于“百兽之王”的认识差异。在西方人心目中,狮子“勇敢、凶猛、威严”,是百兽之王,故有Lion King,而中国人历来认为老虎才是百兽之王;有关“狮”、“虎”意象差异的译例在中西文化中还有很多,如:Hares may pull dead lions by the beard. (虎落平阳被犬欺),beard the lion in his den(虎口拔牙),play oneself in the lion’s mouth(置身虎穴),come in like a lion and go out like a lamb(虎头蛇尾),like a key in a lion’hide(狐假虎威)。其他与动物有关的同构译例还有(as)close as an oyster(守口如瓶),(as)mute as a fish(噤若寒蝉),(as)strong as a horse(强壮如牛),(as)cool as a cucumber(泰然自若)等。从上述译例可以看出,在英语成语汉译时不能保留“异国情调”并非是译者的无能,实乃汉语中那些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佳肴让人无法抗拒,译者在这时“隐身”难道不是明智之举吗?如果用劳伦斯·韦努蒂的“阻抗式翻译(resistant translation)”策略[9],就会译出“强壮如马”和“冷若黄瓜”之类的译文了。当然,韦努蒂的“阻抗式翻译”旨在“抵制美国主流语言文化价值观对翻译文本的暴力归化”[10]。我们在探讨“同构”翻译时,切记不要留下“暴力”或“信马由缰”的印迹,不要从“暴力”的极端走向“自由”的极端。如果那样,就极容易陷入“翻译无政府主义”状态。冯庆华在论述汉语习语的英译时说:“我们可以尝试在译文中运用相对应的英语习语,来帮助英语读者体味习语的‘特殊风味’”[11]。笔者认为,恰当的译法应当使译文尽量接近原文,即译文和原文中的核心要素应当属于同一范畴。如果译文相对于原文中的核心要素被剥离,那译文就很难说是“同构”的,因为“同构”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意义的对等”,尽管翻译过程中存在着信息的损失,但这种损失应以不损害意义为前提。
成语是语言的精华,见之于书面抑或口头。为说明“同构法”在翻译实践的广泛应用,试再看数例。
1.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
译文:天助自助者。
如果译为“上帝帮助那些自我帮助的人”也是可行的,不存在理解的障碍,但在中国读者心里,这种译文却不是个滋味。原因就在于翻译是受意识形态(ideology)影响的,这也是不言自明的道理。功能对等翻译理论恰好给我们译者提供了一个可以跨越这种障碍的途径,因为译者可以根据一个民族的文化背景情况予以适当的“操纵”。即使“龙(dragon)”直译进入英美文化或“show(秀)”直译进入汉语文化后已经被普遍接受,那也不等于说双向文化交流就可以畅通无阻了。事实证明,有悖于意识形态或宗教信仰的译法都是有风险的。文化的双向交流是可取的,但旨在颠覆或入侵“文化他者”(Cultural Otherness)的翻译策略则是阴谋[12]。
2.The pot is calling the kettle black.
译文(1):盆儿叫嚷罐儿黑。
译文(2):半斤八两(或:五十步笑百步)。
可以看出,译文(1)是很好的直译,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一种纯粹“生物学意义”上的“绝对同构”,即从翻译的本体论上来讲,这种译法是最好的,它既有丰富的意象,也有饱满的意义。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不会遇到文化陷阱,没有文化缺失,因为中西文化都有这种非常形象生动的修辞手段。译文(2)是意译,即本文所主张的“功能同构”。对比译文(2)和原文,它们所具有的语言特点(简洁生动)和语言功能(传情达意)是相似的。因此,用同构概念解释翻译问题是很有意义的。我们可以把译文(1)这样的直译称之为“垂直映射”,把译文(2)称之为“远距映射”。在翻译实践中,译者经常会发现自己在“绝对同构”和“功能同构”之间徘徊,因为要考虑的因素实在太多,诸如文化、风格、读者对象、译作定位等。当面临多种选择时,译者应综合各种因素以求更适合翻译目的的译文。
3.throw the handle after the blade
译文(1):刀身丢失后连刀柄也扔掉。
译文(2):A.破罐子破摔B.孤注一掷C.破釜沉舟。
对比译文(1)与原文,我们发现这种译文在汉语中基本是不能被接受的,它们虽然绝对同构,但译文(1)较之于译文(2)则逊色不少。原文为成语,而译文(1)显然不是,只是对原文的一种阐释性翻译(hermeneutic translation)。从功能对等的角度考虑,译文(1)与原文没有形成理想的同构。译文(2)给出了三种选择,第一种最贴近原文,第二、三种从“适当的度”(range of adequacy)上来讲,已经离原文有点远了。奈达在修正“功能对等”这一概念时说,“总体看,因为不存在完全对等的译文,所以最好将‘功能对等’理解为一个适当的度。不同的译文可代表不同程度的对等。这就意味着‘,等值’一词不同于数学意义上的相等,它只是一个近似度,也就是说,译文和原文的功效可以达到怎样的相似。”①In general it is best to speak of"functional equivalence"in terms of a range of adequacy,since no translation is ever completely equivalent.A number of different translations can in fat represent varying degrees of equivalence.This means that"equivalence"cannot be understood in its mathematical meaning of identity,but only in terms of proximity,i.e.on the basis ofdegrees ofcloseness to functional identity. (Language and Culture:Contexts in Translating by Eugene A.Nida)因此,对于有些译文,“功能同构”比“绝对同构”更有说服力。
事实上,上述三例说明了在运用同构翻译策略时,译者应注意译文相对于原文的适用性。相对而言,“功能同构”要比“绝对同构”的适应性大得多。虽然不同文化之间的共性大于差异,但我们经常更多面对的却是差异。同构翻译可以使我们跨越文化的鸿沟,可以把译文从“直译圭臬”的窠臼中解放出来。在当今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这种策略顺应了“翻译即交际”这一翻译思想,能够较好地起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
三、同构翻译的成因和意义
一般来说,同构翻译的形成主要由语境的差异和语言符号系统间的差异等引起。
首先,自然环境孕育了人文环境和文化语境。在笔者看来,语境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自然地理、风土人情、宗教信仰、生活习惯等方面。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反映文化独特性(cultural specific)的一项非常重要的表征。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由于语境差异,原作中的某一种表达方式在译入语中没有相似或对等的表达方式,或同样的形象在出发语与目的语中分别代表不同的文化意象。”[13]因此,我们把grow like mushroom译成“如雨后春笋一样地生长”,而不会译成“如蘑菇一样地生长”。尽管中国人也知道蘑菇生长速度不亚于雨后春笋,但我们习惯上不这么说,就如同“兄弟之间不言谢”一样,一旦改变加入异质反而别扭,不如不变。不同文化语境的差异致使源语和目的语无法实现对等,更不用说“等值”了。但翻译还是要进行下去,因为交际是无法阻挡的。同构翻译策略无论在解释拟声词还是“文化负载词”(culturally-loaded words)[14]的翻译时都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其次,语言符号系统间的差异也是同构翻译策略被提出的重要原因。翻译的核心是语言活动,这是不言而喻的,“但纯语言学的翻译研究却一直不能回答困扰翻译理论家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可译性和对等,因为翻译所涉及的不仅仅是语言因素,还有大量非语言因素。符号学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有一个优越性是不言而喻的,即符号学使翻译跨出了纯语言研究的范围而进入了一个更加广阔而绚丽多彩的天地——文化的比较研究,能够全面系统地描写翻译的非语言因素(超语言因素)。”[15]我们说原文和译文是同构的,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其核心要素即意义不能改变。同构译文更多的指向交际和语用,因此文化要素的移植或多或少地会受到损害。同构的概念可以在符号学的大背景下展开,即使超语言因素因各种原因不能在译文中传达出来,但只要核心意义得以传达,则这种译文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在翻译实践中,我们经常会面临很多棘手的问题,尤其是涉及到负载有文化信息的翻译问题。语言中独特的文化内容往往是不可译的,但不能因此就撒手不管,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也不可能因为文化差异而裹足不前。实事证明,同构翻译策略很好地体现了“翻译即交际”这一原则,最大限度地提升了目的语读者对源语文化的理解,是实现本族语文化与源语文化对话的有效方式。同构强调功能的对等和意义的传达,容忍文化异质的流失,但这种容忍是建立在“逼真翻译”(translation of verisimilitude)所不能胜任的基础之上,流失也是无奈之举。同构译文中所失去的文化异质部分可以通过必要的手段,如脚注或尾注等予以补偿。
四、结语
本文从功能对等角度对同构翻译现象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探讨。首先,探讨是尝试性和经验性的,缺点甚至谬误在所难免。其次,文章未对文本类型进行界定,因此同构概念的普遍适用性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第三,本文仅从两方面对同构翻译现象进行了梳理,同构翻译概念是否在同一文本类型中具有更广泛的适应性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总之,笔者希望通过这种尝试,使有关同构翻译的概念、策略及批评研究进一步深入。比如,
可以从类像性概念出发对同构翻译现象进行论述,
使其置身于更广阔的视域中。
[1] Hofstadter,D.R..Goedel,Escher,Bach.an Eternal Golden Braid[M].NY:Basic Books,1979.
[2] Nida,EugeneA.Language,Culture,and Translating[M].Shanghai:Shanghai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3.
[3] Gentzler,Edwin.ContemporaryTranslation Theories[M].Shanghai:Shanghai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4.
[4] ChristianeNord.TranslatingasaPurposeful Activity:Functional Approaches Explained[M].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9.
[5] 卓新光,王晶.顺应理论视角下的文化专有项翻译策略[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 [6] 高永晨.英语动物拟声词及其翻译[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8):49~50.
[7] Nida,Eugene A.Language and Culture:Contexts in Translating[M].Shanghai:Shanghai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11.
[8] 傅敬民.思维视角的英汉拟声词研究及其翻译[J].上海科技翻译,2001(4):7~11.
[9] Venuti,Lawrence.The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M].Shanghai:ShanghaiForeign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6.
[10] 王东风.帝国的翻译暴力与翻译的文化抵抗:韦努蒂抵抗式翻译观解读[J],中国比较文学,2007(4).
[11] 冯庆华.红译艺坛——《红楼梦》翻译艺术研究[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9.
[12] 孙艺风.翻译与异质他者的文化焦虑[J].中国翻译,2007(1):1~5.
[13] 吕萍.文学翻译中的语境问题[J].中国翻译,2004 (5):59~62.
[14] 姜秋霞.审美想象与文学翻译的“等值阈”[J].中国翻译,2001(6):49~52.
[15] 叶子南.高级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10
Isomorphism in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from Perspective of Functional Equivalence
ZHU Zhe,LIU You,GUO Hua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Technology,Xuzhou 221116,China)
Isomorphism,considered as a means of domestication,can be found everywhere in translation practice.In Nida’s opinion,it falls into the category of functional equivalence.In view of the impossibility ofabsolute/complete equivalence in translation,the articlemainlydeals with the importance of isomorphism in respect of the readers of the target language.The author also holds that the information lost in isomorphic translation can be compensated through other means,hence transferring more possible information embedded in the source language.
isomorphism;functional equivalence;domestication;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H315.9
A
1009-105X(2010)04-0135-05
2010-09-20
2010-11-10
2009年度中国矿业大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OW091204)
朱哲(1972-),男,硕士,中国矿业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
刘优(1983-),女,中国矿业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研究生;
郭华(1987-),女,中国矿业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研究生。
——以指数、对数函数同构问题为例
——积累AABB式拟声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