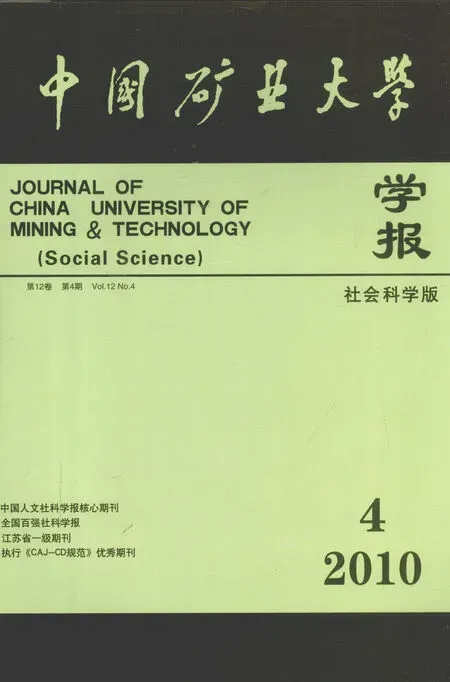论马克思政治哲学视野下的自然权利问题
马俊峰
(西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甘肃兰州 730070)
论马克思政治哲学视野下的自然权利问题
马俊峰
(西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甘肃兰州 730070)
古典政治哲学试图从政治与哲学的关系来阐释城邦政治哲学的诸问题。自霍布斯以降,权利成为现代政治哲学研究的核心议题,针对权利合法性和正当性的追问,自然法成为现代政治哲学关注的焦点。面对现代性危机,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自然法和自然权利在政治哲学中起到的作用。然而,如果我们从马克思政治哲学视角反思现代性危机之时,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的自然权利产生于人的物质生产,人类正是通过物质生产活动创造一个又一个辉煌的历史篇章。
政治哲学;自然法;自然权利
20世纪70年代,随着罗尔斯《正义论》的发表,标志着政治哲学在西方的复兴,而社会契约论、自然法等观念也逐渐从人们遗忘的角落走出,进入政治哲学的话语中心。哲学家、学者、专家再次把他们的目光投向政治哲学,期待着政治哲学将西方引出现代性危机。然而,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惊呼,现代政治哲学不仅不会拯救西方,反而加速了现代性危机,导致了西方文明的衰弱。现代政治哲学是现代性事业的产物,它自己本身也遭受到现代性的浸染和毒害,它是一种无力消解现代性的毒素。也就是说,政治哲学已经病入膏肓。就此而言,无论维特根斯坦还是海德格尔,他们都有着同样的感触,即现代性危机其实质就是西方哲学的危机,启蒙理性加速了哲学的终结和死亡,因此,为了拯救西方哲学和西方文明,必须回到古希腊,恢复古典政治哲学,克服现代性危机。然而,这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行的,我们拭目以待。
(一)
现代政治哲学继承了近代政治哲学的衣钵,即自由、正义、权力、权利、平等、民主等范畴,并对近代自由主义传统作一定的修正,恢复论证个人权利和国家关系的理论基础——社会契约论,同样也复兴了自然法在政治哲学和法理学中的重要地位,这便使西方政治哲学呈现出空前盛事。但是危机依然存在,它并没有因为政治哲学的空前繁荣而自然消失。这主要是由西方政治哲学内在的矛盾所决定,西方政治哲学所阐述的自由、正义、权利、平等等理念,从表层上讲,它是自由主义所倡导的价值,宣扬人的基本权利;从深层上讲,是在资本主义的语境下,强调资产阶级的人权,因为这些理念是从属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是建立在资产阶级私有制之上的,它是服从于有产阶级的利益的观念。正如马克思所言:“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想、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为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1]72。因此,当统治阶级把这种观念永恒化,用来禁锢和控制人们思想的时候,它也就演变成为一种虚假的意识形态。
近代政治哲学从自然法中演绎出人的自然权利,并确认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属于人的基本权利,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可见,自然法在近代政治哲学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首先,依据自然法确定人的生命权,每个人都享有生命权,这是任何人无法剥夺的,否则,就是蔑视人权,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摩西十戒就有一条:不许杀人。它以上帝的命令告诉人类,禁止人类互相残杀,以便保持人类的繁衍。虽然它是神法的内容,但当人的理性参与了永恒法,就构成自然法。从这个意义上讲,“不许杀人”也是自然法所欲求的。其次,自由是人类珍贵的价值,它不是由外在物赋予人类的,而是人类本性使然。从自然法角度讲,在古希腊,遵循自然就是正确的、好的,人们服从善的原则,就是自由。在古希腊宇宙论、目的论语境中,城邦正义表现在城邦使人们求善,人人成为好公民,而那种有德性生活在城邦的公民自然而然是自由的。近代以来,霍布斯、洛克等人相继从自然法出发,推论出人的基本权利,但霍布斯依据物体运动本性,提出自由就是没有障碍的状况,进一步讲自由就是干涉的阙如,这就构成了自由主义的消极自由观。霍布斯从人的恐惧和暴死的本能出发,考察人为了抵制和防御暴死和恐惧,人们试图通过寻找超越个人力量的力量,以求保护自己的安全。基于这样的认识,人们认为必须交出自己的权利,订立契约。这样,以社会契约的形式就组成利维坦,而利维坦是能够很好地保障人们权利的实现;同样,它会使人们可以自由的生活。但是,由于霍布斯、洛克等人对人性和人本身的认识较为抽象,致使他们的学说存在许多致命的缺陷,使得构建的学说在解决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时,存在着很多不能自圆其说之处,受到功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激烈批判。再次,财产是人能够独立和自由的前提,一旦人拥有财产,人才能有自由和安全的可能性,如果财产被剥夺,人就随之丧失安全、自由、尊严。而财产依据自然法确立,实体法仅仅使用国家权力给予人所拥有的权利以保护。自然法使得“强制统治弱者”成为合理的和合法的,实体法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事实,这就表现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1]98因此,自然法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学领域和政治学领域,为资产阶级利益的实现和权力顺利运作提供了很好的辩护。而从自然法演绎出的自由、正义、平等等观念更是掩饰了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丑恶面目。
我们看到,问题的实质在于近代政治哲学依据自然法演绎人的自然权利,这一思路本身是成问题的,为什么呢?我们知道,自然法在古希腊指永恒价值,从安提戈涅遵循自然法而舍弃实体法,掩埋哥哥的事件本身显示了自然法高于实体法,原因在于实体法不具有永恒价值,只是显示了统治者的利益和偏好而已,是一种特殊的价值,这也体现了绝对价值与相对价值的冲突。自然法具有很强的道德功能,它规定了人的道德义务。在中世纪,神法扮演着绝对价值的角色,但对于人而言,它是无法被人理解的。所以,阿奎那毅然决然地把自然法引入神学,为人理性行动提供原则,并进一步将神学理性化。近代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资产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打出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其实质是在自然法的语境中来谈这些观念,自然法成为构建他们政治哲学和法理学的依据。他们力图借助自然法将自己的权利永恒化,这一点被马克思识破,马克思通过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进一步指出,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自然法基础上的经济学,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企图通过他们的政治经济学掩盖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手稿》通过对劳动异化的剖析,进而展开对自然法的批判,他认为资产阶级自然法对人性和人本身的理解是成问题的。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对人是什么的问题作了实质性的诠释和说明。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进一步批判了代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观念,如正义、平等、自由、权利等观念。另一方面,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的正义、平等、自由、权利的真正内涵,也为无产阶级解放指明了方向,并为人的解放勾勒出美好的蓝图。马克思通过对政治经济学和法的关系的深入研究指出,法是特定社会历史的产物。为此,马克思把市民法的产生追溯到生产领域,考察生产关系的主体是在自愿生产的历史中建立起来,资本家依据对生产资料的拥有成为劳动产品占有者的主体,工人依据自己的劳动力成为产品生产者的主体。这样,在主体之间建立起一种法权关系,并明确了主体之间的责、权、利关系,从而揭示了一定的法的形式根源于经济关系,即经济基础决定了建立在上层建筑之上的意识形态,法的形式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因此,“如果资产阶级从政治上即利用国家权力来‘维持财产关系的不公’,它是不能成功的。‘财产关系的不公’是以现代分工、租代交换形式、竞争和积累等等为前提,决不是来自资产阶级的阶级政治统治,相反,资产阶级的阶级政治统治倒是来自这些被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宣称为必然规律和永恒规律的现代生产关系。”[2]
马克思通过对构成法权关系的资产阶级经济关系的研究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反映了一种不平等的、剥削的经济关系,因为“资本主义的财产权利在生产过程中变成了它的对立面。它变成了不交换就可以占有另一个人劳动产品的权利。”[3]这样,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就充分体现了资产阶级政治统治利益,资产阶级通过国家权力维护财产关系,以便努力保护他们的利益不受损害。恩格斯在给施密特的信中写道:“在现代国家中,法不仅必须适应于总的经济状况,不仅必须是它的表现,而且还必须是不因内在矛盾而自己推翻自己的内部和谐一致的表现。而为了达到这一点,经济关系的忠实反应便日益受到破坏。法典愈是很少把一个阶级的统治鲜明地、不加缓和地、不加歪曲地表达出来,这种现象就愈是常见:这或许已经违反了‘法观念’。”恩格斯继续说:“经济关系反映为法原则,也同样必然使这种关系倒置过来。这种反映的发生过程,是活动者所意识不到的;法学家以为他是凭着先验的原理来活动,然而这只不过是经济的反映而已。”[4]其实,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法律常常穿上了政治权力、进步、社会利益等意识形态的外衣,掩盖了资产阶级统治的现实,而资产阶级所宣扬的自由、平等其实就是劳动力买卖的自由和商品交换的平等,并集中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的利益。正如马克思针对古典自然法学派的自由、平等的权利理念批判之中指出的,“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他们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5]
从上所述我们看到,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出发,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分析人的自然权利,指出它是一定社会历史产物,是指一个社会特定人群的基本权利,这种权利是通过统治者的权力来加以保护和实现的。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点,那么生活在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就会持有一种宿命论的观点,认为资产阶级是天经地义的统治者,而无产阶级天生就是被统治者,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就像一位哲学家所说的,老鼠生来是为猫吃的,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用来欺骗无产阶级的惯用伎俩。从历史上看,资产阶级在封建社会后期,也没有获得其存在的合法权,恰恰是在其与农民阶级联合,向封建贵族斗争中取得了合法权。当资产阶级取得合法权之后,开始将资产阶级的权利永恒化,通过意识形态的宣传和控制,巩固了资产阶级政权,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无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们不是先天的被统治者,而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可以说,一切现实的和合理的,一旦丧失了它存在的条件,它也就丧失了存在的合理性,必将被另一种更合理的东西所取代。随着社会的发展,资产阶级的反动性以及自身的经济基础决定着它必然走向历史的对立面,终将被与历史发展一致的阶级——无产阶级所埋葬。而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个人》也仅仅是资产阶级最后的盛宴,没有什么东西在历史长河中是永恒的,资本主义的胜利只是暂时的。所以,全世界无产阶级是人类的希望,只要他们联合起来,就能争取人类的解放。
(二)
自然法是政治哲学和法理学的核心内容,它与终极目的、意义和价值、德性和义务之义是相联系的[6]23。古典政治哲学的正义范畴正是依据自然法获得了合理的诠释,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依据人的自然本性,将人分为金、银、铜、铁四种,认为只要每个人能够各司其职,各尽其能,那么城邦秩序就稳定;只要每个人不僭越自己职能,追求美德,城邦便成为正义城邦。如果我们考证古希腊人对自然的观念,我们就会发现,在古希腊,自然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它预设了道德判断,因而它意味着正确、好的、正当的,是永恒的,是不能够改变的,是绝对的。只要人遵循自然,就能够过上美好的生活。这就是说自然代表着一种绝对价值,表现了一种美好的理想状态。然而这仅仅是一种应然的状态,是无法在现实中实现的,这很大程度上与古希腊追求至善相关,为什么呢?因为古希腊人是在宇宙论、目的论框架下认识事物和看待城邦的,他们这种认识方式决定着他们的观念是一种艺术创造和想象。如马克思说言,高效率的“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7]实际上我们会看到,柏拉图的《理想国》就是想象的艺术作品,在想象中不乏表现出古希腊人对理性审慎使用,一边敬畏城邦神,一边又用理性的眼光审视着城邦的政治事务,自然法与实体法同时控制着人的行为。
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的理性取代了想象,不再是像古希腊人用想象征服自然力,而是用人的理性征服自然,自然在理性面前不再像在想象面前是整体的,而是支离破碎的。当人能够与自然抗争,能够支配世界时,个体(人)不再需要其他人的帮助就能获得他所需要的或欲求的,这样,就会出现个体(人)与个体(人)为各自能够占有某一物,或者因分配不公而产生冲突,就像霍布斯描述的自然状态,人与人的关系就像狼与狼的关系,一切人对一切人关系就是战争关系。由于人的本能驱使,对暴死的畏惧,就订立契约,结束战争状态。他们建立起的利维坦,它有足够的强大力量,可以保护国家公民的基本权利的实现。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在社会契约论框架内诠释了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的关系,阐述了他们的政治哲学思想和法理学观点。当然,他们扭转了政治哲学发展的方向。正如《政治哲学史》所写:“马基雅维里的新政治哲学的目的在于通过排除人类的自然的终极目来确保实现公正秩序。同样,培根和笛卡尔的新自然科学的目的在于用简单明了的方法确保实现智慧,而不靠宇宙的自然可理解性。同样,霍布斯试图以科学知识和大众的启蒙为基础来确保实现公正秩序,他的新形式的自然法是根据对横死的恐惧这种最强烈的感情,根据人类开端,而不是像以前的观点那样根据理性和人类的终点(目的)推论出来的,结果霍布斯强调追求权力——这甚至排斥了马基雅维里所赏识的追求荣誉的崇高——从而导致的视野的进一步缩小。在施特劳斯看来,洛克使这一重点的转变——从义务论与人的目的转向权利和作为主体的人——甚至走得更远,因为他主张以解放生产的欲望作为根治自然的吝啬的方法。卢梭,尽管或勿宁因为他的努力重返自然和恢复美德尊严,又进一步提出总意志以作为正义的保证,从而使对自然法的诉求变得完全多余。”[8]其实,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布诺赫看来,自然法表达了一部不间断的思想史,也即一部维护人的自由尊严的斗争史,通过建立权利、制度和法律关系来防止人们堕落、声名狼藉以及遭受羞辱。马克思指出哲学的任务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这也是自然法和自然权利没有现实的潜能。布诺赫说“虽然突飞猛进地发展了,但还不是人类社会可以决定自然。”
但是无论怎样,我们看到近代西方政治哲学正是沿着“马基雅维里的时刻”前进,道德和政治迅速分离,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国家和社会也随之分离,权力论取代了至善论,道德作为政治的基础变得不可能,道德律或自然法是派生于自然权利,它不是道德事实的义务,而是一种道德事实的权利。因而,自然权利在近代政治哲学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
(三)
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在古典学说意义上被看作是“自然正确”、“自然正当”,或更准确些译为“古典的自然正义说”。而从现代学说意义上指西方17世纪以来兴起的所谓“自然权利”或“天赋权利”说[9]10-11。我们这里所提到的自然权利即人的权利,是在现代学说意义上讲的。一般来说,自然权利指人的生命权、人身安全权、自由权、财产权、反抗压迫的权利,它们构成了人最低限度的权利。作为一个正常的人,或者政治组织、集团、甚至国家都不会蔑视这些关于人的基本权利。正是基于人们共同对人的最低限度权利的这种认识,在1948年,联合国大会就通过《世界人权宣言》,该《宣言》承认人人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禁止奴役,任意逮捕、拘禁或放逐,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人人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等基本人权。
从本体论(Ontology)上讲,自然权利意味着人的自然本性,人之为人所存在的本质属性,这种对人的自然权利的本体的思考,使得古希腊人从“自然正当”或“自然正义”角度来理解人的自然权利。他们预设了人的完善性,人通过城邦的道德教化,追求美德,遵从自然正义,人就能够达到善,城邦就可变成正义城邦。人们对道德义务的履行,就是对自然权利的分享。近代笛卡尔以来,不再以外在客观德性为尺度,以自然本身诠释自然正义,而是从我如何从我的意识中获得关于外部世界的认识,即我究竟如何认识事物?这样,人自身成为自然法、自然权利和政治哲学关注的中心,“权利优先正义”取代了“正义优先权利”,即古典的自然法所论证的自然正义转化为现代学说意义的自然权利,权利成为近代政治哲学核心话题。
从认识论(Epistemology)上看,古希腊人并没有把自己从自然中区分出来,他们与自然和谐相处,正如斯多噶学派所言,按照自然生活,就是按照理性生活,对自然的沉思,也就是对人自身本性的认识。因而“自然正义”构成他们理解自然权利的根据,也成为他们履行道德义务的准则。笛卡尔使哲学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关注意识和方法,而不再关注外在客观存在。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命题,这使“理性不仅是正确的法的认识工具,也是其源泉。理性,人的理性!赋予人以自然法律,不再在所谓逻各斯,自在存在的概念,永恒法、没有经院哲学中所谓预设的真理,人完全受自身认识能力的引导。不再是权威和传统决定什么当是‘正确的法’,相反,仅应涉及什么在理性上是理智的,‘合乎理性的’。法哲学挣脱了神学,自然法世俗化了。”[10]既然人是世俗化的实在,依据逻辑就可以推论出关于人的自然权利和义务了。这样,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或原子式的实体,就走进了近代政治哲学的视野,当自由主义主张的个人权利获得自然法的认可,并通过实体法给予有效地确定和保护时,自然法与实体法的内在张力随之消失,自然法的超验性正义也随之荡然无存,而制定法则拥有独断的权威,从而容易产生极权和专制。
从价值论上看,古希腊人是在宇宙论、目的论视野下来理解自然的,认为万事万物都是有生命的,它们是有一定目的、目标或终极。按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每个自然同时是自身的目的”,而阿奎那则认为“自然的发展有其终极目的”。这意味着终极是存在的一种状态,其性情和效力在于达到完美之境。因此,古希腊的宇宙论、目的论是“德性论和价值论发达伦理学之基础,合乎自然的权利有益于个体生命臻于完善,并推动着生命朝终极目标奔腾不息,……因此,自然权利超越了现实,是一种‘理想之境’。”[6]28-29近代哲学家把自然看作是征服的对象,它不再认定自然本身就是价值,这使自然正义的价值功能丧失。随之本体论转向认识论,认识论成为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认识论使得人的理性成为价值判断的尺度和准则。理性的自信使得人们完全相信,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理性制定法律,并遵从自己制定的法律,这样,自然法就变得多余。认识论使人关注人自身,关心人的权利,于是,就产生“自然法”转为“自然权利”,而“自然权利”转变为“人的权利”,权利优先善就否定真正的善,即否认“自然正义”或“自然正确”,由此使西方走向虚无主义。就此而言,我们从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看到,自由主义仅仅主张人的天赋权利,认为每一个人有权利追求他自己理解的幸福。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所有的善都是一样的,不存在谁比谁高,这就消解了“诸神之争”,“自由主义宣称其目的是一视同仁地尊重所有宗教、所有种族、所有性别、所有历史文化传统,但其结果实际则是使得所有宗教、种族、性别、历史文化传统都失去了意义,都不重要了,都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因为都只有私人领域的意义,并不具有公共意义。这在施特劳斯看来,当然正是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9]51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如果我们从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方面要重新审视自然权利即人的权利,思考如何使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人的普遍价值和特殊价值、理性和感性、规范和事实、理想和现实有机统一起来,那么,我们就要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切入,重新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承继资产阶级优秀文化和政治文明的基础上,进一步诠释关于无产阶级的人权观念,阐发无产阶级的正义观、自由观和平等观。正如怕舒卡尼斯所言:“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角度批评资本主义法理学必须接受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批判,如马克思给我们做出的示范那样。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这一批评必须首先闯入一片空白的领域,不仅要抛弃资产阶级法学家以他们那一阶级和时代的需求为出发点而苦心经营的抽象和理论,还要通过分析这些抽象的概念,展现他们的真实内涵和法律形式的历史局限性。”[11]为此,我们必须从以下方面展开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
其一,我们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考察自然权利和自然法,揭示自然法是一定社会历史的产物,是对事物和人事的普遍客观性的反映,没有什么超越于客观事物之外永恒的东西。自然权利或天赋权利也是指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之中人的权利,权利不是先天的或天然的,由于社会文化传统不同,人们在社会中拥有不同的权利,这由习俗、文化、教育程度、财产状况、种族、性别等造成。不同的社会,人们的阶级差别不同,其权利的享有不同。尽管有最基本的人的权利,或者说最低限度的人权,但这都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背景下被认定的,没有什么超社会的人权。
其二,从实践的角度重新审视自然权利和自然法。近代以来的纠缠于唯理论和经验论,唯理论开启了先验的权利论,这对法国大革命产生了强大影响,引起了很大的社会震荡,产生了法国的《人权宣言》。它宣称人权是自然的、天赋的、人人平等具有的、不可剥夺的。经验论开启了经验的权利论,它对美国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产生了美国的《独立宣言》。它宣称,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被造物主赋予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我们看到,这些法的观念、权利的观念都是一种意识形态,如马克思所言:“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12]。资产阶级对法和权利的认识源于他们在社会运动中对自身阶级利益的认识,资产阶级试图通过宪法予以确认他们的人权,通过实体法予以落实和贯彻,充分实现自己的利益,从而保障自己的权利。对于工人阶级而言,工人阶级是无法真正享有宪法所规定的人权,因为工人阶级是处于被统治的地位。所以资产阶级宪法所规定的人权仅仅是资产阶级的人权。
其三,从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的解放视角出发,审视关于资产阶级所谓的自然权利和自然法确立的人的价值,重新反思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法哲学和政治哲学关于人的自然权利的抽象性。我们看到,一方面自然权利抽象性表现为把资产阶级的特权普遍化、永恒化,从而模糊了享有基本权利的主体身份。在法权关系之中主体拥有财产权的不同,在实际享有被赋予的基本权利时,形式权利和实质权利产生张力,使得不同主体享有不同程度的权利,如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和资本家都具有法权所规定享有的权利,但是由于他们各自所拥有的财产、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不同就不能享有宪法赋予的人的权利。另一方面,自然权利的抽象性体现了资产阶级的阶级观念和经济利益。这就是说,我们仅仅强调人身权利和政治权利,更重要的是要确立能够充分享有这些权利的经济权利,否则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始终是不平等的。如恩格斯所言的“平等应当不仅是表面的,不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尤其是从法国资产阶级自大革命开始把公民的平等提到首位以来,法国无产阶级就针锋相对地提出社会的、经济的平等的要求,这种平等成了法国无产阶级的特有的战斗口号。”[13]这就意味着无产阶级只有通过社会革命,创新制度,在人的经济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之后,相应地,人的政治权利和其他权利也就能够得到充分实现。这时,人不仅能获得彻底解放,而且能够获得全面和自由的发展。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331.
[3] 古尔德.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28.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488.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99.
[6] 科塔斯克·杜兹纳.人权的终结[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2.
[8] 列奥·施特劳斯,克罗波西.政治哲学史[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1084.
[9] 甘阳.《列奥·施特劳斯政治哲学选刊》导言[M]//斯特劳斯.自然权利和历史.北京:三联书店,2003.
[10] 考夫曼,哈斯默尔.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79.
[11] 帕舒卡尼斯.法的一般理论和马克思主义[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18.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12.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48.
Natural Rights from Perspective of Marxist Political Philosophy
MA Jun-feng
(School of Politics and Law of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Lanzhou 730070,China)
Classical political philosophy tries to explain the city’s various problems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fro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s and philosophy.Since Hobbes,right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modern political philosophy study.In order to answer the question about the legality and justification of right,the natural law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modern political philosophy.In face of the modern crisis,people started to re-examine the natural law and natural rights to play the role in political philosophy.However,if we reflect on modern crisis from Marxist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philosophy,historical materialism tells us that the natural rights of people come from the material production through which man creates glorious exploits in history one after another.
political philosophy;natural law;natural rights
D091.4;A164;D0a
:A
:1009-105X(2010)04-0001-06
2010-08-31
2010年度甘肃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西北师范大学“知识与科技创新工程项目”(NWNU-KJCXGC-SK0303-13)
马俊峰(1969-)男,哲学博士,西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