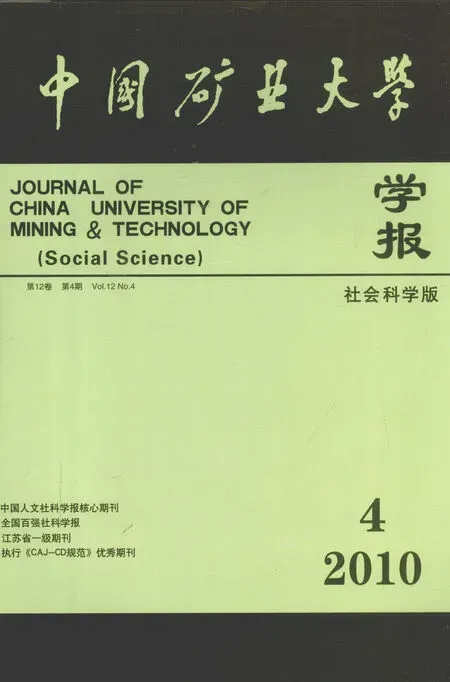宪法爱国主义——公民凝聚力和政治忠诚的再塑
许 洁
(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江苏南京 210094)
宪法爱国主义
——公民凝聚力和政治忠诚的再塑
许 洁
(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江苏南京 210094)
当下中国的国家认同和爱国主义主要是建立在民族主义之上,但随着多元文化主义的挑战,尤其是边疆的分离活动动摇了传统爱国主义理论的根基。因此,狭隘的民族主义不足以实现公民对国家的普遍认同,进而无法有效维护国家的统一。在这个意义上,重塑爱国主义价值观就成为我国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哈贝马斯的宪法爱国主义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再塑公民政治忠诚的新视角。即:将公民对于一国宪法的认同作为国家认同的主要价值来源和支点,进而以此为基础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国家认同;民族主义;宪法爱国主义;政治忠诚
一、问题的提出
爱国也许是一个需要永恒探讨的话题,就整个中国近代史而言,从清末的变法维新到孙中山的民国建制,再到共和国的诞生,爱国主义是压倒一切的主题,人们以各种可能的方式践行着自己的爱国情怀,这种表现为国家主义的爱国情怀,其正当性似乎是无需论证的。但今天这种爱国主义开始受到民族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的挑战,爱国主义要继续维护其正当性,就必须能够回应民族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的挑战。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再需要爱国主义,恰恰相反,在失去了传统的束缚后,当下的中国更迫切地需要一种爱国主义,使它成为社会团结和社会动员最为可靠的力量。只是需要探讨,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爱国主义?换言之,在当代社会,公民对于国家的认同到底应当建立于何种基础之上?
传统的政治理论始终在追求“政治单元和民族单元的合一”[1]1。遗憾的是,现今世界以“纯洁”民族建构的国家廖廖无几,绝大多数国家仍旧是以族群为基础建构的,因此所谓的“政治单元与民族单元的合一”便具有了另外一层涵义,即以“政治单元”重塑“民族单元”,在多元文化与族群之上建构统一的政治民族,于是,国家的模式也便有了另外一种表达方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因而便有了中华民族,美利坚民族,德意志民族的称谓。所以当费孝通先生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来表述中华民族时,他所诉诸的国家认同基础既不是血统和语言,也不是文化和历史,而是意识。而当下的中国可以说是继承和延续了这种复杂的多元格局。但问题是,中华民族这个概念从清末提到现在,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中国认同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边疆分离活动表明经由中华民族体认的国家认同正在遭遇的尴尬。在多元文化与族群普遍存在的基础上,究竟如何藉由新的认同,型塑新的国家?客观地讲,任何单一的思考都无法应对这个复杂的问题,但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的宪法爱国主义理论或许是较好的选择。
二、哈贝马斯的宪法爱国主义理论
宪法爱国主义理论源于战后德国,是作为传统民族主义的替代物和对立面提出的。提起宪法爱国主义,人们自然会想起尤尔根·哈贝马斯。实际上这一理论的首创者是雅斯贝尔斯的学生——德国政治思想家斯登贝格(Dolf Sternberger)。早在1959年,斯登贝格就开始思考“宪法国家的爱国主义情感”,并将其称之为“激情的理性”[2],随后,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诞辰30周年之际,斯登贝格发表了《宪法爱国主义》一文,开始明确使用“宪法爱国主义”这一概念。在斯登贝格看来,国家不再只被理解为族群共同体或文化共同体,而是法律共同体。这样,对国家的认同就从民族主义中拯救出来,用宪法爱国主义来防范民族主义可能导致的道德危险,因而被米勒称之为“保护性宪法爱国主义”[3]24。
哈贝马斯借鉴了斯登贝格的宪法爱国主义,并且肯认了这种基于“基本法的政治秩序和原则”的政治认同,但他同时认为,斯登贝格的宪法爱国主义本质上仍旧是民族认同,而他希望公民藉由批判性的反思而发展出“后民族认同”——一种超越传统民族认同的多元族群状态,聚焦于更具普世主义的“权利和民主程序”,而非特定的历史和社群。在哈贝马斯看来,传统的民族认同中存在着一个紧张关系,即“民主和立宪国家的普遍主义的价值指向和一个民族据以将自身与外在于它的其它民族区分开来的特殊性之间的紧张”[4]。为了弥合、消解这种紧张就需要寻找一种更高层次的政治认同。而“宪法代表一种形式的共识。公民们在处理集体生活时需要有这样的原则,这些原则因为符合了所有人的利益,因而可以得到所有人的理性赞同。这样一种社群关系是建立在相互承认基础上的,每个人都可以期待别人待他如自由和平等之人。”[5]这样,宪法就具有了凝结不同政治文化的基点和质素。哈贝马斯认为,民族和传统文化所形成的共同体是“前政治性的共同体”,它的成员身份不是公民,而是民族或文化群体成员。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共同体与民族或者传统文化共同体不同,它的维持框架不是自然的血缘或文化亲情,而是刻意构建,因此也是“非自然”的社会公约。这个社会公约就是宪法。社会成员由宪法获得政治共同体成员的公民身份,承担起公民身份也就意味着把与此不同类的民族或文化身份搁置起来。社会成员对国家的忠诚和热爱应当是一种政治性的归属感,是他在以宪法为象征的政治共同体内的成员身份的表现,这就是哈贝马斯的“宪法爱国主义”。一方面,公民应透过政治整合建立对共同政治文化的忠诚,而将前述宪政合理性深植到个人信念以及行为之中;另一方面,也可以在此共同基础上意识到并尊重多元文化社会中不同的文化社群。确实,对于哈贝马斯来说,宪法爱国主义具有超越性的一面,但他并非要建立世界政府和大同世界,而是试图在多元文化与族群之上建构一种基于宪法所包含的抽象性的程序与原则的“理性的集体认同”。但这种认同也不是凭空产生的,而且它必然存在于具有特殊文化认同的个体意识和行为中,因此哈贝马斯说:“对于这些同样蕴含在其它共和宪法中的宪法原则,如人权和人民主权,每一种民族文化将依据自己的民族历史发展出不同的阐释。建立在这些阐释之上的宪法爱国主义可以取代原来民族主义占据的位置”[4]138换言之,不同的族群文化在对宪法原则的阐释中形成了“重叠共识”,用米勒的话讲是“为自由且平等的公民在共享的社会空间寻找共同生活的公平条件”[3]52。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哈贝马斯“宪法爱国主义”的对象并非是单纯抽象的宪法观念,而是为了避免在一个共同体内,主流文化对亚文化的侵蚀,从而使得共享的政治文化与他们的前政治认同分离。因此,宪法爱国主义不能建立在任何族群文化之上,但需要建立在多元族群文化所共同构成的民族文化之上。套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讲就是“多元共体”。因此,在宪法爱国主义中,族群文化权利不但没有被压制,反而得到了提升。“公民必须能够在社会保障形式和不同文化生活形式的相互承认中感受到他们权利的公平的价值。”而对抽象的程序和原则的认同,恰恰是为族群文化权利的实现提供了制度性的保障。现在,我们就不难理解,哈贝马斯为什么总是不厌其烦地强调多元共识了。或许我们还可以这样解读:宪法就是公民在公共领域经过商谈理论达成话语共识而形成的基本要素。因此,宪法爱国主义是凝结公民政治忠诚的最佳方式。它为自由民主的立宪政体提供了一种感情支撑,没有了这种情感的支撑,所谓的立宪政体也就成为了镜中月,水中花。因此,米勒说“宪法爱国主义概念化了公民为维持一种特殊形式的政治规则而需要的信念和态度”[3]51。
其实,从斯登贝格的宪法爱国主义到哈贝马斯的宪法爱国主义直至晚近的米勒,其核心的问题都是如何超越民族主义的国家认同,寻找新的集体认同形式,只不过斯登贝格诉诸于传统的共和爱国主义,而哈贝马斯旨在建构一种后民族的“理性的集体认同”。而米勒试图建构一种超越德国语境的一般性的宪法爱国主义,但实质上仍未超出哈贝马斯的论述。阅毕掩卷,一个问题却不停地在拷问我们,即:这种以宪法爱国主义取代传统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真的是历史的趋势,时代的必然吗?或者如孙中山所言“世界大潮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那么,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之间的张力是如何被消解呢?换言之,宪法爱国主义是如何可能的呢?
三、从民族爱国主义到宪法爱国主义的转向
1.从民族主义到爱国主义的困顿
当今世界,民族国家是构成世界体系的基本模式,由此决定了民族主义是任何人无法逃避的政治情感。那么,究竟什么是民族主义?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或许如同奥斯丁对时间的追问一样:“时间是什么?如果无人问我则我知道,如果我欲对发问者说明则我不知道”。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感觉。的确,到目前为止,关于民族主义没有一个定义能为人们普遍接受,也没有一种解释能够全面且准确地把握民族主义的所有特征和内容。这不仅是因为民族主义本身表现形式的斑驳复杂,更重要的是它并非是依赖于一套理论说辞才成立的。它已然深入到现代人的骨髓和血液之中。诚如厄内斯特·盖尔纳所说,“身属一个民族,不是人性固有的特点,不过现在似乎已经显然成为人性固有的特点了。”[1]8反之,如果一个人没有民族,就会像失去影子的夏米索没有了根基,没有了归属感。人们惯常所感知和理解的民族仅仅是“一些血缘共同体,它从地域上通过栖居和相邻而居而整合,在文化上通过语言、习俗传统的共同性而整合,但没有在政治上通过一种国家形式而整合。”[5]657这便为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分裂埋下了伏笔。诚然,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似乎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前者显示的是对祖国的热爱,后者却意味着对民族的忠诚。但当国家以民族建构的形式出现时,二者便具有了合流的趋势。对民族的忠诚自然就转化为对民族国家的热爱。而民族国家的出现恰恰是催生民族主义的土壤。追根溯源,近代意义上民族国家的产生,自《威斯特法尼亚条约》起其端绪,历经近世三次资产阶级革命,尤其是法国大革命和美国大革命,开启了民族国家这一政权组织形式并最终成为今天世界格局的基本叙事方式。哈贝马斯就曾说,“近代民族国家的成就在于,它同时解决了这样两个问题:即在一个新的合法化形态的基础上,提供了一种更加抽象的新的社会一体化形式。”[4]131也就是说,现代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已从路易十四的“朕即国家”过渡为公民对国家的认同,进而由这种认同产生对国家的忠诚与热爱。哈贝马斯还认为:“这种民族意识转变最初发生在城市里,主要是受过教育的市民阶层,然后才在大众中得到呼应,……民众的民族意识逐渐加强,凝聚成为民族历史上广泛传播的‘想象共同体’(安德森)。而这种‘想象共同体’成为新民族集体认同的核心。”[4]130“在民族意识的大熔炉中,个体出身的天赋特性被转化为一个有意构造之传统的诸多后果。天赋的民族性让位于一种人造的民族主义,一件精心打造的成品。”[5]658在掀起社会思潮涌动上民族主义确实拥有巨大的能量,因为它能给人以最大的政治想象空间。“一个政治力量是成功还是失败,就要看他对民族情绪的利用到家不到家,如果能够得到民族主义的支持,这种政治力量就会成功,反之,就会失败”[6]。诚如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Hobsbawm)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不对这个词有所了解的话,那么简直无法理解人类近两个世纪的历史。
正是由于民族主义巨大的政治鼓动性和情感号召力,民族主义才成为了一把名副其实的双刃剑。当它表现为“进攻性民族主义的时候,在狂热地捍卫自身文化的同时对其它文化及其承担者轻则拒斥、压制、重则必欲毁而后快”[7]。于是便有了希特勒试图通过种族灭绝来实现本民族的扩张,此时的爱国主义早已演变成流氓者的庇护所;当它表现为文化自决的民族主义时,在一个多民族国家,特别是当非主体民族感觉到自己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或者没有得到应得的利益和地位时,狭隘的民族主义必然蜕化为肢解民族国家的利器和杀手锏,前苏联的轰然解体,车臣的骚乱,便是最好的注脚。历史既已一路走来,留待我们后人的便是现实。殷鉴尚存,不得不令我们警醒。正如哈贝马斯所言,这种基于前政治的“出身共同体”而聚合在一起的民族,由于缺乏政治整合,因此没有能形成良好的政治文化,实际上是不足以维系一个国家的统一和团结的。“既然这些因素从一开始就没有能防止国家的分裂,那么它们又为什么一定是国家统一的条件?没有共同政治文化的统一是脆弱的。这样的统一也许有经济或其它理由,但难免因经不起考验而再次分裂。”[4]正是这种民族认同的模糊性,加之国家构成族群的复杂性,其间的冲突必是内在的。
这个最初为国家提供政治合法性的源泉如今成为了难以贯穿的逻辑,由此便抛给我们一个棘手而复杂的问题,如何寻找一种新的理论模式?它不但要解决公民对国家的认同,还要解决公民由国家认同所激发出来的爱国主义情感,从而最终形成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和团结。换言之,在多元主义的自由民主之下还可能存留何种形式的爱国情感?显然,民族主义已无法担此重任了。
2.宪法爱国主义的可能
首先,以普遍的公民身份包容差异的族民身份。哈贝马斯认为,一个人在宪法之下所获得的民主共和国公民身份与他作为民族共同体的一员并不决然对立,因为对于公民来说,最为重要的不是具有相同的民族背景,而是具有民主共和国的公民身份;不是学会在民族文化中生活,而是在政治文化中生活;不是去寻根问祖,而是学会如何批判地查视自己的利益以便进入理性的协商程序[4]137。居于一国的国民首先应当被理解为宪法辖制的公民身份,民族是由公民组成的,而不再仅仅是血缘共同体。这样便成功消解了普遍价值指向和特殊认同之间的矛盾,克服了扭曲民族认同的分离主义和沙文主义。他指出,一旦公民身份的地位在宪法民主政体的法律和政治文化中确立下来,民主政体自身便可以获得公民认同感,从而逐渐摆脱其对这种自相矛盾的民族观念的历史依赖性,形成对民主的宪政原则及其构建的政治共同体的忠诚。这样,处于非主体民族地位的公民便不会再以一个他者的身份出现在共同体中,从而摆脱被边缘化的命运。
其次,以政治文化吸收族群文化。哈贝马斯认为,现代国家依靠对宪法原则的解释形成了共同的政治文化,使它不再植根于一个前政治共同体的自我理解之上。而宪法原则因为符合每个人的平等利益,可以获得所有人的合理同意,因此能够使相互陌生的公民彼此承认为同一政治共同体的成员。“公民们愿意用这样一些原则来指导他们的共同生活。这些原则,因为它们符合每个人的平等利益,可以获得所有人的经过论证的同意。这样的一种联合体是由相互承认的关系所构成的。在这种关系之下,每个人都可以期望被所有人作为自由的和平等的人而受到尊重。每个人无例外地都可以受到三重承认:每个人作为不可替代的个人,作为一个族裔或文化群体的成员、作为公民(即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成员)都应当得到对其完整人格的同等保护和同等尊重。”[5]660所以,民族国家对自身宪法原则的自我理解培植了一种共同的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尽管主流文化会对非主流文化产生排斥,但由于政治文化依靠的是确保所有的公民平等自由权利的宪法原则,根本不必依靠人们在种族、语言和文化上的同质性。宪法爱国主义所力图实现的,就是通过以维护多元为核心的政治文化来统合一国范围内不同族群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使个体能够集体地呈现他们的认同。
以美国为例,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以欧洲白人为主导的移民国家,所有的族群一起构成了美利坚民族,一个以美国宪法为核心的政治法律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内,一方面宪法保护各少数族群的自我文化认同,另一方面通过确立统一的公民身份和共享的政治文化实现对国家的认同。当然不同的族群对这两种认同的内在张力是不同的。但是从马丁路德金的遇害到黑人总统奥巴马的上台,其间蕴含的基本思路——通过强化国家认同来消解族群政治的紧张——告诉我们,宪法爱国主义实现的“可能”。
再者,宪法爱国主义是通向正义理论的桥梁。长久以来,宪法仅仅被认为是一个预先确立的、抽象的原则性社会契约。但在哈贝马斯看来,除了这些功能和定位以外,宪法还应被理解为社会价值秩序的载体,即宪法不但是一个国家统治合法性的来源与基础,而且是国民所遵循的“共同价值”的表达和依据,是其他具体共识和妥协的基础。文化多元主义的事实和确保公民权利的任务决定了民族国家层次上的整合力量只能是法,它既是在文化和种族方面各不相同的亚共同体之间的“公分母”,又是该民族中自由平等意志的体现,哈贝马斯把这个层次上的共同体称作“法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内,不同的伦理生活共同体可以在同一个其核心为普遍主义原则的现代法律制度下和平共处,经公民授权的公共权力犹如被锁在笼中的狮子,不得随意向公民发威。而“以法的形式构成的公民身份所依赖的是以公共福利为取向的公民的不可用法律来强制的动机和意图的和谐背景的呼应”[5]663。这样,宪法爱国主义便实现了理性和美德的统一。应该看到,哈贝马斯的宪法爱国主义背后是隐含着民主商谈和话语共识为其理论架构的,也是实现“共同价值”的中介。经验社会心理学的大量证据表明,对共同任务的参与可以产生一种强烈的凝聚感,即使参与者没有意识到他们有任何先前的文化的、社会的、伦理的共性。相应地,只要公民认为自己在参与一项自我管理的共同实践,这本身就能成为一种互相认同和凝聚力的来源。宪法正是以这种方式成为表达多元社会共识的最重要手段。在其中,公民可以通过参与构建民主的宪法事业而形成一种理性的集体认同,而这一超越族群的相互认可又成为团结一致和感情归属的凝聚点。宪法爱国主义作为政治忠诚的一种表达方式,它本身不是正义理论,但却是实现正义理论的桥梁。
这样,“一种新的独特的爱国主义已经被培养出来,这种爱国主义恰好是建立在宪法自身基础之上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完整的宪政国家之中,并且这甚至就是祖国的表现方式”[2]。
四、中国语境下的宪法爱国主义
当然,作为一种理论,哈贝马斯所持有的宪法爱国主义观并非完美无缺。相反,对宪法爱国主义的质疑、异议甚至诋毁自其诞生起就一直不绝于耳。有人认为,宪法爱国主义太过单薄,“是一种苍白的学院思想,无法取代一种健康的民族意识,是给教授们准备的爱国主义”[4]152;还有人认为,这种基于对制度的忠诚根本不足以自圆其说,而只能是一种“用来遮盖分裂鸿沟的聊以自慰的绣花毯”,是在重建奥斯丁的尘世“天城”;米勒甚至指责说“就连宪法爱国主义到底是什么这一最根本性的问题仍没弄清楚。”[8]无论以哪种形式,这些质疑的实质都在于宪法爱国主义是否能够在原则的普适性及认同和归属的特定性之间取得平衡?这种建基与宪法原则和民主程序之上的政治认同是否足以唤起维持一个民主国家统一和稳定的强烈归属感,真正为多元社会提供一种可行的民族主义替代物?
尽管有众多的质疑,但瑕不掩瑜,宪法爱国主义自有其合理的内核和蓬勃的生机——那就是对民主自由基本人权的普遍尊重。因而现代社会的爱国主义必然是一种宪法爱国主义,它在确保国家统一的同时确保公民与族群的权利得到真正实现。而现代国家的构建必须完成的根本任务,首先在于实现公民在归属感上从对民族忠诚向对国家忠诚的转换。而对于中国这样正在向“现代社会”迈进却仍然没有到达“目的地”的多民族国家而言,所面对的正是如何在多元文化与族群关系上建构统一的中国认同。就当下中国的爱国主义而言,实际上依然是建立在民族主义基础之上。所谓“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但遗憾的是,传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并没能将民族分离主义挡在国门之外,“西藏问题”与“新疆问题”正在显示着民族爱国主义的尴尬。毫无疑问,我们不能再天真地认为主体民族的爱国主义能够得到这个国家所有民族的认同和支持。
宪法爱国主义为我们提供了较好的选择。但是,尽管我们和哈氏的理论有诸多相同的质素,但仍有空间和时间向度的差距。毕竟,哈贝马斯的宪法爱国主义是基于欧洲的情况,基于契约论的国家理论,也就是在一个现代国家高度发达下的理论形态,而我们在谈到族群政治,国家认同的背后隐含的却是如何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一个初级版的宪政国家的问题。这是我们必须直面的第一轮挑战,是无法逾越的。因此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出发。
从历史上看,“中国各族群是多中心起源的,然后慢慢的融汇成现在的中华民族。它不仅是一个历经数千年逐渐形成的自在的民族实体,而且是近百年来抵抗西方列强的过程中逐渐成长起来的自觉的民族实体。”[9]而中华民族的再造实际是将天下观的伦理秩序转型为国家观的法律秩序。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儒家文化在脱离了政治制度的建制化链接后,也失去了凝聚力。“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实难为继。其实,从“华夷之辨”到“夷夏之防”早已暗示了文化本身无法体现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到了近代,由于外敌入侵,各族人民同仇敌忾,在避免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培育了共同的民族意识和情感,构造了具有一体性的中华民族。而到建国初期直至改革开放前,阶级认同超越甚至取代了族群认同,为共和国维持稳定提供了基础。但随着阶级意识的淡化,这个逻辑也被打破了。而我们亦无法通过树立共同的敌人再现民族统合的合法性。
从现实来看,我国的爱国主义宣教缺少必要的道德证成。我们仅仅知道——“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是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是各族人民的精神支柱,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国培养四有新人的基本要求”(新华网,《爱国主义教育》)。但这种大而空的话语符号,其后的所指无法让人们清晰地看到幸福的落脚点,毕竟它不似康德的绝对律令,近宗教化的让我们在某种意义上理解为善而善,为正义而正义的正确性。因为爱国主义本身不具有天然的道德性。否则,希特勒的党徒就有了充足的辩护理由。爱国主义也可以成为“积极地为了微不足道的原因杀人与被杀”(勃兰特·罗素)。因此,便有了不加思考地参加一场国家之间的战争;作为人大代表几十年听党指挥不投反对票的现象出现,这样的爱国不是爱国,而是直接丧失了反思质疑的理性能力。
那么,到底什么才能担当型塑转型期中华民族一体性的基础呢?这个问题不是没有答案,哈贝马斯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真正稳定的国家统一应当体现为公民们因分享共同的政治文化而表现出来的宪法爱国主义。这就是费孝通先生的“高一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10]在当下的体现,这种“多元一体的中华格局”最终应落实为以宪法为核心的法权结构安排。但是对于没有西方法治传统的中国要实现宪法爱国主义并非易事。首先,树立宪法的绝对权威,继而实现意识形态的政治认同到宪法认同的转化。在现代国家,基本人权价值以关怀和尊重每个个体而成为普遍之善的主要体现,将这些基本人权价值予以宪法化。因此,该宪法的基本要素便可以期待所有的公民予以认可,就具有了行动的力量。而国家行为因受到这些基本人权价值的限制,对内不易蜕变为暴政,对外不会重蹈法西斯覆辙。这样一来,国家认同就是一种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认同。它在确保国家统一的同时确保公民与族群的权利得到实现,同时也是共和国稳定和维持的情感基础。其次,培养公民意识,以公民身份包容民族、种族、宗教等身份。这种公民身份不仅仅是对权利的彰显,而且更要强调公民伦理,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需要公民恪尽公民的责任,尊重他人、克制私利、守法、理性等等。尽管教育会表现出强制性,但只要教育的内容和目标与道德相容,那么强制就具有正当性。如果民主制度下的公民资格能够成为实现各民族的理想生活方式的机制,那么,它就可以成为团结一切外来者的一体化力量[4]139。尤其是对于中国目前的社会状况。再者,建构一种公共领域的协商民主,使得公民能够享有充分的政治参与权,尤其是在涉及少数群体的利益上,要提供一个开放的公共领域,通过一定的协商机制,而非诉诸少数服从多数的所谓集中制,从而避免出现“多数人的暴政”。其实,只要不自外于宪政,何妨让各族群文化“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呢!
这就是中国语境下宪法爱国主义的诠释。在这样的国家中,政治正义与个人幸福完全的联系在一起,人们爱国不仅是爱自己的最高利益与幸福,还热爱凝结为正义良知法律和道德的政治共同体。生活其中的人们会因为其爱国情怀的自愿性和理智性而不断的深化,而且是有益于自己国家的所有人的幸福的深化。这自然就成为了李泽厚先生谓之的“社会性公德”,而非“宗教性私德”,从而使它-“爱国”-的合理性勿庸置疑。
结语
当然,宪法爱国主义也非一揽子协议,但概莫若此,重新唤起公民的爱国忠诚,恐怕只能是海客谈瀛,空中楼阁而已。从宪法到宪政,是一个新的长征,其间必会有很多未定之数。但只要个体和群体都认同宪法,愿意在宪政框架内解决问题,统一
多民族国家的持续稳定和谐就会可能。或许当哈贝马斯说“目前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最后一个古老帝国中国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4]126时,权且算是对我们的期许吧!
[1] 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和民族主义[M].韩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2] 斯登贝格.宪法爱国主义[J].陈克勋,赖骏楠,译.清华法治论衡:第十二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2):492.
[3] Jan-wener-muller 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 Princeton [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7.
[4] 尤尔根·哈贝马斯.包容他者[M].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5] 尤尔根·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M].童世骏,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
[6]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激进与保守[M]//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203.
[7] 顾昕.柏林与自由民族主义思想[M]//刘军宁.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北京:三联书店1998:237.
[8] 米勒.宪法爱国主义的一般理论[J].徐霄飞,译.清华法治论衡,2009(12):179.
[9]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1.
[10]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9:13.
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Rebuilding Citizens’Cohesion and Political Loyalty
XU Ji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Nanjing 210094,China)
Contemporary China’s national identity and patriotism is still built on nationalism.But w ith the challenge of multiculturalism,particularly the border separation activities have shaken the foundation of traditional patriotic theo ries.Therefo re,if w e are still limited by bigoted nationalism, neither the citizen’s universal recognition of China can be obtained nor the national unity can be maintained.In this sense,how to reshape the values of patriotism has become a majo r p roblem w e Chinese must face.Habermas’s theory of 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 p 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of remodeling political loyalty of the citizens.We should use the citizens’app roval of the country’s constitution as a main source and fulcrum of the national identity.In thisway the long-term stability of our country can be kep t.
national identity;nationalism;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political loyalty
D647
A
1009-105X(2010)04-0029-06
2010-08-30
许洁(1971-),女,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