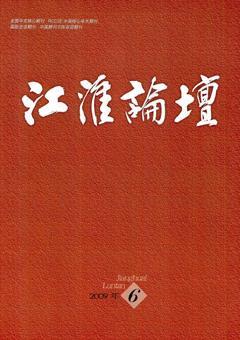论艺术家的自恋之爱
缪丽芳 常 锐
摘要:本文通过对艺术家自恋心理进行分析,尝试探究其爱情的特征及表现形态。艺术家的爱情呈现出一幅“想象的激情”的心理图像,由此揭示出他们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尴尬处境,以及最终以孤独作为他们的归宿的命运。
关键词:自恋; 阈限; 想象的激情; 对象力比多
中图分类号:J03文献标志码:A
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爱情始终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在两性的接触中,在人们相互间的吸引中,蕴含着生命的伟大秘密、创造的秘密。艺术家——这些动人爱情诗篇的谱写者所经历的爱情都有着一种扑朔迷离的色彩。他们中的一些人一方面是理想爱情之高蹈者,另一方面却是始乱终弃的实践者,他们一面幻想着完美绝伦的幸福生活,一面又成为被现实撞碎的生命之舟。一些学者对艺术家们的爱情与婚姻进行了归类整理和透视分析,比如关鸿的《诱惑与冲突》,但是他唯美而诗化的语言和理想主义的情怀似乎还未能道出事实的真相,这些现象的背后似乎还隐藏着更深层的心理动因。艺术家的爱情表现出怎样的特征?这种模式形成的根因何在?女性在艺术家的爱情生活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地位?艺术家的理想爱情在现实中存在开花结果的可能性吗?这种爱情的最终归宿在哪里等诸多问题,尚可做进一步的探讨。
一、 自 恋
要破解艺术家的爱情密码,我们先来探究一下人类心灵深处的一个奥秘:自恋。
自恋(narcissism)一词来自于一个美丽的希腊神话中那喀索斯(Narcissus)的动人故事。美少年那喀索斯对美丽的回声女神爱可(Echo)的美貌都无动于衷,俯身掬一捧清水来喝时看到自己水中的倒影,立刻爱上了它。他一年到头守在潭边,凝视水影,日渐憔悴,最后落水而亡。在他倒地的地方开出一朵迷人的水仙花,人们称它为“那喀索斯”[1]63。
正式提上日程的心理学研究,首先是霭理士·纳克的《性心理学》。霭理士首先提出“自动恋”( auto-eroticism)这个词,指的是儿童独处的时候所自然涌现的性活动,一切不由旁人刺激而引发的性情绪的现象都可以叫做“自动恋”。“影恋”或“那喀索斯现象”是自动恋的一种,也是最极端与发展得最精到的一种。[2]1241914年弗洛伊德首次在《论自恋》一文中从病理学方面系统论述了自恋的问题。他认为,自恋是力比多对自我的投注。他将自恋分为原始自恋(primarynarcissism)和继发自恋(secondary narcissism)。原始自恋,即把力比多投向自我及养育自己的女人,这被假定为每个人都有的正常的自恋。由于妄自尊大和转移对外部世界的兴趣,当力比多投向客体贯注遭遇挫折而折回自身的时候所产生的自恋,被称为“继发过程”(secondary process),这是病理性的自恋。[3]弗洛伊德将力比多分为“自我力比多”、“对象力比多”,对象力比多即力比多向对象的投注,这两种力比多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荣格在《心理类型学》中把“自我力比多”和“对象力比多”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加以深化发展,由此区分出两种基本的人格即“内倾”与“外倾”。[4]荣格认为,力比多的流向有两种,一种是外向的,即力比多的“外倾”,一种是内向的,即力比多的外倾”。外倾是指力比多的外向转移,荣格用它来表示在主观兴趣向客体运动中主体与客体间的明显联系。内倾意味着力比多的内向发展,表现了一种主体对客体的否定性联系。“内倾”也即力比多向自我的投注,但荣格已经将之归纳为一种人格的类型,并指出艺术家普遍都具有这种特征。弗洛姆认为,自恋是自性欲和“对象——爱”之间的一个必然阶段。[5]他提出“自爱”这个概念,认为爱自己和爱他人是统一的。值得注意的是,《爱的艺术》一直讨论的是“爱的能力”问题,而弗洛伊德讨论的是“爱的能量”问题。“能力”和“能量”之间是要做出区分的,即自恋者向自身贯注力比多时充满爱的能量,却并不意味着他有“爱的能力”。
自恋是否可以归结于一种病理现象呢?弗洛姆说:“从生物学的生存观点看,自恋是正常的合乎需要的现象,自然必须赋予人大量的自恋,以便他能够做其生存所必须的事情。”[6]61在这里看来,自恋似乎是“正常的、合乎需要的”。但另一方面,弗洛姆也说道:“对自恋者来说,唯一完全真实的东西是他们自己,是情感、思想、抱负、愿望、肉体、家庭,是他们所有的一切或属于他们的一切,都光彩焕发、实实在在。身外的人与物都是灰色的、丑陋的、暗淡无光,近乎虚无。”[7]某些自恋者失去了基本的共情能力,甚至在受刺激时会发生自残或攻击性的行为。怎样看待自恋的“正常”与“非正常”问题?在这里要引入“阈限(threshold)”这个概念。它是指一种状态转入另一种状态的临界值,也可指一连串量变而达成质变的临界值。举一个日常生活的常见例子:转氨酶指标的正常值是0—40,那么40就是一个由正常转向“失调”或“亚健康”的阈限。若超过上限2.5倍,并持续半个月以上,可能为肝胆疾病,并为肝细胞损伤导致;那么上限的2.5倍,就是由“亚健康”走入疾病的阈限。而在整个过程中转氨酶的升高是一个渐进的连续过程,比如当指标是39 时,虽然没有突破阈限,但已经近乎这个点了,那么健康状况已经发生威胁。所以,用“转氨酶升高”来反应一个人肝脏的健康状况,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趋势。自恋也是如此。“原始自恋”是每个人都有的,力比多向外投注遭遇挫折而折回自身,这在每一个人身上基本也都会发生。但是程度较轻的并不能归入病理现象。随着程度强弱的不同,分明表现为基本的自恋性倾向、自恋性神经症、自恋性人格障碍。最为严重的可能疯狂。由于原始自恋和继发自恋实际上在每个人的身上都是存在的,只是程度强弱不同,所以无法把自恋的概念归入病理现象之中。而且,每个人身上的自恋因素受环境诱导而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强弱。在接收相关紧张刺激的时候,自恋性倾向可能跨过“阈限”,而进入神经症。在相对放松的环境中,“自恋性人格障碍”也可能退回到“自恋性神经症”。自恋,在一个人的身上,也呈起伏波动的状态,只有到了“人格障碍”或疯狂的地步,医生才诊断其为病人。在前面三种状态的时候,也只是“转氨酶升高”的状态。这种状态,其实,人已经感到不适,但又不能归入“精神病患”。
在这里,或许有必要对文艺心理学的一些术语提出商榷。自恋是每个人身上都有的,只是程度的差别。霭理士在《性心理学》中指出:“最广义的自恋包括一切自我表现里所含蓄的自我恋爱,自恋的人不限于性生活有什么变态或病态的人,也包括科学家、探险家与爬高山登绝顶的人在内。”[2]125
所以弗洛姆才说:“一个是最理想的自恋而不是最强的自恋有益于生存。”[6]75他把自恋区分为“良性自恋”和“恶性自恋”,并认为假如自恋是良性的,而且不超过一定的限度,它便是一种必要的和有价值的倾向。
弗洛伊德学派的思想一开始引入中国的时候,就将这种人人都有的,但在某些人身上倾向较强的心理倾向称为“变态心理”,比如说朱光潜的著作《变态心理学派别》、吕俊华的《艺术创作与变态心理》。这是对“常态心理”、“变态心理”中的渐进过程没有做仔细思考导致的,且“变态”两个字不仅是“非正常”,还有人格上的贬低的意味。虽然说可以在定义中说明,但这个词已经约定俗成地带有许多负面的情绪色彩。如果说突破了“健康”的阈限,可以采用“病态”,这个词程度要轻一些。如果没有突破阈限,只能说是“异常”、“特殊”。本文倾向于把较强倾向的自恋称为“特殊心理”。本人所说的“自恋者”取其“狭义”。不包括正常的“基本自恋”,而是指突破健康范围的自恋性倾向者、自恋性神经症,也包括已经发生病理状况的“自恋性人格障碍”,以及极端情况下的疯狂。
自恋是力比多向自我的投注,所以自恋者的第一个表现特征就是注意力与兴趣高度集中于自身。自恋者常常缺乏对外部世界的兴趣,如过分喜欢谈论自己、希望时刻成为他人注意的焦点。欧文·斯通在《梵高传》中写道:“在这儿的这些人全部都是个性很强的人,是狂热的自我中心者和激烈反对因循守旧的人,提奥管他们叫作偏执狂。”[8]乔治·奥威尔在总结作家写作的动机时,居于首位的是“绝对的自我主义”、“渴望让人觉得聪明、渴望受人关注、渴望死后还被人怀恋、渴望报复那些在你童年时代冷落你的成年人,等等。假装这不是一个动机,而且不是一个强烈的动机,实属自欺欺人。”[9]
艺术家是高度关注自身的人。比如梵高对自画像的情有独钟,托尔斯泰在每天的日记中都记录下自身的变化等等。卡夫卡在日记中写道:“我那样做很可能多半是出于虚荣心,把桌布上的稿纸推来推去,用铅笔敲敲桌子,把人家在灯下挨个儿看了一遍,想以此吸引某个人拿走我写的东西仔细看看,然后对我表示钦佩。”[10]86
妄自尊大是自恋者的第二个显著特征。托尔斯泰在日记中写道:“我还没遇到过一个人像我这样道德高尚,并且相信我不记得自己一生中有什么时候不追求善,不准备为了善而牺牲一切。”[11]50萨特在访谈中谈到:“我从没有遇见一个同我相匹敌的人”[12]。这种“妄自尊大”又是和他们的“使命感”紧密相连的。对于艺术家来说,“使命感是不可丧失的,无论是冷静思考还是文学经验都代替不了使命感。”[13]萨特说:“我正想成为这样的人,一个只通过自己来思想,用他所想的和感受到的照亮全城的人。”[10]90
二、 想象的激情
拉康将爱分为两种:一是“想象的激情”,乃是欲求被爱之人的爱;从根本上讲,是想把他人捕捉在作为对象的人之中的企图;而是“积极的礼物”,这是在象征层面上构成的,它“总是超越想象迷惑而朝被爱的主体而存在,朝向他的特殊性。”[14]
“想象的激情”是自恋之爱,“积极的礼物”是对自恋之爱的超越。
自恋力比多的第一个住所是在自我里面,而自我在某种程度上是力比多的永久指挥部。这个自恋的力比多转向对象,因而成了对象力比多,它还能变回到自恋力比多。前文提到过“自恋力比多(ego-libido)”与“对象力比多(object-libido)”之间存在着对立。一方面用得越多,另一方面用得越少。所以,自恋力比多是一种流动的能量,而不是固定不变的。
自恋之爱产生的第一步是自恋力比多在体内的积聚。力比多可理解为生命的能量或心理的能量。它与性欲有关,具有先天性。艺术家是心理能量较为充沛的人。力比多在体内聚积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骚动不安、情绪不稳或心理失调等多种情况,需要投射于对象,合理释放,能量才能平衡。此时,当外界寻找不到合适的投注对象时,心理能量就会折回自身。在特定情境下对象的某种特质与个体投放能量的内在心理结构趋同时,产生了“爱”的感觉。这就好像汽油已经准备好,对方就是火种,点燃了其自恋力比多。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爱过一次就无法再爱的,也有可以进行连续的高强度的恋爱的,当然更多的是在一次爱结束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复原或冷淡再次去爱,这与每个人心理能量的大小是密切相关的。
当自恋力比多转化为对象力比多的时候,呈现出怎样一种情形呢?我们对待对象的方式成为了我们对待自己的方式。“当我们陷于爱之中时,大量的自恋力比多溢到了对象身上。在很多爱的选择形式中,对象被当作我们自己的某种未能到达的自我典范的化身。我们爱它是因为它具有那种我们自己的自我所力求达到的完善性。现在我们打算通过曲折的方式把它作为一种满足我们自恋性的手段。”[15]
这种“爱的激情”是体验“爱的感觉”(to love)的渴求,而不是寻找“被爱”(be loved)的需要。这个成为火种的对象,是艺术家所投放力比多的对象,实际上是自恋的对象。
自恋之爱的第一个特征就是“理想化”。在所有正常的爱的关系中,都包含有自恋的因素。在这些正常的爱的关系中,特别是年轻人的爱情,总包含着对爱的客体的过高的评价,甚至也包含着将自身的形象投射到爱的客体上,而对于艺术家而言,他们习惯于将这种“理想化”发挥到极致。
将想象的内容添加到对象的光环上,添加得越多,赋予的意义越深、越崇高,爱的感觉就越强烈。恋爱的最初阶段,便是这样一个意义赋予的过程。如米兰·昆德拉所说:“爱情,始于一个隐喻。”如安德烈·莫罗亚在《追忆似水年华》的《序》中所说:“我们在邂逅相逢时用我们自身的想象做材料塑造的那个恋人,与日后作为我们终身伴侣的那个真实的人毫无关系。”[16]
看看艺术家们在激情的想象中留下的华丽篇章吧:徐志摩在初识陆小曼的时候写下了《雪花的快乐》:“飞扬飞扬飞扬——啊,她身上有朱砂梅的清香!那时我凭借我的身轻,盈盈的,沾住了她的衣襟,贴近她柔波似的心胸——消溶、消溶、消溶——溶入了她柔波似的心胸!”雪花与小曼在他心中唤起的是何等纯洁美好的形象。徐志摩受浪漫主义思想的影响,将追求爱情的完满作为他人生的目标。在他追求林徽因时,从他与梁启超的通信中可以看到他这一人生态度。梁启超劝他:“呜呼!志摩!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17]31 志摩回信说: “嗟夫吾师!我尝奋我灵魂之精髓,以凝成一理想之明珠,涵之以热满之心血,明照我深奥之灵府。”[17]32当托尔斯泰初识索菲亚时,内心的斯磨是怎样的缠绵,在《托尔斯泰日记》中可见一斑,郁达夫在邂逅王映霞时,那滚烫的情书可熔化冰山,“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求之而不得的苦痛让人落泪。
但是爱情的高强度和高热度并没有给他们一个美好的结局。这种类型的爱很自然不能持久,当他们十分熟悉时,他们的亲密感就越来越失去神奇般的个性,直到他们对立、失望和相互厌倦,扼杀了最初的激情。但是,他们在开始时并不知道这些。“实际上,他们被痴恋的强烈感情所驱使,以此来互相证明他们爱的强烈感情的‘狂热,而这恰恰证明他们先前是何等的寂寞空虚。”[18]3
艺术家的爱常常是这样一种“想象的激情”,是相遇时短暂的强光,由于其过度的理想化,在爱的最初会将对方尊奉为“女神”,而一旦发现现实中对象的种种缺点,就会走入另一个极端。
徐志摩与陆小曼的爱情进入婚姻之后,并不尽如人意。他曾“从你的苦恼与我从你的苦恼与悲惨的情感里憬悟了你的高洁的灵魂的真际,这是上帝神光的反映”[19]74,他也曾认为陆小曼是“一朵希有的奇葩”[19]74,但婚后发现小曼生活奢侈,爱慕虚荣。托尔斯泰在日记中连篇累牍地记录了对婚后生活的不满:“同她相处越来越难。不是爱,而是要求爱,这种要求接近憎恨并且渐渐变成憎恨。”[11]135他们之间的矛盾到最后白热化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于托尔斯泰81岁的高龄而依然离家出走,最后死在一个旅馆,而郁达夫则在他著名的《毁家诗抄》中把王映霞指责得体无完肤。想象的激情就像是一个个流光溢彩的肥皂泡,看起来活泼有生气,被现实轻轻碰触一下就踪影全无。
自恋之爱的第二个特征就是爱的冲动强烈,但爱的能力贫乏。
艺术家具有强烈的激情式的冲动,他的爱停留在理想的精神世界里,而在现实世界里,他不能为对方付出,反而降为一个婴儿,他们把全部的爱贯注到艺术中去,也可以说贯注到对全人类的无限的爱中去。而这种艺术之爱,却从全方位毁坏着艺术家的生活。梵高在书信集中说:“里契本在什么地方说过一句话:对艺术的爱意味着丧失掉实际生活中的爱。我相信这是非常合乎事实的;但另一方面,实际生活中的爱使你讨厌艺术。”[20]
荣格在《心理学与文学》中这样说:“创造力像汲取一个人的全部冲动,以致一个人的自我为了维持生命的火花不被全部耗尽,就不得不形成各种各样的不良品行——残忍、自私和虚荣(即所谓自恋)——甚至于各种罪恶。艺术家的自恋,类似于私生和缺乏爱抚的孩子一样,这些孩子从年幼娇弱的年代起就必须保护自己,免遭那些对他们毫无爱意的人都作践蹂躏;他们因此而发展出各种不良品行,后来则保持一种不可克服的自我中心主义或者终生幼稚无能,或者肆无忌惮地冒犯道德准则和法规……特殊的才能需要在特殊的方向上耗费巨大精力,其结果也就是生命力在另一方面的枯竭。”[21]
从艺术家所写的情书及他的著作来看,他经常可以为了所爱的对象而死,我们甚至觉得对方根本不配拥有这样的感情,但从现实生活来看,他对所爱的人在进行着掠夺和剥削。他们并不为被爱者的成长和幸福积极奋斗,虽然开始时貌似他愿为了对方付出一切,到最后,被爱者却反而囊括进了他实现个人野心的框架体系之中。
有成就的艺术家男性居多。在他们的情感体系中,两性关系往往极具剥削性、掠夺性。这与他们的艺术理想有关,也与他们的男性自我中心主义有关。沈从文对张兆和的追求,是因为他欣赏其美貌与才华,他也以为自己可以给她理想的生活。但最后,张兆和成为了一个贤妻良母,兼助理及高级秘书。在他们的书信中,张兆和对这种生活也是相当失望的。郁达夫的妻子也是美女兼才女,但最后她之所以为人所知,确实因为郁达夫的名声。罗丹和卡米尔是师徒兼情人的关系,但是与罗丹这样的大师相伴,卡米尔的雕塑才华却一直处在被抑制的状态。因为罗丹只让她做一些助理性的工作。她最后的归宿是被罗丹抛弃以后进入疯人院。托尔斯泰的妻子索菲亚是一个极具艺术修养与才华的人,最后写下的唯一作品就是日记,而这些日记唯一价值就是成为后人研究托尔斯泰的资料。她为托尔斯泰生了多个孩子,辛苦操持家务,却让托尔斯泰觉得其庸俗而琐碎。陀斯妥耶夫斯基和其第三任妻子安娜,看起来像幸福的一对了,那是建立在安娜无限崇拜她的丈夫,以及以一个宗教徒的牺牲和忍耐来成就了他们的婚姻。诗人的妻子,不应是个凡人,而要有着伟大的母爱与牺牲精神。这些可爱的女性,或许原本可以施展其才华,留芳后世,但艺术家们汲取了他们的生命力,而最终也磨灭了她们的才华。
这样说或许有失偏颇,有人说她们也可靠自我奋斗来实现自我的价值。但遗憾的是,她们没有艺术家那样自恋。在经济拮据的困难时期,沈从文也曾劝张兆和翻译些书,而张兆和出于现实生活的考虑放弃了。倘若沈从文有能力持家,张兆和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时间和资源,但这是不可能的。也许,对于艺术家身边的女性来说,她们最大的成就不是创造出作品,而是激发艺术家的灵感,并且为他们打点好一切杂务。
三、 混沌的孤独
进入婚恋状态以后,艺术家与其爱人的矛盾焦点到底在哪里呢?首先是艺术家们要求更多的时间与空间。孤独是艺术家的一种独特的心理特质和生活状态。孤独,意味着持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查看人生的视角,意味着冷静而清醒的批评态度,意味着对时间和空间的独占。
艺术家常常是孤独的,他的自恋特质使他与人群格格不入,在社交上容易陷入尴尬的境况,他们我行我素,桀骜不驯。但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又强烈地渴望着交流和理解,当受挫时更增加了他们的自我防御,他们便构筑起一个空间来维护自己的尊严。有时他们声称爱上了这种孤独,他们在独处的世界里感到别样的宁静,孤独既成为了一种自我保护的姿态,又成为他逃避现实的手段。艺术似乎是他们摆脱孤独的一个出口。但当写作日益成为他们的生存方式,孤独又成为了保有创作的条件。一开始,他们是因为孤独而创作,但后来,他们持有孤独,创造孤独,以保持自己的创作状态。杜拉斯说:“你找不到孤独,你创造它。”“写书人应该与周围的人分离,这是孤独。”[22]爱情、婚姻,是两个人的相融相济,一旦建立了爱的亲密关系,个人的时间不可避免地要遭到侵犯。这是艺术家惧怕婚姻的深层原因之一。
以卡夫卡为例,我们可以看到艺术家在保持孤独和渴望婚姻之间的挣扎。
卡夫卡这样说:“我在面对任何一种干扰时总是怀着战战兢兢的恐惧紧紧地抱住写作不放,而且不仅仅抱住写作,还有写作必须的孤独。”[10]129渴望孤独,害怕婚姻会对创作造成不利影响,是卡夫卡不愿与费莉丝结婚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必须经常孤独。我做出的成绩只不过是孤独的一项成就。”[10]107“为了写作我需要离群索居,不是‘像个隐士,这样还是不够的,而要像个死人。这一意义上的写作是更深沉的睡眠,也即死亡;正如人们不会也不可能把一个死人从坟墓里拉出来一样,人们不会也不可能在夜里把我从写字台旁拉走。”[10]106
卡夫卡认为写作是他气质中最能出成果的方向时,一切都朝它靡拥而去,从而让能博取在性生活、吃、喝、哲学思考、特别是音乐方面的乐趣的一切才能都荒废了。在所有这些方面他都已干枯萎蔫了。这是必然的,因为他的力量就其整体来说实在太少了,只有集中起来方能勉勉强强地为写作这一目的服务。从而,“我只是由于我的文学使命才对其它一切没有兴趣而冷酷无情。”[10]95
但是,既然如此渴望孤独为何又要与费利丝恋爱呢?自恋者是渴望通过他者的眼睛来欣赏自己,犹如在镜中确证美好自我的存在。他与费利丝一直是以通信的方式恋爱,这种方式既可让对方欣赏自己却又不会影响现实生活,对于卡夫卡来说,维持这样的状态或许比婚姻更好。但费利丝是渴望结婚的,这时,双方的意志发生了碰撞。最理想的状态是,既有婚姻,又可保持孤独,如卡夫卡所描述的:“我曾在信中对你说过,至少在秋冬两季中我们每天将只有一小时在一起,那种寂寞孤单你今天作为生活在你所习惯的、与你适应的环境中的少女已经很难想象了,而你作为妻子要熬受这般寂寞孤单就更艰难了——这样的一种生活你能设想吗?”[10]109这就是卡夫卡为费利丝所设想的婚后生活,也只有她甘心乐意地接受这种生活,他才能持有他的孤独。这样就能两全其美了。但是以另一个人的忍受痛苦来成全自己的“修道院”式的文学之宿命,让卡夫卡的良心受到责备。更重要的是费利丝如何承诺,他都并不相信婚后能保有孤独。他说:“使我不结婚的主要原因是对我写作工作的考虑,因为我认为这种工作受到了婚姻的威胁。”[10]110
他毅然选择了孤独,但这种孤独并不是一以贯之,清澈而明晰的,因为他渴望爱和交流的内心的触角,一次次向外伸展,继续寻求灵魂的伴侣,但同样的,又继续缩回自我的孤独之中。
季·吉皮乌斯在《妻子们》一文中说,无论是托尔斯泰,还是陀斯妥耶夫斯基,都称不上“幸福的婚姻”,虽然他们的妻子是“天才人物的女仆”,她认为,对于一个天才人物,很难设想一位“理想的”妻子,艺术家最好不要结婚。[23]
不结婚是否就可以保持其创作天赋和孤独的状态呢?自恋力比多在不断地要求释放,艺术家的情欲也在一次又一次地波动,那种孤独的状态并不具有一种纯粹的特质,而恰恰弥漫着混沌的气息。
“真正的爱是产生爱的能力的一种表示,它蕴含着爱护、尊重、责任和了解于一身。”[18]49这样的爱在很多艺术家的身上是稀缺的。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在席卷着女性的爱,燃烧着自身的同时,能创造出非同寻常的作品来。艺术作品,正是从那样一种既真实又虚幻的火焰中烧铸而就的。
参考文献:
[1]葛斯塔·舒维普. 古希腊罗马神话与传奇[M]. 叶青,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63.
[2]霭理士. 性心理学[M]. 潘光旦,译注.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3]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文集·性学三论与论潜意识[M]. 车文博主编,长春:长春出版社,2003:122.
[4]荣格. 心理类型学[M]. 吴康、丁传林、赵善华译,西安:华岳文艺出版社,1989:453.
[5]弗洛姆. 弗洛伊德思想的贡献和局限[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51.
[6]弗洛姆. 恶的本性[M]. 薛冬,译. 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9.
[7]弗洛姆. 弗洛姆著作精选——人性·社会·拯救[M]. 黄颂杰,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689.
[8]欧文·斯通. 梵高传——对生活的渴求[M]. 常涛,译.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391.
[9]乔治·奥威尔. 我为什么写作[M]. 刘沁秋,赵勇,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246.
[10]卡夫卡. 卡夫卡文集(第四卷)[M]. 祝彦,张荣昌,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11]列夫·托尔斯泰.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十七卷)——日记[M]. 陈馥,郑揆,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12]宋兆霖选编.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访谈录[M].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100.
[13]康·帕乌斯托夫斯基. 金蔷薇[M]. 戴骢,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22.
[14]黄作. 不思之说——拉康主体理论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55.
[15]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M]. 林尘,张唤民,陈伟奇,译. 陈泽川校. 上海:上海译文版社,2004:121.
[16]马塞尔·普鲁斯特. 追忆似水年华[M]. 李恒基,徐继曾等,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1995:6.
[17]邹吉玲. 徐志摩与陆小曼[M].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
[18] 弗洛姆. 爱的艺术[M]. 刘福堂,译.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6.
[19] 韩石山. 徐志摩书信集[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74.
[20] 平野. 梵高——插图本书信体自传[M]. 成都:四川人民文艺出版社,2002:267.
[21] 荣格. 心理学与文学[M]. 冯川,苏克,译. 北京:三联书店,1987:136.
[22] 杜拉斯. 写作[M]. 桂裕芳,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10.
[23] 弗·索洛维约夫. 关于厄洛斯的思索[M]. 赵永穆,蒋中鲸,译.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182。
(责任编辑文 心)
——过渡礼仪观照下格萨尔与奥德修斯的英雄成长历程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