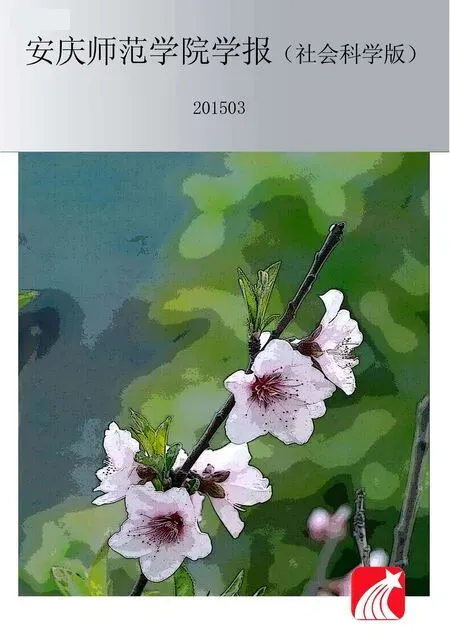《占有》中“阈限”人物的心理成长
网络出版时间:2015-06-25 13:03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34.1045.C.20150625.1612.009.html
《占有》中“阈限”人物的心理成长
张 涛
(1.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芜湖241003;2.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上海200241)
摘要:英国当代著名女作家拜厄特在其代表作《占有》中通过细致刻画男女主人公罗兰和毛德的心理成长,表达了对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群体身份构建这一重要主题的关注。伴随小说叙事的展开,两位主人公的心理发展历经动态的四个阶段:一开始两人受制于他人和传统,同处于不能独立的阈限阶段;在发现19世纪诗人信件这一过渡性客体后,他们逐步意识到走出自我封闭,和过去发生对话的必要性;在第三阶段两位学者进一步感受到完成相互主体间性交流是实现平等自我的关键环节;最终他们在关注外部世界和人际交往的基础上成功跨越了成长所处的过渡阶段,抵抗住了后现代思潮对学者身份的消解,共同完成了各自心理的成长。
关键词:《占有》;心理成长;阈限; 过渡性客体;主体间性
收稿日期:2014-11-13
作者简介:张涛,女,安徽安庆人,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561.074
DOI:10.13757/j.cnki.cn34-1045/c.2015.03.012
英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安·苏·拜厄特 (A. S. Byatt) 的小说《占有》(Possession) 在1990年一经出版就大受欢迎,并成功获得当年布克小说奖。拜厄特作为学院派小说的代表人物之一,从她的首部作品《太阳的阴影》起,就一直观照后现代文化语境中青年艺术家和学者身份建构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这一主题在《占有》中得到进一步的拓深:作者在叙事过程中巧妙地设置了两个空间,将维多利亚时期和20世纪并行,成功架构起当代知识分子身份与历史传统和经验间的联系,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罗兰和毛德探求历史真相的旅程也是他们认识自我、寻求独立身份的过程。讨论将集中于两位主人公如何跨越“模棱两可、似是而非”(betwixt-and-between)的阈限状态[1],结合现代心理学中相关“过渡性客体”、“主体间性”理论,深入探究人物在与历史交流以及现实人际互动中获得的构建独立主体性的动力。
一、阈限阶段一:受制的主体
阈限(liminality)一词来源于拉丁文“limen”(门槛)。冯盖普(Van Gennep) 在其著作《仪式的通道》(1909) 中首次提到了这个概念,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这一概念才通过英国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 (Victor Turner)的著作得以广泛运用。目前,阈限理论早已超越仪式研究的范围,被运用于多个研究领域。在文学评论范畴中,学者们认为此概念有助于理解文化身份、性别主体性和生存空间等方面的讨论。
男女主人公在《占有》中是以一种“似是而非”的含混状态出现:从表面上看,两人都受过高等教育,智力上十分成熟;但另一方面,二人的心理却受到周围其他人的影响和操控,处于不能独立的孩童期。这种矛盾状态决定了他们同处于既不是成人又不是孩童的阈限阶段。首先,男主人公罗兰尽管已博士毕业,心理上却是个听命于长者的小孩。对他施以重要影响的人包括他的母亲、导师布列克艾德以及他所研究的维多利亚著名诗人艾什。在这三人的阴影笼罩之下,罗兰没有自己独立的身份,他的存在总是渗透着其他人的影响力。第一个干涉罗兰自由发展的就是他的母亲,作为一名毫无成就的英语专业毕业生,她努力控制自己的儿子,让他按照自己的期许生活。虽然感激母亲希望自己优秀所付出的努力,罗兰也逐渐意识到母亲全方位的干涉导致他一直处于被动满足他人希望的状态,不具备去完成自己的追求的能力。导师布列克艾德是第二个给予罗兰消极影响的人物,作为研究艾什的专家,布列克艾德在事业上并不是很成功。他与罗兰的亲密关系很像是父子,罗兰无论是学术上还是心理上都受这个精神之父的影响。与此同时导师没能关注罗兰工作取得的积极成果,使其十分沮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男主人公在发现秘密信件后并没有立即向导师汇报。但无论如何,罗兰无论是心理上还是经济上都不能和导师真正分离。最后,罗兰研究的19世纪诗人艾什也在消解着他的自我身份。罗兰全情投入到对艾什的研究中,在小说第一章,他一边读着艾什曾经拥有的《新科学》,一边想着“艾什曾以手指抚摸、以双眼审视这些句子,阅读起来又自有另一番乐趣”[2]4(文内《占有》引文均由笔者译自同一英文版本,详见参考文献[2],所给页码来自英文版本)。很明显罗兰对艾什怀有类似于偶像崇拜的强烈感情。随着研究的深入,他渐渐能理解艾什脑中复杂的迷宫,却尚未意识到这里隐含的危险:在充分了解艾什的同时往往忽视了自我的独立思维,看任何问题时习惯探求艾什的角度,从而失去自我的表达方式。
聚焦于女主人公毛德,会发现即使作为一个业已成名的拉莫特研究专家,她同样处于心理受人控制的处境。她的前男友伍尔夫是最重要的消极因素,在他的眼里,毛德是一个他想要控制的客体,他只是要像占有物品般占有毛德。另外一个控制欲极强的人物是同样研究拉莫特的美国女性学者莉奥诺拉·斯特恩教授。和毛德一起时,她总是从身体上和心理上侵犯着毛德的私人空间。这种亲密让毛德感到不安,但她也不知如何去表达自己的想法。面对莉奥诺拉的长篇大论时,毛德往往只能被动地保持缄默。可见,面对威胁自己自由的行为,毛德像个不懂得该如何应付的小孩,因而她需要经历心理成长,以表达出自我的心声。
在阈限第一阶段,两位主人公都受制于身边有着亲密关系的人,因为惧怕被他人控制,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与外界隔绝,躲进自我研究的一方狭小天地,他们相信唯有这样,才能保持自我的独立和自由。为了走出这种阈限,成长为独立、平衡的个体,他们要经历自我反思、自我发现的成长过程。
二、阈限阶段二:发现过渡性客体
小说中罗兰和毛德的心理成长始于他们与一个重要客体产生联系。英国著名的儿童精神分析师和儿科医生唐纳德·温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提出了著名的“过渡性客体”(Transitional Object)的理论。在儿童心理学上,它是指当婴儿意识到与母亲的非共生性以后,为缓解由此引起的对现实的焦虑与孤独感而创造出的一个部分主观取向、部分现实取向的过渡性情景。这个客体帮助孩子意识到自己与他人他物的不同,通过这个客体,发现自我的存在。[3]14-15在罗兰和毛德的身份构建过程中,19世纪两位诗人的私人通信成了帮助他们成长的过渡性客体,帮助他们走出后现代的怀疑与不安,找到自我的确切存在。
小说第一章始于罗兰在伦敦图书馆查阅曾属于诗人艾什拥有的《新科学》一书,无意发现书中夹放着未署名的诗人的私人信件。罗兰私自窃取了这两封信,但他认为这不是恶意的行为,而是有利于保护这些信件。如果向世人公布,它们就会很快消失在伦敦博物馆并且再也无法找到。从心理分析的角度上看,罗兰的行为对应于温尼科特提出的过渡性客体是婴儿发现外界世界的关键。它是婴儿第一个认知的非我所有物,占有它意味“婴儿由完全主体向客体转变的过程”[3]6。罗兰将这些信私藏,认为他们可以带给自己事业上的成功,随着调查的深入,这些信更是助其认识到自己是这个宽广世界中的一部分。美国心理分析学家杰西卡·本杰明 (Jessica Benjamin) 在评论温尼科特的过渡性客体时说:“客体与主体相关,它是主体意识中的一部分,不需要是真实、客观独立的存在。”[4]37一旦孩子意识到如何使用这个客体,孩子才能够把客体置于自身之外,不再要求无所不在地控制它。在罗兰的眼中,一开始他就把信作为自身的一部分。随后,当他学会如何去使用这些信,他就准备好在心理上放弃拥有这些信。
只有过渡性客体的拥有者才能够去改变或毁坏这个客体。 罗兰一开始也表示他还不清楚如何去发现这些信的真正价值。罗兰首先想到是确认信上未署名的神秘女性收信人是谁,经过一系列调查,发现很有可能是与艾什同时代的一位不太著名的女诗人拉莫特,这个发现引导他遇见了拉莫特的专家毛德。初次见面,罗兰就感觉到毛德在感情上与他人刻意保持的距离,她说话时有种高高在上的贵族口吻且脸上没有笑容。因为两人都有被他人控制和干涉的阴影,一开始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疏离的,毛德也不相信罗兰的推断,但在拜访贝利家老宅思尔庄园时他们无意中找到了拉莫特保存的她与艾什的大量通信。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两个习惯自我封闭的人走到一起,决心要查出被历史掩埋的19世纪两位诗人之间的爱情故事。
随着两人调查的展开,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组既并行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两个时空和情节。霍尔姆斯指出拜厄特使用两个情节就是要对比现代人情感上的荒芜和维多利亚主人公们内心的强烈和活力。[5]62在20世纪的故事情节中,大量学者形象被生动刻画,尽管他们研究的领域不同,但无一例外地忽略了两位诗人作品中的情感表达。罗兰和毛德同样受制于这些后现代的分析方式,他们对身份和自我感到不安和困惑。这些当代学者们对“他们眼中尚未被理论所肢解而丧失了生命力的维多利亚世界表现出向往与渴慕”[6]55。而19世纪两位诗人遗留下来的这些信件使得罗兰和毛德能够与先辈们进行直接的对话,两位诗人那种面对感情的坦诚和勇气、敢于表达自我存在的信念,让两位现代学者看到了后现代解构一切思想体系统治之外的广阔世界。不仅仅是对于爱情的信念,艾什和拉莫特对于知识的追求和讨论“无不体现了这样一种试图解释自我,阐释世界,寻求所处时代内在精神实质的维多利亚时代精神”[6]51。所以,依靠这个过渡性客体,罗兰和毛德能够沿着两位诗人的生活轨迹重回历史,探寻真相,更能借此摆脱束缚找回自我。
三、阈限阶段三:与他人互动的主体间性
伴随着罗兰和毛德合作的深入,两人间的互动和联系日渐密切,这对他们彼此的心理成长都至关重要。讨论这点需要介绍一个重要概念“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它涉及心理、哲学、美学等各个方面。这一概念主要是打破了传统的主客二元对立的模式,强调认识的主体和对象不再是主要和次要的关系,而是相互对等的主体间的对话。杰西卡· 本杰明就指出:人根本上是社会动物,而主体间性强调个体应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实现成长。这一过程发生的前提是当一个主体遇到另一个主体时,能够意识到对方虽不同却又相似于自己,可以分享类似的经历,所以主体间性使心理认知从主客关系转变到主体和另一主体的关系。[4]19-20罗兰和毛德的合作符合主体间性的特征,他们之间的积极互动能够帮助彼此重建对和谐人际关系的信心,完成自我的心理成长。
两人之中,罗兰首先开始认识到毛德是一个分离独立的个体。本杰明指出,当主体间性被意识到时,一方想要和另一方建立起一种非控制性的关系,并希望得到对方的回应和认同。[4]49但在小说中,尽管从一开始罗兰就努力想要向毛德表示友善,毛德还是不为所动,与他保持疏离、冷淡的合作关系,对他的友好没有积极地回应。在思尔庄园发现大量遗留的两位维多利亚诗人的通信后,毛德甚至建议他们分开,分别对自己感兴趣的诗人进行研究,那时“两人之间宛如结霜般十分冷漠”[2]143。但随着接触的深入,毛德逐渐认识到罗兰是个不具备侵犯性的共事者,所以她也开始愿意尝试与之进行交流。关键的转折点出现在两人追随19世纪两位诗人的身影到达约克郡时,罗兰告诉毛德:“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我这一生——真正想做的——就是拥有空无。一张空荡荡的干净的床铺。我脑中总是浮现着这样一张放在干净的空荡荡的房间里的干净的空荡荡的床,什么都不需要,也没什么好要的。”[2]290令人吃惊的是,毛德回应罗兰自己也拥有同样的梦。这个空床的意象引起了各方不同的理解。霍尔姆斯认为这个意象进一步凸显了虚无主义的无力,使罗兰和毛德更能够直面现实,听从自己内心本性的驱使[5]324。考虑到两位主人公都曾受制于那些企图控制他们的人,很多人同意空无的床恰恰象征着两人对独立的向往。毋庸置疑的是这个共同的梦想将两位主人公的距离拉近了很多。他们意识到彼此就是那个不同却又相似的另一个主体的存在,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主客体控制和被控制的关系,而是平等的交流。所以在小说中男女主人公开始第一次私人交流,他们决定放下关于调查两位诗人的事,只是单纯地去享受两个人旅行的快乐。这一天,罗兰和毛德真正地跨出了互动的第一步,这对曾经封闭自我的他们来说是个全新的开始。前面提到主体间性的一方需要得到另一方的认同。这个认同不仅包含对方的肯定回应,更是人们找到自我的重要途径。个人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才能认识到自我[4]21。由此信件已经不是他们心理成长的主要推动力,主体间性成为他们去认识世界和他人的最好助力。
四、跨越阈限:完成自我身份构建
约克郡的旅行标志着两位主人公走出内心封闭的开始。当罗兰和毛德变得亲近时,小说叙述了他们内心对爱情的怀疑。这种矛盾的态度体现出过去被制约的消极人际关系影响到他们与外界的情感互动,但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是表现出两人需要重新审视在后现代理论语境下如何完成个体情绪和欲望的表达,这是形成主体身份的重要基础。罗兰和毛德“出生在一个不信任爱情的时代文化氛围中”[2]458,谙熟各种批评理论,深受后现代理论解构意义、质疑感性的影响。罗兰怀疑这样浪漫的爱情不是“他们的命运而只是受到他人故事的驱动”,甚至担心爱情看似将“二者杂乱的世界理顺,是否真实的情况恰恰相反”[2]456。毛德同样对爱情怀有恐惧,害怕感情的依赖导致自由的丧失。学者们普遍认为,拜厄特将维多利亚时期的爱情故事和当代学者追寻真相的故事并置,就是为了揭示现代理论对感性化的个体认知能力产生的负面影响。因此,罗兰和毛德真正意义上的成长,必然取决于他们是否能打破惯有理论思维的禁锢,释放自己的感知能力和创作能力。
小说后半部分描述两位学者积极地交流,逐渐消除了对爱情的怀疑和不安。这种稳定关系的建立以双方的自由、独立为前提。毛德首先意识到独立、平等的互动实际有益于自我的认知和表达。她感受到罗兰的存在不会威胁到自己的自主性,反而能够帮助她表达自我。有学者指出,毛德情感上的这种进化使得她意识到“爱情不应该使被爱者成为占有物”[7]132。对爱情全新的理解促发两人真正打开心门,勇于接受对方。作者在临近结尾时展现出一幅温馨的画面:他们依偎而坐,头靠在一起,闻着对方头发的味道,感受着彼此的温暖[2]548。由此,他们达到了一种 “另一人存在时仍感受到独立、自在”[4]49的和谐状态,两人间有效的主体间性的互动使得双方成为有利于自我成长的积极存在。
正如本杰明所强调的,在主体间性关系中,平等和控制的矛盾关系一直存在。一直到小说的最后,拜厄特也没有明确指出这对年轻的学者是否最终获得爱情的成功,他们的未来也存在变数。但是作者给读者留下了积极的信息:小说结尾时罗兰和毛德更好地理解到内心的需求,在事业上也找到了属于他们的个体知识的表达方式。罗兰开始创作诗歌,不再囿于用艾什的角度看世界,挣脱了批评话语的桎梏,真正地发出自我的声音。毛德正着手写一篇关于拉莫特的名为“阈限,门槛,棱堡,要塞”的论文,这一系列名词表面上传递出拉莫特作为一名女艺术家和一名渴望真爱的普通女子的矛盾处境,其实也暗含着毛德对于自己曾经处于的阈限状态的回顾和反思。全书的最后一段描绘了毛德对外在世界产生了一种全新的感官体验。这种对感知力的兴奋和满足,无疑表达出两位主人公获得了情感和心理上的新生,已成功跨越阈限过渡到成人阶段,能够成熟地看待和处理外界的事务。
拜厄特在《占有》中延续了对知识分子身份构建的关注,借由两位主人公的阈限成长之路,表达出后现代思潮对学者身份构建的消极影响:由于感受到活在前辈的文化荫庇之下,当代知识分子们想要拼命否定一切,惯用解构的眼光看待周围,这恰恰凸显出他们缺失自我身份的困境。所以他们应像小说中的罗兰和毛德一样,以史为鉴,继承前人的知识和精神,重视自我,敢于交流,才能获得心智上的成熟。
参考文献:
[1] 维克多·特纳.象征之林——恩登布人仪式散论[M].赵玉燕,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96.
[2] Baytt, A.S. Possession: A Romance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3] Winnicott, D.W. Playing and Reality [M]. London: Tavistock, 1971.
[4] Benjamin, Jessica. The Bonds of Love: Psychoanalysis, Feminism, and the Problem of Domination [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8.
[5] Holems, Frederick M.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Postmodernism and the Treatment of the Past in Contemporary British Fiction[M]. Victoria: U of Victoria, 1997.
[6] 金冰.“维多利亚时代”的后现代重构——兼谈拜厄特的历史想象和现实观照[J]. 当代外国文学, 2007(3): 48-57.
[7] Bronfen, Elisabeth. “Romance Difference, Courting Coherence: A. S. Byatt’s Possession as Postmodern Moral Fiction.” Why Literature Matters: Theories and Functions of Literature[C]. Ed. Rudiger Ahrens and Laurenz Volkman. Heidelberg: Universitatsverlag C. Winter,1996:117-34.
责任编校:林奕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