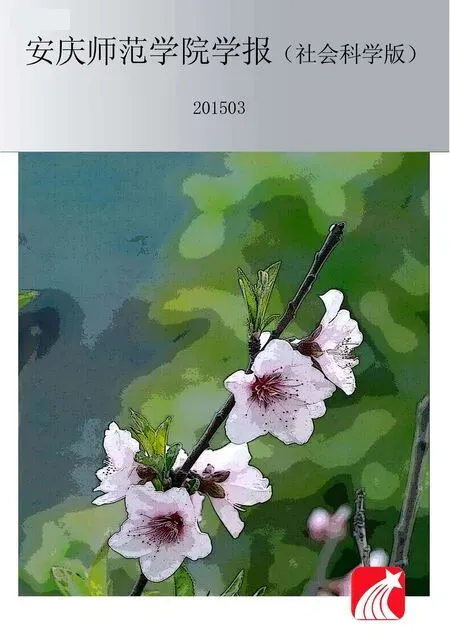方东树的诗体正变论
网络出版时间:2015-06-25 13:03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34.1045.C.20150625.1612.006.html
方东树的诗体正变论
郭 青 林
(安庆师范学院文学院,安徽安庆246133)
摘要:方东树诗体正变观受其雅正的诗学取向制约, 强调变而不失其正,重视“变”对诗歌创新的积极意义,目的在于明确诗歌创作之正途,对清中期以后的诗歌创作有着重要影响。他继承了前人正变思想的合理内核,并与其通变论相结合,揭示了制约诗歌史发展两大核心要素,发展并总结了传统诗歌史观。
关键词:桐城派;方东树;正变;诗歌史观
收稿日期:2015-03-27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文学史学视域下的《昭昧詹言》研究”(AQSK2014B013)。
作者简介:郭青林,男,安徽庐江人,安庆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博士。
中图分类号:I207.22
DOI:10.13757/j.cnki.cn34-1045/c.2015.03.002
中国古典诗学中的“正变”思想,主要是以儒家伦理观念为思想基础,旨在维护王道,排斥异说,树立儒学正统的权威。因此,崇正诎变是其基本思想倾向。孔子所谓“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论语·阳货》[1]),以正色(朱色等)、正声(雅乐)排斥变色(紫色等)、变声(郑声)即是例证。移至诗学领域,正变批评成为古典诗学批评重要方式之一。“正变”观念因时而异,故诗学上的正变批评在各个时代的倾向也有所不同。作为桐城后学中坚,方东树诗文俱擅,学界研究成果虽较为丰硕,对其“正变”观念却少有关注。方东树受其学术上的儒学正统观念及诗学上的雅正取向的制约,崇正而不诎变,既继承了前人关于“正变”的学说,又具有其自身之特点。本文试就此略作讨论。
一
从诗学史上看,“正变”观念移植于诗学批评,始自汉儒以“正变”论《诗》,《诗大序》云:“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2]认为“变风变雅”的产生是因为社会政治及风俗的衰败。汉儒以“正变”论诗,其特点是以时代盛衰来论诗歌风向的变化,着眼于诗歌的政教功能,所论虽只限于《诗经》,却开启后世以“正变”论诗之先河。
魏晋南北朝时,随着辨体意识的加强,各类文体观念得以形成,加上思想上的复古与崇变之争,正变批评开始越出汉儒以时世论诗的局限,出现从诗歌音调、艺术风格的角度来论及诗歌的正变。如挚虞有“夫诗虽以情志为本,而以成声为节。然则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3]古诗以四言诗为“正”,而三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等,皆从四言流出,是“非音之正”,也就是“变”,这是以音调来论正变。刘勰亦有“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4]67四言以雅润为“正”,五言以清丽为“宗”,以五言较四言,风格为异,故五言为“变”,这是以风格来论正变。挚虞以四言为正,五言为变,具有明显的崇正抑变之倾向,刘勰虽以“五言”为“变”,但并无崇正抑变之意。
唐、宋时期诗学正变批评,或着眼于诗歌发展的历史,或着眼于诗歌的创作倾向,如:
古今诗体不一,太师之职,掌教六诗,风、赋、比、兴、雅、颂备焉。三代而下,杂体互出。汉唐以来,铙歌、鼓吹、拂舞、予俞,因斯而兴。晋宋以降,又有回文反复,寓忧思展转之情;双声叠韵,状连骈嬉戏之态;郡县药石,名六甲八卦之属,不胜其变。(《珊瑚钩诗话》卷三)[5]
太史公论《诗》,以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以余观之,是特识变风、变雅耳,乌睹之正乎?昔先王之泽衰,然后变风发乎情,虽衰而未竭,是以犹止于礼义,以为贤于无所止者而已。若夫发于情止于忠孝者,其诗岂可同日而语哉?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王定国诗集序》)[6]311
前则论隋炀帝诗文创作旨向归于雅正,后则是苏轼从《诗》的创作旨向论其正变。从倾向来看仍是崇正抑变。此外,还有就艺术风格论正变的,如苏轼在《书黄子思诗集后》就论及“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6]559就有以魏晋之“高风绝尘”为盛为正,以李、杜之“英玮绝世之姿”为衰为变的意思。
至元开始,诗学上的正变批评开始转向,如方回《送俞唯道序》云:
大概律诗当专师老杜、黄、陈、简斋,稍宽则梅圣俞,又宽则张文潜,此皆诗正派也。五言古,陶渊明为根柢,三谢尚不满人意,韦、柳善学陶者也。七言古,须守太白、退之、东坡规模。绝句,唐人后惟一荆公,实不易之论。[7]
依次列出律诗、五古、七古、绝句之正体,虽未言变,显就是从诗体立论。正变批评的诗体转向,魏晋六朝时即有端倪,中经唐宋酝酿,至元代这种转向由潜在转为显豁,杨士弘编的《唐音》就以正变为标准来选分唐诗,“于是审其音律之正变,而择其精粹,分为‘始音’、‘正音’、‘遗响’”(杨士弘《唐音序》)[8],将唐诗纳入正变批评体系之中,确立了诗体正变批评机制,使得诗体正变逐渐成为明清两代诗学核心议题之一。明代高棅、许学夷继承杨士弘的正变批评思路并加以细化,高棅的《唐诗品汇》“随类定其品目,因目别其上下,始终、正变、各立序论,以弁其端。”认为唐诗众体兼备,“莫不兴于始,成于中,流于变,而陊于终。”(《唐诗品汇序》)[9]在考察初唐、盛唐、中唐、晚唐诗歌的流变中品评高低得失,其立足点就是唐诗的源流正变。许学夷的《诗源辨体》本着既“寻源流”,又“考正变”的原则,以为“诗自《三百篇》以迄于唐,其源流可寻而正变可考也。……统而论之,以《三百篇》为源,汉、魏、六朝、唐人为流,至元和而其派各出。析而论之,古诗以汉、魏为正,太康、元嘉、永明为变,至梁、陈而古诗尽亡;律诗以初、盛唐为正,大历、元和、开成为变,至唐末而律诗尽敝。”[10]卷一将整个唐以前的诗歌史纳入源流正变批评之中。至清代,叶燮的《原诗》对诗学史上正变批评在理论上作了深刻的总结,对诗歌的源流、本末、盛衰、正变均有辨证的分析,这里不再赘论。
从“风雅正变”到“诗体正变”,所体现出来的正变观念,“其要义在于以‘正’为源,以‘变为流’;同时即是以正为盛,以‘变’为衰。源流、盛衰、正变各各相当,是‘正变’说的宗旨所在。”[11]要义在此,故崇正抑变之倾向自然难免,尤其体现为诗歌史上的复古派之主张。就复古而言,复古并非只是恢复古诗旧制,其目的往往为了新变,如唐代陈子昂等人诸论。方东树在诗学上继承了这一进步思想,其“正变”观念既有“尚变”的性质,亦有其自身的理论特点。“正变”可以时代论,如“风雅正经”和“变风变雅”之说,也可以诗体论,如五古以汉魏为正等。方东树的“正变”属于后者,侧重揭示各种诗体的演变轨迹,以辨明其体制为直接目标。
二
方东树虽未直言“正变”,但其诗论却是围绕着“正变”而展开的。他以为“文章之道必师古人,而不可袭乎古人。必识古人之所以难,然后可以成吾之是。善因善创,知正知奇,博学之以别其异,研说之以会其同,方其专思一虑也。”(《答叶溥求论古文书》)[12]师古并不是盲目地学古,而是先要对古人的作品进行鉴别,即要“知正知奇”。在中国古典诗学中,“正变”与“奇正”义有不同,但在强调诗歌创作的独特性、创造性上是一致的。对一首诗而言,其“奇”处也就是“变”处,因此,方东树所说的“知正知奇”是可以侧重从“正变”角度来理解的。他曾在《昭昧詹言》卷二十一,附论诸家诗话中引戴叔伦语、严羽语云:
古人诗,譬行长安大道,不由狭邪小径,以正为趋,则通于四海,略无阻滞。……夫大道乃盛唐诸公之所共由者,予但由乎中正,自能成家。[13]480
严沧浪曰:禅家者流,乘有大小,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学者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若小乘禅,声闻辟支果,皆非正也。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第二义矣;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13]493
方东树以为学古人诗一要“以正为趋”,二要从最上乘入手,取其正宗、正体,汉、魏、盛唐之诗是诗歌之正宗体式,故应作为取法之对象。故所谓“知正”当指诗歌之正体而言。大历以还及晚唐之诗“皆非正也”,“非正”即是“变”、于诗就是“变体”,对于“变”,他引顾亭林语云:
诗言志,诗之本也;太师陈之以观民风,诗之用也;荀子论《小雅》曰:“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声有哀焉。”此诗之情也。建安以逮齐、梁,辞人之赋丽以淫,失诗之旨矣。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变者。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人皆道。今取古人之陈言,而一一摹仿之,可乎?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之则失其所以为我。[13]481
诗文沿袭一久,便渐趋于衰,其“变”是因为不得不变。盛唐诗一变为中唐,再变为晚唐,原因在于“沿袭”而不能新变,或者能新变却“失诗之旨”,违背诗歌之正宗属性,使得诗歌之原有的体性被改变,呈现出另一种面目。然而“变”并不是总是朝着积极的方向,“变”以使诗盛,也可以使诗“衰”,所谓“盛者得衰而变之,功在创始。衰者得盛而沿之,弊在趋下。”[13]483故方东树称“变”为“奇”,侧重强调“变”所带来的积极意义。 “知奇”也就是“深究乎文家之变”(《答友人书》)[14],即要求学诗者善于辨别古人诗歌的创新之处。“知正知奇”虽就学诗而言,却体现了方东树的对诗歌正变现象的高度重视,他对历代重要诗人诗作均作仔细的评论,就是本着“知正知奇”这一原则来展开的。
方东树有着强烈的“辨体”意识,其“正变”思想,主要属于“诗体正变”。在《昭昧詹言》中,他分别对五言古诗、七言古诗及七言律诗的体制特点作了明确的区分,并列出各个诗体的正宗典范,如:
五言以汉、魏为宗,用意古厚,气体高浑,盖去《三百篇》未远;虽不必尽贤人君子之辞,而措意立言,未乖风雅。惟其兴寄遥深,文法高妙,后人不能尽识,……非徒使正色绝响,亦恐无以待青城山天下豪杰之士。[13]51
诗莫难于七古,七古以才气为主,纵横变化,雄奇浑颢,亦由天授,不可强能。杜公、李白,……二千年来,只此二人。其次,则须解古文者,而后能为之。观韩、欧、苏三家,……纯以古文之法行之,所以独步千古。南宋以后,古文之传绝,七言古诗,遂无大宗。[13]232
七律束于八句之中,以短篇而须具纵横奇恣开合阴阳之势,而又必起结转折章法规矩井然,所以为难。[13]375
方东树以为,五言古诗的“正色”为“用意古厚,气体高浑”、“措意立言,未乖风雅”、“兴寄遥深,文法高妙”,依次揭示五言古诗在艺术风格、运辞、手法、文法等各个方面的特征,并以汉、魏诸诗作为典范加以析论。而七言古诗则“以才气为主,纵横变化,雄奇浑颢”,在创作上须以古文之法行之等,这些都是七言古诗正宗体制在艺术上的特点,其诗歌典范主要是李白、杜甫。相对于七言古诗之自由,七言律诗受体式拘束而更难:束于八句,既要有“纵横奇恣开合阴阳之势”,又必需“起结转折章法”。作为七言律诗正宗体制的典范,他有“二派”之说[13]378,一派是杜甫,诗如司马迁文,以疏气为主,雄奇飞动,纵恣壮浪,凌跨古今,包举天地,是诗之极境。一派是王维,其诗如班固文,以密字为主,风格庄严妙好,高贵华美。杜甫、王维诗风各异,但均是七言律诗的典范之作。
有“正”就有“变”,上述三种诗体,均有其“变体”。就五言古诗来说,方东树认为“大抵古诗皆从《骚》出,比兴多而质言少。及建安渐变为质,至陶公乃一洗为白道,此即所谓去陈言也。后来杜、韩宗之以立极。其实《三百篇》本体固如是也”[13]63。汉、魏五古是“正体”,陶渊明及杜甫、韩愈五古则为“变体”。而七古以李、杜为“正体”,则韩、欧、苏等为“变体”。就七言律诗而言,除前述“二派”之说,他还有“七家”之论[13]379,唐代为李商隐,李商隐诗兼有杜甫、王维二派之特点,宋代为黄庭坚、陆游,明代为李梦阳、李攀龙,陈子龙、钱谦益。这“七家”之外诸家,如大历十子、白居易、苏东坡等,“皆同莂记,不与传灯。”[13]379七律既以杜、王为“正体”,那么李义山、黄庭坚、陆游等七家就为“变体”。可以看出,如就五古而论,这里的“正”与“变”实际就是“源”与“流”,如就七古、七律而言,“正”与“变”就是“盛”与“衰”,方东树对“诗体正变”的看法继承了诗歌史上以源为正,以流为变或者以盛为正,以衰为变的诗歌史观,不同的是,他是从创作论的角度加以发挥,更重视的是“变”对于诗歌创新之意义。
三
方东树对诗歌“正”、“变”关系的理解受朱熹的影响。他于诗曾云,“惟朱子之言,乃真有见于其黑白者”[2]32故常援引朱熹之语,作为自己论诗之依据,这在《昭昧詹言》中屡屡可见。朱熹论“风雅正变”,着眼于性情之邪正,以性情之邪正论“风诗之正经”和变风、变雅(《诗集传序》)[14],论“诗体正变”则着眼于创作,“余尝以为天下万事皆有一定之法,学之者皆循序而渐进。……向后若能成就变化,固未易量,然变亦大是难事。果然变而不失其正,则纵横妙用何所不可;不幸一失其正,却反不若守古本旧法以终其身之为稳也。”(《跋病翁先生诗》)[15]他认为诗歌创作须遵一定之法,并且能够成就变化,但须做到“变而不失其正”。对此,方东树云:
姚姬传先生尝教树曰:“大凡初学诗文,必先知古人迷闷难似。否则,其人必终于此事无望矣。”先生之教,但言求合之难如此,矧其变也。盖合可言也,变不可言也。近世有一二庸妄巨子,未尝至合,而辄矜求变。其所以为变,但糅以市井谐诨,优伶科白,童孺妇媪浅鄙凡近恶劣之言,而济之以杂博,饾饤故事,荡灭典则,欺诬后生,遂令古法全亡,大雅殄绝。则又不如且求合之,为犹存古法也。[13]33
为何?首先,假人盛行,就听不到真话。因为假,所以真就成了另类。在假人盛行的环境和语境中,谎话和鬼话,就如同迷魂药,怎样快活,就怎样挠你,让你在云山雾罩里,分不清什么是正直、什么是龌龊。你喜欢听好话,就一筐一筐送给你。你喜欢恭维,他就随时马屁伺候,让你意淫不能自拔。你吹我,我捧你。彼此都知道虚情假意,却不点破。假话就成了糖,真话就成了刺。
“合之难”是指诗歌创作合古人之“正”难,古人之“正”存于古法,故是可以言明的,但“变”无定则,故不可以言明。求“合”难,但求“变”更难,因为“变”得不好就会“一失其正”,“荡灭典则”,因此,为诗之道,当先求“合”而后求“变”。这里的“合”与“变”就是“正”与“变”,先“合”后“变”,是为了以“正”制“变”,使“变”而不失其“正”。方东树同朱熹一样从诗歌创作角度论正变,在思想倾向上也与之一致,持“变而不失其正”之立场。
以七律为例,方东树云:“今定七律:以杜七律为宗”[13]420作为“七家”之一的黄庭坚诗则是杜诗之“变”,方东树以为:
山谷之学杜,绝去形摹,尽洗面目,全在作用,意匠经营,善学得体,古今一人而已。[13]450
欲知黄诗,须先知杜;真能知杜,则知黄矣。杜七律所以横绝诸家,只是沉著顿挫,恣肆变化,阳开阴合,不可方物。山谷之学,专在此等处,所谓作用。[13]450
黄庭坚学杜专在“沉郁顿挫,恣肆变化”,他虽能“绝去形摹,尽洗面目”,即能够“变”,但其“变”并不脱离杜之“沉郁顿挫,恣肆变化”之风格,故能够“知杜”就能“知黄”。方东树“变”杜,但并不离杜,即“变而不失其正”。
方东树论文亦是如此,“夫文章小技,然必有入理之功,经世之用,开拓其心胸,遗弃乎浅俗,出入乎经子,游观于事物,深究乎古今文家之变,而后以其雄直之气,瑰杰之辞,以求中乎法律,逼肖乎古人,而不袭其形貌。”[14]“中乎法律,肖乎古人”即归于古人之正体,“不袭其形貌”即力求变化,合而言之,即变而不失其正。如前文所论,伸正诎变是中国古典诗学正变批评的主流倾向,在方东树这里,只伸正但不诎变,就正变关系言之,他更重视变,但方向是“不失正”。通观《昭昧詹言》诸卷,凡所论及多就“变”而言,这体现了其“尚变”之思想倾向,他所以强调“不失正”,根源在于对儒家诗教观念和风骚传统的坚持。如:
屈子则渊渊理窟,与风、雅同其精蕴。陶公、杜公、韩公亦然。[13]3
五言诗以汉、魏为宗,……措意立言,未乖风雅。[13]51
大家冠绝古今,所以能嗣风、骚,比于经者全在此处。[13]376
陶、杜、韩、苏等大家诗皆为一代诗之正体,这些诗之所以为“正”,是因其“未乖风雅”、通于《经》、《骚》。
方东树论诗体“正变”受其诗学取向制约。从“崇真黜伪”言之,他强调诗歌的“变”,就是追求诗歌的“真”,从“崇雅贬俗”来看,他强调诗歌的“正”,就是追求诗歌的雅。“变而不失其正”就是为了使诗歌既真又雅。从这个角度来看,“正”与“变”是相互依存,相互生发的,“正”而不能“变”,会使诗歌失于真,“变”而不能“正”,则会使诗歌流于俗。再从诗歌史上看,“朱子曰:‘李、杜、韩、柳,亦学《选》诗,然杜、韩变多,柳、李变少。’以朱子之言推之,苏、黄承李、杜、韩之后,而又能变李、杜、韩故意,离而去之,所以为自立也。”[13]32诗体之“变”来源于“正”,“正”亦源于“变”,如苏、黄之学杜、韩可谓之“变”,而苏、黄能自立一宗,又成为后人取法之对象,亦成“正”。杜甫为诗之“正”,但却成就于其“含茹古今之变”。在方东树看来,“正变相生”是推动诗歌史演进的一重要动力。
四
大致说来,诗学史上的复古派诗学思想如格调派诗学,沈德潜云:“有唐一代之诗,凡流传至今者,自大家名家而外,即旁蹊曲径,亦有其精神面目流行其间,不得谓正变盛衰不同,而变者、衰者可尽废也。”(《唐诗别裁集序》)[16]虽言“变”不可废,但从其论诗总体倾向来看,向以汉魏、盛唐为宗,对中唐以后的诗,特别是宋诗尤为不满,可谓能“知正”而不能真“知变”。与之相反,持新变之说的如“性灵”派,正如许学夷所云:“袁中郎论诗……其论《骚》《雅》之变,至于欧、苏,无甚乖谬。至论国朝诸公,恶其法古。……故一入正格,即为诋斥;稍就偏奇,无不称赏。”[10]卷三十五论诗主变,而不主正,可谓“知变”而不“知正”。方东树强调“知正知奇”,旨在纠二派之偏。他对“正变”的理解,是建立在整个诗学史考察基础之上的,在《昭昧詹言》卷二十一,他对历代诗家诗论予以摘评,旨在明确诗学之正途,其“正变”观是以此为最终目的的。
方东树的诗体“正变”观与其“通变”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知正知奇”是为了“善因善创”。“因”就是袭,即继承之意,“创”就是创新,即为“变化”之意,“善因善创”就是善于继承、善于创新,合而言之,即“通变”之说。
在《答叶溥求论古文书》一文中方东树曾以水相喻,对其“通变”观作了形象的阐释,认为古今之水正是在“同”与“不同”的基础上相续成流的,文章创作也遵循此规律,既要继承古人创作之精神,又要加以创新,具有新特质。此虽论文,实通于诗。在他看来,诗歌创作中如不能处理好因创关系,就如水之断流一样,诗歌史就不能向前发展。而处理好因创关系,前提是明诗体之“正变”。方东树继承严羽之论,认为对古人之诗歌,既要取法于正,从第一义入手,继承其精神血脉,又要善于创新,成就自家之面目。方东树的诗体“正变”观是其“通变”论理论基础,虽旨在指导创作,扶正后学,却揭示了诗歌史发展的两大核心要素,文体论意义上“正变”与创作论意义上“通变”,实是左右诗歌史发展的主要力量,他把前人从“诗体”和“时代”两个角度来描述诗歌史发展落实到作者的见识及创作能力上,与前人的诗歌史观相比,无疑具有新的质素。
方东树的“变而不失其正”之倾向与刘勰的“酌奇而不失其贞”[4]148是一脉相承的,但刘勰旨在调和复古与新变,有折中之意,方东树则基于其理学立场和古文视野,旨在纠格调与性灵二派之偏,恢复诗之正道。方东树以为正变相生,正与变相统一,这又与叶燮“惟正有渐衰,故变能启盛”[17]之正变理论相近,体现了正变理论在清代诗学批评上走向终结之态势。方东树的诗体正变观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对清中后期诗坛创作具有重要影响,后来的宋诗派前期诗歌创作正是遵循方东树这一示诗途径进行创作,写出了一些艺术价值较高的作品。
参考文献:
[1]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181.
[2]孔颖达,等.毛诗正义[M] //李学勤.十三经注疏.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4.
[3]挚虞.文章流别论[M]//欧阳询. 艺文类聚:卷五十六. 北京:中华书局,1965:1018-1019.
[4]范文澜. 文心雕龙注[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5]张表臣. 珊瑚钩诗话[M].四库全书本.
[6]苏轼. 苏东坡全集[M].北京:中国书店,1986.
[7]方回. 桐江集[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
[8]张震. 唐音评注[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
[9]高棅.唐诗品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10]许学夷. 诗源辨体[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11]陈伯海. 释诗体正变[J].社会科学,2006(4).
[12]方东树.考槃集文录[M].光绪二十年刻本.
[13]方东树. 昭昧詹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14]朱熹.诗集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8.
[15]朱熹.晦庵集[M].四库全书本.
[16]沈德潜.唐诗别裁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7]叶燮.原诗[M]// 丁福保.清诗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569.
责任编校:汪长林
On the Norm and Deviation of FANG Dong-shu’s Prosody
GUO Qing-li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nqing Teachers College, Anqing 246133, Anhui, China)
Abstract:The norm and deviation of Fang Dong-shu’s prosody is constrained by his elegant and orthodox poetic orientation, focusing on changes without losing its norms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significance of changes in poetic innovation. The purpose is to make clear the right path of poetic creation, thus exerting great influence on the poetic composition after the Middle Qing Dynasty. He inherited the reasonable core of the previous thoughts on norm and deviation. Combining the core with his concept of “tongbian”, he not only revealed two constrain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poetry history but also developed and summarized traditional views on poetry history.
Key words:the Tongcheng School; FANG Dong-shu; norm and deviation; views on poetry hi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