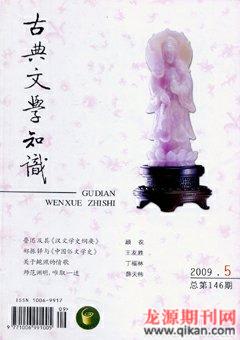鲁迅及其《汉文学史纲要》
顾 农
一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上中叶,鲁迅为教学的需要撰写了《中国小说史略》;1926年9月,他应林语堂的邀请到厦门大学任国学研究院研究教授,同时在国文系(亦称国学系)任教,为此撰写了《中国文学史略》。其时厦大国学院内外矛盾重重,鲁迅很快就离开了这里,南下广州,任职于中山大学,所以他在厦门编文学史只从事了很短的时间,留下了一部未完稿,就是通常称为《汉文学史纲要》的这部著作。
十六卷本《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九卷对所收《汉文学史纲要》一书有如下的说明——
本书系鲁迅一九二六年在厦门大学担任中国文学史课程时编写的讲义,题为《中国文学史略》;次年在广州中山大学讲授同一课程时又曾使用,改题《古代汉文学史纲要》。在作者生前未正式出版,一九三八年编入《鲁迅全集》时改用此名。
十八卷本《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九卷对所收《汉文学史纲要》一书则有新的说明——
本书系鲁迅1926年在厦门大学担任中国文学史课程时编写的讲义,分篇陆续刻印,书名刻于每页中缝,前三篇为“中国文学史略”(或简称“文学史”),第四至第十篇均为“汉文学史纲要”。1938年编入《鲁迅全集》首次正式出版时,取用后者为书名,此后各版均同。本版仍沿用。
这两份说明写得很客观。据此可知,这份讲义最初名为《中国文学史略》,而1938年和此后两版全集都采用了《汉文学史纲要》这一书名。这一书名虽然一向流行,其实却比较难以理解,甚至也不是最恰当的——这里的“汉”字究竟是指“汉族”呢,还是指“汉朝”?好像都不清楚,也不太容易讲得通。当然,1938年版《全集》开始采用这一书名自有其根据,因为在厦门大学国文系的课程表上用过“文学史总要”、“文学史纲要”这样的名目,而且当年油印本讲义的第四至第十篇的中缝处都写有“汉文学史纲要”的字样。这个名目有人认为可能出于鲁迅本人的意见,而更大的可能则是印制讲义的人以意为之,而这一失误当时未及订正。至于中山大学油印本讲义改题《古代汉文学史纲要》,大约是从上古到汉朝的意思。不久就发生了“四•一二”政变,鲁迅在这里实际上讲得很少,大约也就只到汉朝为止——他本来是打算讲到隋的。
同一本书有三个书名,用哪一个好呢?为了防止误会,继续采用《汉文学史纲要》这一传统书名,是可以的;不过最好的办法似乎是采用《中国文学史略》,该讲义开头用的正是这几个字。1926年9月25日鲁迅致许广平信中用的也是这个名目(“如果再没有什么麻烦事,我想开始编《中国文学史略》了”)。直到1928年2月24日鲁迅致台静农的信中,还说过“中国文学史略,大概未必编的了”。可知《中国文学史略》这一书名最为确切有据。可是由于已出的诸版《全集》影响极大,《汉文学史纲要》这一书名早已深入人心,所以现在也只能尊重这一已成之局。
二
厦门大学当时规模很小,全校仅有三百多名学生,正式来听鲁迅讲文学史课程的学生只有十多人,其他许多乃是来自校内外的旁听者。但鲁迅编撰这部文学史讲义时态度非常认真,1926年9月14日他写信告诉许广平说:“我的功课,大约每周当有六小时,因为玉堂(按即林语堂)希望我多讲,情不可却。其中两点是小说史,无须预备;两点是专书研究,须预备;两点是中国文学史,须编讲义。看看这里旧存的讲义,则我随便讲讲就很够了,但我还想认真一点,编成一本较好的文学史。”鲁迅对文学史著作要求很高,一般的讲义他固然不甚以为然,就是正式出版的著作,他认为好的也很少,稍后他说过“文学┦贰…我看过已刊的书无一册好,只有刘申叔的《中古文学史》,倒要算好的,可惜错字多”(1928年2月24日致台静农的信)。鲁迅为自己悬了一个很高的目标,“想好好的编一编,功罪在所不计”(1926年9月22日致许广平的信)。其间许广平曾提醒鲁迅要考虑学生的实际水平,作为教材不宜过深:“对于程度较低的学生,倘使用了过于深邃充实的教材,有时反而使他们难于吸收,更加不能了解。”对此鲁迅未置可否。看来他编撰这部文学史讲义不仅是为了供一时教学之用,还有着更高远的学术追求。
鲁迅的工作异常刻苦,1926年10月28日致许广平的信中说:“倘连编三四点钟讲义,便觉影响于睡眠,所以我讲义也编的很慢。”鲁迅本打算在离开厦门之前编到汉末,而实际上只写到司马迁、司马相如。鲁迅在北京女师大执教时曾经系统地选讲过汉代从司马相如到蔡邕的辞赋和散文,材料相当熟悉,可惜没有来得及写下来。他对已经编成的这份讲义并不满意,对老朋友说“编制太草率”,“挂漏滋多”(1926年9月19日致沈兼士的信),这不完全是客套。
编写文学史需要大量图书,鲁迅一方面利用厦门大学的藏书,一方面自己到处买书,他从上海先后邮购得《说文解字》、《世说新语》、《晋二俊文集》、《玉台新咏》、《才调集》、《唐艺文志》、《元祐党人传》、《眉山诗案广证》、《建安七子集》、《汉魏六朝名家集》、《八史经籍志》、《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历代诗话》及其续编、《经典集林》、《孔北海年谱》、《玉溪生年谱会笺》等等,从苏州邮购得影宋本唐诗、《峭帆楼丛书》、《徐庾集》、《唐四名家集》、《五唐人诗集》、《穆天子传》、《花间集》、《温庭筠诗集》、《皮子文薮》等等,托孙伏园在广州购得《乐府诗集》、《山海经》、《资治通鉴考异》、《笺注陶渊明集》等。从上述书目看,当初鲁迅至少打算将讲义编写到唐,而对汉魏六朝一段尤多研究的兴趣。后来鲁迅重新考虑写文学史,也大抵只准备写到唐。
离开厦门前夕,鲁迅计划此后的工作,有这样的自白:“我今后的路还当选择:研究而教书呢,还是仍作流民而创作?倘须兼顾,即两者皆没有好成绩。或者研究一两年,将文学史编好,此后教书无须预备,则有余暇,再从事于创作之类也可以。”(1926年12月3日致许广平的信)鲁迅认为研究和创作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工作模式,难以同时并举。他曾对国文系同事罗常培教授说过,研究需要沉下心去搜集材料、处理材料,人的才智沉下去了就浮不上来,浮上来也就不容易沉下去,所以研究同创作不能同时兼顾。
事实上后来鲁迅在“四•一二”政变以后曾一度打算退却,回到文学史研究上来;“革命文学”论战中,鲁迅腹背受敌,又一次考虑过今后专门从事文学史研究。据冯雪峰回忆,1929年至1931年间鲁迅“翻译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时候,他常常谈起的多是文学史的方法问题。鲁迅先生一向已注意到文艺与时代及社会环境的密切的关系,这时候似乎更觉得非先弄清楚历代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不可。记得他说过这样的话:‘中国更需要有一部社会史,不过这当然更难。这时他对俄国社会史的有价值的著作及西欧的艺术史(如霍善斯坦因等人的著作)都极有兴趣地细阅,我觉得这和他自己准备写文学史不是没有关系的”。(冯雪峰《鲁迅先生计划而未完成的著作》,《回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重写文学史,确实是鲁迅此时考虑得很多的一个问题。1929年初夏鲁迅回北京省亲,一度打算从旧居的藏书中择取若干带回上海,来编写文学史以及《中国字体变迁史》,但后来由于忙于更迫切的战斗,这两项工作都没有动手做。
1932年夏,鲁迅与瞿秋白深入讨论过文学史上的一系列问题,现在还可以看到当年6月10日秋白致鲁迅的一封长信(此信当时未发表,现藏于上海鲁迅纪念馆,曾收入《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题作《关于整理中国文学史的问题》),十分可惜的是,鲁迅的议论未尝见诸文字。
鲁迅还曾经设想写出若干篇像《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那样的文学史片段,逐渐积累起来;事实上也未及动手。后期鲁迅始终没有沉下心来从事学术研究的客观条件,火热的现实斗争强烈地召唤着他。既执著于短兵相接的当下,又不能忘情于长线的学术研究,这样就难免产生出矛盾和苦闷来。集学者与战士于一身,总是难免要有这种苦闷的,鲁迅内心深处的这种矛盾典型地见之于1929年省亲期间致许广平的几封信、1933年6月18日致曹聚仁的信以及同年12月27日致台静农的信等等文件之中。
往往是社会最黑暗,鲁迅自己处境也最困难的时候,他就会想到关起门来研究文学史;然而也正因为太黑暗了,他又不得不义无反顾地拿起杂文为匕首和投枪,“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鲁迅说得好:“潜心于他的宏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且介亭杂文•序言》)后期鲁迅没有能够回到文学史上来,就学术而言固然是一个无可弥补的损失,但就中国革命事业的大局而言,他的选择是勇敢而明智的。
三
《汉文学史纲要》凡十篇,内容丰富,有许多闪光的东西,至今读去仍然可以得到很深的启示。
从撰写的体例看,本书叙述史料多于评论,征引甚博,作者议论无多,他的意见大抵即寓于材料的取舍安排之中。凡有断语,都简明精当,无可移易。例如本书指出,诗歌产生于文字形成之先,源于劳动,而文字的起源则“所当绵历岁时,且由众手,全群共喻,乃得流行,谁为作者,殊难确指,功归一圣,亦凭臆之说也”。又如关于秦代文学,可讲的内容本来不多,鲁迅则列举具体材料,介绍当时的情况是:一方面群臣相与歌颂始皇之功德,刻于金石;一方面是东郡的老百姓刻陨石以诅始皇,而石旁居人为此付出了生命。这里鲁迅没有直接发表什么议论,但已经把当时的形势和气氛都说清楚了。
鲁迅写文学史特别重视知人论世,决不孤立地分析文本。周室衰微,诸侯并争的局面必然促使思想和文学的活跃,其中既有从不同立场出发来挽救时弊的志士,也有为一己之利禄奔走呼号的游士,于是“著作云起”,蔚为大观;而屈原的诗歌创作则与当时楚国内部两派的纷争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崇高的人格和卓绝的才华交相为用,一起构成了他作为伟大诗人的基础;其后学宋玉等人,则“虽学屈原之文辞,终莫敢直谏,盖掇其哀怨,猎其华艳,而‘九死未悔之概失矣”,于是只能成为主要以文采著称的二流人物。
鲁迅对文学史的观察是全面的,他既注意叙述文学发展的主流,同时也不忽略支流,例如《诗经》中的大、小二雅,古代学者多强调其怨诽而不乱、温柔敦厚的一面,近代学者则看重其激切抗争的一面。鲁迅在《纲要》中对这两个方面都有所论述,他当然更重视那些“激楚之言,奔放之词”,但在文学史里他并不只论述自己所看重的作品。鲁迅后来说得好:“中国古人,常欲得其全,就是制妇女用的乌鸡白凤丸,也将全鸡连毛带血全都放在丸药内,方法固然可笑,主意却是不错的。删夷枝叶的人,决得不到花果。”(《且介亭杂文末编•“这也是生活”》)片面的考察将无从得到全面正确的结论。
关于汉乐府,鲁迅写道:
武帝有雄才大略……复立乐府,集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十数人作诗颂,用于天地诸祠,是为《十九章》之歌。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谓之“新声曲”,实则楚声之遗,又扩而变之者也……是时河间献王以为治道非礼乐不成,因献所集雅乐;大乐官亦肆习之以备数,然不常用,用者皆新声。至敖游宴饮之时,则又有新声变曲。曲亦昉于李延年。
以下还提到《郊祀歌》十九章,并引出了祀南方赤帝之《朱明》一首的全文。这样,几个方面的情形就都讲到了。如果只讲乐府民歌,便容易失之于偏,无从明白乐府的真实情况。将感知的注意力导向一个尽可能广阔的范围,乃是思维技能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原则;研究文学史最忌作狭隘片面的观察而必欲得其全,《纲要》在这些方面都作出了榜样。
鲁迅分析作家也相当全面。例如东方朔,鲁迅既讲他“恢达多端”的一面,又讲他“切言直谏”的一面,并且指出他的思想也相当复杂,刑名、黄老对他都有影响,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弄臣:“朔盖多所通晓,然先以自衒进身,终以滑稽名世,后之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语,附著之朔;方士又附会以为神仙,作《神异经》、《十洲记》,托为朔造,其实皆非也。”这与他先前研究小说史论定“见(现)存汉人小说皆伪托”相呼应,寥寥数语,已足以概括东方朔其人。鲁迅讲司马相如也是如此,既讲他的《子虚》、《上林》、《大人》诸赋,也分析他的短赋,还提到他的经学和小学,立论相当完备。
鲁迅评论古代文学家每多独到的见解,如关于孔孟,鲁迅并不因为他们在思想史上有各自不同的地位而让他们在文学史上有相应不同的地位,因为从文学的立场来看,《论语》“略无华饰,取足达意而已”,而《孟子》“渐有繁辞,而叙述则时特精妙”,后者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显然更重要些。至于庄子,虽然其思想相当复杂,对后代也有不少消极的影响,而其文学成就在诸子中则应属最高。
鲁迅评论作家作品,极其重视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异同,深入地予以评论。例如汉初的贾谊和晁错同为著名政论家,“为文皆疏直激切,尽所欲言”,“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此其相同者。不同之处则在贾谊文采斐然,但其议论却不免有些书生气;晁错对问题的见解要更深刻些。例如“以二人之论匈奴者相较,则可见贾生之言,乃颇疏阔,不能与晁错之深识为伦比矣”。过去人们往往更加看重贾谊,特别是他一生坎坷,“司马迁哀其不遇,以与屈原同传,遂尤为后世所知闻”,而鲁迅的观察则深入一层。评价政论散文,首先须看其政见的深度如何,一味关注文采,则未免轻重失衡。
作家是否具有创新精神,在文学史上是否有开拓性的贡献,是鲁迅研究文学史特别注意的地方。在汉赋的作家群落中,鲁迅特别重司马相如,原因即在于他“不师故辙,自摅妙才,广博宏丽,卓绝汉代”。具体地说,“盖汉兴好楚声,武帝左右亲信,如朱买臣等,多以楚辞进,而相如独变其体,盖以玮奇之意,饰以绮丽之辞,句之短长,亦不拘成法,与当时甚不同”,由骚体赋一变而为散体大赋,司马相如自有开创新风之功。鲁迅的这一结论现已为文学史界广泛接受。后来鲁迅还从另一角度论述司马相如的特异之处:“他常常称病,不到武帝面前去献殷勤,却暗暗的作了关于封禅的文章,藏在家里,以见他也有计划大典——帮忙的本领,可惜等到大家知道的时候,他已‘寿终正寝了。然而虽然并未实际上参与封禅的大典,司马相如在文学史上也还是很重要的作家,为什么呢?就因为他究竟有文采。”(《且介亭杂文二┘•从帮忙到扯淡》)这里又见出鲁迅对于文采亦复十分重视。鲁迅没有片面性。胡适从“白话文学”的角度几乎全盘否定了司马相如,又有许多人因为反对贵族文学、宫廷文学而竭力贬低汉赋;鲁迅却不像他们那样偏激。
为了指出作家的特点,有时不仅要在同一文体之内进行比较,还要作跨文体的比较。《纲要》中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最著名的当推关于司马迁《史记》的论断:“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两句话就把《史记》的史学价值与文学价值都讲得很透彻了。
除分析作家作品以外,鲁迅尤致力于研究和总结规律,从宏观的高度综述文学现象的发生、发展、变化、趋势、影响。他往往以寥寥数语讲清了文学史上一些重大问题。例如楚辞,鲁迅有如下简明深刻的概述:“然则《骚》者,固亦受三百篇之泽,而特由其时游说之风而恢宏,因荆楚之俗而奇伟;赋与对问,又其长流之漫于后代者也。”又如法家与文学的关系、四言诗的源流与影响等问题,也都有简明中肯的概述。还有一些规律的总结,则更超出一般文学史的范畴,而达到更高的层次,如第十篇《司马相如与司马迁》开头便道:
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而一则寥寂,一则被刑。盖雄于文者,常桀骜不欲迎雄主之意,故遇合常不及凡文人。ぴ诜饨ㄉ缁,这确实可算是一条规律。天才往往寂寥孤独,遭遇不佳,中国文学史上这一类事情反复出现,一经鲁迅点破,令人豁然开朗。鲁迅本人的际遇其实也是如此。
鲁迅研究文学史很注意吸收古今中外的研究成果,例如叙述《楚辞》的影响即引用《文心雕龙•辨骚》,分析四言诗的起源则引用任昉《文章缘起》;近人成果列入参考书目者有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诗经研究》、《楚辞新论》,范文澜《文心雕龙讲疏》,游国恩《楚辞概论》等等,其著者除胡适算是鲁迅的朋辈,谢无量年辈也比较高之外,其余都是学术界的新秀。此外,参考书目中还列入海外汉学家的论著,如日本儿岛献吉郎的《支那文学史纲》、铃木虎雄《支那文学之研究》,指引学生去参考、比较、研究,以养成开阔的视野和胸襟。在厦门,鲁迅还亲自翻译铃木虎雄的一篇论文《运用口语的填词》。鲁迅研究古代文学始终有一种面向海内外的开放眼光。
在材料的安排上,鲁迅详近略远,大体依时代先后排列,有大作家时列专篇,如老庄(第三篇)、屈宋(第四篇)、李斯(第五篇)、贾晁(第七篇)以及两司马(第十篇),其余则述其概况,如汉代列有《汉宫之楚声》(第六篇)、《藩国之文术》(第八篇)、《武帝时文术之盛》(第九篇),点面结合,错综成史。以大作家立篇时,往往兼顾有关的次要作家,如《老庄》篇中兼叙儒墨;而在概述全貌时则突出重要作家,如《藩国之文术》篇中重点讲严忌、邹阳、枚乘、刘安。这样就能做到纲举目张,头绪分明,为文学史的编撰体例开创了新的范例。此后不少文学史著作都采用了类似的章法。
四
离开厦门以后,鲁迅没有再写文学史专著,但曾就文学史问题做过讲演,最重要的一次是在广州讲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此外他在杂文和书信中也常常提起古代的作家和作品,其命意多不过是拿来作为论据或谈资,每有借古讽今的言外之意,而无意于就有关问题作专门的学术研究,但由于鲁迅本来就是学养极深的专家,所以即使是只言片语甚至几句开玩笑的话,也往往大有意味,发人深思,益人神智。鲁迅的文章中又有若干篇比较集中地谈到中国文学史上有关问题的,例如《选本》(作于1933年11月24日,后收入《集外集》)、《杂谈小品文》(作于1935年12月2日,后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至九)》(作于1935年12月18~19日,后亦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可与《汉文学史纲要》互相参证发明。
鲁迅一直希望有新的文学史著作问世,可惜他本人因为忙于战斗而未能动手,1927年以后,始终未能回到文学史研究上来,最成片段的仍然只有先前这一部未完成的《汉文学史纲要》。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