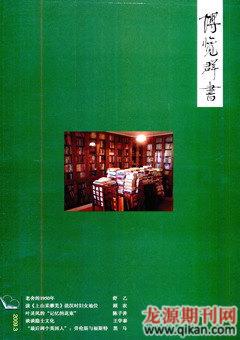百年后的文学史“清算”
朱易安
《文学史学原理研究》,董乃斌主编,河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6月版,40.00元
中国文学史的种类繁多,据说至少已有1600多种,但从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中国文学史算起,恰好一个世纪。写文学史有没有规律?什么是文学史的范式?如何认识和表述文学史发展轨迹表现出来的规律性现象?构成文学史的基本要素是什么?等等等等,真是应该“清算”一下,以便对众多的文学史成果作一些理性的思考,从理论上对文学史学科进行科学的总结。2008年6月,董乃斌先生主编的《文学史学原理研究》出版,我们欣喜地看到,文学史原理的探索已经推进到一个相对成熟的境地。
《文学史学原理研究》是近年来为数不多、分量颇重的理论研究著作,它的问世,使得已经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的系统工程有了一个比较完满的结局。事实上,它的价值还远远不止这些,对于文学史学来说,这几乎是一块有开创意义的里程碑。《文学史学原理研究》对文学史学的学理、学术范式、研究方法的阐释、文学史学理论框架的建构作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全书共分十章,前四章是文学史学理论框架,涉及文学史学的对象、性质及其定位,文学史本体,文学史的构成与功能,文学史的规律与研究方法;后面六章则是专题论述,包括文学史研究主体,文学史类型学,文学史范式论,文学史史料学、编纂学以及文学史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几乎包含了文学史学所涉猎的方方面面,在专题论述方面,作者以科学的宽容的态度,吸纳了近二十年来关于文学史学学科研究中的学术成果,作出比较合理的解释。
文学史学的理论研究,难度不言而喻。其难一,是文学史的复杂和多元性;其难二,是文学史学学科的初创性;其难三,是理论建设本身。《文学史学原理研究》最大的成功是理论框架的建构,并将这一理论框架设定为开放型的,以求促进文学史学学科和文学史学理论的发展。
关于文学史本体的论述,可以从局部体现作者的匠心独运。既是全书的核心,也是最精彩的部分。这一部分中,作者提出了“四本说”作为理论框架,即“文本”、“人本”、“思本”和“事本”,同时根据现有的成果建立了文学史形态的指标体系。在论及“四本”时有许多精辟的断言。例如,关于“文本”,作者论述了作品如何成为经典的途径,不同时期的经典变换,认为“把历代文学作品,即文本视为文学史本体,使文学史的研究和编撰有了可靠的基础”。同时又指出,“作品的人史率”“是一个有价值的参数”(56—57页)。关于“人本”,作者指出,“人本”的意识同时还存在于文学批评史和历史学中,“以时代为序,以作家为纲”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文学史家的一种共识”(73页);文学史的“人本”“不仅是指创作者,而且也应当包括接收者、消费者——他们实际上是另一个层次和另一个阶段的创造者”(76页)。“思本”除了对文学思想、文学批评史的包含,还归纳了三个方面的情况:第一,文学史家所持的“学术理论或指导思想”;第二,“文学史家从文学史的流程中概括出来的”“具有规律性意义的认识”;第三,文学史家的“寄托”和“议论”,“前者与史家的动机有关,后者与史家的心态有关”(82—88页)。“事本”则被定义为“凡与文学相关的人间种种事情,无论大小轻重,无不被人发掘开垦”(96页)。
在四本说中,“事本”说的提出,更具有理论构架的开放性。“事本”的命题,可能最早是中国诗歌的流传中对“本事”的关注,也与近二十年来叙事文学研究成果遍地开花的状况有关,但作者提到法国朗松关于文学社会学的影响,以及关于开放性体系的说法,这便使我再次回味董乃斌先生关于文学史无限性的论述(28—42页)。他说:“一切以史料为基础、为出发点和核心的具体研究(无论实证还是析论),都可纳入文学史研究的范畴,这种研究还可能是有限的吗?”(31页)以这样的“无限性”收纳包裹进有限的“原理”,难度是可想而知的。虽然作者多次重申“开放性”,但确定的“要素”或者新生的要素必须包罗万象、言之成理,这就再次回到本文开头时说到的难度,即没有一种理论可以涵盖所有的现象。在当下实证研究学风盛行的今天,完成《文学史学原理研究》这样开创性的理论研究,不仅其勇气和获得的成果弥足珍贵,在学术争论和商榷中,研究者建设性的心态则更加珍贵。
通读全书以后,再度感受到“四本说”的确定,对于文学史学来说,不仅是对现有文学史成果的形态归类,而且是对文学史构成的要素的界定。其实,无论何种形态的文学史,都少不了上述四种要素。或者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是不同的文学史著作,某种要素更突出而已。对这些要素的综合或者分别使用,其实是史家基于特定历史时期以及个人审美经验的自觉行为。或者说,文学史的写作,其实是对文学发展阐释的一种话语权。记得20世纪90年代讨论重写文学史的问题,提倡文本细读的回归,潜在的意义就是,你误读了文本,我们重新读过,以纠正你的误读。所以,说到底,重写文学史,是对文学发展历史的新阐释,是一种话语权的博弈。博弈中,也往往是一些非主流的文学现象挤进主流。这种论争非常有意义,这一个过程不仅出现了许多新成果,孕育了文学史学这样一个新的学科,更重要的是,文学版图以及与文学相关的周边逐一被开发,逐一被认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复杂的多元的世界,而且,也似乎预示了它的无限性。当文学史的成果呈现出复杂和多元,话语霸权也许就很难一统天下,取而代之的,将是话语权的分置与合作。《文学史学原理研究》在专题研究中,分章论述了类型学、范式论、史料学和编纂学等,包括在不少章节中不断阐释没有能够专设一章的问题,例如情感的问题(103页)。作者在书中也多次强调文学史本体的多样性和开放性,甚至在论述文学史的构成和功能也不断强调:“文学史的功能不是一个常数,更不是一个死数,而是活生生的,开放式的。变动不居的。”(145页)将理论研究形成一个开放的框架,面向未来,这也许是《文学史学原理研究》最有意义的方法论。
作者说,“四本”中,“人本”是核心,我并不反对。但又觉得随着文学史当前和未来功能的延伸,这个核心也许会转移。最近读到美国罗伯特·达恩顿(Rohen Damton)的《屠猫记》,作者在序言中说:
本书探讨的是18世纪法国的思考方式。书中试图陈述的不只是人们想些什么,而且包括他们怎么思考——也就是他们如何阐明这个世界,赋予意义,并且注入感情。这种探究的途径在法国称之为“心灵史”,也可称作“文化史”,因为那是以人类学家研究异域文化的同一方式处理自身的文明。那是“民族志”观察入微所看到的历史。
“心灵史”的提法,已经在国内有一定的影响,这里提到的“思考方式”和“注入情感”,成为许多交叉学科关注的要素,对文学史本体要素将意味着什么呢?也许,将验证一句名言:“世界是平的。”
本文编辑杨剑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