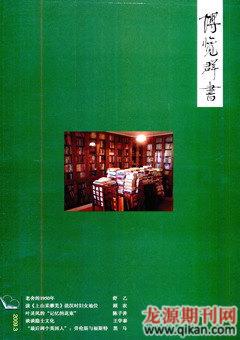市民之子老舍
吴福辉
前几天在中国评剧大剧院看完《正红旗下》出来,打出租车回家。北京的司机爱跟乘客唠嗑可能世界闻名。这次唠的不是政治局开会,而是看的什么剧。我说是老舍小说改编的曲剧,因为老舍诞生110周年了。这司机搭茬就说起了老舍,我就“考”他想看看北京的老百姓到底知道老舍什么。他说他“看过”(不是“读过”)《四世同堂》、《骆驼祥子》、《茶馆》,最惊人的是知道《我这一辈子》!一个城市的普通市民,竟能如此纯熟地道出属于这个城市的作家来,我看也无人再出老舍之右了。
我自己接近老舍的历史,也与接近这个城市相始终。没在北京定居之前,我只读过《骆驼祥子》,看过电影《龙须沟》、《茶馆》,通过《养花》、《想北平》这些零星散文,懂得了北京人爱花的习惯,老城墙上会长红酸枣,坐在积水潭这个说不上有多大多小的湖边,可以整天在那里看蝌蚪或蜻蜓,不嫌烦。可是,都无实感来支持老舍给我的这点北京印象。只是住到了这儿,这才有可能如醉如痴地观看“人艺”原班阵容的《茶馆》演出,经过反复阅读剧本来咀嚼老北京的味道;这才有机会由舒乙领着去看老舍的出生地小杨家(小羊圈)胡同,后来又变成引了中外友人去看小杨家(小羊圈)胡同;才在灯市两口丰富胡同的老舍故居改造前,多次去寻“丹柿小院”的真迹,去觅那满院的花事;才为了老舍生平展览去西直门“国招”向《四世同堂》电视剧摄制组索要正在拍的剧照。现今,我只要走到北京西北角的护国寺、新街口一带,就会自然觉得与别处不同,异样地亲切起来。
如果要用一句话回答“老舍的意义”,我肯定会毫不迟疑地说,那是老舍和北京市民(主要是底层市民)血浓于水的联系。
可以列数他的许多“意义”。比如他对确立现代长篇小说的贡献,比如他对都市的表现和想象,对北京文化的传承,他的平民幽默、风俗讽刺的独创性,文学语言克服“新文学腔”而使“五四”白话接近大众获得新生命等等。但是这里的哪一项,可以脱离掉“北京市民”这个总项呢?都市,严格来讲是市民社会的都市,在老舍这里就是北京市民社会,而不是上海市民社会,也不是东南沿海城市的市民社会。文化是市民的文化,幽默是市民的幽默,语言是市民的语言,什么都是经过市民这一“巾介”而实现的。假如撇开了“市民”来谈老舍,无疑是隔着锅台上炕。
老舍对于旧中国北京下层市民真是再熟悉不过了。曲剧《正红旗下》的第一幕,把原小说的大部分人物、场面都集中到晚清“老舍出生”、“旗人过年”来表现。这是中国年,火火爆爆的。好看,赏心悦目,是艺术化的大众的狂欢节日。讲究礼节、客套、上下尊卑长幼。贫穷到东赊西借了,也要体体面面撑着。热闹背后,大群懵懂、善良而吃牢铁杆庄稼的人,和少数自立谋生或揭竿反抗的先觉者的对照,透出庞然大物的封建王朝气数已尽。我们看其他老舍的作品,民国以后,存活的仍然是保守而可爱的老市民人物鲜活的形象,他可没少批评他们。《二马》的老马先生,《离婚》的张大哥,《四世同堂》中的祁老人:因循,要脸,知足,萎缩,退婴,中庸,随遇而安。《离婚》里的“张大哥是一切人的大哥。你总以为他的父亲也得管他叫大哥”。这个张大哥一生只做两件事:“作媒人”撮合婚姻;“反对离婚”,让天下人都尽量凑合活着。因为“生命只是妥协、敷衍,和理想完全相反的鬼混”(《离婚》)这是老派市民的生活哲学。但他们的为人多么可爱、真诚。到了民族危亡的抗战,在《不成问题的问题》里,老舍给我们叙述了一个农场的故事,问我们:是靠老市民的人情关系来办农场,还是靠本事、靠农业技术来办农场?就像放置在国家面前的一个严肃话题,任你选择。仿佛告诉你,选对了就兴国,选错了就亡国似的。
正派的贫苦市民,后来越来越多地成为老舍小说的主体。《骆驼祥子》、《月牙儿》里面的拉车的、卖身的、干杂活的,《四世同堂》里祁家长孙媳妇韵梅为代表的自重、自尊的市民女性,《我这一辈子》里的巡警们:市民的悲剧每日都以喜剧的形式在上场出演。这就像改编后的曲剧《正红旗下》的第二幕,把老舍父母的家庭的贫苦作一抒情展示。舒母把铜钱放在桌上算生活开支账目,既要正派地先还欠钱,又要顾一家几口的油盐柴米的那段唱词,是设计得很好的。从自己家庭的贫苦,可椎及大众的贫苦,老舍在日后母亲的家教下,与广大市民心心相通。其中巡警人物的写法,最能体现他的与市民同体的本色。巡警在旧时虽然维持的是旧社会的秩序,但从事底层巡警的大部都是贫穷的市民子弟。他们在派苛捐、收杂税、勒索百姓的同时,很多人还保护过街坊儿,同情更加孤苦无援者,做着好事,还无时不受上级的欺压。他们本身就是下层市民的一个组成部分。理解巡警,需要老百姓的眼光,需要普通市民的立场。可见老舍已经具备了这种市民性的眼光和立场了。
至于老舍对“新派”、“洋派”市民的嘲笑,也是贯串他所有创作的。他离他们比较远,只能给他们画漫画,涂上白脸。这是写趋时的市民。曲剧《正红旗下》里有不辨教义、单为取利的“教民”出现。在其他老舍作品里,也有《牺牲》里的洋博士,《新韩穆烈德》、《猫城记》里不足取的时髦知识青年等。他们的文化处境,按照老舍的说法是,“新旧的东西都混合在一处,老的不肯丢掉,新的也渐次被容纳。这点调和的精神仿佛显出一点民族的弱点”(《选民》)。除了讽刺新时髦,完全循着旧路子走的青年也遭他讽刺。青年市民一代可以在老中国环境里毁灭自己的理想和人性,《牛天赐传》里年轻的牛天赐在一个封建商绅结合的颓败市民家庭中被养育成“废物”,一个“竹筒儿”,空的,就是见证。总之,面对盲目政治投机型、工商实利型的青年市民他觉得难过,比老一代市民的守旧更容易引起他的感慨和激动。
而他自己虽然成长于“五四”之后,也出国开过眼界,懂得世界的事情,却归根结底,具有人世以来自然形成的市民性情、气质、品格。可以经过他的传记材料、亲朋好友的回忆文章,了解到这一点。在我的心目中,老舍再穿上西装,手执“司的克”(他用手杖是因腿有关节炎症),他还是一副本分、诚心、有礼、和悦、义气、讲理的样子。他本人继承的正派市民的精神,和他的人物相贯通。他的融于市民,高于市民,自然是无须多少文字来证明的。
曲剧《正红旗下》演到第三幕,也就是最后一幕,是老舍父亲这个正派本分的守护北京城门的旗兵之死。据老舍自述:“我不记得父亲的音容,他是在那一年与联军巷战时阵亡的。他是每月关三两饷银的护军,任务是保卫皇城。联军攻入了地安门,父亲死在北长街的一家粮店里。”(《吐了一口气》)那年是1900年。剧中就演绎了这么一段,但没有加很多花哨的枝节。最后一刻见到老舍父亲的就是舅舅家多才多艺、且主张旗人自立谋生的二哥福海。福海的形象是并未完成的《正红旗下》原著中给人最大好感的形象。现在的剧里,他和老舍父亲两个人似乎融合了。最后老舍父亲脱下布袜子交给福海,在生活里都是事实。只是闭幕前一再让福海“跪安”的那一声,真是惨极,也算是虚构的老舍式的幽默吧。戏由开场是老舍之生,到闭幕老舍父亲之死,完成了普通市民生生死死的过程。
不晓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奢谈自己是“农民之子”,谈起来已是一派壮志豪情。于是,“市贫”的成分变成了一个暧昧的符号,不是出身小商小贩,就是小店员小职员小市民,因为已经从“市民”里剔除了资本家,也剔除了工人。没有人会说自己是“市民之子”。而老舍就是地地道道的“市民之子”,而且是下层市民的优秀儿子。不是吗?他可以为“市民”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