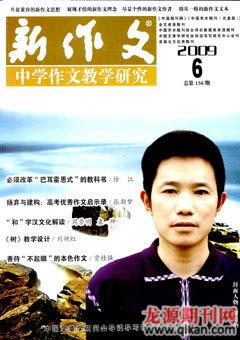由《青花瓷》谈“类叠”修辞
赵 侠
同学们都很喜欢周杰伦演唱的歌曲《青花瓷》,但对歌词中一些句子所运用的修辞手法却不太了解。比如就有同学经常问“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这句中为什么要用两个相同的“等”字呢?“帘外芭蕉惹骤雨门环惹铜绿,而我路过那江南小镇惹了你”这句中连用了三个“惹”字有什么特殊意义呢?
其实作词者方文山在这里使用了一种特殊的修辞,这种修辞我们把它叫“类叠”。所谓的“类叠”修辞,也就是指同一个字词或是词句,在一句话或一段话中接二连三的反复使用。如上例中的“等”字在一句话中使用两次,“惹”在一句话中使用了三次,这就是“类叠”。我们根据“类叠”使用的不同情况,可把这种修辞分为叠字、类字、叠句、类句四种。
一是“叠字”
即同一个字词在一句话中连续使用两次或两次以上。如女词人李清照的《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散文家朱自清的《春》:“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北朝民歌《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等,都是属于“叠字”。
二是“类字”
即同一字词隔离使用。这种形式与“叠字”不同的是“叠字”是在同一句中,如“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句中的“偷”“嫩”“绿”都是在一个句子里。而“类字”则是在不同的句子里,如“关心石上的苔痕,关心败草里的鲜花,关心这水流的缓急,关心水草的滋长,关心天上的云霞,关心新来的鸟语”句中的“关心”,“这种乐器在我国民间很流行,剃头店里有之,裁缝店里有之,江北船上有之,三家村里有之”句中的“有之”,“为何连分手都不跟我争吵,撂下一句话就想逃跑,让我爱难平,恨难消,情难灭,梦难了,心难过,你却放手,一了百了”句中的“难”等。
三是“叠句”
这种形式修辞的特点是同一语句连接使用。如“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句中的“爱上层楼”在两个相同的句子中连续使用,“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句中的“盼望着”两个相同的句子连续使用等,都是属于“叠句”类。
四是“类句”
这种形式的特点是同一语句隔离使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叠句”是连接使用,而“类句”则是隔离使用,即不是相连的,而是相分隔的。如“就算换了时空,变了容颜,我依然记得你眼里的依恋,纵然聚散由命,也要用心感动天;就算换了时空,变了容颜,我依然记得你眼里的依恋,纵然难续前世,也要再结今生缘”句中的“就算换了时空,变了容颜,我依然记得你眼里的依恋”并不是连续在一起的,中间还隔着其他的词语,“朝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声啾啾!”在这句中的“不闻爷娘唤女声”;“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酒一样的长江水。醉酒的滋味,是乡愁的滋味,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句中的“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都是这样的。
以上谈的是“类叠”修辞的类型,下面我们再来谈一下“类叠”修辞的作用。
使用这种修辞手法可以活画物的情态,表现出某种理趣。方文山说,他之所以在词中连用三个“惹”字,主要是从六祖慧能那句著名的偈语“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中得到的体会。因为“何处惹尘埃”其实也可写成“何处‘沾尘埃”,或“何处‘染尘埃”,但因为沾与染的语意都没有“惹”来的强烈,沾与染只是一种与他物接触的用词,但“惹”字却有不请自来的招惹之意,主动性很强,比较具侵略性与戏剧性。也因此,我用“门环惹铜绿”,而不用“门环染铜绿”;还有另一句歌词我也是用“而我路过那江南小镇‘惹了你”,也不用“而我路过那江南小镇‘遇见你”是同样的道理。我们从词中可以看出这里的“惹”字非常传神,活画了“芭蕉…‘门环”“江南小镇”的情态,富有理趣。
使用这种修辞手法可以表达某种强烈的感情。如“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这里运用“类字”,节奏和谐,显得感情洋溢,有力地抒发了春的变化和作者对春的喜爱之情。
使用这种修辞手法可以突出景物特点表现景物特征。如“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在这里,作者有意地把“嫩”和“绿”相叠,这不仅包含着“嫩”、“绿”之意,而且还包含着“很嫩”、“很绿”之意。这样就写出了小草的娇嫩程度和极绿的色彩。由于相同词义的重复,就在原有词义的基础上强化、突出了所写事物的特征,人们读了之后,那既嫩又绿的小草仿佛就在我们的面前,给我们以鲜明的形象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