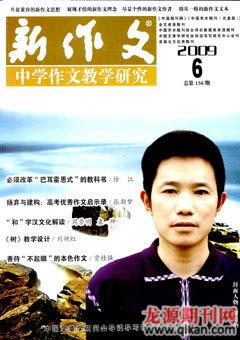必须改革“巴耳霍恩式”的教科书
徐 江
当我在电话中把题目《怎么办——语文课改中的迫切问题》读给天津耀华中学语文组一位老教师的时候,他立刻说你的讨论题目胎于列宁一篇经典文献。是的,恐怕语文界,特别是在语文界承担重要任务的教材编写专家很少有人能作出这种反应。列宁的文章是《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列宁选集》,第220页——389页),此文是为了解决当时俄国革命运动中的“迫切问题”应该“从何着手”而写的。我把这个题目稍加改动作为讨论题目,则是为了解决我们今日语文课改中的迫切问题“从何着手”而写的。我之所以从这样的话题说起,正是借用列宁的眼光看一看我们今日的语文课改问题。列宁的《怎么办》中所讲“空桶”、“稀饭”、“巴耳霍恩”、“理论”、“实际”等关键词引起我把它们和语文课改作相关联想的兴趣,而且觉得很有现实意义。也许有人会觉得奇怪,列宁二十世纪初关于俄国工人运动的文章与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语文课改怎么搭连在一起呢?其实,我们脱离开当时的阶级斗争背景,从其思维方式去认识这篇经典文献的时候,会深深地感到列宁的话语所具有的警示和启迪意义。这篇文章很值得语文界,特别是编教材的专家一读。
一关与“空桶”、“稀饭”和语文的联想
“空桶”,是列宁对当时那些只会喊“空洞”口号的所谓的工人运动理论家们的讽刺说法。列宁嘲讽他们像克雷洛夫寓言中的“空桶”一样,这些人虽然也在前进的“车”上,但“一路上晃晃荡荡”,发出的都是“刺耳”的“响声”,对当时工人运动除了干扰之外,没有任何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一切当然会使人想起我们语文课改的现实状况。语文课改进行到当下,说来时间也不算短了,各种各样的口号、说法及不断翻新的做法可谓不少,动静可谓不小。但实际效果却不佳,这些“口号、说法、做法”有没有“空桶”的性质特征呢?语文界有没有“空桶”式专家呢?谁来为一线教师解决点儿实际问题呢?语文课改正在渐渐地让人们失去兴趣与信心,或者说正在销蚀着人们改革的积极性。2006年8月底在《中国青年报》上一篇“豆腐块”式的消息就清楚地揭示了这一尴尬的现状。消息说某地举办课改观摩会,许多语文老师对此反应冷漠。紧接着在该报九月初又有某中学语文老师公开撰文说明为什么对课改冷漠。大家都感到累了,确实也够累的。
语文课改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根本问题是在“教什么”的问题上,“今天”与“昨天”没有实质的改革,教师的专业发展没有得到有效的帮助也没有发展,学生的语文素养前后没有什么本质的变化,人们在比较中没有改革的成就感。这种现状让人们自然去思考所谓“课改”不就是一个“空”的口号吗?久而久之,谁不疲沓呢?然而语文课改是必须要进行下去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要求一线教师在“教什么”上承担改革的责任,千头万绪“从何着手”呢?我以为就是抓教材改革,“教本,教本,教学之本”。“用什么教”规定着“教什么”乃至“怎样教”。“用教本指导课改,用教本保证课改。”这将是课改的必由之路。
我曾在《人民教育》杂志撰文《中学语文“无效教学”批判》,语文界对此不甚服气。其实中学语文界从其使用的教材这一根本性的教育源点就已经规定了语文教学的无效性,也就是说语文界在教学前所选“用什么教”(即教本)自身存在的巨大缺陷就已经先天地、隐性地决定了教学行为的无效结果。该教的,教本中用错的教;不该教的,充塞于教本,教师没法教;甚至该教的内容东鳞西爪,不能构成一个有序的系统。用这样的教本,语文教学的有效性怎么会不打折扣呢?况且目前一线教师专业素质与课改要求本来就有一定的差距,没有一个好教本,怎么可能把语文教学的有效性提上去呢?所以,目前的课程改革必须改革目前使用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因为它本身暗含着规定课程改革失败的因素。这不是危言耸听。当然,人们不会轻易认可我的评断。岂止是不认可,简直会嗤之以鼻。我已经想象到反对者轻蔑的冷笑。然而这正是语文的可悲之处,因为人们不能从语文的角度对语文进行思考,非语文因素干扰着人们对语文的反省。尤其是那些在规定语文“教什么”问题上具有强势话语权的专家们,怎能把我们这些非语文界的普通人的批评当做一回事呢?他们会说你们不了解情况呀,现在的教材很好呀!真的是这样吗?为了说清教材本身存在决定课改失败的因素,那么就再回到列宁《怎么办》关于“空桶”的形象思维,如果把语文教科书看做是一只“大桶”,我认为那些教材编写专家们在语文教科书这个“大桶”内“装”的是知识的“稀饭”,虽然它不是“空桶”。
这个“稀饭”说也是源自列宁的《怎么办》。他以工人的口气抨击那些“空桶”理论家说:“我们并不是一些单靠……政治的稀饭就能喂饱的小孩子,我们想知道别人所知道的一切,我们想仔细了解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想积极参加所有一切政治事件。为了这一点,就要知识分子们少讲些我们自己也知道的东西,而多给我们些我们还不知道,并且是我们自己根据自己工厂方面的经验和‘经济方面的经验永远也不能知道的东西。”(《列宁选集》,同前,第288页)在这里,列宁要求“知识分子们”能够超越工人现实存在的状况在更广阔、更深远的背景下帮助他们认识并解决面临的实际问题,而不是与他们站在同一水平线上,以他们已经知晓的“政治稀饭”充作“精神食粮”。
当然,今天重温列宁这些话,不是从政治背景下认识问题,而是从如何教育人的角度去思考。读着列宁的话,我想到课堂上读书的学生,于是模仿列宁替工人说话,也想替学生讲上几句——“我们不是一些靠这样的课本所讲这样的知识稀饭就能喂饱的小孩子,我们渴望仔细了解语文学习各个方面的规律,特别是解读和表达方面的系统东西。面对一篇一篇、一册一册的语文课本,我们不能局限在积累这些课文讲了什么。而是在积累课文讲了什么的基础上还要积累怎样读出它们讲了什么,积最它们怎样就能讲出什么。这一个一个‘怎样之类的实际能力,应当像上数学课一样,在一个逐步递升的过程中得到充实、提高。绝不是如目前这样,假如你三个月不听课,没有什么了不起。在语文学习上不会感到有什么缺憾和损失。为了这一点,我们希望编写教材的老师和使用这些教材教导我们的老师少讲些我们已经懂了的或者说很容易懂的东西,而多给我们些我们还不知道,并且是我们自己根据自己的学习和生活经验很难知道而又是我们非常需要的东西。”与此要求恰恰相反,目前所谓的“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看不出它有什么值得进行“实验”的新东西,看不出它有什么“标准”意义,它
和以前不搞课改时没有什么两样,它规定了一线教师不能满足孩子们学习语文的要求。于是乎,我又想起人们总挂在嘴上的一个话题,要提高学生学语文的积极性,说什么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那么请大家再听一听列宁批评那些“空桶”理论家的话吧——“少讲些‘提高工人群众积极性的空话吧!……你们没有资格给我们‘提高积极性,因为你们自己恰恰就缺乏积极性!”(《列宁选集》,同前,第289页)是呀!指责孩子们缺少语文学习积极性,指责孩子们对语文不感兴趣,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为什么不想一想这个产生问题的根源是不是跟那些对语文不感兴趣而又在语文界具有强势发言权的理论家们有关系呢?如果他们对语文课改有兴趣而又负责的话,为什么还没有编写出比课改前有很大提高的教科书来呢?孩子们对语文不感兴趣,是不是跟语文教科书“大桶”内“装”的“饭”太“稀”有关系呢?教材中所选定的课文,课文后所设定的内容导引思考题以及“表达交流”有关的理性知识等等,真正能构成学生读、说、听、写诸方面语文能力的东西是不是“稀”少呢?
二、必须改革现行“巴耳霍恩式”的实验教科书
巴耳霍恩是何许人也?他怎么和现行课标实验教科书相关联呢?巴耳霍恩是列宁在《怎么办》中讲的一个出版商,他是十六世纪德国莱比锡人,他出版了一本很糟糕的识字教科书。书中有一幅招牌性的插图,画的是一只雄鸡,不过他画的雄鸡并不像通常那样脚上有距的雄鸡,而是脚上无距的雄鸡。不仅如此,在雄鸡旁边还画了两枚鸡蛋。课本上写了一行字:“约翰·巴耳霍恩的修正版”。距,就是鸡脚上与向前的三只鸡爪方向相反的另一只小爪,它本来是应该有的,而巴耳霍恩的教科书却把它“修正”掉了。公鸡是不下蛋的,在公鸡旁画两枚鸡蛋是何意思让人费猜。所以说,这位出版家的招牌画中“该有的没有,不该有的却有”。从那时起德国人就把这样愚笨的胡乱“修正”行为称之为“巴耳霍恩式的修正”。我以为现在流行的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就是地地道道的“巴耳霍恩式教科书”——“该有的没有,不该有的却有”。这样的教科书怎么会促进课程改革呢?现行的课程改革实验教科书面临必须改革的命运。下面就讲些具体的。
在这篇论文中详尽地对目前流行的课标实验教科书“巴耳霍恩性”的问题进行分析论述是没有这个必要的,我选择一个问题做例子就足矣,因为我在前边四篇论文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下面我只是就有关议论文的写作规律进行讨论。
人教社实验教科书“表达交流”部分有关议论文写作讲了如下几方面的问题——“学习选取立论的角度”、“学习选择和使用论据”、“学习论证”、“学习议论中的记叙”、“学习辨证分析”、“学习横向展开议论”、“学习纵向展开议论”、“学习反驳”共计八个话题,看起来不算少。单就这几个话题看,其中“学习议论中的记叙”表达就不当。准确说是这样的——“学习议论中如何陈述事例”,而不是“议论中的记叙”。因为“记叙”是为了“保存”、“解释”已经发生的事件,同时表达作者的情感,而议论中举事例则是为了让人接受、理解作者的“论点”,两者在本质上是不同的。此外,“使用论据”与“议论中的记叙”两个问题显然后者关于议论过程中事例的陈述与“使用论据”中的如何使用事例是共同的问题,分在两个话题之中岂不混乱?不看其具体内容,仅看这几则分标题便已呈现出总体内涵“稀”之端倪。明确地说,我所谓“稀”之说还不在于这些问题表述有某些不妥。我批评教材内涵“稀”之焦点在于“缺”。任何一位有生活常识的人都知道,“饭”之所以“稀”的关键问题就是少“米”。在有关议论写作理论常识部分,课标实验教科书缺少最基本的论证意识阐述,即论证是什么,论证的基本方向是什么。有关议论的“上位”性思维空间是空的。这就是“该有的没有”。
我主张要加强议论的“上位”性理论知识的讲述及实践训练。比如我会把“论证意识”作为一个重点话题“装”在语文教科书这个“大桶”内,具体阐明“什么是论证”以及“论证方向”等问题。当然,我对“什么是论证”的解释不同于中学语文界流行的传统观念——所谓“论证是用论据证明论点的过程”,这个“论证”观念是片面的,因为它强调的是“证明”,而“论证”并不仅仅是“证明”。
“证明”说作为“论证”基本理论必须要摒弃,同时应该构建新的“论证”观,这种理论建设就是课改的重要组成部分,用新构建的理论教育学生就是课程改革。语文界对此认识很不足,没有意识到这才是根本的改革。列宁在《怎么办》中早就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列宁选集》,同前,第241页)很显然,“没有科学的理论,就不会有科学的教育”。语文课改难以为继,其瓶颈就是语文界自身有关语文教育的“理论思想发展方面的冷淡和无能”。而在这方面,作为语文教学之本的课改实验教科书的编辑者“冷漠和无能”,在教科书中“该有的没有”,更是先天地、隐性地直接规定了语文教育的无效性。他们看不出这一点,也正是自己不懂语文有关理论。
当然,“该有的没有”,还包括能够承载重要课程内容的典型范文以及相应深入的设问导引。
至于“该没有的却有”,恰恰把前边说的问题倒过来了。不能典型地表现课程内容的课文和弱智化的设问导引却严重地存在着,关于这一切在前边已经论及,为了让大家更清楚地认识这一问题,我再补充一点儿:如《记念刘和珍君》课文后问:“文章叙述了刘和珍君哪些事?从中可以看出刘和珍是怎样一个人?”如《故都的秋》课文后问:“说说作者选取了哪些景物,写出了故都的秋怎样的特点”等等。这些内容是读后自明的问题,引导师生把精力放在这方面不就是无效教学吗?
说到这里我还要顺便提及一种更愚蠢的设问导引,当然需要说明这个问题不是人教版的课改教材,而是某出版社组织的新版课改实验教材——《米洛斯的维纳斯》课文后的设问:—下面两幅画(齐白石的虾和油画《蒙娜丽莎》)你认为清冈卓行可能会对哪一幅画评价更高些?请说说理由。(见《语文学习》2006年第5期)这两幅画,是两个民族两种文化、艺术、审美等不同风格的表现,各有千秋,不具有可比性,更不能是此非彼。因其太典型,所以在说及“巴耳霍恩式”教科书“不该有的却有”时,提出它以引起人们的注意。这更是令人深省的问题,而且这说明“巴耳霍恩性”的问题也并不仅仅是人教版有,可见这个问题是有普遍性的。
至于我在前边文章中批评课改实验教科书的篇目安排是一堆放得“乱七八糟”的“石头”,这从根本上讲,是因为教材编辑专家们自身从理论上就不懂得“构造体系”应该理解为是一个“有等级的对象序列”,而且这个“有等级的对象序列”其构成元素应该从较低级的对象起始。然而当读者打开课改实验教科书目录时,他会发现第一单元是以毛泽东的词——《沁园春·长沙》为首的诗词。无论是从审美欣赏、写作艺术借鉴哪一方面说,这些文学样式在文学中都不是“较低级的对象”。这种编排对于高一学生来讲,那诗中的意境和形象的理解远不如先学其他课文诸如《故都的秋》《囚绿记》等散文有些积累之后会更好一些。面对这样毫无秩序的排列,还是让我们读一读列宁《怎么办》中的话:“当石匠建造一座巨大的和前所来见的建筑物而在各个地点放置石头的时候,他总要拉一根线测定放置石头的适当位置,指明全盘工作的最终目的,不仅使每一块石头而且每一小片石头都能得到使用,使它们互相衔接起来。形成一座完整而统一的大厦的轮廓。”(《列宁选集》,同前,第371页)“拉一根线”、“适当位置”、“互相衔接”、“最终目的”,在这些关键点上现今语文课标实验教科书的编写专家都处于十分模糊的状态。
最后,我还是用列宁在《怎么办》里的话来表达我的忧虑——“现在……我们需要的……是在实际上解决问题”(《列宁选集》,同前,第369页),“在这方面……可以用两句话来表示:没有人,而人又很多。”(《列宁选集》,同前,第338页)语文界号称专家的“人”很多,而务实研究的不能说“没有”,但可以说“很少”。否则,我们的语文会是另一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