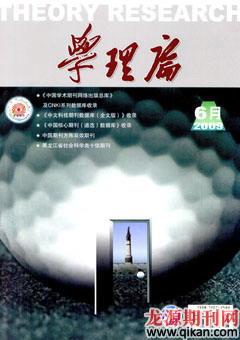现代文学名作四篇解读
索晓海
摘要:不少文学名作需要重新解读,杜运燮诗作《山》不是对于奋斗作一般意义上的讴歌,而是表现精神追求者的生存状态;林语堂散文《祝土匪》善用反语,文中隐藏着五层逻辑关系;鲁迅小说《伤逝》批评了当时青年“五分热”的病症;沈从文小说《丈夫》揭示的仍是湘西与都市文化的冲突和差异。
关键词:文本解读;《山》;《祝土匪》;《份逝》;《文史》
中图分类号:I02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14—0125—03
《山》:精神追求者的生存状态
杜运燮这首诗描写山的形象,表现的却是精神追求者的生存状态。袁可嘉指出“山”在诗中是精神活动的象征物,“可能折射了一位志高意远的艺术追求者的胸怀”[1]。实际上,它还可以是科学家或人文学者的生存状态。
全诗共分五节:
“来自平原,而只好放弃平原; /植根于地球,却更想植根于云汉; ”这是诗歌开头的两句。人生有取便有舍,第一句写舍:为了追求,迫不得已只好放弃常人的生存状态,不能像常人那样生活。第二句写取:追求的高远。诗人接着写的是,山幻梦般的形象正是茫茫平原的升华,大家因此自豪有他,他却永远不满。这是第一节。
第二节进一步写追求如何高远。无论变化万千的天空、无尽光热的太阳、博学含蓄的月亮、笑眼的星群和生命力最丰富的风,描绘的都是高处所见的景物。而高处不胜寒,成就事业要耐得住寂寞,因而就有了“戴雪帽享受寂静冬日的安详”这一句。
高处虽不胜寒,但也自有高处的乐趣。第三节写高山瀑布唱着悦耳质朴的山歌,是写精神生活带来的愉悦。这样的生活是孤独的,充满了对于知识的渴望,因而始终有“孤独的古庙”、“暮鼓晨钟单调地诉说某种饥饿”的意象。
第四节写这样的精神追求者得到人们的羡慕、追随,却并不随俗,忘乎所以,而是依然故我,孤独地生活着,只在梦里回到凡人的生活中,“回到平原上唯一甜蜜的童年回忆”。
最后一节写精神追求者为了追求牺牲了许多常人的生活乐趣,“他只好离开它必需的”。虽然有高处的乐趣,得到了常人享受不到的生活境遇,“可以鸟瞰,有更多空气,也有更多石头”;但毕竟也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他没有桃花,没有牛羊、炊烟、村落”,这一切都是为了永不满足的精神追求。
《祝土匪》的五层逻辑关系
林语堂散文《祝土匪》巧用反语,正话反说,其间有五层逻辑关系:
第一层由莽原社引出“土匪”。“莽原”一词与“草莽”相近,因而有自然令人联想到“土匪”。所以文中这样说:“因为莽原即非太平世界,《莽原》之主稿诸位先生当然很愿意揭竿作乱,以土匪自居。” 这是因为刘百昭等人称反对章士钊的人为“土匪”、“学匪”,才有这样的反语。
第二层由“土匪”引出“学者”。这两个概念原本有着天壤之别,那些自居为“学者”的现代评论派成员以此傲气逼人,行为却令人气愤。作者三十年代后期创作的《京华烟云》还描写那些“教授的卖弄学问,都是求取总长或顾问职位的敲门砖。由于他们对统治者所作所为每每予以粉饰或解释,尤其是站在统治阶级的观点,就以向日本借款一事,他们说那是政府唯一能存在的理由。”
第三层推论“学者”与真理的关系。学者本是真理的探索者,然而带引号的“学者”却摆出一幅中庸稳健的姿态,一副假面孔,顾及的是自身的利益;表面不偏不倚,实则丧失了敢于讲真话的锐气,与真理隔着千山万水,“去真理一万八千里之遥”。
第四层推论真理与“土匪”的关系。“土匪”与“学者”恰好相反,“既没有脸孔可讲,所以比较可以少作揖让,少对大人物叩头。”因此,“惟其有许多要说的话学者不敢说,惟其有许多良心上应维持的主张学者不敢维持,所以今日的言论界还得有土匪傻子来说话。”“土匪”比“学者”更接近于真理。
第五层再由“土匪”引出“学者”,进行对比。由于“土匪”比“学者”更接近于真理,因此“有史以来大思想家都被当代学者称为‘土匪‘傻子过”,因此“土匪有时也想做学者”,这是真正的学者,是真理的探索者,这要等到当时所谓的“学者”“夭灭伤亡之时”。
“五分热”的涓生
时人论及《伤逝》,常常将它与鲁迅创作该作之前两年的讲演《娜拉走后怎样》联系起来,说明作品对于子君出走后出路的思考:由于无钱,要么堕落,要么回去。因而生发出作品的主题意蕴——仅靠个性解放是没有出路的,要紧的是社会解放。然而子君不同于娜拉,娜拉是已婚女性脱离家庭,独自走向社会,这对于断绝了经济来源、尚无经济地位的女性来说自然要冒极大的风险;子君起初也是脱离家庭(娘家),却并不孤独,因为她按照自己的意愿建立了一个小家庭。此时堕落不大可能,回去也未必需要。从男主人公涓生这方面看,更不存在一个类似要么堕落,要么回去的问题。失业使涓生经济拮据,似乎是小家庭走向崩溃的决定因素。但在小说里,失业是人为迫害的结果。“这在会馆里时,我就早已料到了;那雪花膏便是局长的儿子的赌友,一定要去添些谣言,设法报告的。到现在才发生效验,已经要算是很晚的了。”这一情节从根本上讲是封建伦理不见容于新青年,而不是一个经济地位、经济权带来的问题。涓生的手记接着写道:“其实这在我不能算是一个打击,因为我早就决定,可以给别人去钞写,或者教读,或者虽然费力,也还可以译点书,况且《自由之友》的总编辑便是见过几次的熟人,两月前还通过信。”往后的生活虽然贫困艰辛,但谋生之路并未堵死。何况涓生一直坚信“生活的路还很多”。子君既已与涓生结合,其出路就是小家庭的出路,而不仅仅只是作为女性个体出走后的出路。如果说小说写的就是在当时经济制度下这样的新型小家庭必然破毁,那么《娜拉走后怎样》并未如此论述,小说中也看不出这样的意图。
真正导致小家庭破毁的原因在于人物性格,在于爱情的流失。为了弄清这个问题,笔者查阅了鲁迅同期创作的杂文作品。较《伤逝》早三月创作的《华盖集·补白(三)》中,作家提到了梁启超所批评的“五分钟热度”(没有持续性的无理性冲动),认为“五分热”是国民的一种通病,是缺乏现实感和韧性的狂热。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在这里不仅批评了爱国运动中袖手旁观且责人太严的看客,也批评了天真的青年。
但是,别有所图的聪明人又作别论,便是真诚的学生们,我以为自身却有一个颇大的错误,就是正如旁观者所希望或冷笑的一样:开首太自以为有非常的神力,有如意的成功。幻想飞得太高,堕在现实上的时候,伤就格外沉重了;力气用得太骤,歇下来的时候,身体就难于动弹了。为一般计,或者不如知道自己所有的不过是“人力”,倒较为切实可靠罢。
涓生又何尝不是这样“五分热”的患者!当时他是怎样将纯真热烈的爱表示给子君的,事后不久竟然都记不清了。然而生活是严酷的,并不总是那么浪漫。繁重的家务劳动使子君终日劳累,因小油鸡与房东小官太太的暗斗又使子君不快(在那个时代,没有高压锅、洗衣机、煤气灶等家用设施,家务劳动比现在繁重得多)。及至涓生失业,两人间的裂痕骤然扩大。为了生活,译书与规定的吃饭时间发生了冲突,引起涓生的不满;饭菜不够吃,只得杀了油鸡,赶走了小狗阿随,家庭生活变得十分凄清。涓生不能面对现实,又开始了飞得太高的幻想。
在通俗图书馆里往往瞥见一闪的光明,新的生路横在前面。她勇猛地觉悟了,毅然走出这冰冷的家,而且,——毫无怨恨的神色。我便轻如行云,漂浮空际,上有蔚蓝的天,下是深山大海,广厦高楼,战场,摩托车,洋场,公馆,晴明的闹市,黑暗的夜……。
而且,真的我预感到这新生面便要来到了。
这岂非“太自以为有非常的神力,有如意的成功”吗?然而,涓生意识不到自己正患着的“五分热”的病症,于是将一切都怪罪于子君。责难子君浅薄,将子君看作累赘。哀莫大于心死,涓生一时热烈的爱至此已化作乌有。于是发生了“慌语”与“说真实”的两难:前者能勉强维持现状,却因爱的流失成为虚伪的做戏,“虚伪的草稿便写在自己的心上。我的心渐被这些草稿填满了”;后者是诚实的做派,却将真实的重担卸给了子君,使得子君“就要负了这重担,在严威和冷眼中走着所谓人生的路”,最终导致了子君的死亡。涓生忏悔的正是后者,悔恨自己“将真实说给子君”,因此打算今后“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而真正需要忏悔的“五分热”的行为,却被他彻底地忽略了。
《丈夫》写了什么
沈从文的短篇小说《丈夫》写了什么?人们都说,他写了主人公“丈夫”的觉醒。怎样的觉醒呢?在1980年代阶级话语语境中,人们强调的是穷人的经济窘境,以及在这一窘境下,主人公的愚昧、人性扭曲和最后的觉醒。于是,小说中的一段话被当作经典来引用:
地方实在太穷了,一点点收成照例要被上面的人拿去一大半,手足贴地的乡下人,任你如何勤省耐劳的干做,一年中四分之一时间,即或用红薯叶子拌和糠灰充饥,总还不容易对付下去。
然而吴福辉先生指出,这段话是后来补添的[2],有人考证是1957年补添的。这就说明沈从文这篇小说的重点原本不在于揭示旧的经济制度对劳动者的压迫。如今,更多的学者相信,“丈夫”的觉醒是一种夫权意识的觉醒。“丈夫”在妓船上体验到夫权沦丧的痛苦,宁愿扔掉钞票,回到山里自己的家乡,而这一描写自然暴露出沈从文自身的男性中心意识。吴福辉对此也曾表示怀疑:“沈从文的湘西世界里,男人对女人的‘性禁锢本就松弛,性爱转让所标示的夫权危机自然对男女双方都没有那么严重,这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2]的确,小说中的年轻夫妇就不大在意这一切。他们同当地其他人一样,平淡地将在妓船上卖淫称作“生意”,认为“在名分上,那名称与别的工作同样,既不与道德相冲突,也并不违反健康”。“一个不亟于生养孩子的妇人,到了城市,能够把每月从城市里两个晚上所得的钱送给留在乡下诚实耐劳种田为生的丈夫,他在那里就可以过上好日子。名分不失,利益存在”,似乎是何乐而不为的好事。这体现了湘西具有原始气息文化氛围中蒙昧人格懵懂的思想特征,与都市中人的财迷心窍是不同的。在人物出场之前,小说用了大段的文字来作背景铺陈就是这个原因。如果仅仅只是揭示“丈夫”夫权意识的觉醒,并无必要做这样的铺陈,并无必要将他放在这与湘西其他地方不同的特殊背景下来描写。这段铺陈中有一处对于理解全文的旨趣是十分重要的:
做了生意,慢慢地变成为城市里人,慢慢地与乡村离远,慢慢地学会了一些只有城市里才需要的恶德,于是这妇人就毁了。但那毁,是慢慢的,因为需要一些日子,所以谁也不去注意了。而且也仍然不缺少在任何情形下还依然会好好的保留着那乡村纯朴气质的妇人,所以在城市的小河妓船上,决不会缺少年青女子的来路。
接下去展开了不少有关这类女子装扮、神情举止变化的细致描写。小说所叙述的小河妓船的位置接近于城市,这里有着现代城市文化的背景,这同名作《边城》里的背景大不相同。《边城》中也有娼妓制度,但人们重义轻利,守信自约,因而才有这样的情形:“短期的包定,长期的嫁娶,一时间的关门,这些关于一个女人身体上的交易,由于民情的淳朴,身当其事的不觉得如何下流可耻,旁观者也就从不用读书人的观念,加以指摘与轻视。”沈从文在小说中时常提到娼妓制度是一种“古老的职业”,并非现代都市所特有,可见其批判的重点不在娼妓制度本身。在《边城》这样特定的文化背景下,不觉得、不指摘、不轻视才不是作者需要否定的行为。试想将“丈夫”放在这样的背景中,作者还会写出《丈夫》那样的结局吗?《丈夫》里的世界的确绝然不同,这里有蛮横的醉兵踢船辱骂,张口闭口炫耀钱;还有好色的巡官假借“考察”之名来嫖娼。对比《边城》,水手、妓女互相咬着嘴唇、颈脖发誓,“约好了‘分手后各人皆不许胡闹,四十天或五十天,在船上浮着的那一个,同留在岸上的这一个,便皆呆着打发这一堆日子,尽把自己的心紧紧缚定远远的一个人”,这种情形在《丈夫》里是不曾有的。两篇小说,两种文化背景。“丈夫”来自湘西乡下,家乡应当有着与《边城》相同或相近的文化背景。他骤然来到大不相同的文化背景中,感到无法适应。这样的不适应,在他初见水保时就已经表现了出来。水保的装扮让他感到更加拘谨。虽然在交谈中,水保的随和渐渐解除了他的拘谨,但水保临走时丢下了的那句话:“告她晚上不要接客,我要来”使他产生了疑惑和误解。及至看到后来发生的那些丑事,更坚定了他回到乡下的决心。可见这篇小说的旨趣,与其说是表现“丈夫”某方面的“觉醒”,不如说是展示湘西与都市文化的冲突和差异,并对后者浓厚的商业化色彩及其由此形成的堕落风气作出批判。
提及“丈夫”这样的湘西蒙昧人格,读者最易联想到《萧萧》中的主人公萧萧。这篇小说也有着强烈的文化冲突背景。凌宇先生曾指出:“在沈从文创作品格中,鲜明地体现着湘西苗族文化、汉族文化和西方文化三条文化线索的交织”。[3]《萧萧》这篇小说正反映了这三条文化线索之间的冲突:一是围绕对“女学生”的议论,反映湘西文化与现代城市文化间的冲突,这大体上是凌宇所谓“中西文化的撞击”在湘西地区的折射。只是这与《丈夫》不同,沈从文在这篇小说中不是侧重于对都市文化的批判,而是相反,透过萧萧婆家人的无知,鞭笞了国民的保守性格。二是围绕对萧萧的处罚,反映凌宇所谓苗汉文化撞击的现象。萧萧怀上了长工花狗大的孩子,将受到沉潭或是发卖的处罚。然而,萧萧婆家人对此一开始就是犹豫、不坚决的。他们手足无措,“各按本分乱下去”;及至等待萧萧发卖的日子里,也是“大家全莫名其妙,只是照规矩象逼到要这样做,不得不做”;萧萧生下儿子后,婆家人更放弃了任何处罚。在湘西文化背景中,作为中国主流文化的汉族儒家文化是一种侵入现象,却往往停留在形式表面,而没有彻底同化到深层,这才有了“照规矩”“不得不做”的矛盾现象。正因为在一个地区存在多种文化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人们才容易产生困惑,在突发事件面前不知采取怎样的文化立场,从而无所适从,手足无措。可以想象,这种矛盾的情形在中原汉族地区是很难发生的。
从这样的视角看《丈夫》,主人公来到大不相同的文化背景中,情绪烦躁不安,急于逃离,就不难理解了。如果抹去小说中的的文化冲突背景,“丈夫”的性格特征就无从把握,一个憨厚本分的山民,一个“年青简单的人”就可能被指认为扭曲了人性的贪婪市侩,就有了所谓的“觉醒”一说。
参考文献:
[1]袁可嘉.读杜运燮诗精选一百首[J].文学评论1998,(3).
[2]吴福辉.人性的升沉.赵园编写,见《沈从文名作欣赏》[M].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06).
[3]凌宇.从苗汉文化和中西文化的撞击看沈从文[J].文艺研究1986,(2).
Interpretation of four famous literary works
Suo Xiaohai
(Institute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Jianghan University,Wuhan Hubei 430056)
Abstract: Many famous literary works need re-interpretation. Du Yunxie's poem Mountain is not eulogizing to striving in general sense but show existent state of the pursuer of spirit. Lin Yutang's prose Extol Bandits good at using irony and this paper hide five logical relation. Lu Hsun's novel Death Mourning criticize degradation ‘five-minute enthusiasmof the young at that time. Shen Congwen's novel Husband reveal the cultural conflict and difference of Western Hunan and the Urbans.
Key words: the text interpretation; Mountain ; Extol Bandits; Death Mourning; Husb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