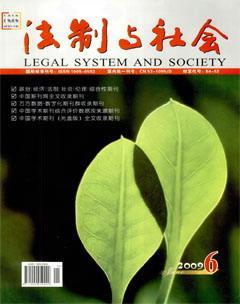从舆论监督与民意裁决看司法公信力
潘舒雨
摘要在民主的法治社会,法官的独立审判权与媒体的舆论监督权都有它的功能和价值。然而掌控社会重大传播资源的新闻媒体以其强大的舆论价值导向极易造成“新闻审判”,给司法审判带来巨大的压力。寻求法官的独立审判权与媒体舆论监督权之间的平衡应当着眼于司法的公正性与权威性,以提升司法公信力,促进社会立法完善和司法公正。即使在民主日趋完善的社会里,要求司法审判要经得起历史检验和社会评判也并不意味着当时的民意可以左右司法裁判。所谓“国法人情”是以理性的民意推进立法的完善,但绝对不可以民意裁决践踏法律的尊严。
关键词司法独立舆论监督司法公信力民意裁决法律理性
中图分类号:D9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09)06-157-02
一、司法独立与舆论监督
(一)司法独立的含义及其价值分析
我国司法权的独立主要表现为审判权的独立,应当包括法院司法权独立、法官个人独立、司法审级独立。法官的个人独立是指法官的独立审判权,即法官在审理案件时,根据对事实的裁判和对法律的认知,独立自主地对案件作出裁判,不受外界势力左右。
孟德斯鸠曾指出:“法官除了法律,没有别的上司,法官的责任是当法律运用到个别场合时,根据他对法律的诚挚的理解来解释法律……独立的法官既不属于我,也不属于政府。”司法权应独立于立法权和行政权,法官的审判只对法律负责,而不受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的领导或指示;法院的审判活动不受另一法院的干涉,上级法院不能干涉下级法院的具体审判工作,法官审理案件不受各方面意见的影响,按自由心证原则行使职权。
法官独立审判,其根本追求是公正件处理案件,维护司法权威,保障司公信力。公正是司法工作的灵魂和根基,而独立性是公正性的必要条件。
(二)舆论监督的概念及其价值
随着民主观念的深入发展,媒体传播已然成为舆论监督的主要渠道。宪法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其中当然包括新闻媒体。
从价值层面上看,媒体舆论监督表现为表达自由的理念,也是现代法治社会公民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体现了社会对新闻媒体的尊重和满足。表达自由使社会自治和依法而治成为可能。民主政治就是人民把支配范围有限的公权力委托给他们选出的代表,但保留监督公权力行使的自由,包括通过新闻、网络等媒体的监督。表达自由也被誉为社会秩序的“安全阀”。
二、法官的独立审判权、媒体的舆论监督权之间的关系
(一)共同的价值追求
西方思想家总是从对新闻自由的倡扬以及对压抑新闻自由的专制制度的批判中寻找支持媒体监督的理论根据。受此影响,在对中国现实中媒体与司法关系的分析时,媒体被当作与基本政治制度相对抗的大众立场的代表者,而司法又总是被看作基本政治制度的替身或代表。然而民众对这种政治基础主观、随意并且很不稳定的认识很容易导致媒体舆论监督权行使上的重大偏误。在现代社会政治结构中,媒体与司法是具有共同使命的、共同维系社会秩序的两个基本要素。法官独立审判权与媒体舆论监督权具有的共同价值追求就在于保障审判的公正性。在现代民主社会中,舆论监督和独立审判这两种基本价值都以社会成员的权益和福利为终极目的,都以保证审判的公正性为行动准则和目标。
(二)天然的排斥
法官裁判以法律为依据;而相对于理性的法律判断,媒体更多地会倾向于道德化运作,甚至以道德标准去责难司法机关依据法律所作出的理性行为,从而把道德与法律的内在矛盾具体转化为媒体与法官之间的现实冲突。张仲秋先生在《中西法律比较研究》中曾指出:“中国法律道德化与道德法律化这种双向运动,使法律失去了本性,也失去了成长的力量”。中国长时间道德统治的传统使我们不能轻视道德的力量对法律的挤压,虽然正统的道德与法律往往是一致的,但是脱离法律的道德化评判,对中国的法治显然是弊大于利。
(三)二者的平衡
法官的独立审判权与媒体舆论监督权的对抗性与统一性应当平衡于司法的公正性与权威性,提升司法公信力。
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媒体舆论监督对法官保持自身廉洁公正起着保障作用;同时,媒体也能够提供充分的信息,以便法官全面深入地了解事实。
媒体也应当秉持客观公正原则对对个案进行客观全面地报道与评论,而不应带有片面性、倾向性,更不能主观臆断,妄下结论。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客观性是监督的基础,公正性是监督的出发点和归宿,失去了客观性就失去了公正,所谓监督也就不存在了。
笔者认为,当二者发生冲突时,舆论监督应当让位于法官独立审判这一更高的社会利益,以保证司法的稳定性、权威性,提升司法公信力,稳定司法秩序,保障公正裁判。
三、许霆案:从司法公信力与民意裁决看中国司法现状
(一)司法公信力不容置疑
法院判定盗窃金融机构罪无可厚非。盗窃罪的成立关键两个要件:非法占有的故意以及秘密窃取。第一,在第一次柜员机发生错误时,许霆主观上尚未产生非法占有的故意,可以认为这是民事上的不当得利行为,但是在后来的170多次行为当中,他非法占有的故意已经非常明显。第二,许霆辩解说“人不知道,机器知道”,不管是出于无知还是因为侥幸,他的所谓“替银行保管”的行为都以他认为别人不知道为前提;而刑法中所谓秘密窃取也只要求行为人主观上以为别人不知,却不要求别人事实上不知,因为法律需要惩罚主观恶性。
一直到二审结束,此案一直都是舆论非议的焦点。法院的改判也印证了部分学者的预测:维持盗窃罪的判决,在量刑上作减轻处理,报请最高法院核准。《刑法》第63条第2款:“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的案件,必须经最高人民法院的核准,其判决、裁定才能发生法律效力并交付执行。”我们有理由提出质疑:究竟是一审法院有直接减轻刑罚的权力,然后在经历两审终审之后报请最高法院核准,还是在一审法院做出减轻刑罚的裁决之前,事先请示最高法院。这显然属于有待解决的程序问题。人们质疑:在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广州中院是否在此前向最高法院进行了“内部请示”,改判五年的结果是否出自最高法院的授意。
从无期改判5年有期,当然是司法对民意的善意回应,但从反响来看效果似乎不佳,反倒有儿戏之感,以至于引来了阵阵唏嘘和嘲讽,嘲笑前后判决的巨大反差,甚至断言司法在许霆案两次审判过程中被某种力量所玩弄。笔者认为,此案对司法公信力的伤害源于立法和司法两个方面。第一,此案情节相对于普通的盗窃行为确实轻微许多,也判无期重刑。立法机关确实不应该以“社会发展,经济生活复杂化”为借口为立法的严重滞后开脱,因为此案在世界、在中国已远远不是首例。第二,不论是法律权威的树立者、维护者还是服从者,都不愿看到司法屈从于舆论,以一个荒唐的理由推翻一个合法的判决。
有些人开始探究媒体的责任,认为媒体过度干预了司法行为,影响案件判决的公正性与独立性。但是,在面对媒体狂轰滥炸的意见时,司法究竟该如何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如何在以媒体为代表的民意中求得法律价值和社会舆论之间的平衡?更何况,在一个媒体声音多元化的时代,也没有完全一致的所谓“社会舆论”,“特案特判”固然具有不可质疑的法律价值和逻辑正义,但媒体只要足够关注,法院就“特案特判”,就无法逃脱司法屈于舆论压力的嫌疑。但是司法必须依其自身规律行事,并以其独立的品格坚守法律的底线。判决应尊重民意,却不可屈从于民意。许霆案重审,法院自然可以依法改判,只是法院还应在裁判文书中,明确告诉民众之所以如此定罪与轻判的理由。
所谓公正审判就是法官在作出裁判时,应该处于公正无偏的立场,不得受到法庭外的力量或信息或在审判中未予承认的证据的影响。因此,法官只有独立地坚持法律特有的理性才能保障司法树立司法的权威,保障司法的公信力。
(二)舆论监督的界限
法官要求获得真正独立,除了法院本身内部需要建构一种自由开放的体制外,同样需要外部平和的舆论环境,但这种环境必须是客观的、公正的。
英国法律规定:“对正在进行中的审判活动进行任何形式的误导或发表有失公正的言论都构成藐视法庭罪。英国法官可以毫不犹豫地对未决诉讼进行评论的传媒给予处罚。”美国虽标榜新闻自由,但法院如果认为传媒获得的有关案件审理的情报可能妨害司法公正,则可以采取事前限制,禁止传媒发表他们已获得了新闻。中国媒体的舆论监督的发展步伐不断加快,这是好事,但同时也要严格遵守言论自由的道德限制和法律限制。所谓法律限制,就是指尽快出台《新闻法》对规制媒体的舆论监督至关重要。而所谓道德限制就是应当明确新闻界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不可随意利用民愤大肆炒作甚至沦为民意的泄愤工具。
涉及到司法领域,舆论监督应当仅限于程序正义的实现,可以包括事实认定以及审判程序,而法对于法律结果正义的实现,只能事后监督,以避干扰司法之嫌,保证司法公正审判,维护司法权威。应该说,只要程序正义得到遵循,实体法律适用正确,就没有改判的理由,即使必须改判,也不应该是迫于舆论压力。如果确实认为适用该项法律违背了罪刑相适应原则,也是立法机关应该考虑的问题,而媒体绝对不应当以立法的滞后性来责难司法的合法性,甚至利用民意左右司法判决。但是,舆论监督仍然可以通过报道和评论促进立法的完善。
在这里,就媒体监督的作用与界限,可以将许霆案与孙志刚案加以比较。两案有重大区别:媒体关注孙志刚案时从一开始就把矛头对准了不合理的收容制度,而不是简单地追究打死孙志刚者的责任问题。因此,媒体在对孙案穷追猛打的过程中始终没有偏离废除收容制度的努力,而且最终的结果就是对收容制度的废除。从制度上解决问题正是媒体在孙案中体现出来的睿智与正义。而许霆案的争议则对最核心的立法滞后问题却讨论较少。如果立法层面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许霆案轻判了,昆明同类案件是否应该重审重判?通过媒体对司法判决结果进行施压,很难说不是形成了一个恶劣的先例,甚至有人说,媒体在许霆案中表现出来的一边倒式的起哄很难说不带着挟持民意的阴谋,左右司法的狂妄。
(三)荒唐的民意裁决
也有人大代表这样指出:“案子改判说明,我国的法律不但是严肃的、有原则的,同时也是有人情味的,为许霆这样的当事人提供了程序上翻案的无限可能。而其最终得以改判,也正说明法律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意志。”
民意对法律批判的焦点在于法律本身没有体现时代的进步,那么法律的滞后性就决定了它永远不可能是胜者。而不管法律科学与否,仅仅因为舆论的压力,在不先行修改法律的前提下,以“民意”推翻合法的判决是对法律的羞辱。且不论法院是否是为了平息民愤而轻判,起码我们看到有无数个脑袋在替法官进行审判,这些脑袋戴着民意的帽子让法官左右为难。
在许霆案的幕后,所谓“民意”在很大程度上是沸腾的民怨,甚至已经脱离了基本的道德底线。当从无期减轻为五年的时候,许霆在获得更长一段时间自由的同时却使自己的人格先行破产。而即使那些现在为许霆案奔走的人们,又有几个在生活中能真正信任许霆,给许霆人格上一点点的尊重呢?早在汉代,司法就将盗窃定义为“不告而取,取非其物谓之偷”。这是道德化了的法律,也是道德的底线。当“民意”极力为许霆的行为辩解时,我们看到了道德的缺失浮出水面,而我们迟早要为这缺失买单。有人举西方司法的例子,却忽略了作为中华民族价值观的根基传统道德。肖扬院长说“司法裁判要经得起历史检验和社会评判”,但突破了道德底线的民意本身就难以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更无资格检验和评判司法的理性。
所谓“国法人情”是以理性民意推进立法的完善,但不能以民意裁决践踏法律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