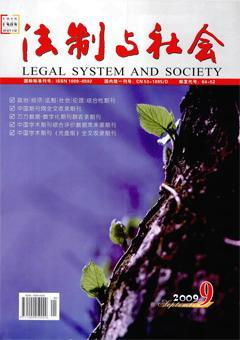论自然法
宋联洪
现代西方社会法学家弗兰克视法律的“稳定性”与“确定性”为“基本法律神话”豍,认为这只不过是幼儿对父母依赖心理的残存表现而已。与此类似,将自然法看成正义之永恒表达,同样是不切实际之幻想,是虚构的法之“基本神话”。正如美国大法官霍姆斯所说:“所有人心里都有一种对理论知识的要求,这种要求是如此的强烈,以至无法用别的方法获得,就只好在醉梦中寻找。依愚之见,这种要求就在于哲学家想证明真理为绝对的努力背后,存在于法律家对普遍有效的准则的追求背后,该普遍有效的准则名之为自然法”。
一、自然法的起源
哲学,作为法学之母,根据人们的不同认知方式:惊异、怀疑或震撼(雅斯贝尔斯语),可以分为本体论、主观论和存在性哲学。自然法源于柏拉图为代表的客观本体论——惊诧于世界:存在者存在,而无不存在,迫使人们去探求、去发出疑问。存在(之现象)是不可把握的,只有当人尊重蕴含于存在中之规律时,存在(自然)才听命于人。存在(自然)本身就包含着秩序和建构,一种事物和关系的“自然”秩序就显现其中;同理,在人生活的共同体中,处处原地就有法。“惟有从本性上,把法理解成一种外在于我们的思维和意志的既存之物,唯有不否认法之存在属性,才可能有真正的自然法学”。豏“因而,本体论哲学当红之日,就是自然法风光之时。自然法之花只是盛开在基本的存在信赖之沃士中”。豐唯有信赖自己,信赖世界的传人,才会信赖自然,信赖自然法。可见,自然法作为人类秩序观念之表达,公正之准则,古已有之!
相反,以普罗泰戈拉为代表的主观认识论——怀疑于世界:我们不能确定,感觉是否欺骗了我们,思维是否陷入了矛盾,行动是否误入歧途?所以,我们所感和所知的一切,切不可自以为是,必须先被质疑之!正如笛卡尔提出:怀疑一切可怀疑之事,康德也要求剔除“形而上学”,原因就在于此。歌德曾批评道,“哲学不再顾及客体”,“我们现在处于一种倒退时期,因为它是主观的。”人们的目光不再对准存在之事物,而是思维之主体;不再从信赖角度去理解存在,而在沉溺于永恒的怀疑之中——先在的秩序不再重要,首要的是“法的知识”(施塔姆勒语),一个由立法者绝对权力创立的(实证主义)法律的总称而己,而自然法被视为虚无缥缈的“理论产品”。豑由此,实证主义法学开始与自然法分道扬镳!
如果说自然法与实证主义法学还是在用理性,虽然远非全面,来思考世界的话;那么存在性哲学就是在用情绪来抗争!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性哲学——震撼于世界:人生活在责任、疾病、死亡、战争、瘟疫与毁灭等边缘状态之中,发现自身软弱无力,以致于如此的渺小;但“困境教人思考”:或者视而不见,或者凛然正视之。“存在性哲学就是呼吁人们去抗拒那种溺入只是苦苦挣扎这种非本真的冲动,在此种抗拒中自己决定自己的前途命运”,豒实现自决,实现自我。但对“世俗法不可避免的抗拒之经历,以及用绝对价值衡量所带来的法之可疑性”,豓结果使法走上非确定性和任意性之路。
可见,自然法的产生决非空穴来风,其总是相伴于人们在闲暇时对世界之反思:现象世界与理念世界孰优孰劣?偏重于前者或后者,或超越二者之争!
二、自然法的缺陷
由上可知,在历史长河中,自然法并不是始终如一地一枝独秀,总是处于与其他法学流派的争斗中,但由于它存在于远离现实的彼岸,看不见,摸不着,而被披上神秘的面纱,被视为真、善、美的王国与各种思想的理想避难所。然而,正如它批判实证主义者马克斯·韦伯的价值无涉论与凯尔森的纯粹法学一般,此处的优点被对手讥为致命的缺点:首先,根本不存在自然法所声称的绝对的、超时代之内容。其次,根据康德“纯粹”知识理论,一种其能认识事物的形式,不是出自知性,而是源于经验的内容,只是后天的东西,而且也不是纯粹的。
为拯救自然法,历史主义法学者施塔姆勒不得已为之,提出所谓“可变的自然法”豔。这意味着,自然法是一种历史的范畴。无论是古时亚里士多德的“城邦生活”和斯多葛派的“自然生活”,还是中古时西塞罗的“理性生活”和奥古斯丁的“上帝生活”,都反映出自然法的这种历史性、不确定性和虚妄性。所以,菲尼斯说,自然法不能对人们精神之失败或行动之暴虐负责,更不能视之为进步的“同义语”。豖因为“在它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它大部分时间所发挥的都只限于一种渐进的乃至保守的功能”。(登特列夫语)
那么,为什么革命之志士、保守之绅士却都对自然法都情有独钟呢?答曰:此乃人性之“偏好”——在决意行动之时,总得苦苦追寻一个最能说明事物之性质,最能证明自己所主张的正当性之根源、之准则。当然,此模式最好能不证自明、又令人信服,这样一来,具有公理性的自然法自然就“人见人爱”了。它以演绎推理为基本方法,但推理的成立须以前提正确为必要条件,而要证明前提的正确,又必须证明另一前提的正确,不得己,一个“应当”来自另一个“应当”,豗这样就会陷入无穷回归的荒谬逻辑!为此,只好假定真理的先验自在,不证自明,但这样,“又使结论的科学性归于虚无”,豘正是在此,自然法被冤家对头——以经验为内容的实证主义法学派批得“伤痕累累”。
此外,以演绎推导出的自然法,仅表现为极其少有而又高度抽象的原则,如“爱你邻人”、“切勿伤人”等,表面看来,越是抽象,越是灵活,以达到不变应万变的目的;实际则是,先验既定下根基不稳的缘故。因为它将主体与客体相分立、理念与世界相剥离,随心所欲地从理论上、逻辑中予以证实,直抵自我先在设定的目标而无被“直观”之危险。所以,不但进步的孟德斯鸠鼓吹自然法之自由观念,就连反动的希特勒也大谈特谈自然法之道德良心。正如伊诺曼描述道:“官方的国家社会主义法律思想体系,尽管在内容上与传统的自然法体系完全不同,但在方法上比实证主义更接近自然法思想”。豙
显然,自然法作为绝对真理之化身表明,不但人们“追求直理是危险”的(福柯语):对于个人,可能像千万个布鲁诺那样,招致杀身之祸;对于群体,可能像“抽象”的第三帝国那样,招致暴政,更可能是徒劳的拉德布鲁赫试图超越自然法与实证主义之争,提出相对主义的“二元论”,兼采纯粹性的形式和有重大表现力的内容,然而,“四不像”迫使他过早地“缴枪投降”豛了。正如澳大利亚法学家斯通评论综合法学派人物霍尔:“这种目的尽管在思想上可取,但也许抱负过大”。豜最终,人们无奈地又回到自然法与实证主义的老路中兜圈子。可见,自然法决不是贞洁的“圣女”,而是一位善变的“双面人”而已,其是天使,还是恶魔,取决于所用之意欲。真乃:蔺相如,司马相如,名相如,实不相如也!豝
三、自然法的崩溃
前述表明,自然法乃是人们对溺于其中之世界的反思:变动不居的现象世界之后隐藏着一个理念(本质)世界。所以,自然法是建立在信赖基础之上的反思,这种反思的对象——抽象之理念经过了一个自我否定的过程,直抵其“本真”状态。在古希腊,赫拉克利特称其为逻各斯,其因为真而表现为善,故苏格拉底有“知识就是美德”之论;而亚里士多德的“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的门前告示,更是将追求事物的知识即真作为交往的准则,成为判断他人是否为善的标准。这种追求事物的真即为善的观念,经过斯多葛亚学派与自然和谐的生活即为善的观点,再发展到中世纪上帝作为至真、至善、至美的全能而发展到极致。这一时期的自然法也就是逻各斯的外化,并非来自某个人的意志与权威,而是来自于自然规律,虽然,这时的自然法要屈尊于神的意志。
至此,当自然法如日中天时,休谟不经意地问道:事物的知识为一种真,即一种事实,而善为社会的意义,即价值,怎么能从事实必然推导出价值呢?这看似轻松的致命一问,使作为真、善的统一载体的自然法轰然倒地。如果说,休谟从逻辑上对自然法(理性)之作为真善的统一提出了疑问;那么,卢梭则从历史的角度对“知识就是美德”进行了驳斥:“人生而自由,但无不在枷锁中”,暗含着“无知即美德”。面对自然法无可奈何的分裂,康德试图将事实和价值在美学领域统一起来;但同时,在理论上将事实(纯粹理性)和价值(实践理性)截然分开。叔本华不满意康德的自在之物与纯粹理性的划分,将其分别改造为意志世界与表象世界。意志是利己的,但又因常常得不到满足而产生“人生苦短”的厌倦。尼采却意气风发,抨击道:生命虽短,人类却繁衍不断。意志,即生存,生存即斗争、强权,从而,发展了自己的权力意志论;而德福勒和福柯接过尼采的接力棒,——权力意志论,分别提出了自己的意欲论与权力论,前者认为欲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而后者认为权力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它不但在否定,也在肯定。这些思想在法律上最终表现为批判法学与后来的后现代法学。
另一方面,费希特对康德的“自在之物”进行了批判,认为,“自我”才是一切实在的源泉。人的认识和实践来源于自我,人的主观世界与客世界都由“自我”创造。他用“自我”取代了康德的自在之物,走向唯意志论和唯我论。如果说,叔本华从费希特手里拿走了“唯意志论”,那么,黑格尔则抽取了唯我论,将这一主观唯心主义改造成客观唯心主义——绝对精神,认为它是所有事物和整个世界的本源和基础,其发展过程分为逻辑、自然、精神三阶段;在精神阶段,绝对精神又分为主观精神,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其中客观精神的发展又经历抽象法、道德、伦理三阶段。最后,他用绝对精神再次将分裂的真与善统一起来,认为法律无非是依据自由的普遍法则使各个人独立意去相互协调的总和。依此,法律必须以客观的必然即自由的普遍法则为内容,同时法律又体现着人对外部自由普遍法则的理解和运用。因此,法律渗透着人的理性,先前的自然法并非遥不可及!
面对已经不再神秘的自然法,马克思将黑格尔颠倒的绝对理念再次从天国拽回人间,以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为基础,把法的规律性与意志性结合起来,使得自然法之真面目昭然天下:自然法既是被给定的,又是自我创设的;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最终,满目疮痍的自然法不得不实行范式的转换:由“独白式”转向“对话式”!姑且不论对错,如果是这样,自然法还是以前的自然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