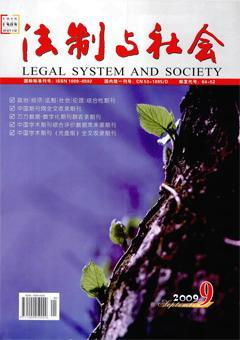简评拉德布鲁赫“价值相对主义”法哲学思想
张 伟
曾经热议一时的“许霆案”早已尘埃落定,作为法律人应该继续关注本案所带给我们在学术研究上的价值和遗留下来的专业问题,从对问题的解决方式中总结并寻找有价值的规律,并把这些规律运用于解决以后出现的类似问题上。我想,这才是比较科学的也是学术研究应秉持的研究路径,也才会避免我们的学术研究出现纸上谈兵和流于形式的尴尬局面。“许霆案”的出现确实有一定的偶然性,正如很多学者所说,它仅代表了一种个案。但不能否认的是,许案的出现确实曾引起了我们整个社会(学界内和学界外)对法律问题的高度关注和讨论,不仅给我们的法律实务工作者们着实出了一道难题,也为我们的法学家们带来了更深层次的学术性思考及不同学术间的思想碰撞和摩擦。对此,笔者想以拉德布鲁赫的的相对实证主义理论为平台,试图从中找到对“许霆案”这类疑难案件相对合理处理机制的理论依据。
“相对主义”思想可以说是拉德布鲁赫整个思想的精髓,也可以说是他超越以往思想的另辟蹊径之处,这在他早期最著名的两部作品《法学导论》和《法哲学》中都得到了清晰展现。在其弟子考夫曼著的《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中也有类似的描述,“在自然法和和法实证主义之间寻求第三条道路,或超越二者,是当今世界范围内法哲学的主题。第一个克服了自然法和法实证主义之间毫无希望的立场之争的是古斯塔夫·拉杜布鲁赫。”①他在1932年版的《法哲学》中将“法概念”界定为是“一个文化概念”,“也就是说,一个关涉价值的现实的概念,它具有为价值服务的意思。法就是具有为法价值、法理念服务这个意思的现实。因此,法概念是指向法理念的。”在其《法学导论》中,拉杜布鲁赫这样描述道“法律的效力只能在毫不脱离民众生活实际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否则民众生活就会拒绝服从它;一项法律只有在其实际运用于大多数情况下时都指望切实可行时,才会产生效力。”② 在笔者看来,这些思想都体现了拉德布鲁赫的“价值相对主义”。拉德布鲁赫的法概念从一开始就显露出两个特性。首先,它不是实证主义的。实证主义法概念的意思是说:法是只要形式上正确发布,而不管其内容善恶都是法。拉德布鲁赫反其道强调,惟有那些与正义相连,并朝向正义的方向,方具有法的品质。③ 其次,拉德布鲁赫的法概念也不是自然法意义上的。因为他看来,“正确的法”不等同于绝对的法价值;自在之价值只属于精神世界,不归现实世界。在《法学导论中》,拉德布鲁赫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描述道“法律将只构成社会现实的上层建筑,只有在道德领域,应然才完全不依赖于现实。”因此按照拉德布鲁赫的看法,现实中所存在的只有“近似的”正确法。
之所以把拉德布鲁赫的法哲学思想称为“价值相对主义”,这是相对于“价值绝对主义”而言的。在法哲学领域,“价值绝对主义”主要体现在自然法和经典的法实证主义思想体系中,因为这两种思想各自均端出了一个“封闭的体系”,正如坚定不移的法实证主义者必定偏爱“主观的解释理论”④,强调法官(和其他的公正评判者)必须遵守体现在法律中的当下立法者的意志。而拉德布鲁赫却是以“客观的解释理论”而著称的,根据客观解释理论,一个公正的评判不仅仅取决于过去的立法者事实上是如何想的,更有赖于今天的立法者以合理的方式来定夺特定情形下的法律目的是什么。据此,我们不难看出,存在于拉德布鲁赫法哲学思想中的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是价值相对的。当然,这也正是被一些批评者所指责的,认为拉德布鲁赫的法哲学没有自成一体的独立的体系,其思想过于中庸,且有“墙头草”之嫌,缺乏一种科学研究的精神,因而是不可取的。面对这些批判质疑的声音,笔者不想对此作过多评价,而只想对拉德布鲁赫法哲学的思想背景和其内容精髓作一个简单厘清,让人们客观独立的去判断其思想是否具有一定的价值,特别是对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是否有所脾益。
拉德布鲁赫的法哲学属于20世纪的法学思想,它是建立在对18世纪的自然法思想和19世纪的法实证主义思想的更新认识之基础上的。用考夫曼的话说,即是对自然法和法实证主义的超越。考夫曼在其著作中这样论述道“只要人们坚持要么选择自然法,要么选择实证主义,不考虑第三者,就不可能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⑤不难看出,20世纪的法学看到了绝对的自然法和绝对的实证主义的弊端 ,即自然法的不确定性和实证主义的僵化性。这也是为什么18世纪盛极一时的自然法,到了19世纪却被打入冷宫,而被法实证主义长期占据统治地位;但进入20世纪后,法实证主义也同样面临质疑和挑战,因其注重强调的“形式逻辑”不能与新时代的社会发展完美契合,不能成功实现其所宣誓的“法之为社会发展服务”的功能。同时,当面临新时代出现的许多新的法律问题时,实证主义却显得一筹莫展。这从哈特和德沃金的世纪论战中可以得到证实;从哈特后期向柔性(包容性)实证主义思想的转向的实例中亦可得到诠释。在笔者看来,20世纪的法哲学,无不包含着“价值相对主义”的思想,也可以说是运用了一种辩证的思维方式。拉德布鲁赫在其《法学导论》中写道:“20世纪的法学似乎想重新接受18世纪的传统。当然,我们在这期间学会了更多的谦虚,首先是从历史法学派那里,尔后又从唯物主义历史观那里。”⑥ 从这里,我们大概可以对拉德布鲁赫“相对主义”理论的思想背景窥见一斑。拉德布鲁赫早期的法哲学思想可归称为“相对实证主义”是有一定理论依据的。首先,拉德布鲁赫追随康德的思想,始终坚持二元方法论,强调实然与应然,事实与价值的区分。他批判自然法的不确定性,认为法的效力从来都是源于“形式”,而非“内容”;“法律的首要使命是法律安全,即安宁。”⑦拉德布鲁赫进一步论述道:“如今(20世纪),人们普遍承认除了‘制定法以外,并不存在实在法。然而这种制定法应满足它的天职,即通过一种权威的绝对命令去解决相互对立的法律观冲突。”⑧按照拉德布鲁赫的观点,法律之所以成其为法律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1.法律的设置必须服务于一种意志,对每一种与之背道而驰的法律观,都可能执行这种意志;2.社会或国家的每项个别法律命令,只在它不“纯粹停留在纸上”时才能被视为“有效”的法律;3.一切由有法律设置资格的意志所设置和执行的法律,方是有效的法律。这些主张(特别是法律成其为法律条件的第1和3项)与实证主义纲要中的一些核心的和组织性的命题是契合的。德沃金在其《认真对待权利》里是这样对法律实证主义的关键性信条进行阐述的:“一个社会的法律就是由该社会直接或间接地、为了决定某些行为将受到公共权力的惩罚和强制的目地而使用的一套特殊规则。这些特殊规则,可以由特定的标准,由与其内容无关但是与制定或形成这些规则的系统或方法有关的检验标准,加以确认和区别。”拉德布鲁赫认为“法律的设置必须服务于一种意志”,这里的“意志”实则是法律实证主义强调的“公共权力”。二者共同认识到法律效力的来源是某种“确定的形式”。是法的“形式”,而非法的“内容”,完成了法律的首要使命——安宁。
但值得注意的是,拉德布鲁赫的法哲学与纯粹的法实证主义又是不同的。正如德沃金所言,并非每位实证主义者都对实证主义的核心命题都有着同样的描述。因对实证主义的“分离命题”有不同的理解,即法律和道德是“必然”分离还是“可以”分离,实证主义内部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回答,因此也有了排他性实证主义或称激进的实证主义(以拉兹为代表)和温和型实证主义或称包容性实证主义(以哈特为代表)之分。温和的实证主义者认为,存在着一个可能承认规则施加道德限制于法律内容之上,法的确定可以是道德的一种功能。而排他的实证主义则否认法律系统可以施加道德限制于法律有效性之上,法的确定从来都不应考虑道德因素。拉兹利用他的“渊源理论”强调,法律的内容和存在可以参考它的渊源,但决不能诉诸道德论证。温和的实证主义认为法律概念包含道德考虑这种可能,而排他性实证主义主张法律与道德的严格分离,这是排他性实证主义在英美等国遭受批判的主要原因,也是德沃金和哈特的世纪论战的主要争论点之一。论战的结果使得哈特转向了温和的实证主义这边,从而使得人们把温和的实证主义思想看成是实证主义对现实的某种程度的妥协。在笔者看来,拉德布鲁赫的法哲学思想从一开始就偏向了温和的法实证主义一边,对法律的界定采用了一种“相对主义”或“辩证”的认识观,这与拉德布鲁赫骨子里具有的道德情怀及其所处时代的社会现实都是密不可分的。无论是二战前还是二战后,拉德布鲁赫的思想都始终贯穿着“二律背反的思维方式”(即“亦此亦彼”、“不但-而且”的思维方式)。所以在他看来,正义、安定性与合目的性这三个部分的最高法律价值只不过说明的是同一理念的三个不同作用方向而已。正义与法的安定性、法的安定性与合目的性、合目的性与正义之间的冲突,是所有法律不可消解的现实存在的紧张关系,——人们也可以说,是所有法律的本质上的矛盾。⑨
在许霆案中,我们不难发现:一审法院的司法审判过程体现了“三段论”的传统司法观,即视相关刑法条文为大前提,案件事实为小前提,定罪量刑是结论的司法观。这种司法观要求法官充当“自动售货机”式的裁判者,可以说是经典的实证主义思想之再现,是与排他性实证主义的价值理念相契合的,因为它禁止法官判案时将“道德、社会政策及法的实效”等因素加以考量,而强调严格按“法律” 办事,因此是一种“价值绝对主义”。但事实证明,这种“价值绝对主义”的理念在我们的当代社会几乎没有什么市场了,人们对许霆案一审判决的非难即是一个很好的佐证。而绝大部分人对许霆案二审判决结果的认同,证明“价值相对主义”赢得的胜利,至少证明它在当代中国社会是受人们青睐的,是法治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的中国司法所需要的。笔者以为,在中国目前还不成熟的法治环境下,要妥善解决好这类疑难案件,必须借助于“价值相对主义 ”理论,特别是拉德布鲁赫早期法哲学思想中的“相对实证主义”思想。在这一法哲学思想体系下,首先是强调法的安定性和确定性价值的,肯定形式意义上的法存在的必要性。同时,又不拘泥于法律形式,而是在坚持形式法的基础上追求法的内在价值。正如拉德布鲁赫1932年在其《法哲学》中谈到的:“没有起码的自然法,法哲学就根本不可能:一个实证的法哲学为了其效用恰恰也需要一个超实证的,即自然法的立场。”若能在的司法过程灵活运用这一法理念,我们的社会就不会出现人们所担忧的“从‘法治退回到‘人治的危险”,也不会因此破坏法律应有的威严。而当面对“许霆案”这样的疑难案件时,我们也就不会再出现像许案一审时那样极端、刻板而遭致大多数人非议的做法,使法官能够在司法的过程中实现情与法的融合,从而使人们一致认为的“法为社会服务”的这一功能真正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