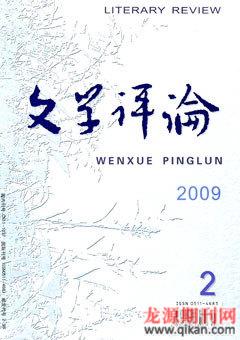从文化研究到文化理论
周 敏
内容提要在全世界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着的文化研究,就其传统和后来的实践看,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对“理论”的忽视,其严重的后果是文化研究对日常生活批判力量的丧失。为了更好地推进文化研究事业,应该适时地发展文化研究的理论维度,这既是学科性的,即从文化研究走向文化理论,但更是理论批判意识的自觉。
如今在全世界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着的文化研究,就其传统和后来的实践看,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对“理论”的忽视或丢弃,其严重的后果是文化研究对日常生活批判力量的丧失。在其新近出版的《理论之后》(Afcer Theory)一书,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伊格尔顿对他所谓的“文化理论”冷嘲热讽,尽显其残酷而优雅的风格:
一切是再明显不过了。研究乳胶(代指性——引注)的文学或肚脐环的政治意涵,是完全按照一句古老且深具智慧的箴言字面上的意义——学习应该是充满乐趣的;就像你可以选择“全麦威士忌的口味比较”或“卧床终日的现象学”作为硕士论文的主题。于是,智识生活与日常生活之间不再有任何罅隙。不用从电视机前离开便能写出你的博士论文是有很多好处的。摇滚乐在过去是那种让你从研究中解脱的娱乐,不过它现在很有可能正是你所研究的对象。智识事务不再局限于象牙塔内,而是属于媒体与购物商场、卧房与妓院的世界。如此一来,智识生活再次回到日常生活;只不过是冒着失去对日常生活进行批判的能力的风险罢了。
虽然他所称的“文化理论”主要是指后现代的法国理论,但实际上这里则更是针对着由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所开创的“文化研究”。它的一个主要特点,一如伊格尔顿上述的描画,就是智识与日常生活的亲密接触,甚至最终可能的融为一体。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提法相接近,这或可叫做“日常生活学术化”吧!对于日常生活,这结果是什么,伊格尔顿没有说。但对于知识或学术,伊格尔顿则明白无误地警告,这将最终导致其对日常生活之批判能力的丧失。
客观地说,伊格尔顿此言真是一个洞见!文化研究的任务,就其传统和后来的实践看,不是批判日常生活,而是捍卫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无论怎样地被“文化工业”所麻痹,但由于它是“生活”,即生命自身的过程,因而便具备天然的合理性、合法性,再者,由于它是以“生活”为基础的对媒介话语的处理,因而就具有天然的免疫力。英国文化研究的一个观点是,它决不相信什么“文化工业”的腐蚀性力量,不相信什么“意识形态”对主体的“询唤”和构造(阿尔都塞)。例如,大卫·莫利就认为,观众不仅仅有自己的语码,那尚是话语的层面,他们更有自己的生活语境,因此其解码就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将媒介话语置于自己的日常语境,如此,生活的力量自会解构媒介话语的强势灌输。如果可以认为“话语”或“意识形态”有时是致幻剂,那么“生活”则就是它们最为彻底的解药。文化研究当然是不想反思日常生活了;相反,它将日常生活本体化、理想化和神圣化,最终的结果就是,它不再能够反思日常生活。这是伊格尔顿的忧虑所在。
文化研究对日常生活的崇拜,来自于雷蒙德·威廉斯对“文化”的新的定义:在其《文化与社会》(1958)中,威廉斯提出“文化”即“全部的生活方式,包括物质的、知识的和精神的”;威廉斯进一步解释说:“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绘,这种生活方式表达某些意义和价值,但不只是经由艺术和学问,而且也通过体制和日常行为。依据这样一个定义,文化分析就是对暗涵和显现于一种特殊生活方式即一种特殊文化之意义和价值的澄清。”威廉斯“文化”定义的创新之处在于将“物质的”生活,将物质性的“体制和日常行为”,纳入“文化”的范畴。尽管他没有将知识的和精神的“文化”剔除出去,但物质性文化的介入,如果不是取消,至少也是削弱了文化的反思功能,最终则会导致其批判功能的丧失。文化不反思,文化只是“无意识”地生活着。而现今广为流行的,“物质文化”概念,其“物质性”除去是指文化的物质形态外,另外一个未被注意的内容就是“无意识”。不是詹明信的“文化无意识”,而是文化,(即)无意识。人们已经接受了这一点:无意识乃是文化最为基本的特征。
作为威廉斯“文化研究”的传承者和发扬光大者,霍尔则基本上是一个理论的“实用主义者”或“机会主义者”。对他来说,理论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否对阐发现实文化问题有用。他曾经向访问他的中国学者表白.理论“其实并不怎么重要,重要的是你们自己的问题。对于理论,你要让它对你发生作用。我的朋友霍米·巴巴说他的工作就是生产理论,而我呢,则是运用理论。我不生产什么理论,就是运用。在霍尔的文化研究中,理论显然只是被降低到“工具—使用”的层次。莫利也不时地嘲笑理论,说理论因其抽象而可以在全球兜售,赚取更多的教席和学生。不过也有人还嫌不够,要求霍尔所领导的“文化研究”应该回归到社会学的本位,肩负起社会学的重任,因为据说霍尔多少还有些“话语转向”或“文本中心”的后现代嫌疑。
文化研究的当前变化可以说愈来愈“非理论化”了。在英国有托尼·本内特的“文化政策”转向,他将文化政策置入文化研究之中,关心文化的“政府性”而非“抵抗性”。本内特是以被称为文化研究的“修正主义者”。的确,他在开放大学接替霍尔社会学教授一职,也可以说象征着英国文化研究一次重大的“修正主义”转向。如果说霍尔是将“理论”转化为“批评”,此时“理论”尚有存留,那么本内特则是将“批评”修正为(实证/科学)“研究”,“理论”终于变得可有可无了。在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好像就从未“理论”过,文化产业研究一直是它的主流,这当然与本内特的言传身教有关(他曾一度执教澳洲)。目前文化研究课程在欧洲高校正呈遍地开花之势,但多是在传媒系科,属于应用型社会科学,很少引起“哲学”学者的关注。上世纪90年代,文化研究抢滩中国,在与文学研究发生过激烈而短暂的交锋后,便旋即毫无争议地转入文学研究者比较陌生的文化产业研究了。文化产业研究者认定,一方面,文化可以经济化——文化不能只是为经济搭台,让经济唱戏,它本身就是经济,就是经济时代的主角;另一方面,经济也要文化化,就是说,经济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效能,通俗地说,为了增加(产品)附加值,也需要“符号化”和“审美化”——这是经济文化化的核心内容。无论本内特们或者中国文化研究者们是否愿意承认,这类对文化的应用性研究,都将导致文化之批判功能的某种程度的沦丧。文化产业研究是没有立场的,如果说有的话,那只有一个,就是替利益张目,而非为“文化”执言。文化研究演变到文化产业研究,它也就完全成了一门实用经济学,它决非“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在其起源处的政治情结至此消释殆尽。如法国理论家波德里亚的符号经济论本来是一种如法兰克福学派那样的社会批判理论,而现在许多中国文化学者却鼓动将它拿来打造产业“品牌”形象。抛弃了批判
理论,文化产业将只会生产“景观”(spectade)或“拟像”(simulacrum,一译“虚像”),一种歪曲真实的虚假形象。君不见,在影视界,我们的前卫编导们不知生产了几多“中国拟像”,不,是“拟像中国”,与真实中国无关的“拟像”。他们不对真实负责。
文化研究在目前中国的另一发展是由各路学者纷纷涌人的所谓“文化批评”,其中情况较为复杂,不可一概而论。但有一点则很明显,就是它对大众传媒如报纸、广播、电视和因特网等等的本体性依赖。文化批评的声音多在这些场所出现。大众媒介是深受市场定律的制约的,发行量、收视率、点击量无时不在折磨着媒介人的神经。在这样的场所,“文化批评”当然不可能有什么独立的作为,它必须跟着市场走,必须吸引眼球,否则就不给上版、上镜、上传。大众媒介似乎有时也欢迎一些“独特”的声音,批评好像还是有自己的空间的,但别忘了,它要你的独特,是用你的独特做卖点!大众媒介时代的文化批评难逃一种伪文化的“大众批评”的厄运。欧洲理论新星齐泽克对文化研究持悲观态度,但他的悲观却不是毫无道理的。他发现,文化研究对权力的反抗正好为权力所需要,因为权力正是通过对差异的承认和整合来建立和稳定自身的。我们不是要整个否定文化批评,它至少还给大众提供了有限的公共空间,我们在此仅仅是想提醒,文化批评,可别忘记了“理论”和“反思”。而对那些只会哗众取宠的、迎合市场的所谓“文化批评家”、所谓“公共知识分子”,他们或贩卖“激进”,或贩卖“保守”,扭捏作态,装疯弄傻,假冒先知,需要声明的是,我们则无须去提醒,因为他们比谁都“清醒”,他们无非是在演戏、“卖”“艺”。
文化研究是“生活本体论”的,而理论则是认识论的,它假定主客体二分模式的永恒性,我们无论如何地“弃智绝圣”,都不能将认识主体取消干净。当我们与自然一体时,我们将不再是能够认识的人,而如果承认我们自己作为人的存在,那么“认识之眼”将是我们最基础的本质。而且,我们知道,“理论”的原义就是“观看”。当年胡塞尔之所以无法改正其“自我”中心主义,非其不为,是逻辑上之不能也。庄子难题“子非鱼”当然是我们人类的局限,但它也给予我们“认识”世界的超越性位置。高举“生活本体论”的文化研究,不管其有意还是无意,将不会形成“观看”因而“批判”生活所要求的距离。
后现代主义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反对认识论,反对主客体二元论的,其实,它反对的是在二元论的认识论中对主体之绝对支配地位的认定,而不是在其根本意义上的认识论。德里达认为意指总是被“延异”,是因为二元论的认识论,能指与所指的对立和张力永远无法克服。就此而言,解构,甚至包括一切后现代的主张,都不是对认识论的取消,而是通过揭示认识论内部的复杂性,而尝试创新认识论。解构是一种新的认识论,一种似乎没有主体或自我的认识论——从前那个主体或自我并不纯粹,总是掺杂着一定的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因而是有局限的、待解构的。
与德里达的解构相反,海德格尔的基础本体论则试图消灭认识论,它将人的一切认识活动都基础化和本体化。认识不再独立于世界,它就是我们在世的生活方式。在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中,“前见”甚至是“偏见”没有什么可怕,它们构成我们的基本存在,是我们理解能够进行的先决条件。没有“前见”,我们无以理解。我们只能在“传统”中理解“传统”。解释学要的是“真理”,反对的是“方法”。在伽达默尔,“方法”是认识论的同义词,而“真理”则是没有“认识”的“传统”。这就是伽达默尔那部名著《真理与方法》要告诉我们的“真理”。但是,当把“理论”、“认识”、“方法”统统本体化之后,这在文化研究,就是“生活化”,那么由谁来执行对日常生活的审视、反思和批判呢?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哲学缺少这个反思的维度,威廉斯和霍尔则是更未曾想到过这个哲学性的问题。而一旦有了这样的问题意识,他们的理论大厦将顷刻间崩塌。
英国文化研究没有“理论”,这是一个明摆着的事实;但在这事实背后则是反思精神的匮乏,是认识论距离的消失。拥抱日常生活,当然不错,因为我们就是日常生活;但这生活从来就不是自在的生活,其中有着多少的文化和观念的沉积呀!换言之,生活从来就是文化的。将文化彻底地生活化,将可能使那些貌似时髦而实质上腐朽、落后、不健康和非理性的文化因素被保护起来,移出我们的批判视野,逍遥于理性的法外。海德格尔与纳粹政府的同流合污不是没有哲学原因的。而真正的唯美主义者就不会如此。唯美主义乃是文化研究所要批判的一种激进的“审美现代性”(如对阿诺德的批评)。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英国文化研究也有向着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方向的努力。英国文化研究本就是英国社会主义者或者左派的社会批判事业。德国著名文化研究学者雷纳·温特教授以威廉斯的著作为例,将英国文化研究当作一种批判理论来理解。他认为:“威廉斯,与1930年代的法兰克福学派或是布尔迪厄十分相像,也提出了一个社会干预性的科学概念,这个概念将学术世界与日常生活联结起来。”但人们不会想到的是,由于对“理论”和“反思”的放弃,其中被重新定义了“文化”的英国文化研究总是呈现出对现存制度的某种妥协。例如20世纪80年代,霍尔号召左派要向右派学习,要从“撒切尔主义”的右派改革中汲取教训。再如,菲斯克对消费社会的游击战理论,莫利关于电视观众对强大媒体的积极接受理论,从另一方面看,其实也是要人们放松对消费和媒介之控制和霸权的警惕和抵抗。他们的潜台词是,我们无需积极地组织抵抗,因为抵抗是天然地发生的。
英国文化研究作为一项学术事业已经在全球展开。在中国,文化研究也有了十几年的历史,而且还在以势不可挡之势向各个学科推进。为了更好地发展文化研究事业,现在,我们必须正视其先天的不足,以及后天的局限。这就是说,我们应当将文化研究从社会学中解放出来,发展其理论的批判性力量,将文化研究作为一种理论,作为一种文化理论。这当然也是一种学科性的要求,但更是一种批判意识的自觉。
作为文化理论的文化研究,将会呈现出一副怎样的面貌?其具体议程是什么?其与现实问题的切点在哪里?这些都是十分复杂的问题。但目前有一点应该毫无疑问,就是结合我国本土的文化理论资源,发展和建构出一种能够回应我们当代现实问题的文化新理论。如此说来,霍尔等“反理论”的宣言在另一方面却也是在昭示我们,理论追求着普遍,然其无往而不在“地方性”之中。地方性的理论,其“普遍性”将不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而是对解决世界共通问题有借鉴,有启发,简言之,有对话的可能。事实上,在全球联结的今天,任何地方问题都是自在地与世界问题相关联。
责任编辑吴子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