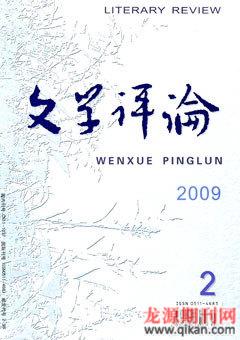宋季两浙路词人结社联咏之风
高利华
内容提要宋元易代之际,两浙路词人结社联咏之风特盛,浙西和浙东虽只一江之隔,但却呈现出不同的风貌。浙西以临安(杭州)为中心,浙东以越州(绍兴)为中心,词人结社之风先形成于浙西,继而向浙东转移。“杭越”不仅仅是地望上的并列,而是标志着词坛创作中心的转移。宋季两浙路词人结社联咏前期以风雅闲适的“西湖词社”创作为标志,其后则以幽深凄婉、咏物见长的“越中词社”为代表。在以地域为创作平台的文学研究中,有必要特别强调宋季“越中词社”实际存在的价值及其对于词史的意义。
一
宋元易代之际,江浙地区活跃着各种各样的词人群体,对此,学术界有各种各样的概括与描述。吴熊和《唐宋词通论》第四章“词派”指出:“宋元之际词坛主要有这样两派”即“文天祥、刘辰翁发扬苏、辛词风,周密、王沂孙、张炎则谨持周、姜衣钵”,刘乃昌认为“南宋末期词”主要分“爱国志士的悲壮词”和“结社唱酬的遗民词”两类;刘扬忠《唐宋词流派史》从创作流派的角度提出了一个新的名称“宋末元初的江西词派”,并且把“宋末元初的江西词派”和“江浙一带的白石派、梦窗派词人”两种不同情调和风格的词派作了一些比较。上述著述从大处人手,从总体上勾勒了宋季词坛的基本面貌,对于把握宋元之际词坛的走向有宏观的指导意义。由于上述著述限于体例,对某一具体的对象研究未及细化,尚留有许多值得探究的空间,因此在此基础上,从地域的角度研究这两类不同词人群体,成为许多研究者进一步深入勾勒还原彼时词坛创作生态环境的有效手段。据此,有的研究者把周密、王沂孙等词人群体称之为“临安词人群”、“临安遗民词人群体”、“杭越词人群”,或径直称之为“浙江词人”,并且指出“宋末元初浙江词坛的审美取向却有着非常明显的地域趋同性”。有的则从宋季词人生活地域的集中,较易于词人互相联络友谊,喜欢结社唱酬的角度,研究他们的结社联唱活动,认为当时确实存在着一个以杨缵、周密等人为中心的“西湖词社”或“西湖吟社”,他们的交游唱和活动十分频繁,社交的痕迹明显,从中可以看出宋元易代之际的某些时代风气、文人心理、生活观念、地域特点、社会审美习俗、文学创作倾向等。
从地域的角度研究宋季词坛的创作现象,从而考究彼时的文坛风气、文人心态和文学创作面貌无疑是可取的,问题是既然是细究彼时的词坛的创作风尚和创作特点,那就有必要进一步还原以地域为平台(中心)的“浙江词人”或者“临安词人群”,“临安遗民词人群体”、“杭越词人群”名称之下词人或词社创作的真实状态。如果要深入考究解剖宋元易代之际词人、词坛创作走向的话,笔者觉得“杭越词人群”的提法比统称“浙江词人”、“临安词人群”较切近实际。但“杭越”不仅仅是地望上的并列,而是标志着词坛创作中心的转移。如果前期是以“西湖词社”为标志,以临安为创作中心的话,那么后期(尤其是人元后)则是以“越中词社”为标志,创作中心则已转移到浙东的越州一带。在以地域为平台的创作群体中有必要特别强调宋季“越中词社”实际存在的价值和越中词坛对于遗民词人创作的实际意义。
众所周知,两浙是宋代经济发达,人文荟萃的先进地区,靖康之变以后,又成为政治文化的中心。然而两浙的东、西从区域史研究的角度说,它们在地理上的差异也是客观存在的。浙东多山地,包括温、处、婺,衢、明、台、越七州,朝廷在越州(绍兴)设置观察使,统领七州,浙西多泽国,包括杭、苏、湖、秀、常、严六州及江阴军、镇江府八地,南宋杭州改称临安是都城,自然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宋季两浙路词人得天时地利之和,结社联咏之风特盛,这是事实。浙西和浙东虽只一江之隔,但文风却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南宋词人结社之风先形成于浙西之杭州、湖州,中心在当时的临安。活跃在宋末词坛的重要群体“西湖吟社”中词人,以西湖为背景,或歌咏节序风物,啸傲山川,或浅斟低唱,吟赏烟霞,以抒情怀。其群体成员如杨缵(紫霞)、周密(革窗)、张枢(寄闲)、李彭老(商隐)等人都是文人雅士、社会名流。他们精通音律,又有文采。杨缵知音识曲,有《作词五要》。张枢乃张鎡之孙、张炎之父,家有园林之胜,周密说他“善音律”是“承平佳公子”,张炎说。先人晓畅音律,有《寄闲集》旁缀音谱”,可见其擅长。周密是临安时期“西湖吟社”的核心人物,与社中人都在师友之间,他们创作观念审美趣味相近,气味相投,交往密切,唱和频繁。临安词人向以江湖雅人自居,哿隋山水。并以优雅的方式生存并创作着。周密《采绿吟》序云:“甲子夏,霞翁(杨缵)会吟社诸友逃暑于西湖之环碧,琴尊笔研,短葛宝柬巾,放舟于荷深柳密间。舞影歌尘,远谢耳目。酒酣,采莲叶,探题赋词。”该群体以临安为中心,优游于湖光山色之间,创作了大量吟咏西湖风光的词作,这是南宋定都临安以来,大量涌现的以西湖为背景词作的一个缩影。流传下来的“西湖十景”的词作大都成于此时。如张矩《应天长》“西湖十景”,陈允平“西湖十咏”词,周密的《木兰花慢》“西湖十景”,真所谓“是古今词家未能道者”。陈允平“西湖十咏”词云:“右十景;先辈寄之歌咏者多矣,誓川周公谨(周密)以所作《木兰花》示予约同赋,因成,时景定癸亥岁也。”景定为宋理宗后期年号。据尹占华先生考证,西湖词社集中活动的时间,当是在宋理宗景定四年癸亥(1263)至度宗咸淳元年乙丑(1265)这三年中。也就是说“西湖十景”词的唱和为词社活动拉开了序幕,他们在开宴梅边,饯春东园,主宾赏音,家姬侑尊,忘情于落花飞絮间,抚尽曲中诸调,极一时之盛。从现存的作品看,临安时期西湖吟社的唱和之作合乐尚雅,词人们往往沉醉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繁华与美丽之中,简直不知今夕何夕。正如周密后来在《武林旧事序》中回忆宝祐、景定间生活“朝歌暮嬉,酣玩岁月,意谓人生正复若此,初不省承平乐事为难遇也”。西湖吟社的词人和词作正是这种背景下形成产生的。周密在南宋后期虽然往来于杭州和湖州之间,但他的创作活动主要是在杭州,他见证了以临安为中心词坛唱和的盛况,也经历了南宋灭亡后西湖吟社今非昔比沉寂。入元以后,临安虽不乏吟事,但词人唱和的中心显然已经向浙东的越州转移。宋季词人结社联吟之风由名人荟萃的京城继而转移到浙东之越州,并不是偶然的现象,这标志着宋季临安时期文人雅士优游士风的终结和越州时期遗民文人咏物联唱之风的开始,宋季元初越中词社唱和带着浓厚的情感色彩和时代苦难的印痕,与I临安时期的唱和性质已大异其趣,而与越地长期积淀的区域性的文化传统却是密切相关的。
二
一般认为越中结社联咏只是西湖吟(词)社或临安词人群的一部分,其实不然。临安时期的西湖吟(词)社的创作结社缘起与创作动机与后来遗民词人在越州的联咏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活动。临安时期的西湖吟(词)社流连光景、宴饮酬唱为主体的风雅韵事,而越中结社联咏是兴寄咏物为主体的唱和活动。结社吟咏的题材和情调自不相同,创
作动机也不一样,地点也由杭州向越州迁移。社中词人虽有重合,但换了人间,换了地域,换了话题,至关重要的是换了结社的心态。彼时西湖山水依旧,而人事全非。面对残山剩水,周密等西湖吟友再也没有歌咏“西湖十景”时的年少锐气和东园饯春分题倚声时的雅兴。他在写给越地词友王沂孙的词中徒叹:“对西风,休赋登楼”,“但梦绕西泠,空江冷月,魂断随潮”。周密后期与越中词人往来频繁,不但参加了越中词人发起的咏物联唱活动,而且还长时间地在越地逗留,创作了《一萼红·登蓬莱阁有感》、《满江红·寄剡中醉兄》、《西江月·怀剡》、《高阳台·寄越中诸友》等一批作品。
地域是词人创作的舞台。周密本齐人,出生在湖州,由于长期寓居杭州,遂成为浙西词社的中坚人物。人元以后他频繁参与浙东词人组织的联咏,融入其中,自然成为越中结社联咏的一分子,词人张炎也复如此。早年张炎以宋贵介公子的身份居临安,与父辈优游吟咏于楼台湖山间,其《木兰花慢》词序有“呈雪川吟社(西湖吟社)诸公”之字样,说明他与西湖吟社有交往。人元后,张炎“无心再续笙歌梦”“怕见飞花,怕听啼鹃”,自称是“写不成书,只寄得相思一点”的“孤雁”,他“东游山阴、四明、天台间”,写下了《台城路·杭友抵越,过鉴曲渔合会饮》、《声声慢·别四明诸友归杭》、《湘月·余载书往来山阴道中》、《忆旧游·登越州蓬莱阁》、《渡江云·山阴久客,一再逢春,回忆西杭,渺然愁思》、《声声慢·寄叶书隐(叔昂室名)》等词作。张炎在浙东一带交游唱和的词人亦大都是越地的同人和隐逸之士,如山阴王沂孙、徐平野、叶叔昂、越僧樵隐、姚江陈文卿等。张炎《木兰花慢·为越僧樵隐赋樵山》:
龟峰深处隐,严壑静,万尘空。任一路白云,山童休扫,却似崆峒。只恐烂柯人到,怕光阴,不与世间同。旋采生枝带叶,微煎石鼎团龙。从容。吟啸百年翁。行乐少扶筇。向镜水传心,柴桑袖手,门掩清风。如何晋人去后,好林泉,都在夕阳中。禅外更无今古,醉归明月千松。
张炎对越僧住处的赞美,表现了词人对理想的隐逸生活的心期。字里行间不难感受到词人的对越地的神往之情。
景炎三年(1278),十二月,元僧盗发六陵,此间张炎正旅居在山阴,与王沂孙、徐平野等唱和。据咏物词专集《乐府补题》提供的资料,周密、王沂孙、张炎、王易简、冯应瑞。唐艺孙、吕同老、李彭老、李居仁、陈恕可、唐珏、赵汝钠、仇远(佚名1人)等14位遗民词人在此期间曾举行过五次大型的集社活动,联吟唱和分咏龙涎香、白莲、莼、蝉、蟹等物,共存词作37首。其中《天香·宛委山房拟赋龙涎香》8首,《水龙吟·浮翠山房拟赋白莲》10首,《摸鱼儿·紫云山房拟赋莼》5首,《齐天乐·余闲书院拟赋蝉》10首,《桂枝香·天柱山房拟赋蟹》4首。词人聚集越地以咏物词的创作来互相酬唱,并将这些在集社活动中的咏物之作汇集为《乐府补题》,其间流露出故国之思、亡国之恨的情感意绪,似与南宋六陵的被掘被盗的政治悲剧相关。《乐府补题》反映了越中遗民词人群体的结社酬唱的基本面貌,其拈题分韵的创作方法,对于我们了解越中词社咏物词创作的形式和文化风尚也大有裨益。
首先,《乐府补题》标明了作品分咏的地点均在越中名流的山房书院。这五题分咏的地点分别是宛委山房、浮翠山房、紫云山房、余闲书院、天柱山房等五处。从现存词作看,越中结社联咏活动的形式是:定点、定词牌、分题咏物唱和的形式,如在宛委山房(陈恕可之居)赋龙涎香,调寄《天香》,同赋者有王沂孙、周密、王易简、冯应瑞、唐艺孙、吕同老、李彭老、无名氏共8人,于紫云山房(吕同老之居)赋莼,调寄《摸鱼儿》,同赋者王易简、唐珏、王沂孙、李彭老、无名氏等5人;浮翠山房(唐艺孙之居)拟赋白莲,调寄《水龙吟》,同赋者周密、王易简,陈恕可、唐珏、吕同老、赵汝钠、李居仁、张炎、王沂孙等9人;又在余闲书院(王英孙之居)拟赋蝉,调寄《齐天乐》,同赋者仇远、唐艺孙、王沂孙、吕同老、王易筒、周密、唐珏、陈恕可等8人;又于天柱山房(王易简之居)赋蟹,调寄《桂枝香》,赋者陈忽可、吕同老、唐艺孙、唐珏4人。五次活动人数不等,最多的聚集9人次,最少的只有4人次。与临安时期西湖吟社社友间规模不大的组合形式比较接近。清代词论家厉鹗为此赋诗;“头白遗民泣不禁,补题风物在山阴。残蝉身世香莼兴,一片冬青冢畔心。”正因为唱和的地点在越州,发起人或组织者在越州,说明当时的越州为词社的生成创设了很好的平台。另外,从周密、张炎的众多词序看,入元之初,他们或寓居在越中,或往来于杭越之间,参与越中词社联吟活动,与越地词人关系密切,他们的词集中一些追忆越中行吟唱和的文字,为我们考察当时越州词坛的盛况提供了有效信息。
其次,《乐府补题》的作者大多是宋元易代时期活跃在词坛上的知名人物,他们的作品完全可以代表那个时期的词坛的整体实力。择其要者,如周密(1232-1308),前期寓居临安,是临安西湖吟社的代表人物,编有《绝妙好词》。在南宋词坛上与吴文英并称为“二窗”,是时往来于杭越间。张炎(1248—1320?),南宋主战名将张俊之后,西湖吟社张枢之子,精通词律,著有《词源》二卷,后人把他与姜夔并称“姜张”,是时寓居山阴。王沂孙,字圣与,号碧山,会稽(绍兴)人,年辈与张炎相仿,有《花外集》,又名《碧山乐府》,存词60余首,是宋末词人中咏物词最多、最工者。清代常州派词人对其推崇备至,把他与周邦彦、辛弃疾、吴文英等称为领袖有宋一代的四家词人。王英孙,会稽人。父为南宋端明殿学士,家资豪富。宋亡之际,好延揽四方名士,林景熙、谢翱、周密、唐珏皆居其家,实为重葬六陵陵骨之主使者,越中词社的实际组织者。唐珏,山阴人。家贫,聚徒授经。宋六陵被盗,曾邀里中少年暗易帝后陵骨葬至兰亭天章寺前,与王沂孙等参加了浮翠山房、紫云山房、余闲书院、天柱山房的词社唱和活动。正是这么一批词名显赫的词人和社会名流活跃在文坛上,他们秉承了浙东文人结社联吟的风气,创作出一大批足以转移文坛风气的咏物词,左右了宋元易代时期词坛走向。
第三,人元以后,浙东文人对元廷的抵触情绪是比较强烈的,特别是在越地发生了元僧杨琏真伽盗发越地六陵事件之后,激起了越中义士的民族义愤。国族沦亡,桑海巨变,皇陵被盗,宗室蒙辱,越中义士如王英孙、唐珏、林景熙、谢翱等冒着生命危险,亲身搜求诸陵遗骨,加以重葬。如唐珏、王英孙亲身经历了护陵义举,本身又是词社中人,他们的情绪和义举不会不对周围的文人,特别是词社中人产生直接的影响。因此,《乐府补题》所咏之物,清代以来许多著名词家都认为《乐府补题》有寄托,并概有所指,有的还作句句比附式诠解。20世纪30年代,夏承焘先生撰《乐府补题考》,发展了清人的观点,他指出:“清代常州词人,好以寄托说词,而往往不厌附会;惟周济词选,疑唐珏赋白莲,为杨琏真伽发越陵而作,则确凿无疑,
予惜其但善发端,犹未详考《乐府补题》全编,援引杂书,为申其说。”认为“补题所赋凡五;日龙涎香、日白莲、日蝉、日莼、日蟹。依周(济)、王(树荣)之说详而推之,太抵龙涎香、莼、蟹以指宋帝,蝉与白莲则托喻后妃。故赋龙涎香屡曰‘骊宫、‘惊蛰……赋莼赋蟹屡曰‘秦宫、‘髯影。”前人的指证也许有过于质实处,所以学术界对清代以来的比兴寄托说一般都持审慎的态度。但《乐府补题》作为一本特定背景下的咏物唱和词集,触物伤怀,采取比兴寄托的手法,抒发亡国哀思、民族情绪应该是情理之中。如王沂孙《齐天乐·蝉》:
一襟余恨宫魂断,年年翠阴庭树。乍咽凉柯,还移暗叶,重把离愁深诉。西窗过雨,怪瑶佩流空,玉筝调柱。镜暗妆残,为谁娇鬓尚如许?铜仙铅泪似洗,叹移盘去远,难贮零露。病翼惊秋,枯形阅世,消得斜阳几度?余音更苦!甚独抱清商,顿成凄楚?漫想薰风,柳丝十万缕。
《齐天乐》不是一首单纯的咏物词,它是有寄托的。当然,这种寄托是指整首词而言,决不是清人端木蜾所理解句句比附式的寄托。碧山的寄托,一方面是由于其寒蝉身世所致,另一方面是由于他表情蕴藉。词中所言完全是词人触物伤情之言,“病翼惊秋,枯形阅世,消得斜阳几度?”作者也有蝉一样的身世,因此,在咏物时,人和蝉台而为一,不可轻分。关于寄托,我非常推崇况周颐的说法:“身世之感通乎性灵,即性灵即寄托,非二物相比附也。”王沂孙在词中,虽然用齐王后尸变为蝉,魏文帝官女莫琼树制蝉鬓“缥缈如蝉”,魏明帝拆迁汉武帝所筑承露盘,“仙人临载,乃潸然泪下”,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并有“忆君清泪如铅水”句等故实,寄慨兴亡之意。其中对蝉凄凉身世、惨痛末路的渲染中流露的幽情苦绪,都写得如此哀婉深切,含蓄而凝重。寄托是性灵的自然流露,碧山借咏物言身世之感,抒国族沦亡之情,感情沉郁,寄托遥深,所以特别真切感人。
当然,越中词人结社联咏唱和的范围远不止咏物,但以《乐府补题》为代表的分题咏物唱和词的大量集中出现,正好说明越中词社存在的客观性,它的产生与存在也是词坛风会转移的必然选择。自北宋以来,咏物词开始有所发展,到了南朱的辛弃疾、姜夔、史达祖,咏物渐成风气。词这种体裁本来就长于表达低徊要眇之情感,咏物让遗民词人们发现了表达情怀新的天地。南宋末年越州宝山的六陵被掘被盗,词人以比兴咏物来抒写亡国之恨、身世之悲,是一种很自然的选择。《乐府补题》所使用的比兴寄托之法,与文学传统和作品样式关系更为密切,比较起来,现实政治的因素或许是次要的。在这个风会转移的过程中,越地遗民词人所建立起来的艺术旨趣和艺术风范最能够代表或凸现彼时的词坛风气,这是我们要注意的,越中词家的联吟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道文学风景。
周济在《介存斋论词杂著》中说:“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歌,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社。”宋季元初越中文人结社联唱其实也是词体文学由传统“应歌”向“应社”转型大背景下的产物。越中遗民词人的交游唱和活动,不同于以往诗人词客的风流雅集,他们的唱和是特殊政治背景下文人的无奈选择,带有易代之交遗民隐逸边缘文化的内涵,是情感抒发的最后支点,因为除此以外他们别无选择。因此,遗民词人之间的结社唱和意识,比起以前来得更为强烈和自觉。赵翼说:“南宋遗民故老,相与唱叹于荒江寂寞之滨,流风余韵,久而弗替,遂成风会。”“越中词社”的实际存在对显示词史的风标走向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
宋季两浙路词人结社联咏有着明显的地缘特点,是地域文化传统和文坛风气使然。
先说地域文化传统。宋元之交浙西的西湖词社和浙东越中词社联咏唱和犹如一波两折,两者关系密切,但因为文化背景不同,又有很大的区别。
浙西之钱塘自唐五代以来城市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吴越国建都于此,特别是宋室南渡建都临安,山川宫阙,衣冠礼乐甲于天下。南宋朝廷偏安一隅,表面上的承平气象,使杭城日益繁盛,朝歌暮嬉,享乐之风遂兴:
(西湖)皆台榭亭阁,花木奇石,影映湖山,兼之贵宅宦舍,列亭馆于木堤;梵刹琳宫,布殿阁于湖山,周围胜景,言之难尽。东坡诗云:“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正谓是也。近者画家称湖山四时景色最奇者有十:曰苏堤春晓、曲院荷风、平湖秋月、断桥残雪、柳浪闻莺、花港观鱼、雷峰夕照、两峰插云、南屏晚钟、三潭映月。春则花柳争妍,夏则荷榴竟放,秋则桂子飘香,冬则梅花破玉,瑞雪飞瑶。四时之景不同,而赏心乐事者亦与之无穷矣。
《梦梁录》中,画家眼中西湖四时景色最奇者之“十景”与西湖词(吟)社中词家笔下的“西湖十景”是何其相似。
周密《武林旧事》之《西湖游幸》也写道:
西湖天下景,朝昏晴雨,四序总宜。杭人亦无时而不游,而春游特盛焉。承平时……大贾豪民,买笑千金,呼卢百万……日糜金钱,靡有纪极。故杭谚有“销金锅儿”之号,此语不为过也。
当时的京城临安确实是一个消费型的城市,文人士大夫生活其间,不可能不受京都文化的影响,以杨缵、周密为中心的西湖词社对西湖的联咏唱和活动,以及文风细腻,词风优雅,正是西湖承平时期文人雅士享乐生活的写照。
浙东多山多丘陵,越地自然环境相对逼仄,自古以来民风强悍、理性、务实,不事浮华。这是越地固有的文化传统,在民风趋向文弱的历史转型之后,这种强悍务实的特点始终以隐性形态积淀在越人后裔的血脉之中,一遇民族生死存亡时期,便会表现出来。建炎四年(1130),当高宗赵构再次返回驻跸越州时,越地臣民纷纷上书上表,呼吁重振河山。高宗受越地民风的感召,应群臣之请,宣布“绍万世之宏林,兴百王之丕绪”的大赦文,意思说要继承先辈创立的福荫,完成国家未竟的功业,并取这两句的首字“绍兴”二字为年号(1131),以示中兴之决心。南宋越地诗人陆游的恢复之志,以及后来浙东学派理性务实的学风,都是对越地传统文化精神的仰承。
在宋末元初这个特殊时期,越中词人的创作从整体上表现为一种移情咏物,表达的沧桑变故的群体行为,他们纷纷结社联咏,在宋季词风衰微之余,抗节遁迹,抒国族之痛,遗民之悲,凄婉之音,都浓缩在以咏物为标志的词作中,这些作品“为两宋词添上个彗星光尾一样的结束”。王沂孙和同时代的周密、仇远、张炎、陈允平、戴表元等都是此际词坛的中坚人物。宋季越中词社唱和带着浓厚的故国之思和时代苦难的烙印,不失为南宋遗民词人最后的心灵守望。
再说文坛风气。两浙路自古就有文人诗酒唱和的风气与文脉,东晋永和兰亭雅集,越地诗酒文会之风由此形成;人唐以后,浙东、浙西一带俨然是文人唱和的一方乐土。如大历年间越州诗人严维、鲍防等发起的以越州州治为中心浙东唱和活动,湖州诗人颜真卿、皎然等组织的浙西湖州联唱等,在诗坛上均产生了开风气的巨大影响。由此而形成的《大历浙东联唱集》、《吴兴集》、《吴越唱和集》、《杭越寄和诗集》等以方镇使府地域为中心的诗歌联唱集、唱和集,说明两浙路文坛联唱的风气已蔚然成风。一逮及两宋,此风从诗坛波及词苑,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晚年起为浙东观察使,知绍兴府,在越中怅望山川,缅怀历史,一口气写下了四首《汉宫春》词,有慷慨纵谈今古的气度,最负盛名的《汉宫春·会稽蓬莱阁观雨》云:
秦望山头,看乱云急雨,倒立江湖。不如云者为雨,雨者云乎。长空万里,被西风、变灭须臾。回首听,月明天籁,人间万窍号呼。谁向若耶溪上,倩美人西去,麋鹿姑苏。至今故国人望,一舸归欤。岁云暮矣,问何不、鼓瑟吹竽。君不问,王亭谢馆,冷烟寒树啼乌。
原唱一出,应和者甚众。张缴《汉宫春》稼轩帅浙东,作秋风亭成,以长短句寄余,欲和久之,李兼善有和词,姜夔作《汉宫春次韵稼轩蓬莱阁》。
两浙路词坛结社联咏的创作风气是地域文化长期积淀一个缩影。以“西湖词社”和“越中词社”为标志的宋季两浙路词人结社唱和活动,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之下的文脉延续。
责任编辑李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