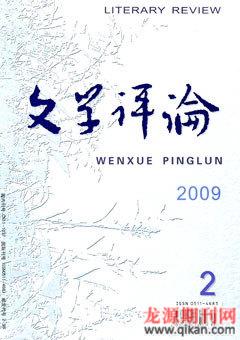《诗纬》与《齐诗》关系考论
王长华 刘 明
内容提要目前学界一般认为《诗纬》源自《齐诗》,在谈到《齐诗》特色时往往直接引用《诗纬》文献来进行论证。本文通过对汉代《齐诗》学与《诗纬》文献进行比较,指出翼奉的《齐诗》学其实是《齐诗》中特立独行的一支,而《诗纬》则是在翼奉《齐诗》学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其在神学道路上较之翼奉《齐诗》学走得更远,几乎堕入了不可知的神秘境界。因此《诗纬》在说解《诗经》方面已经逸出了《齐诗》范围,它与《齐诗》并非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而是两个不同的东西,通行的引《诗纬》论《齐诗》的做法是不正确的。
《诗纬》是与《诗经》相配的汉代纬书之一种,也是汉代《诗经》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诗纬》以天人感应学说为理论基础,认为人的情性与历、律相通,将《诗》三百篇与天干地支相联系,以阴阳灾异观测人事,推知王朝兴衰、君臣关系,以“四始”、“五际”具体推算“革命”、“革政”的关键时期,从而形成了与汉代四家诗不同的解诗特色。但由于其产生的时代文化背景与四家诗大致相同,因此其中有不少说解也难免与四家诗时有相通,尤其是与《齐诗》相通处为多。比如强调以“五际”解诗就是典型一例。这种现象说明《诗纬》与《齐诗》之间的关系理应是密切的。对此,清人陈乔枞在其所著《诗纬集证·自叙》中说:“魏、晋改代,齐学就湮,隋火之余,《诗纬》渐佚。间有存者,或与杂谶比例齐观,学者弃置勿道,书遂尽亡。夫齐学湮而《诗纬》存,则《齐诗》虽亡,而犹未尽泯也。《诗纬》亡,而《齐诗》遂为绝学矣。曩者先大夫尝辑三家诗佚义,以《诗纬》多齐说,其于诗文无所附者,亦补缀之,以次于齐,所以广异义,扶微学也。”他认为《诗纬》多齐说,而《齐诗》因《诗纬》尚存而不至于成为绝学,《齐诗》与《诗纬》在传承上应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如此说来,原本属于“经”学阵营一员的《齐诗》与属于“纬”学系统的《诗纬》之间,必有一个可以沟通两者的桥梁。
事实上,翼奉的《齐诗》学就起到了这个桥梁作用。翼奉原本是《齐诗》学的传人之一,而他的《诗经》学又与《诗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清代已有学者清楚地看出了这一点,如迮鹤寿在其《齐诗翼氏学》中就曾直接拿《诗纬》与《齐诗》翼氏学进行过比照研究。陈乔枞更具体地指出了《诗纬》与翼奉《齐诗》学问的相合处,谓:“翼氏《齐诗》,言五性、六情,合亥午相错,败乱绪业之辞,与《诗汜历枢》言午亥之际为革命,合已哉。”趣样一来,《诗纬》与《齐诗》的关系似乎就变成了《诗纬》来源于《齐诗》翼奉学,而《齐诗》翼奉学则是直接属于《齐诗》系统的。尽管迮、陈二氏并未直接申明《诗纬》与《齐诗》的确切关系,但后人一般都由此而认定《诗纬》是源自《齐诗》的。在这样的认识前提下,不少学者在讨论《齐诗》的问题时便不加论证不做说明而直接引《诗纬》内容而加以证明,仿佛《诗纬》与《齐诗》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诚然,有《齐诗》才有翼奉《齐诗》学,而《诗纬》又颇受翼奉《齐诗》学影响。但是,在汉代四百年间的学术发展中,政治对学术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学派内部与学派之间的对立与融合,使得有汉一代的学术发展出现了相当复杂的情况。概括言之可谓继承与创新并存,“通义”与“别义”同在,那么《齐诗》的发展亦当不会不如此。
一《齐诗》与翼奉《齐诗》学
《汉书·儒林传》较为详细地勾画了西汉经学发展的情况。我们据此,并结合《齐诗》重要学者的本传,先对《齐诗》的传承以及《齐诗》的特色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一)西汉《齐诗》的传承及其重要学者
汉代《齐诗》的创始人是辕固。辕固,“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关于辕固传《诗》的具体内容,当时文献均无记载,只是于《史记·儒林列传》和《汉书·儒林传》中记录着其基本相同的三件行事:在景帝面前与黄生争论汤武受命,敢于触犯窦太后而称窦太后所好的《老子》为“家人言”,还有劝诫公孙弘“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从此三事似可窥见其性格:执着于先秦儒家经义,传承儒家“天下为公”思想,敢于坚持自己的信念,正直而近于固执。徐复观也因此认为辕固“在皇权鼎盛的皇帝面前,强调汤、武革命,可谓能把握儒家政治思想中的真精神,其所习者当不仅限于《诗》”。我们且不论辕固所学是否仅限于《诗》,仅从其性格及对经义的持守精神,完全可以想见《齐诗》传授之初应该是坚持《诗》之本义而不作过多推衍的。
辕固弟子众多,而其中又以夏侯始昌最明。《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载:
夏侯始昌,鲁人也。通《五经》,以《齐诗》、《尚书》教授。自董仲舒、韩婴死后,武帝得始昌,甚重之。始昌明于阴阳,先言柏梁台灾日,至期日果灾。时昌邑王以少子爱,上为选师,始昌为太傅。年老,以寿终。作为《齐诗》的传承人之一,夏侯始昌得到了众多的关注。之所以被认为“最明”,恐怕根本原因还在于有武帝的格外重视;之所以备受武帝重视,则是因为其学说符台武帝的“口味”。众所周知,董仲舒是武帝时以说阴阳灾异、天人感应闻名朝野而深得武帝重用的,同时他认为《诗》无达诂,“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也就是说,他是以天人感应为理论依据,而以阴阳灾异去阐释《诗》等其他经书的经义的。韩婴是《韩诗》的创始人,也通《易》学,其解“经”方式与时人不同:“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推《易》意而为之传”。可见韩婴是善于推衍做《传》来解释经义的,且《易》原本就是上古以来的占卜之书,其思想内涵亦与阴阳灾异相通。而夏侯氏“明于阴阳”,又准确预言了柏梁台灾,可见他也和董仲舒、韩婴一样熟谙阴阳灾异之说,依托于天人感应理论,是善于对经文做推衍式的解说的。其传《齐诗》似亦应如此,与乃师辕固的说《诗》已表现出明显的不同。阴阳灾异的思想和特色就这样被带入了《齐诗》的传授系统之中。
夏侯始昌之后,有东海后苍继续《齐诗》的传承。“后苍字近君,东海郯人也。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经》,苍亦通《诗》《礼》,为博士”。后苍从夏侯始昌学《齐诗》,同时又向孟卿学《礼》。“孟卿,东海人也。事萧奋,以授后仓、鲁闾丘卿。仓说《礼》数万言,号曰《后氏曲台记》。”而孟卿善为《礼》、《春秋》,其《春秋》之学是源自胡母生的《公羊春秋》学,这一派也是以言阴阳灾异见长的。这样一来,后苍的学术其实兼及夏侯始昌与孟卿的学术,也就是说,他兼有阴阳灾异化了的夏侯氏《齐诗》学和以奢谈天人感应为鲜明特色的《春秋公羊》学,所以后苍治《齐诗》,当不会不涉及阴阳灾异的内容。
后苍授学弟子萧望之、翼奉、匡衡三人,都以《齐诗》学闻名,也均位至达官显贵,遂推动《齐诗》达至全盛时期。《汉书》皆有传。萧望之本传载:
萧望之字长倩,东海兰陵人也,徙杜陵。家世以田为业,至望之,好学,治《齐诗》,事同县后仓且十年。以令诣太常受业,复事同学博士白奇,又从夏侯胜问
《论语》、《礼服》。京师诸儒称述焉。……时上初即位,思进贤良,多上书言便宜,辄下望之问状,……累迁谏大夫,丞相司直,岁中三迁,官至二千石。……望之为左冯翊三年,京师称之,迁大鸿胪。……(元帝)制诏御史:“国之将兴,尊师而重傅。故前将军望之傅朕八年,道以经术,厥功茂焉。其赐望之爵关内侯,食邑六百户,给事中,朝朔望,坐次将军。”
翼奉本传载:
翼奉字少君,东海下邳人也。治《齐诗》,与萧望之、匡衡同师。三人经术皆明,衡为后进,望之施之政事,而奉敦学不仕,好律历阴阳之占。元帝初即位,诸儒荐之,征待诏宦者署,数言事宴见,天子敬焉。……上以奉为中郎,召问奉:“来者以善日邪时,孰与邪日善时?”……明年夏四月乙未,孝武园白鹤馆灾。奉自以为中,上疏曰:“臣前上五际地震之效,日极阴生阳,恐有火灾。不合明听,未见省答,臣窃内不自信。今白鹤馆以四月乙未,时加于卵,月宿亢灾,与前地震同法。臣奉乃深知道之可信也。不胜拳拳,愿复赐间,卒其终始。”……奉以中郎为博士、谏大夫,年老以寿终。
匡衡本传载:
匡衡字稚圭,东海承人也。父世农夫,至衡好学,家贫,庸作以供资用,尤精力过绝人。诸儒为之语日:“无说《诗》,匡鼎来,匡说《诗》,解人颐。”……学者多上书荐衡经明,当世少双,令为文学就官京师。后进皆欲从衡平原,衡不宜在远方。事下太子太傅萧望之、少府梁丘贺问,衡对《诗》诸大义,其对深美。望之奏衡经学精习,说有师道,可观览。……辟衡为议曹史,荐衡于上,上以为郎中,迁博士,给事中。……衡为少傅数年,数上疏陈便宜,及朝廷有政议,傅经以对,言多法义。上以为任公卿,由是为光禄勋、御史大夫。建昭三年,代韦玄成为丞相,封乐安侯,食邑六百户。
由上述记载,我们不仅能够看出萧、翼、匡三人都因《齐诗》学而获得很高的地位,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国家大事之中,影响着宣、元、成三帝时期的政局,也使《齐诗》学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而且,同是接受于后苍的《齐诗》,但在三人那里则有了不同的发展:萧望之“施之政事”,把对《经》义主要是《诗》义的理解落实于治理国家、处理政事方面;翼奉虽“悖学不仕”,专心于《诗》之经义研究,但他又好律历阴阳之占,多次以阴阳五际来解释灾异现象,匡衡坚持“师道”,“其对深美”,当朝廷有政议时,则多据经义而提出对策。由此可见,萧、匡二人基本上还是沿袭了传统《齐诗》的说解,只是将其应用于政治,对学术建构和传承方面并无推进。但翼奉却独好律历、阴阳五行之说,并以此持说,上疏皇帝,把夏侯始昌以来原本就充斥着阴阳灾异色彩的《齐诗》学更往前推进了一步,导人更加神秘的占验之中。《诗》几乎变成了占验阴阳、预测灾异的占卜之书,从而逸出了此前经学的范围。如果说翼奉以前的《齐诗》只是掺杂了以阴阳灾异说《诗》的某些因素,那么翼奉的《齐诗》学,则是径直以阴阳五行解诗,以《诗》去解释现实中的灾异现象了。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徐复观在讨论《齐诗》辑佚问题时认为,“其遗说见于《汉书》萧望之、匡衡、师丹各传奏疏中的,多为诸家之通义”,“至于《翼奉传》所载翼奉‘四始五际六情之说,乃受夏侯始昌以阴阳五行傅会《洪范》言灾异的影响,他把这一趋向拓展于《诗》的领域,而更向旁枝曲径上推演,以成怪异不经之说,既无与于《诗》教,亦非辕固之所及料”,已逸出《齐诗》之通义,所以搜集汉代《齐诗》遗说,应以萧望之、匡衡、师丹奏疏中所引《诗》为主,而不能到翼奉诗说中去寻找。
然而,作为同出于后苍门下的三门徒,虽然在具体的解《诗》方式和内容方面存在差异,但是他们毕竟同师于一人,传授的经义也应该是一样的。徐先生将翼奉学完全割离《齐诗》这个“母体”,似乎也有过于武断之嫌。翼奉的《齐诗》学是在《齐诗》通义的基础上做了发挥,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变化,甚至成为《齐诗》的“别义”。我们应依据《齐诗》部分传承学者的资料,和《汉书》中记载的萧望之、匡衡在各自奏疏中谈《诗》、引《诗》的情况,推求一下《齐诗》的特征(或者说“通义”),以此来分析判断翼奉氏《齐诗》学中哪些理论与这些特征相同,又有哪些理论成为“别义”,从而探究翼奉《齐诗》学与《齐诗》具体而微的关系。
(二)西汉《齐诗》特征及与《齐诗》翼氏学之关系
西汉《齐诗》的特色,概括言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以《诗》作为劝谏的工具,以《诗》义比附政治。作为汉代《诗》学之一种,《齐诗》同其他解《诗》之作一样,是具备“谏书”的功能的。其基本模式是依据《诗》的内容,联系《诗》中历史人物或事件,用以规劝当时的统治者要效法古人,修明政治。这在萧望之、匡衡的奏疏中都有表现。比如在面对由于征讨西羌而造成的陇西以北、安定以西民众缺粮,张敞建议罪轻者可以通过上缴谷物救济上述地区百姓来赎罪的时候,萧望之则认为:
古者臧于民,不足则取,有余则予。《诗》曰:“爰及矜人,哀此鳏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边之役,民失作业,虽户赋口敛以赡其困乏,古之通义,百姓莫以为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尧舜亡以加也。今议开利路以伤既成之化,臣窃痛之。”
萧望之引《诗·小雅·鸿雁》和《小雅·大田》诗句,借以证明古时帝王与民众的关系:朝廷物资充足时则惠及百姓,而朝廷物资不足时则取之百姓,这是“古之通义”,所以他劝谏汉宣帝应效法古人的做法,而不要听从张敞的建议,避免开利路而伤教化。
匡衡引《诗》劝谏皇帝的情况在《汉书》本传中记载的更多,限于篇幅,仅举一例以见一斑。
元帝崩,成帝即位,街上疏戒妃匹,劝经学威仪之则,曰:“陛下秉至孝,哀伤思慕不绝于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诚隆于慎终追远,无穷已也。窃愿陛下虽圣性得之,犹复加圣心焉。《诗》云‘茕茕在疚,言成王丧毕思慕,意气未能平也,盖所以就文武之业,崇大化之本也。”
其实,这种“以《三百篇》为谏书”的做法,不仅为《齐诗》之通义,汉代其他三家诗也大体如此。
第二、以“情性”论《诗》。注意到《诗》中的“情性”因素,是汉代《诗》学对于先秦“诗言志”观念的一个突破与发展。虽然汉代四家诗都有关于《诗》中“情性”的论述,但鲁、韩、毛三家论《诗》只是与“情性”论偶有关合,而《齐诗》则将“情性”真正引入对《诗》的解说之中,从而使“情性”论《诗》成为《齐诗》的一个重要特征,这在匡衡与翼奉的奏疏中也有明确体现。如匡衡《上元帝疏》云:
陛下圣德天覆,子爱海内,然阴阳未和,奸邪未禁者,殆论议者末丕扬先帝之盛功,争言制度不可用也,务变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复复之,是以群下更相是非,吏民无所信。臣窃恨国家释乐成之业,而虚为此纷纷也。愿陛下详览统业之事,留神于遵制扬功,以定群下之心。《大雅》曰:“无念尔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经》首章,盖至德之本也。传曰:“审好恶,
理情性,而王道毕矣。”能尽其性,然后能尽人物之性;能尽人物之性,可以赞天地之化。
臣又闻室家之道修,则天下之理得,故《诗》始《国风》,《礼》本《冠》《婚》。始乎《国风》,原情性而明人伦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兴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间内。
臣闻《六经》者,圣人所以统天地之心,著善恶之归,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于其本性者也。陈乔枞云:“雉圭(匡衡)与少君(翼奉)同师,‘《诗》原情性之语,授受渊源,其来有自矣。”以“情性”说诗,并进一步运用到政治中去,是《齐诗》的一个重要特点。
第三、论《诗》杂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之说。从上文提到的《齐诗》传承情况看,《齐诗》最晚到夏侯始昌,已搀人了阴阳五行学说,使《齐诗》的解诗开始奢谈阴阳五行与天人感应。由后苍传授给萧望之、翼奉、匡衡,说诗杂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则成为《齐诗》的重要特征。《汉书·萧望之传》载:
时大将军光薨,子禹复为大司马,兄子山领尚书,亲属皆宿卫内侍。地节三年夏,京师雨雹,望之因是上疏,愿赐清闲之宴,口陈灾异之意。宣帝自在民间闻望之之名,曰:“此东海萧生邪?下少府宋畸问状,无有所讳。”望之对,以为“《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时季氏专权,卒逐昭公。向使鲁君察于天变,宜亡此害。今陛下以圣德居位,思政求贤,尧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阴阳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势之所致也。”
这是“天人感应”学说的典型运用,也是萧望之Ⅸ齐诗》学掺杂有天人感应学说的重要证据。
由匡衡奏疏考察,也可以发现其中较为明显的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说《诗》的内容。如在《上元帝疏》中说:“臣闻天人之际,精祲有以相荡,善恶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动乎上,阴阳之理各应其感,阴变则静者动,阳蔽则明者畸,水旱之灾随类而至。今关东连年饥馑,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于赋敛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称之效也。”考匡衡所学,发现他仅从后苍学《齐诗》,所以,匡衡《齐诗》学中亦应充满天人感应的理论内容。
第四、以地理、风俗说《诗》。对于《齐诗》以地理、风俗说《诗》的特点,江乾益说:“驺子受《禹贡》之影响,创大九州之说,其法则先列中国名山大川,物类所珍,因而推及海外所不能睹者,阴阳家好相阴阳消长之外,并好言地理;天文地理之学,实出自齐学之畛域也。”认为邹衍的“大九州”理论包含了一定的地理学观念;地理学是齐学的内容之一。《齐诗》以地理、风俗说《诗》在四家诗中确实比较突出。如匡衡上书云:“臣窃考《国风》之诗,《周南》、《召南》被贤圣之化深,故笃于行而廉于色。郑伯好勇,而国人暴虎;秦穆贵信,而士多从死;陈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晋侯好俭,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邻国贵恕。”根据颜师古的注解,匡衡所论《郑风·大叔于田》、《秦风·黄鸟》、《陈风·宛丘》、《唐风·山有枢》、《大雅·绵》五首诗,都是从不同的地域出发,以各地不同的风俗特征进行讨论的。更说明问题的例子在《汉书·地理志》中多有,如:
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故《秦诗》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及《车辚》、《四载》、《小戎》之篇,皆言车马田狩之事。
又如:
(郑国)土狭而险,山居谷汲,男女亟聚会,故其俗淫。《郑诗》曰:“出其东门,有女如云。”又曰:“溱与洧方灌灌兮,士与女方秉菅兮。”“恂盱且乐,惟士与女,伊其相谑。”
班固习《齐诗》,在《地理志》中大量以《诗》来验证该地的风俗与地理,正反映了《齐诗》以地理、风俗说《诗》的特色。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总结了《齐诗》的特征,或者叫做《齐诗》之“通义”。下面具体从这四个方面来考察“好律历阴阳之占”的翼奉以及其毕生研习的《齐诗》学对“通义”承继或者进一步突破与发挥的情况。
第一、以《诗》作为劝谏的工具,以《诗》义比附政治,这基本上是汉代经学的一个共同特征,也是作为意识形态的经学对于政治反作用的具体表现。翼奉与其他经学家一样,致力于学术(《诗》经学)的目的是企图以学术影响政治甚至干预政治。在《汉书》本传中,共有翼奉上疏皇帝的四次记载。如关东大水时翼奉奏云:
臣奉窃学《齐诗》,闻五际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蚀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犹巢居知风,穴处知雨,亦不足多,适所习耳。臣闻人气内逆,则感动天地;天变见于星气日蚀,地变见于奇物震动。所以然者,阳用其精,阴用其形,犹人之有五臧六体,五臧象天,六体象地。故臧病则气色发于面,体病则欠申动于貌。今年太阴建于甲戌,律以庚寅初用事,历以甲午从春。历中甲庚,律得参阳,性中仁义,情得公正贞廉,百年之精岁也。正以精岁,本首王位,日临中时接律而地大震,其后连月久阴,虽有大令,犹不能复,阴气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亲亲,必有异姓以明贤贤,此圣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亲而易进,异姓疏而难通,故同姓一,异姓五,乃为平均。今左右亡同姓,独以舅后之家为亲,异姓之臣又疏。二后之党满朝,非特处位,势尤奢僭过度,吕、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爱人之道,又非后嗣之长策也。阴气之盛,不亦宜乎!
很明确,翼奉先是以《诗经·小雅·十月之交》为例,讲了一通天人感应、阴阳五行的理论,以此来说明地震大水等灾异的发生是由于阴气、阳气的盛衰不合。而“阳用其精,阴用其行”,阴阳与人气是相对应的。同时,人气的内逆能够感动天地。当朝廷做到“明亲亲”、“明贤贤”时,圣王就能够“大通天下”。然后,翼奉将话题转到当时的政局,认为当前朝廷“左右亡同姓”,无法做到“明亲亲”,却“独以舅后之家为亲,异姓之臣又疏”,无法做到“明贤贤”,则帝王不能够“大通天下”,所以才会导致大水灾异的出现。通过这样一个看似曲折的说解过程,翼奉最终劝谏统治者要以本姓族人为亲,对于异姓尤其是后宫的舅氏党羽,应该时刻警惕。可以说,翼奉《齐诗》学的功用之一,即是用以劝谏主上。
不过,虽然同样是以《诗三百》作“谏书”,翼奉与其他《齐诗》学者还是存在着不同。像萧望之、匡衡的以《诗》劝谏,几乎都是从诗句的基本内容去推求诗之“本事”,将诗中那段历史与当下的现实政治相比照,以古是今非来说服皇帝要遵循古制,进谏方式呈现为“《诗》——历史——政治”这样一个过程。而翼奉则是从《诗》的天人感应、阴阳五行出发,直接以天人感应理论诠释灾异现象,进而指出政治上的弊端,其呈现为“《诗》——阴阳灾异——政治”这样的过程。所以说翼奉《齐诗》学虽具备以《诗》进行劝谏这一《齐诗》之“通义”,但在劝谏方式上他不是借助于《诗》篇所反映的史实,而是直接以阴阳五行解《诗》,这就使得《齐诗》学从起初的掺杂阴阳五行因素,发展到直接以阴阳五行学说解《诗经》。这是翼奉《齐诗》学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