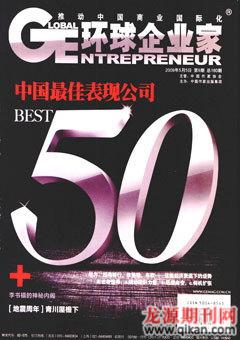公司的渊源
许 宏
世界常常津津乐道于商业领袖的成功,但也别忘了他们是从哪里来的。
最不可缺少的往往最容易被视而不见。在当今世界,人们一生中的很多时间用于工作,而其中大部分时间又用来待在公司中。人们如此置身其中,以至难得去想“公司”究竟是怎么回事,仿佛这一切是自古以来就无所不在的。
最近的全球经济危机提醒了人们,即使看起来基业长青的公司也可能只是“看起来”而已。但这并不是说公司本身会消亡,相反,这种社会组织最精彩的历史还未完全到来。毕竟,公司成长为世界现象只是最近一个多世纪的事情。
对许多人,公司提供的不过是谋生手段,或进一步说,展现自身价值的用武之地。不去公司,还有政府、非政府组织。但这样的选择不是历来就有的。在彼得·德鲁克看来,公司的出现是现代自由社会形成的必要前提之一,它为人们在经济上获得选择的自由提供了现实的可能。
世界范围内,公司从近代开始大规模出现时,经济上的资源大多为国家和地方政权控制,人们难得有自己可以安全支配的财产和生意,个人与其实际雇主“国家”显然没有多少谈判筹码。时至今日,对世界状况今昔的叙述很少从这个角度理解公司在生活中的意义,而对为公司的兴起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物、观念和做法提及的就更少了。常常被津津乐道的总是那些结果,而非孕育结果的原因。并非任何时代和地区的人都能方便地创办公司,企业家的诞生需要有养育他的母体和适合的生长环境,而这是到19世纪中叶才被正式提到世界历史议程上的事。
被忽视的英雄
不仅中国的企业家和研究公司的人可能对罗伯特·洛伊这个名字感到陌生,即使在英国人自己写的历史和时评中都难得将其与商业世界联系起来。只有如今担任《经济学家》主编的约翰·米克尔斯维特2003年出版的《公司:一个划时代观念之简史》中才指出这个遗留百年的疏漏。
其实在洛伊所处时代,他在英国政治上举足轻重。于1811年冬天出生在英国诺丁汉郡一个牧师家庭的洛伊虽然天生是视力极弱的白化病患者,一度被认为连上学的能力都没有,但他不仅读完了大学,还击败《经济学家》第三任主编沃尔特·白哲特当选国会议员,并在56岁时成为英国财政大臣。
不过,洛伊影响最为深远的工作是在44岁担任英国贸易委员会副主席时推动《1856年股份公司法案》的通过,这是人类史上第一部通行全国并影响至今的公司法。此后,英国人创办公司不必再通过国家特许授权的繁琐方式,而且股东在公司破产后不用承担除自己股份之外的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名称及其组织方式开始流行起来。此后几年,数以万计的有限责任公司在英国注册成立,全球公司的历史真正就此展开。
洛伊曾讲道:“我眼下的目的并不是催促实施有限责任制。我是在为人的自由而战——在不受国家多管闲事的干涉下,人们可以自己选择跟谁合作及怎样合作;即使没有多少有限责任制公司建立,我的观点也不会被撼动——我认为我们应采取的原则是不给有限责任公司的成立设置哪怕一丁点的障碍,因为那样做会为了避免一个坏方案的出现而扼杀99个好方案的诞生;要允许它们都有机会诞生,而当问题出现时,给司法机构足够的权力以遏制公司管理中奢侈和欺骗行为的出现,将公司从可能卷入的毁灭中拯救出来。”
这些言辞如今听来可能已毫不新鲜。100多年后的世界,自由选择和自由结成契约组织的权利已在很多地方逐渐从理念落实到日常生活中。但洛伊的观点却提醒今天忙于公司事务的人们,那些为开设公司扫除人为障碍的努力不仅是帮助人们做生意挣钱,归根到底是为了人的自由。
如果“自由”的意思因文化和个人的理解不同而容易产生歧义,洛伊——还有白哲特、德鲁克——的意思是为了恢复人应有的尊严、才能和责任。人争取自由,显然不是为了自由地选择坏,而是能自由地选择好。人争取自由之所以能让人产生好感和尊敬,在于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分,这样可以让健康的生命成长延续。
洛伊在为自由企业制度辩护时,并没有同时为公司可能出现的不良行为辩护。相反,从他的演讲中,不良行为意味着公司可能面临危机甚至是毁灭,而危机和毁灭显然不是争取自由的目的。当然,洛伊指望司法部门遏制公司不良行为的想法在世界公司历史中被证明是远远不够的,一旦轮到司法介入时,一切可能都晚了。
实际上,公司在洛伊的时代前早已出现。最早具有现代雏形的股份公司大约是16世纪中叶获得英国王室特许的英国商人跟俄国沙皇做生意的公司,及稍后的东印度公司。但作为现代经济先驱的英国迟至19世纪中期才有对公司建立有利的公司法,除了既有公司想继续保持垄断地位的原因外,也与这些特许公司自身的形象有关:它们肆无忌惮的投机行为在18世纪初引发了世界最早一轮的股市大跌和信贷危机,并且还参与臭名昭著的奴隶贩卖,那些致力于推动自由事业的改革者们对公司没有足够的好感便不奇怪了。
改变这一切的可见力量在相当程度上源自技术进步,铁路的兴建是其中最显著的现象。地区间——更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因为新工具的出现和推广而前所未有的缩短,这自然引起包括社会各界的兴趣,投资铁路成为贯穿19世纪的欧美世界最热门的商业活动之一。
如果没有新技术的不断涌现而只是对既有资源的买卖,社会就将仍处于缺乏新生命生长的状态,既得利益者对资源的掌控也就容易维持。实现自由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新生命不屈不挠的生长。尽管如今人们对工业革命在英国率先兴起的原因仍无统一意见,但那个时期英国的革新者们所具有的生命力是任何致力于推动自由文明前进的后来者们值得重视的。
万事互相效力
瓦特的经历就很说明问题。这位因改进蒸汽机而为火车乃至整个工业革命预备发动机的工程师被公认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发明家之一,然而荣誉并非属他一人。
从其曾祖父开始,瓦特一家就属于反对国王干涉信仰事务的苏格兰长老会的成员。而作为工程师的瓦特遇到的主要问题来自于行业公会的专制。“瓦特当时是个20岁的小伙子,从伦敦来到格拉斯哥,想以制作数学仪器为生。可是,虽然这个城市没有其他人制造数学仪器,铁匠行会却不允许他开业,理由是他不是该市市民的儿子也不是女婿,又没有拜过这里的师傅。”苏格兰记者约翰·雷在他那本1895年出版的经典《亚当·斯密传》中写道。这个背景对任何经历过社会从专制到自由转变的人来说也许都不太陌生。
跟其他社会的同行不同的是,瓦特遇上了一群人而非仅仅几个人的帮助,这一群人主要来自斯密所在的格拉斯哥大学。
“格拉斯哥大学的领导层虽然在各机构的权限或财产管理等细小问题上争执不休,但在办校方针上却非常有见识,
非常开明,尽力推动学校的发展。”雷在斯密的传记中写道,“在那充满特权的年代,大学也享有其特权。格拉斯哥大学的教授由于在大学校园内享有绝对独立的权利,他们让瓦特担任了该大学的数学仪器制造者,拨出一间房子做他的车间,又在校门附近给了他另外一间,让他出售产品,以此战胜瓦特受到的压迫。”
根据雷的记述,斯密“喜欢出入瓦特的车间,因为瓦特虽年轻,但谈吐不凡,富有创见,对周围有才学的人有很大吸引力。而瓦特对斯密也总是抱有深深的敬意。”
创建于1451年的格拉斯哥大学的校训是“道路、真理、生命”,源于《圣经》中的耶稣对自己的称呼,他告诉门徒不要忧虑人生的道路,认识了神,就认识了通向真理的生命之路。这与后来在北美创建的哈佛大学——美国最古老的公司——的校训“真理”如出一辙。实际上,很多世界知名的大学都拥有类似的校训。作为特许授权而建立的大学帮助了一名被政策歧视的外来务工人员,这虽然不能像公司法那样为所有想创业的人扫除制度上的重大障碍,但也是一切处在从专制到自由转变的社会值得学习的做法。制度上的改变显然不是在法律条文颁布之后才开始的。进入立法的程序,往往意味着生米已经煮成熟饭。
格拉斯哥大学给予瓦特的不仅是作为工作室和商店的房间。大约在1762年,23岁的化学老师约翰·罗宾逊启发26岁的瓦特如何利用蒸汽作为机器运转的动力来源。此前,瓦特从未见过蒸汽机工作。当时已有小批量生产的蒸汽机,是一位叫做托马斯·纽科门的英格兰五金商人在1712年左右发明的。格拉斯哥大学帮助瓦特获得了一部需要修理的蒸汽机,经历十多年的研究和实验,又有另一位教授朋友及同道企业家的资金支持,瓦特将纽科门蒸汽机的效率提高了3倍,1775年获得专利保护,第二年投入商业使用。
瓦特的成就反过来也促进了第一批具有现代意义的商业企业家的诞生。他跟合作伙伴马太·博尔顿于1775年成立的博尔顿一瓦特合伙人公司是那个时代最成功的制造业组织之一,这个公司持续了120年之久。这些公司不仅生产出工业革命的发动机,对工作人员的尊重也开始写进商业组织的历史,工人有了初步的社会保险,工作场合保持干净、通风和照明,而且拒绝雇佣童工。
在2004年《福布斯》评选的历史上对当今商业世界影响最大的20位商人中,博尔顿是最早的一位,今年是他逝世200周年。他和瓦特及参与过他们事业的所有人开启了德鲁克所谓知识工人、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的时代。在这个新兴世界中,公司成为人们大规模生产物质和精神财富的集散地,而这一切的根基都与人的自由紧密相关,虽然很多时候的很多事情会让人忘记这个让人肃然起敬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