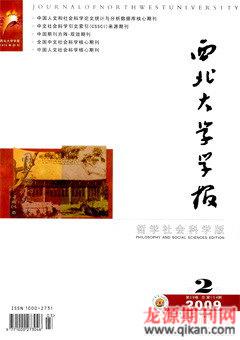论黄仲则的山水游历与诗歌创作
李小山 甘宏伟
摘要:为了探究黄仲则的精神品格与诗歌风貌,选择其山水游历为研究视角,采用了文献分析和文本细读等研究方法,结论认为山水游历占据了黄仲则生命的重要位置,可以作为解读其心灵与诗歌创作的一条线索。游历的见闻、客寓的感怀成为他诗歌的重要内容,同时,山水游历亦是促其诗艺大进、诗境大变的关键因素。
关键词:黄仲则;山水游历;诗歌创作;诗境之变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09)02-0015-04
黄仲则(1749—1783),名景仁,字汉镛,又字仲则,江苏武进人,著有《两当轩集》。他是清乾隆时期的著名寒士诗人,诗名在当时已受人推重,袁枚誉其为“今李白”,清人包世臣《齐民四术》中称之“乾隆六十年间,论诗者推为第一”。笔者在研读黄仲则的过程中,深感其心灵世界与其诗歌世界是相即不离的一体两面,且二者又均与其山水游历有密切、内在的联系。山水游历不仅让黄仲则寻求到了心灵的寄托和精神的归宿,游历的见闻、客寓的感怀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他诗歌中的重要内容,同时,游历亦是促其诗艺大进、诗境大变的关键因素。总之,山水游历占据了黄仲则生命的重要位置,可以作为解读其精神品格与诗歌创作的一条线索,由此入手,或可使其人格的深刻性和诗歌的丰富性得到较好的说明。
一、酷爱山水游的寒士诗人
黄仲则幼年丧父,家贫无依,后以母老,客游四方,觅升斗为养。作为一名寒士诗人,他一生游历南北,弹铗依人,其间虽不免因家贫而“出为负米游”,然实性喜山水,邵齐焘称其“生来寤寐爱青山,但恨郡郭无烟鬟”,足迹遍及江浙、荆楚、燕赵、齐鲁、关中之地。乾隆三十一年,黄仲则与洪亮吉于江阴逆旅订交,随后同在常州龙城书院从学清中叶学人兼诗人邵齐焘。乾隆三十三年恩师邵齐焘去世,仲则深感“益无有知之者,乃为浪游,由武林而四明,观海;溯钱塘,登黄山;复经豫章,泛湘水,登衡岳,观日出;浮洞庭,由江以归。是游凡三年,积诗若干首。”。洪亮吉《黄君行状》称其“年甫壮岁,踪迹所至,九州历其八,五岳登其一,望其三。”黄仲则自乾隆三十一年十八岁时起,至乾隆四十八年病逝于离家千里之外的解州止,常年游历或客寓在外,山水之游可说是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黄仲则性喜山水,竟至于全然忘记饥寒病苦的境界。《清史列传·黄景仁传》称其“性高迈,好游,尽观江上诸山水,每独游名山,经月不出,值大风雨,或暝坐崖树下,牧者见之,以为异人。”他“少长遍游江、浙诸名胜,以为未足,每读《离骚》,欲吊屈原所自沉处”,杭州友人仇丽亭辈,以湖湘道远,且怜其病,劝其勿往,仲则以词谢之云:“一事与君说,君莫苦羁留。百年过隙驹耳,行矣复何求?且奈残羹冷炙,还受晓风残月,博得十年游。若待嫁娶毕,白发待人不?”乾隆三十四年冬,终襆被独游湖湘,酹酒招魂,吊屈原、贾谊,作《浮湘赋》以寄意,悲慨伤怀。
乾隆三十四年春,黄仲则二次入徽州,欲游黄山,但因病虐未果。乾隆三十七年,二十四岁时,第三次入徽州,下定决心游黄山,《重至新安杂感》即表明了这种不容释怀的心绪:“山灵重与开生面,虐鬼何能阻再游。旧物尚余双蜡屐,此身无恙一扁舟。”
疾病和困顿似乎总是伴随着这位傲骨嶙峋的诗人。四处干谒寻求救济的辛酸他是尝遍了的,奔波劳苦而又清高孤独的心灵似乎只有在山水之间才会得到深深的安慰与彻底的解脱,这或许是黄仲则酷爱山水游的一个深层心理原因。
二、游历所得的精神认同
对于一个注重精神生活的天才诗人来说,黄仲则的游历并非仅为徜徉于山水之间,赏心娱情,他的山水之游更多怀有追寻自我精神认同的目的。而他所心仪的则主要是屈原、贾谊、杜甫等这些不遇于时的骚人诗客。乾隆三十五年春,黄仲则游湖南,经过耒阳,特意拜谒杜甫墓,作有《耒阳杜子美墓》:“得饱死何憾,孤坟尚水滨。埋才当乱世,并力作诗人。遗骨风尘外,空江杜若春。由来骚怨地,只合伴灵均。”当年杜甫困于耒阳舟中,饥寒交迫,绝粮数日。后来耒阳县令送酒和牛肉至,以至醉饱而死。前人多为之曲解掩饰,黄仲则是惯于穷饿的诗人,非常理解杜甫当时的处境,则直言出之。更让黄仲则深有同感的是杜甫的“埋才当乱世,并力作诗人”,骚怨之地岂只有屈原、杜甫,黄仲则不亦是一位吗?杜甫的遭遇引起他的共鸣,发出了盛世寒士的哀叹。
杜甫平生无大得意事,天宝五年以后,尤其安史乱起,又遭兵戈乱离、饥寒老病,历尽辛酸。杜甫是因战乱所逼而不得不辗转漂泊,他亲身经历了唐王朝由开元盛世而至安史之乱的过程,亲眼目睹了无数的灾难场面。黄仲则身处太平盛世,却因贫困潦倒而四处漂泊,亦会见到些灾难场景,感受到乾隆盛世由盛而衰的迹象,如《苦暑行》等所表现即是。而从一定意义上说,黄仲则比杜甫更为不幸。杜甫虽由盛世而遭战乱,但他所处的时代是帝王时代的上升期,思想氛围宽松自由,他可以将目光投向生民疾苦与国家安危,尽情地抒写百姓苦难,谴责诛求黩武,甚至直刺皇帝,当然更可自由倾吐一己的感慨。黄仲则虽逢盛世,但盛世却是帝王时代的衰败期,自明朝以来的专制集权进一步强化,王朝的统治更多是靠极度专制甚至恐怖来维持。加之满清统治者念念不忘自己入主中原所遭到的因强烈民族情结而致的坚决反抗,所以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清王朝的思想箝制最为严酷,文祸最多,最惨,最为荒唐,持续时间也最长。乾隆时期,文字之狱更是达到了顶峰。在这样的一个盛世中,文人学士们谁还能像杜甫那样尽情倾吐抒写?杜甫于乱世中的动地歌吟,在黄仲则这里只有化为盛世中的独自歌哭,故而其所注目亦多为自身的饥寒贫苦,诗中自然更多的是对自己游历见闻及客寓感怀的抒写、对个人遭遇不幸的哀叹和愤慨,而有些诗作或借题发挥、或旁敲侧击所表现出的胆识也就显得十分难能可贵了,“埋才当乱世,并力作诗人”之愤激,亦因之而格外深沉。
屈原、贾谊的遭遇为历代不遇的文人骚客频频吟咏,黄仲则此次游湖湘的重要意图便是为酹酒招魂,以吊屈贾,从其词《水调歌头(仇二以湖湘道远,且怜余病,劝勿往,词以谢之)》中,可分明感知此种情愫:“离击筑,谖弹铗,粲登楼。仆虽不及若辈,颇抱古今愁。此去月明千里,且把《离骚》一卷,读下洞庭舟。大笑揖君去,帆势破清秋。”友人孙星衍在诗中亦尝言及仲则此行曰:“南浮汩罗招屈原,洪涛浡潏颠乾坤。寸磔幽怪偿厥怨,长蛟泼血江为浑……洞庭为酒君山尊,八九云梦胸中吞。胸中垒块谁共论,扣舷大啸呼灵均。”湖湘之游,仲则得遂夙望,既有《浮湘赋》以寄意,又有《屈贾祠》以伤怀:“雀窥虚帷幙草盈墀,日暮谁来吊古祠。楚国椒兰犹白化,汉庭绛灌更何知?千秋放逐同时命,一样牢愁有盛衰。天遣蛮荒发文藻,人间何处不相思。”盛世衰世都有同样的不遇之愁,湖湘之游,黄仲则寻求到了自己的精神与心灵的认同。
乾隆三十九年七月,黄仲则与洪亮吉同应江宁乡试,再度落第,于重阳节后作诗赠别钱企庐,其二云:“痛饮狂歌负半生,读书击剑两无成。风尘久已轻词客,意气犹堪张酒兵。霜满街头狂拓戟,月寒花底醉调筝。谁能了得吾侪事,莫羡悠悠世上名。”其三云:“肯容疏放即吾师,花月文章皓首期。那觅酒能千日醉,不愁音少一人知。身名已分同飘瓦,涕泪何曾满漏卮。幸有故人相慰藉,濒行抛得是相思。”其中所表现出的萧瑟悲苦之情皆因他“万斛才源倾似海,一生困顿遇偏奇”而生。
黄仲则还对李白特别表示出倾慕之情,他在《太白墓》中赞之云:“高冠岌岌佩陆离,纵横击剑胸中奇”,“乾坤无事入怀抱,只有求仙与饮酒”,并称“我所师者非公谁”。饮酒、仗剑而游好山水,体现着李白的豪情,亦是黄仲则的精神与心灵的寄托。李白“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人名山游”(《庐山谣》),写下了许多山水名篇,或表现其豪壮开阔的胸怀,或表现其与天地自然融为一体的气质。黄仲则游历山水,亦写下了不少得谪仙之气的作品。李白吟唱“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陪侍御叔华登楼歌》),“我不弃世人,世人自弃我”(《赠蔡山人》),黄仲则云“公(邵齐焘)卒,益无有知之者,乃为浪游”。二人皆因不得知遇,人生的困惑、生活的窘迫所致的内心愁苦就在登山临水或拜祠谒墓中得以缓解、释放。因山水游历,仲则更显出与李白的精神契合,“自湖南归,诗益奇肆,见者以为谪仙人复出也”。
三、诗风诗境之转变
山水之游不仅让黄仲则追寻到精神的归宿,获得灵魂的升华,而且触发了他的诗情。中国古代,游历之风盛行。山水游历常成为历代诗人创作的重要源泉或助力。屈原被放,历游长江、洞庭、沅湘等地,积聚的深厚悲痛与哀思发为诗歌,刘勰即言:“屈平所以能洞鉴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晋宋山水诗人谢灵运自出任永嘉太守后因不见知,常怀愤愤,遂肆情江南山水,体道适性,留下了诸多垂范后世的佳句。永明诗人谢眺,沉浮于政治涡流之中,因畏祸而投身于山水间,亦创作出情意盎然之作,李白赞叹之:“解道澄江静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金陵城西楼月下吟》)。唐代游山历水、读书山林之风炽盛,许多诗歌经典之作可以说是因诗人的游历而成就,而众多诗人仅凭其山水佳制已足以彪炳千古。宋代的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屡遭贬谪,在外任与谪居期间,留连山水清境,众多山水景观因他的题咏而荣膺千秋佳名。而得山水之助亦使其诗境益新,东坡曾有言:“游遍钱塘湖上山,归来文字带芳鲜”(《送郑卢曹》)。此言正上承刘勰,下启陆游:“不向岳阳楼上醉,定知未可作诗人”(《再赋一绝》)。清人赵翼亦说:“放翁诗之宏肆,自从戎巴蜀,而境界又一变。”
明清时期,八股取士制度大兴,诗坛多为身居官位的文人才士操柄,诗歌创作总体上处于或取法汉魏六朝或尊唐宗宋的宗派争鸣之中,而学古又把主要精力放在诗法、诗艺、诗境等形式技巧的追求上。在野者包括众多寒士诗人,或附于某个宗派,或受整个诗坛风气的影响,亦很难跳出笼樊。在此大背景下,因漂泊游历而得山水之助便易创作出脍炙人口的佳篇,诸如元明之际高启的《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山水长卷《徐霞客游记》虽为散文,但亦有不少诤情盎然的佳作。
黄仲则亦是其中一位,他在游历之中,同样写下许多山水诗篇,“自念绑所游处,举凡可喜可愕之境,悉于是乎寄”,得江山之助与人文之熏陶,其中亦多有佳者。其吊谒屈贾、倾慕李杜等游历之作前已有所述及,它如《春雨望新安江》表现其愁怨之后的放旷:“明当放溜趁新涨,卧听船鼓催逄逄”,《笥河先生偕宴太白楼醉中作歌》:“请将诗卷掷江水,定不与江东向流”,发其万古之幽情,又结以自负之豪气。总之,黄仲则的山水诗追求的不是静幽的境界,而有着强烈的主体感情,是诗人心灵与山水交会时的自我精神的写照。因此,丰富的游历是其诗歌能以真情感人、以诗情取胜的重要原因之一。
山水游历亦是促其诗艺大进、诗境拓展的关键因素。从早年起,“好做幽苦语”就已成为寒士诗人黄仲则诗歌的鲜明特色,如邵齐焘称其“家贫孤露,时复抱病,性本高迈,自伤卑贱,所作诗词,悲感凄怨”,洪亮吉《北江诗话》评仲则诗“如咽露秋虫,舞风病鹤”。的确,黄仲则在诗歌中所表现的感情和风格最著的是他的抑塞苦语。从早年的悲感凄怨之词,至流寓京师时的辛酸苦寒之调;从“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之沉痛,至“茫茫来日愁如海,寄语羲和快著鞭”之伤心;从“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霄”之孤冷,至“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剪裁”之凄惨,此类孤愁苦寒独自歌哭之语在黄仲则诗集中比比皆是。瞿秋白《赠羊牧之》云:“词人作不得,身世重悲酸。吾乡黄仲则,风雪一家寒。”郁达夫云:“要想在乾、嘉两代的诗人之中,求一些语语沉痛、字字辛酸的真正具有诗人气质的诗,自然非黄仲则莫属了。”都是深为黄仲则的这类诗感动而发,但也无庸讳言,其诗亦因之而不免有题材狭窄、诗境逼仄之不足,若从求全责备的角度说,这其实也可以认为是历代寒士诗人诗作之通病,有如吴蔚光《两当轩诗钞序》称仲则似“东野(盂郊)穷而长吉(李贺)夭”。
然而更应注意的是,黄仲则在常年游历中,面对祖国的壮美山河,置身于开阔雄奇的自然山水和深厚博大的人文景观,诗心容有会意,诗情因而激发,诗境得以拓展,诗风为之一新,变抑塞为磊落,变局促为开阔,变哀怨为激越,变悲苦为苍凉,超越一己之苦吟,冥合万有之奥博。此类诗作数量不多,然更弥足珍贵,其风格,或可称为“沉郁清壮”。如乾隆三十七年,黄仲则三入徽州游黄山时,作有《铺海》一诗:“我欲云门峰,化为并州刀。持登天都最高顶,乱剪白云铺絮袍。无声无响空中抛,被遍寒士无寒号”。既有李白的奇特想象,又有杜甫的仁者襟怀,与其诗中惯见的“贫是吾家物”(《移家来京师》)、“征衣我最单”(《九月初二日小雪》)、“只知独夜不平鸣”(《杂感》)之类的风格情调显然不同,其“被遍寒士无寒号”一语亦超脱了一己之悲欢与独自之歌哭,堪可追配杜子美的“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又如乾隆三十二年游杭州作《观潮行》:“伟哉造物此巨观,海水直挟心飞腾……才见银山动地来,已将赤岸浮天外……殷天怒为排山入,转眼西追日轮及。一信将元渤湃空,再来或恐鸿濛湿”,海水裹挟着诗心,诗情飞腾翻涌,诗境格外雄奇阔大。末言“吴颠越蹶曾几时,前胥后种谁见知?潮生潮落自终古,我欲停杯一问之”,融入春秋时吴越争霸的历史风云,今昔沧桑的慨叹,停杯一问的潇洒,在潮生潮落奇丽景观之映衬下,给诗作平添了几许沉郁厚重。又有《后观潮行》:“鹅毛一白尚天际,倾耳已是风霆声。江流不合几回折,欲折涛头如折铁。一折平添百丈飞,浩浩长空舞晴雪……潮头障天天亦暮,苍茫却望潮来处……独客吊影行自愁,大地与身同一浮”,最后虽仍归结为自身的羁旅之愁,但因得江山之助力,能够将身世浮沉与苍茫大地融为一体,颇具几分杜甫的“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之深沉阔大之境界。无怪乎前辈诗人袁枚极为推赏,称仲则“看潮七古冠钱塘”。翁方纲《悔存诗钞序》称黄仲则诗:“尚沉郁清壮,铿锵出金石,试摘其一二语,可通风云而泣鬼神,何必读至五百首哉!所以兢兢致慎,删之又删,不敢以酒圣诗狂相位置者,欲使仲则平生抑塞磊落之真气,常自轩轩于天地间,江山相对,此人犹生,正不谓以长歌当痛哭也。”所谓“江山相对,此人犹生”,正可移作仲则沈郁清壮的诗境之变与其山水游历之密切联系之形象说明。
借出游以提高诗艺、转变诗风,在仲则亦有意为之。《清史稿·黄景仁传》言其“尝自恨其诗无幽并豪士气,遂游京师。”就效果而言,游历对他诗艺诗境的提高拓展之功也是无庸置疑的。黄逸之《黄仲则年谱》引《玉麈集》称其“自黄海归,技日益进,同辈悉敛手下之。”汪佑南《山泾草堂诗话》称:“仲则生不逢时,每多清迥之思,凄苦之语,激楚之音,自出游后,得山水之助,诗境为之大变,扶舆清淑之气,钟于一人,盖天才也。”都是言山水游历对黄仲则诗艺、诗境之变的重要作用。
尤其自湖南归,其诗益奇肆,“雄宕之气,鼓怒于海涛”,即得益于他“揽九华,陟匡庐,泛彭蠡,历洞庭”之游历。其间所作,诸如:“洞庭一泻八百里,浮云贴天天浸水。君山一点碍眼青,却似今日酒酣别君之块垒”(《洞庭行》),“拟向江山作主人,却因商妇悲迁谪。我亦天涯有泪人,对此茫茫惨无泽。吁嗟乎!泪亦不必落,愁亦不必愁。君不见,茫茫九派向东流,千古万古无时休,我家乃在东海头”(《晚泊九江寻琵琶亭故址》),山水之境与诗人之情交融,奇崛宏肆、沉郁清壮,有别于“幽苦语”之哀感凄怨、辛酸沉痛。
[责任编辑赵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