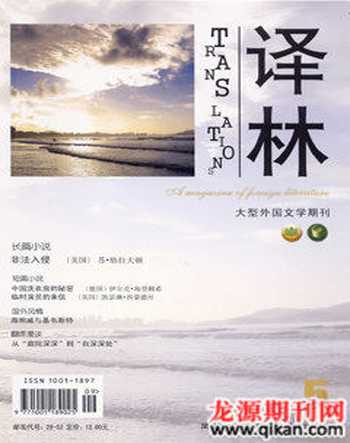美学对文学翻译的主宰作用
摘要:本文从美学的角度,就笔者新近所译王尔德的《道连·格雷的画像》中的几个片段与其他版本的译文做对比分析,通过对行文谋略与逻辑思辨两个方面的讨论,可见翻译与美学的不可分割性及美学敏感度对翻译思考所起的主宰作用,并可见审美角度的不同对译文产生的不同影响。
关键词:审美意识 行文之美 逻辑之美
翻译到底是什么——艺术?科学?技艺?与之有关的论争与论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已久,但无论持哪一学派的译论主张,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究竟不应也不可能离其宗——它“既是艺术,也是科学,也是技艺。优秀的文学翻译工作者必须对语言的美学方面有敏感性,同时要掌握最切近的自然对等的表达技艺”(注:转引自郭建中《当代美国翻译理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4页。)。简言之,文学翻译应该是以严谨的科学方法、高超的语言技艺、敏锐的审美知觉力最终达到艺术美的境界。而笔者近期在翻译王尔德的《道连·格雷的画像》(注:郑晓园、魏文峰(译)《道连·格雷的画像》,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过程中,尤其体会到翻译工作者的美学敏感度以及不同的审美角度对译文产生的重要影响。以下就《道连·格雷的画像》不同的译文片段作一分析,以阐述审美意识如何在翻译过程中起主宰作用。
一、行文之美
唯美主义大师奥斯卡·王尔德的《道连·格雷的画像》已有多个译本,所有译者,无一例外地被小说的语言所折服,因为“王尔德的语言是其最精彩的成就,认可和拒斥都是流畅的”(艾尔曼:序言)(注:理查·艾尔曼《王尔德全集》,第4卷序言,赵武平主编。中国文学出版社,1984年。)。孙法理先生在其《道林·格雷的画像》译序中指出“《道连·格雷的画像》是极少的唯美主义小说之一。它具有很强烈的唯美倾向,不但文辞绚丽,意象新颖,有许多带有王尔德特色的俏皮话、幽默话、似非而是之论,矛盾诡辩之辞,妙语连珠,精彩纷呈……”(注:孙法理(译)《道连·格雷的画像》,青岛出版社,2000年,第3页。)黄源深先生在他的译作前言中认为,王尔德的作品最吸引人之处是“机智的对话,凌厉的语言,发人深思的议论……他使用的语言常常一针见血,直抵痛处;而他的议论又总是似非而是,似是而非,迫使你去细细品味、辨别和思考。正是这些,给了读者和观众别处所领略不到的愉悦,一种美的享受”(注:黄源深(译)《道连·格雷的画像》,上海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页。)。而荣如德先生对王尔德语言特色的感觉与孙、黄有所不同,在其所译《道连·格雷的画像》的“代前言——折翅的悖论大师”中,他说,“王尔德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并不是他的唯美主义艺术观,也不是像燃放焰火那样从他笔下喷发出来的妙语悖论,而是他明白晓畅的文笔”(注:荣如德(译)《道连·格雷的画像》,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12页。)。“明白晓畅”,是王尔德的语言风格,也是荣先生译本的语言风格,正如吴学平在“国内王尔德研究述评”一文中,提到已有的几个《道连·格雷的画像》译本时所说,“荣译本属上乘之作,读之既能品尝到王尔德优美的语言,又能感受到他简洁的文风,读后有一种领略到原作神韵的痛快淋漓。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对王尔德爱用而又难译、曾被余光中先生叹为‘悠然心会,难与他人说的悖论(paradox),荣先生也译得美妙精致。”(注:吴学平“国内王尔德研究述评”,《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1期,第153页。)
然而,仔细阅读《道连·格雷的画像》,我们可以看到,王尔德“明白晓畅的文笔”,止步于第十一章。这一章,作家任其思想自由驰骋如天马行空,酣畅淋漓地将他对维多利亚时代社会弊端的鞭挞及对新的享乐主义的呼唤一气呵成。这一章,游离于故事之外,失去了前后情节的联系。这一章,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散文或杂文。它有散文式的抒情,还有杂文式的犀利。它文风骤转,文句复杂,段与段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思想所至笔之所及。既然作者跳出小说故事的局限,借小说人物抒发思想,而且文笔骤然繁复,类似颇具哲理的散文,则译者也应以等同的风格,通过行文中的散文元素转达原文的意境美。且既然没有了故事情节作依据,就更要通过微妙隐晦的文字线索力寻本来就微妙的思想主线,一如茅盾先生所说,“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注:转引自郭建中《当代美国翻译理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76页。)下面试以本人对小说第十一章中某些片段的处理与荣先生的作一比较分析:
例一:
Yes:there was to be,as Lord Henry had prophesied,a new Hedonism that was to recreate life and to save it from that harsh uncomely puritanism that is having,in our own day,its curious revival.It was to have its service of the intellect,certainly,yet it was never to accept any theory or system that would involve the sacrifice of any mode of passionate experience.Its aim,indeed,was to be experience itself,and not the fruits of experience,sweet or bitter as they might be.Of the asceticism that deadens the senses,as of the vulgar profligacy that dulls them,it was to know nothing.But it was to teach man to concentrate himself upon the moments of a life that is itself but,a moment.
荣译文:
是啊,诚如亨利勋爵所预言,要有一种新享乐主义来再造生活,使它挣脱不知怎的如今又出现的那种苛刻的、不合时宜的清教主义。当然,新享乐主义也有借助于理性的地方,但绝不接受可能包含牺牲强烈感情的体验的任何理论或体系。因为新享乐主义的目的就是体验本身,而不是体验结出的果实,不管它是甜是苦。扼杀感觉的禁欲主义固然与之无缘,使感觉麻木的低下的纵欲同样与之格格不入。新享乐主义的使命是教人们把精力集中于生活的若干片刻,而生活本身也无非一瞬间而已。
荣先生的译文,自始至终遵循王尔德“明白晓畅”的文风,读来甚感明白晓畅,有一种理性的美。然而,对于文风骤转的第十一章中某些片段的风格,是保持“明白晓畅”,还是随着作者笔调的变化而变化,尽力表达其文学美感,是笔者在翻译中的着力思考点。诚然,“写作和翻译一开头就得确定语气和基调,在语言和形式上约定力度与节奏。”(注:郭建中《当代美国翻译理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19页。)但是,如果原作本身的基调突变——从“明白晓畅”的讲故事突然转成犀利的议论,译文一味“晓畅”到底似不能传原作之神韵。如译文中的“要有一种……不知怎的如今又出现……”,如“新享乐主义的目的就是……而不是……”,又如“新享乐主义的使命是教人把……而生活本身也无非……而已”,读来似乎有点“说明文”的感觉,少了点散文的美味。因而,笔者在翻译时试图通过刻意重复代词“它”和将逗号改成分号来达到句式的对称,从而凸显句意的对照。或运用多样化的标点(破折号、引号等)来加重语气,起到强调的效果。遣词造句也力求更文学化一点,在散文特有的韵味中传达作者犀利的思想:
是的,正如亨利勋爵所预言,一种新的享乐主义将要诞生,它会再造生活,拯救我们的生活于严酷的清教徒教条——这种过时了的清教徒主义正在莫名其妙地卷土重来。诚然,新的享乐主义将是有理性的,但它绝不会接受任何以牺牲情感体验为代价的理论或体系。因为,它是为了“体验”本身,它并不在乎“体验”导致的结果——不论结果是甜是苦。禁欲主义使感觉窒息;低俗的放荡挥霍使感觉麻木。新的享乐主义与二者风马牛不相及,它要教人学会关注并享受稍纵即逝的生活的每一瞬间。
例二:
Out of the unreal shadows of the night comes back the real life that we had known.We have to resume it where we had left off,and there steals over us a terrible sense of the necessity for the continuance of energy in the same wearisome round of stereotyped habits,or a wild longing,it may be,that our eyelids might open some morning upon a world that had been refashioned anew in the darkness for our pleasure,a world in which things would have fresh shapes and colours,and be changed,or have other secrets,a world in which the past would have little or no place,or survive,at any rate,in no conscious form of obligation or regret,the remembrance even of joy having its bitterness and the memories of pleasure their pain.
真是一段值得诵读的美文!它极富节奏感和韵律,我们在翻译时也应力求达到其散文诗一般的意境。
荣译文:
我们所熟悉的现实生活又从黑夜的不现实的幽暗中归来。在什么地方暂时中断的生活,我们还得在什么地方把它续下去。由于必须继续在那个令人厌倦的、一成不变的习惯圈子里打转,一想到这点,你就会不寒而栗,或者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欲望:但愿在某一个早晨我们睁开眼睛看到的世界已在黑夜中焕然一新,使我们为之喜出望外:在那个世界里,万物的形状和色彩都是新颖的,而且起了变化,新装将裹着新的秘密;在那个世界里,旧事物几乎没有容身的地盘,幸存下来的至少也不再出于必要和悔恨,因为即使回想欢乐也有辛酸味,追忆快感也难免痛苦。
荣先生的这段译文继续秉承其流畅的风格,不无美感。只是,这段译文中的某些处理似乎仍可更“诗化”一些,或者说“说明文”的感觉仍然太足。究其原因,可能是某些连接词的过于理性化减弱了原文的韵味。上文中的“由于”、“而且”和“因为”,无不在增强行文理性衔接的同时削弱了原文的抒情味。虽然英语是非常注重衔接设计的一种语言,但是王尔德在这一段中却没有用任何“由于、因为”之类的因果连词,而是一连三个“a world“后接三个定语从句,当中穿插各种形式的短语,令行文抑扬顿挫,起伏有致,颇具诗韵。伯顿·拉夫尔(Burton.Raffel)在《散文翻译艺术》中说,“对译者最重要和最困难的要求,是美学方面的”。他指出,译者必须“在一种新的语言中重现原著特殊的力度、内在的含义和外在的形式,并且在一种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中重现原著”(注:转引自郭建中《当代美国翻译理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21页。)。而散文翻译如何重现原著的美?伯顿·拉夫尔认为,“散文翻译只有尽可能地重现原作句法结构,才能重现原作的风格。重现原作风格是散文翻译的关键。‘文如其人,如果散文翻译忽视或不能重现原文的风格,就不能说是成功的翻译。”(注:转引自郭建中《当代美国翻译理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26页。)因此,笔者在翻译此段时力求保持原作的句法结构,同样一连用三个平行句“一个……的世界”来体现原文的韵味:
我们熟知的真实生活从不真实的夜影中回归,在哪儿离开它的我们又不得不在哪儿再次面对。想到我们不得不继续那种令人厌倦的一成不变的陈规旧习,可怕的感觉悄然袭来;抑或,我们生出狂野的渴望,渴望我们会在某个早晨睁开眼睛时高兴地看到一个崭新的世界,一个在黑夜中重建的世界,一个万物的形状和色彩都更新、起变化、有着别样秘密的世界,一个过去的一切都无处容身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幸存者无需怀揣任何义务和遗憾,甚至欢乐的回想也有苦涩,愉快的记忆也含痛苦。
这一段的翻译处理,除了与原文保持一致,使用平行结构(parallelism)以外,重复使用“渴望”一词,也是从译文的美学效果出发的,第二个“渴望”令此句顿生诗意。此外,笔者在翻译时字斟句酌,反复诵读,以求将读原作时体会到的散文诗一般的优美韵味传达给译文的读者。“令行文略具丰腴之美”应该是笔者对这一段译文在审美意识主宰下的审美再现所做的注脚。
二、逻辑之美
“在翻译实践中,语义、逻辑、审美三个平面是相互交织、相辅相成的。语义把握常常需要逻辑的调整、修正和校正(adjustment,modification,and calibration,简称AMG),再经过审美的判断、优选和定夺(judgment,optimization,and finalization,简称JOF)才能最后赋形于译文”(注:刘宓庆“翻译的美学观”,《外国语》,1996年第5期,第2页。)。
《道连·格雷的画像》文风简洁(除了第十一章)。但是,对翻译而言,简洁亦有简洁的难处,有时,原文越是简洁,译文越是找不到贴切的表达。此时,“逻辑思辨”——抓住逻辑主线,进行逻辑梳理,应该是翻译工作者最得力的武器——“逻辑美,乃翻译之大美”。
小说的第一章有一段对话,其中的“myself”一词究竟如何译,实在不是一件易事,实在是需要进行“瞻前顾后,左顾右盼”(注:毛荣贵《翻译美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57页。)逻辑梳理的:
“I know you will laugh at me,” he replied,“but I really cant exhibit it.I have put too much of myself into it.”
Lord Henry stretched himself out on the divan and laughed.
“Yes,I knew you would; but it is quite true,all the same.”
“Too much of yourself in it! Upon my word,Basil,I didn't know you were so vain; and I really cant see any resemblance between you,with your rugged strong face and your coal—black hair,and this young Adonis,who looks as if he was made out of ivory and rose—leaves.”
这是画家的朋友亨利勋爵劝画家将他的得意之作“道连·格雷的画像”拿去展出的一段对话。王尔德的“put too much of myself into it”,有些译本译成“倾注了太多自己的东西”。而笔者则译成“倾注了太多的自我”。以下是笔者的译文:
“我知道你会笑我,” 他回答,“但我真的不能将它展出。我在这幅画里倾注了太多的自我。”
亨利爵士在沙发上伸直了身子,大笑起来。
“是的,我知道你要笑话我的,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事实。”
“太多的自我!哎呀,巴兹尔,想不到你竟是这么自负。你的脸粗犷强硬,头发乌黑如煤,而他看起来却像是用象牙和玫瑰叶子做的,我实在看不出你和这位年少的阿多尼斯之间有何相似之处。”
“太多的自我”和“太多自己的东西”从审美的角度究竟哪个更好,笔者在翻译时对此进行了反复思考。首先,直觉感到“太多自己的东西”过于直白了一点,即从“信、达、雅”的角度离“雅”有一点距离,即使是对话,即使可以很随意,毕竟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贵族阶层、艺术家阶层,谈吐是应该更文绉绉一些的。且下文乃至整部小说的用语,也都符合他们的贵族、艺术家身份,都并不十分口语化。其次,“太多自己的东西”在此何所指?为何选用如此模糊的一个词来取代睿智的王尔德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too much of myself”?但既然不止一位翻译前辈没有将“myself”直译为“自我”,应该一定有其道理。或者“太多自己的东西”比“太多的自我”更能“达意”?但,按笔者的理解,“self”包含个体本身的精神与肉体,即“spiritual self”和“physical self”,汉语里的“自我”包含的也是这两层。而“自己的东西”在不同的语境中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解——或许这就是它被选用的理由——因为可根据语境任意理解,所以具有“达意”上的安全。不过,那似乎是一种模糊的安全。当我们读下去,亨利勋爵说“你的脸粗犷强硬,头发乌黑如煤,而他看起来却像是用象牙和玫瑰叶子做的,我实在看不出你和这位年少的阿多尼斯之间有何相似之处……”此时,逻辑推理告诉我们,“倾注了太多的自我”在“达意”上是贴切的,因为这儿的“自我”明显是指“自我形象”,而汉语并不习惯用“自己的东西”来指代形象方面的东西。那么,既然达意贴切,又贴合人物的身份语言,我们用更雅一点的“自我”而不用“自己的东西”应该是比较好的选择。然而,上述对话出现在故事展开之始,那时还没有过多的上下文可供我们做进一步的逻辑思考。因此,“太多的自我”之译只能是暂定的,随着故事的进展,我们需要不断地“瞻前顾后,左顾右盼”,根据逻辑的合理性来做最终的取舍。果然,第九章的对话使我们再次面临“太多的自我”还是“太多自己的东西”的考虑,那是画家向他的模特儿表白心中的秘密之时:
“Dorian,from the moment I met you,your personality had the most extraordinary influence over me.I was dominated,soul,brain,and power,by you.You became to me the visible incarnation of that unseen ideal whose memory haunts us artists like an exquisite dream.I worshipped you.I grew jealous of every one to whom you spoke.I wanted to have you all to myself.I was only happy when I was with you.When you were away from me,you were still present in my art...But I know that as I worked at it,every flake and film of colour seemed to me to reveal my secret.I grew afraid that others would know of my idolatry.I felt,Dorian,that I had told too much,that I had put too much of myself into it.”
“道连,从我遇到你的那一瞬间,你的人格就对我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影响。我,我的灵魂、我的头脑、我的才智,都被你支配了。你成了我心中不可见理想的可见化身,这不可见的理想像个瑰丽的梦,令我们这些艺术家魂牵梦萦。我崇拜你,你和谁说话我都嫉妒。我想独自拥有你,只有和你在一起时我才感到快乐。即使你不在我身边,也仍然存在于我的艺术里……在我创作时,一笔笔、一层层的色彩似乎都在揭示我的秘密。我开始担心别人发觉我对偶像的崇拜。道连,我觉得自己已倾诉得太多,把太多的自我融进了画里。”
从第九章中画家的这一段自我表白里,终于可以看出将“too much of myself”译作“太多我自己的东西”的理由:这“我自己的东西”中包含了画家对模特儿的崇拜以及心中许多特殊的微妙的感情。此时如果坚持用“太多的自我”是否仍然“达意”?笔者极其犹豫,甚至多次将“太多的自我”推翻。最终,“我,我的灵魂、我的头脑、我的才智,都被你支配了”让笔者认定“太多的自我”仍然有其逻辑合理性。因为,如果说在第一章里,这个“自我”引出的下文是外形方面的“自我”,那么,在第九章里,这个“自我”则是精神层面的。王尔德极其聪明地用“too much of myself”囊括了一切,我们也尽可用“太多的自我”把一切都囊括。这一个“myself”用得何其精妙,任何一种别样的表达都会是多余的,都不会比它更美。因此,让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文字保留它的精妙——只要无损原意。
三、结语
“翻译是一个文本的‘来世(afterlife)。文本因经过翻译而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并获得了新的生命”(注:转引自郭建中《当代美国翻译理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76页。)。以审美意识的自觉性和敏感性,本着合理的逻辑思辨、科学的分析方法,力求再现唯美主义大师王尔德的唯美主义小说中多样化的语言之美,是笔者努力想要在《道连·格雷的画像》重译本中达到的目标。虽然译作一定存在许许多多的不足(笔者在写此文时,已经发现很多可以进一步改进之处,足见“美”之没有止境),但是,通过以上的分析讨论,粗略可见,无论是行文谋略还是逻辑思辨,归根结底都是一个审美的过程,“原语中的语言美是否(及如何)能成功地体现在译语中,实际上都受到人的审美价值观的制约和局限”——“翻译永远伴随着审美”(注:刘宓庆“翻译的美学观”,《外国语》,1996年第5期,第3页。)。
(郑晓园: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邮编:200093)